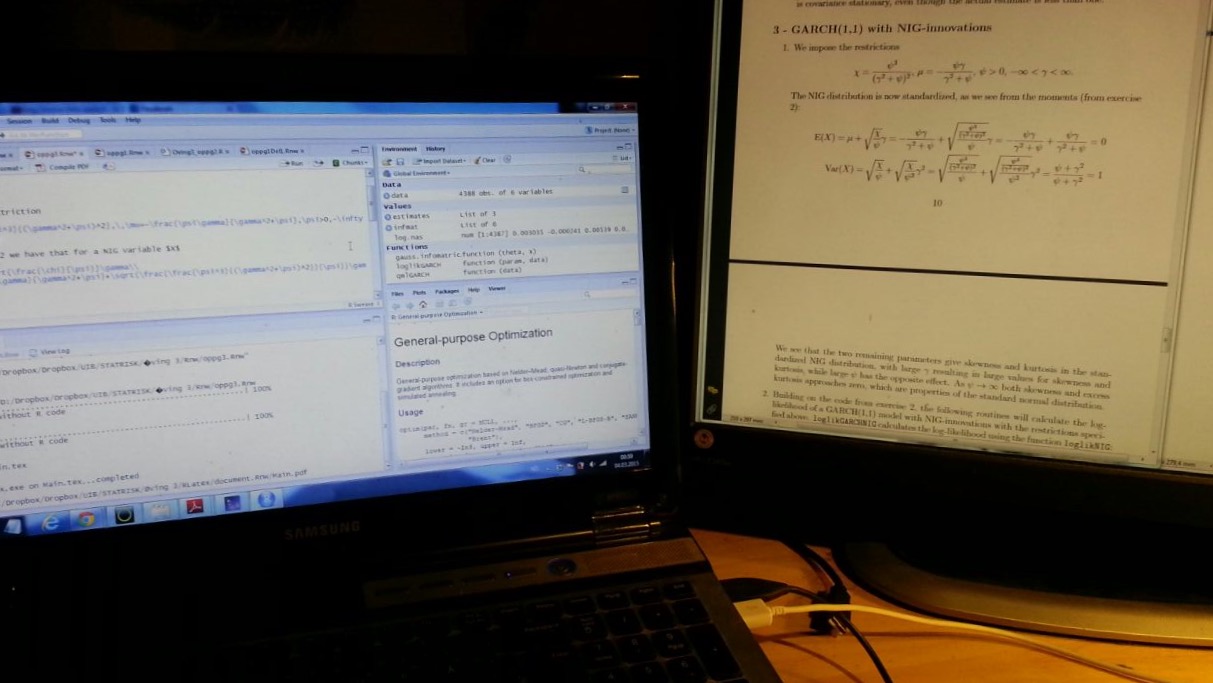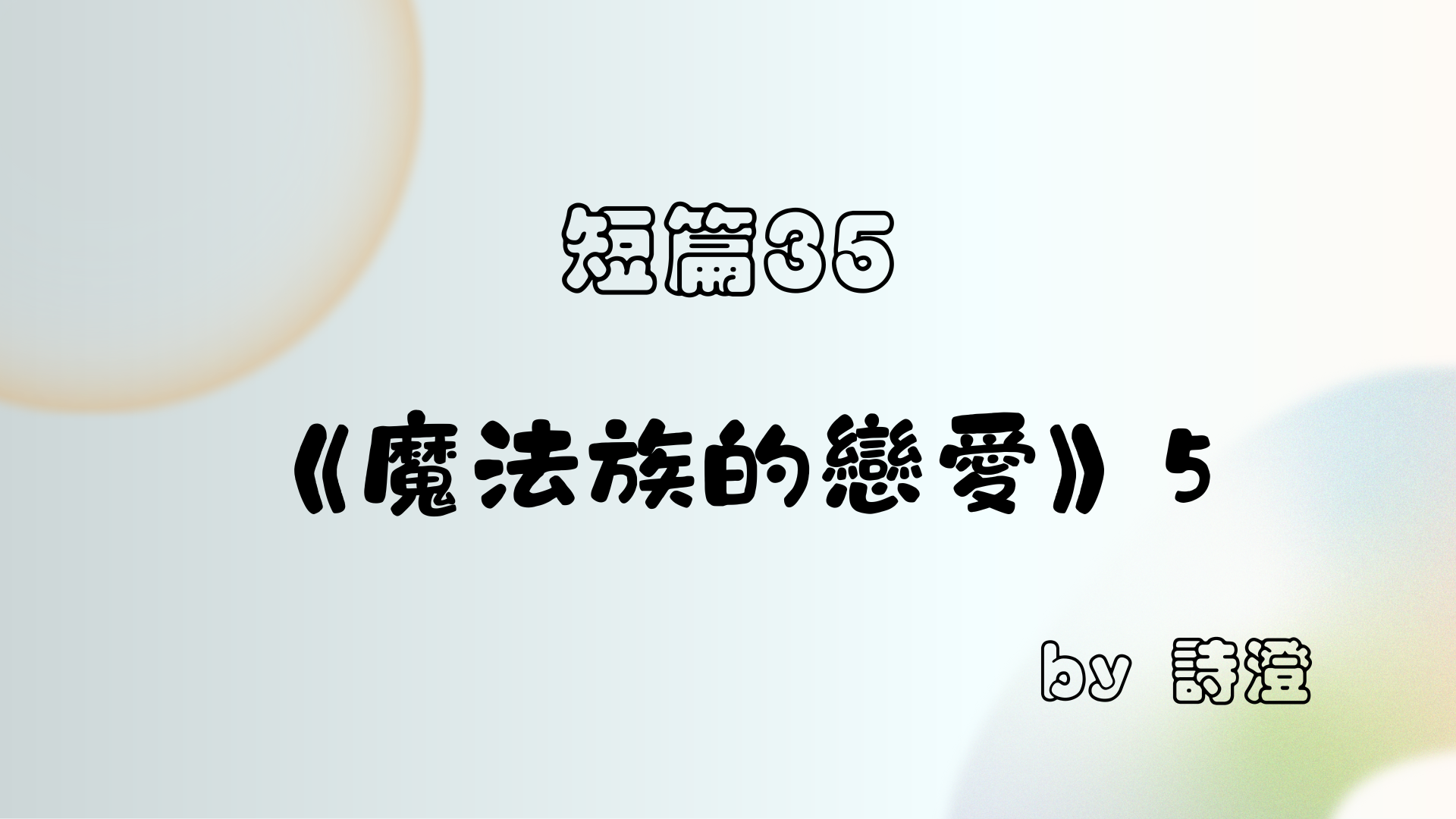我叫阿珊,全名是關凱珊,我知道你一定會笑,所以我自少已討厭別人叫我的中文名,即使是父母也要叫我的英文名Sandy。
我父親在上海街有間洋貨辦館,就是那種滿櫉窗都是長頸、路易十幾、金牌等洋酒及古巴雪茄的鬼佬士多。跟普通街坊士多不同的地方是,我們的客人大多是西裝革履的斯文人,不是洋行老闆,也是銀行經理,有幾個政府公務員也是我們熟客,聽父親叫他們「乜官物官」很恭敬的,我想也有些來頭。多年來望著這些男人在父親的舗頭出入,練就了我看男人的功夫,要知一個男人本事與否,看他腳上穿的鞋已知道七、八分。
其中有個周先生是賣茶葉的,父親說半個九龍的酒家也是他客人。有次他帶兒子來跟我父親寒喧一番,兩個男人一喝酒便沒完沒了,他兒子無聊地在店內打圈,撞上也在店內的我,他馬上低頭盯著自己一雙黑漆皮鞋。
我當時剛上中學,看他比我大,但害羞得緊要便覺得好玩,問他名字,他連名帶姓說周嘉華。
「喂,你識唔識飲酒?」我問。
「下!無飲過。」他就是老實。
「咁渣架,我都飲過啦!」
「爸爸話大個先俾飲。」
我拉他到店後,開了一支長頸,倒了一小杯,我先喝一口,難飲得要命,但裝著很享受地望著他說:「好醇,好香,你試下。」
我替他倒了滿滿一杯,他竟然一飲而盡,沒幾分鐘,他滿臉通紅,我望著他瞇起的雙眼,白皙的臉皮底下一片粉紅,覺得很可愛,連我也感到混身赤熱,我知道自己喜歡上他。
辦館樓上有間小裁縫店,老裁縫有兩個兒子,分別叫阿強阿輝,阿強跟我兩個哥哥很熟絡,經常一齊踢波。這個阿強有時會借故找我說兩句無聊話,我知他想甚麼,但我不會看上他的,見他終日一對破波鞋四處走,便已經不是我杯茶,我好歹也是千金小姐,父親疼死我,怎會配上個窮裁縫兒子?
後來,周嘉華一個人來到辦館,父親知道他找我,招呼他在家裡等。那晚,他儍儍的跟我們一家人吃飯,父親問他一句他答一句,我完全不敢看他,母親笑得連飯也沒空吃。
但有些東西勉強不來,特別是感情這回事。
跟他談話平淡如喝白開水,吃飯就是那兩間餐廳,一間中餐一間西餐,每次逛街要先問准母親,母親說夜晚不要留在街上,他在天黒前一定回家。有次我說想去長洲住度假屋,他說母親不准他在外面過夜。
「依家係你同我拍拖,定係你阿媽?」
「阿媽話⋯⋯」
「夠啦!唔好再提你阿媽呀!」我整整三個星期沒接他的電話。
除夕夜,我跟同學去了蘭桂坊,倒數之後,我撥了電話給他,他母親接聽:「妳仲乜咁夜打嚟?佢瞓左啦!」「拍」一聲便收線。
我從未被人這樣罵過,以為我在高攀你們嗎?那晚我喝了很多,回家都是天旋地轉。
在家門口撞到阿強,我問他是不是喜歡我?他說是,我便衝上去與他吻起來,自此我們便一齊。
阿強入了黑社會後,改名叫阿風,他很會說話,很懂得氹我,我說喜歡的,他一定買給我,他帶我見到很多刺激的玩意,跟他一起每天都很快樂。我生日,他帶我往澳門度假慶祝,不久,我有了他的BB。
父親知道我和阿風的事,罵我是蠢貨,是自作賤,有公子不要揀個乞兒。他沒有來我的婚禮,母親說他是真的氣上心頭,他有心臟病,叫我別找他了。我想到父親從前很疼我,一把眼淚嘩啦嘩啦地流,哭得像個小丑。
兒子出世後,阿風想叫他阿聰,問我好嗎?我想了想,説:「叫嘉華,好嗎?」
這樣,兒子叫吳嘉華。
阿風開始早出晩歸,有次嘉華半夜發高燒,我找他他說要講數行不開,BB猛哭嚇得我慌了。老爺陪我坐的士去廣華看急症,醫生說再遲幾小時的話,嘉華要成為白癡了。
我每次見到阿風也跟他吵,他說我嫌他窮,我覺得很委屈,嫌他?我有公子不要嫁給他,是嫌他?我想起父親罵我的話。
我知道阿風外面有女人,是卡啦OK的PR,好似叫Connie或Wandy,還有了BB,但其實我並沒有太多感覺,我已經不愛他了,這樣的男人還有女人會喜歡,原來蠢的不只我一個。
有天我帶著嘉華,在街上見到周嘉華,他比我認識他時多了幾分穩重與帥氣,真有大家少爺的模樣,不再像個呆子,他拖著女朋友,長得很美眼睛大大,比我漂亮。他問我BB的名字,我說:「叫阿聰,爸爸改嘅。」
他一離開,我的眼淚便像缺堤一樣。回到家,老爺問我發生甚麼事,我說沒甚麼,只想睡一下。
我在房內割脈,那傷口三吋長,如果不是老爺的話,我已經死了。
出院後,阿風多了在家,他問我想吃些甚麼,我根本沒心思理他。我覺得自己的靈魂已經支離破碎,生活被困在沒門的囚牢,我只想躺在床上絲毫不動,不去想這世界的一切。
這夜,我依舊躺在床上,聽到阿風在跟那個女人傾電話。而我則開始做夢,夢中的周嘉華喝了很多,兩頰像盛放櫻花,是我最喜歡的桃紅。
完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