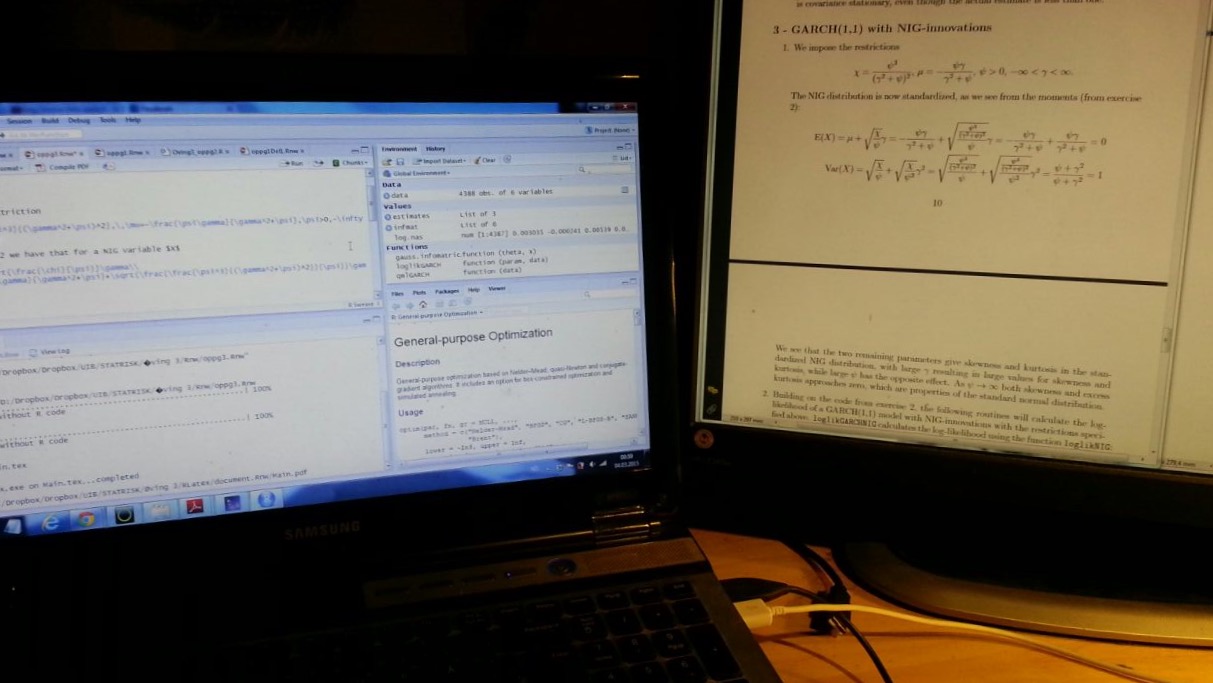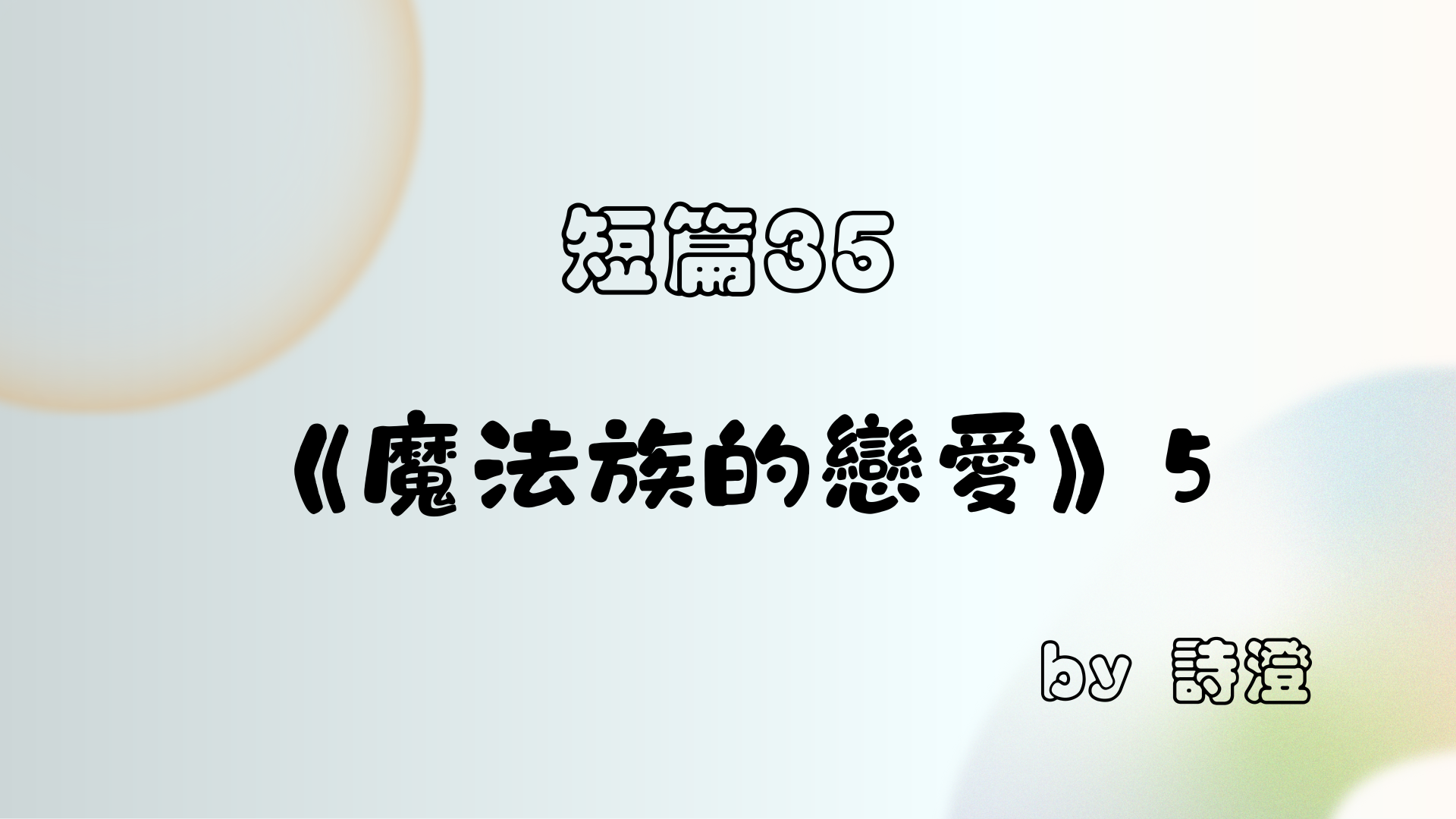我叫愛娜,在家裡三兄妹當中,我排中間,排中間代表了甚麼呢?代表了我的成長過程中,一直都是被父母所忽略的。例如哥哥出世時,因為他是祖父母的第一個男孫,父親是個傳統潮洲男人,哥哥的出現自然很受大家的歡迎,父親在彌敦酒樓擺了十二席滿月酒,聽母親說她結婚都只是擺了十圍,父親那晚喝得爛醉,比做新郎哥還要高興。但到三年後我出世時,父親說既然哥哥都擺了滿月酒,不好意思再打攪親戚朋友,就不要再擺甚麼滿月酒了,自己一家人吃餐飯就算,怎知到了我滿月那天,碰着打颱風,天文台掛了個十號風球,街市當然一早關門大吉,母親只好開了兩罐午餐肉,煲了幾隻紅雞蛋就當做替我做滿月飯。
我滿月時還沒有名字,那個颱風叫「愛娜」,父親就用這個愛娜做我的名字。
哥哥剛出世不久,父親用了半個月人工買了一台日本照相機,對很多尋常人家來說是新玩意,父親替哥哥拍了很多照片,有些還是在香港公園、山頂、沙田城門河這些地方拍的,可以知道父親當時很高興帶着哥哥四處去遊玩。但我呢?母親說我還未出世,那台相機就被父親弄壞了零件,維修費很貴,父親肉痛去修理,又沒有錢再買一部新的,所以我出世後幾乎沒有拍過一張照片,現在翻開舊相簿看到的,我的小時候的照片,都是跟其他親戚小孩一起的合照。
我問母親,父親有像哥哥小時候一樣,帶我四處去嗎?母親說:「你爸爸那時候剛剛被調去離島,返屋企嘅日子都少,邊有時間帶妳去玩。」
但我對這個解釋一直存在懷疑,因為我發現弟弟小時候的很多照片,都是在新界的彭福公園或荔園拍的,母親解釋因為弟弟出世後,父親又被調回市區了,而且他也修好了照相機。
但我其實對父親這種偏心的舉動,沒有太大的不滿,因為作為一個在潮洲家庭長大的女孩子,老早就習慣長輩們那種重男輕女的生活習慣了。父親有兄弟姐妹,就是我的叔叔姑姑,每逢過年過節幾個家庭一起吃飯娶會時,父親與叔叔們都只會打牌抽煙看電視,煮飯、洗碗、執枱、切生果的功夫全倚賴一屋的女人包括我和幾個表姐妹,甚至幾個表弟都學會指使我,但我只會一個鬼臉回敬他們。
我不喜歡父親的是他的做人態度,他是那種愛苟且偷安的人,沒上進心愛偷懶貪小便宜,但又喜歡認屎認屁,自以為做份政府工好有本事。他只是在渠務處做個低層職員,很典型的小公務員性格:上班找機會蛇王,要做事滿嘴不滿,如果不是因為他做的是政府工,以他的性格老早被人炒了。
有一次我對在廚房煮飯的母親說:「我將來搵男人,一定唔會搵個似阿爸嘅。」
母親當時語氣帶點輕蔑的說:「又睇下妳識到個咩男人咁巴閉!」
對比父親的偏心,我更討厭母親的刻薄。
很正常地,倆兄弟都遺傳了父親懶惰的根,對讀書從來不上心,哥哥讀完中三便出來做散工,每份工做不了一個月,後來因為借了高利貸,家裡報警很多次,攪得很麻煩,最後要父親用了大半退休金幫他還債是後來的事。弟弟算是好一點,他做救生員很多年,夏天姑且可以養活自己,但一到冬天他便躲在家裡上網打遊戲機,他這種生活方式都竟然能夠在大陸娶了個女人做老婆,還替他生了個小孩,我有時很懷疑這天底下有那種女人會喜歡上這種養自己都成問題的男人?
男人故然沒出色,找上這種男人的女人更是白癡。
但我身邊偏偏就滿是這種男人,我樣貌像母親,有個高鼻子和尖下巴,身材剛發育,身邊就有幾個狗公男同學喜歡圍着我轉,幾個都是幼稚蠢貨,十幾歲的中學生了,書包還經常塞着幾本日本漫畫,放學就愛鑽遊戲機中心,我當然不會看上他們一眼,但有時指使他們替我買一下零食或攞下書包倒是好使好用。朋友說我這樣很衰,我說這是他們攞嚟衰,不是我的問題。
有天放學後,跟幾個女同學去吃波蘿冰,突然有個男生走到我身邊,將一個書包拋向我,說:「喂!幫我睇住先!」
「前面撞車呀!」一個女同學指指前面馬路,剛才那個男同學走到一輛小巴前面,爬到車底,將一個被撞倒的阿婆拉出來。
「原來係陳俊樺。」一個女同學認得那個男生。
「陳俊樺,咩班架?」他引起我的興趣。
「中六A班,籃球隊隊長,妳唔知咩?」
我為甚麼要認識他?怎麼他不先來認識我?這種自以為是的男生,我見到就討厭。這時候,陳俊樺回來我們身邊,說聲「唔該」想取回自己的書包。
「好彩你返嚟攞返,下次我一定掟落垃圾筒!」我掉回給他。
想不到他竟然說:「無下次啦,我都唔鍾意人地幫我攞嘢!」
這算甚麼態度?自以為是!當自己是男明星嗎?望着他越走越遠的背影,我越想越氣,但晚上腦子裡常想着他,我一定非常恨他,否則,就是喜歡上他。
後來,我加入了學校啦啦隊,經常有機會看到他,但他好像忘了我一樣,我有好幾次借故引他住意,他都當我透明,我覺得自己很賤,為甚麼要這樣送上門呢?我決定離開啦啦隊。
有天小息時,在走廊上撞到他,我故意裝作沒看見,他突然停着我身邊,問:「點解離開啦啦隊?」
他這舉動已引起幾個女同學注意,我覺得自己臉頰都緋紅了,說:「乜你知嘅咩?」
他說:「返嚟啦!妳走左之後,我地隊連輸幾場!」然後他就走了。
我很討厭他這種自以為是的態度,但又有那個女孩聽到這種說話不心動呢?我不爭氣地回去啦啦隊,在一次校隊贏得校際冠軍的慶祝會後,我被他帶了到禮堂後的雜物房內,在黑透了又悶熱的房間內,他像變了另一個人,瘋了般向我索吻,他那隻張狂的手伸入我的上衣,鑽進我的胸圍內撫弄,乳房被他抓得很痛,我被他的舉動嚇怕了,想推開他,但又享受着這種偷摸的興奮,就這樣,我成了他的女朋友。
「有咩唔好?我依家好失禮你?」我站在學校操場上,幾乎是對他大叫出來。
「唔係……總之我有時間就搵你啦!」他轉身就衝出學校了。
有次我在學校門口等他,發現他跟一個女同學一齊行出來,那女生還是我的朋友,倆個人有講有笑,我忍不住衝上去問他們是甚麼關係?
「喂!妳唔好咁啦!學校嘅嘢妳又唔知!」阿樺拉開我說。
「唔知?咩唔知呀!你依家偷食呀,唔知!」我哭出來。
「咩偷食呀?妳最多咪係前度,阿樺大巴前度啦!」那個女同學回了我這一句。
我已經紅了眼,衝上去就是一巴掌摑向那個女生臉上,然後三個人很難看的一片混打,我都忘記細節了,到可以冷靜下來時,我們三個人已經坐在校務處內,幾個老師在另一旁研究怎樣處置我們,我望着面前的阿樺,問:「咁依家即係點?即係同我分手?」
阿樺的說話,令我對他訴死了心,他說:「妳鍾意啦!想見就見,唔見就唔見。」
我最討厭男人拖泥帶水,又是一個無出息的男人。
這件事,驚動了三個人的家長,有人說要報警,有人說是誤會,有人說要退學,結果是我被退學,阿樺往美國留學,那個女的我理她是生是死。
後來我調往一所女子中學,生活平淡只有不停的八卦無聊事,畢業後在一間同樣平淡無聊的外資公司做個小文員,在那裡我認識了他,他叫偉國,人如其名,一樣的平淡沒趣,街上千百個平凡男人的其中一個,拍拖一年多,他說想結婚,因為這樣抽公屋會容易一點,我沒有考慮便應承了他,回家後跟母親說了聲:「我要嫁啦!」便躲進房裡,那一夜我哭了很久,之於哭甚麼,我自己都說不清。
今天,偉國說收到房屋署的信,我們被派到天水圍一間公屋,他表現得很興奮,說不如吃一餐日本放題慶祝,我說好呀!他說:「咁妳收工去排隊先,好爆架。」
我站在柯士甸道的行人路上,人龍前面還有大約三十多人,我像他們一樣,過着很平庸的日子,活在很平凡的人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