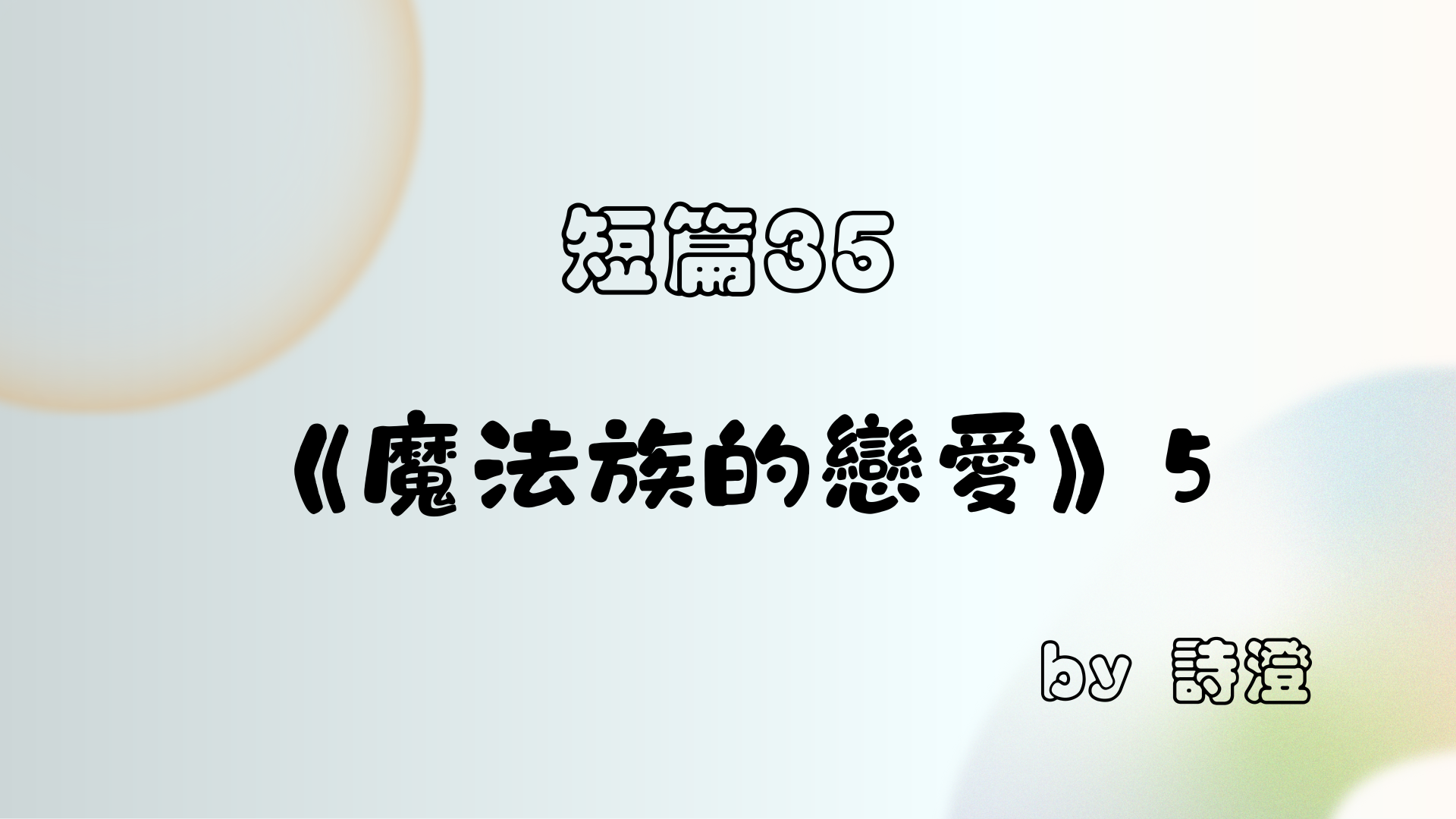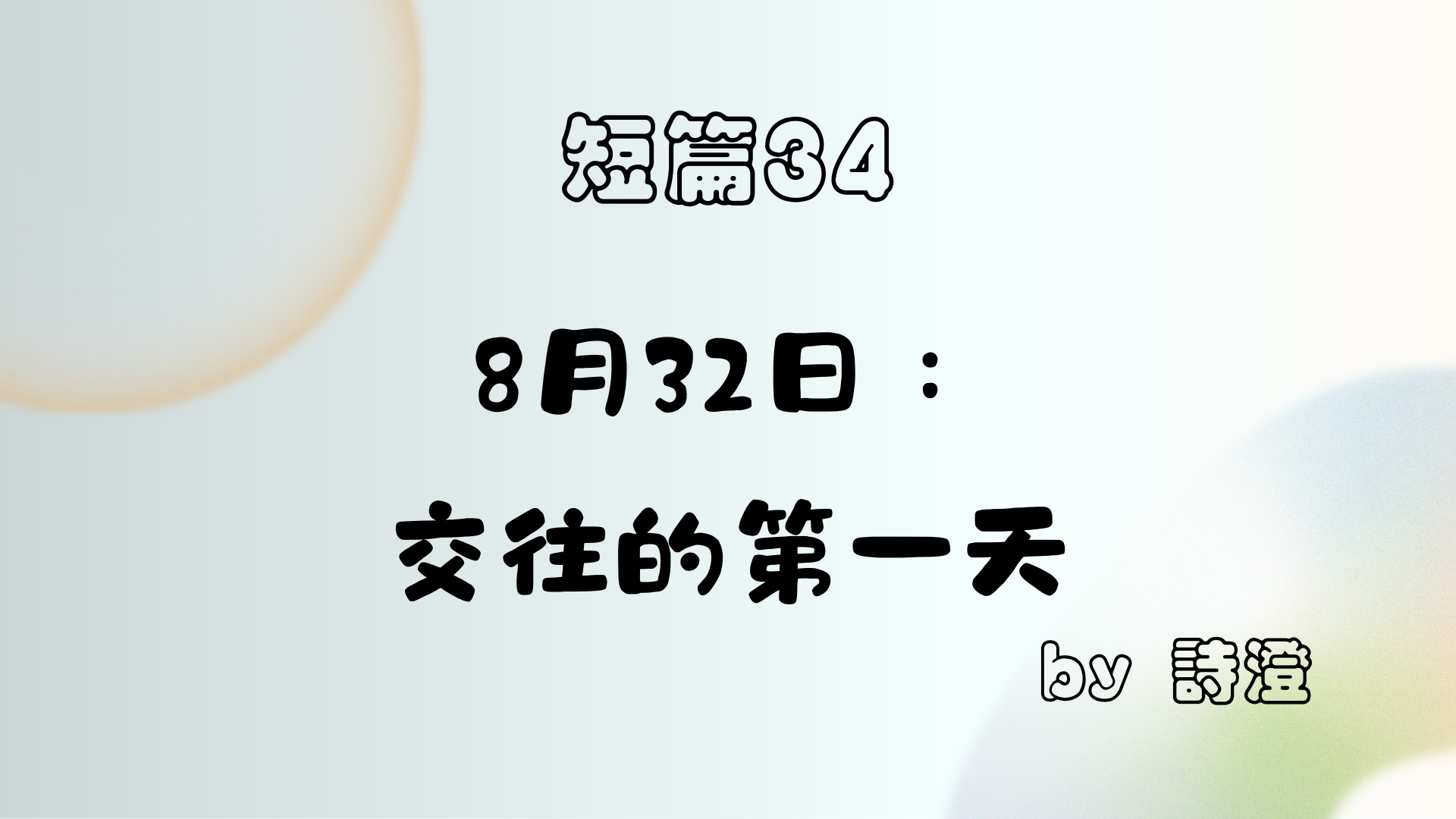第一章:偷生
一九八零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辽西的北风像刀子一样割过煤矸石山,将矿区的煤尘卷得漫天都是。十一月刚过,一场大雪便将金家沟裹成了个素白世界。
金玉莲站在自家院子里,双手浸在冰冷的肥皂水中,机械地搓洗着堆成小山的脏衣服。这双手曾经也是细腻的,如今却已粗糙开裂,手指关节处冻得通红发肿,裂开的口子里渗着血丝,浸在碱水里钻心地疼。
可她不敢停。停了,小丽明天就没得吃。
“妈,外面冷,进屋吧。”十七岁的金小丽从屋里探出头来,声音清脆如铃。
金玉莲抬头,看着女儿那张如冰似玉的脸庞,心里五味杂陈。小丽长开了,眉眼间有她年轻时的影子,却又更添几分清冷。女儿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袖口短了一截,露出纤细的手腕。那是前年做的衣服,已经跟不上小丽抽条的身子了。
“你回去看书,妈快洗完了。”金玉莲温声说,手上的动作却更快了些。
屋里传来翻书的沙沙声。小丽今年高二了,成绩在矿中学里数一数二。老师说,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考大学有希望。可大学的学费从哪儿来?金玉莲不敢想,只能埋头洗,一件,两件,三件……矿上工人的衣服脏,煤灰混着汗渍,不用大力搓不干净。
她今天接了十二件,洗一件五分钱,一天能挣六毛。一个月十八块,刨去母女俩的吃穿用度,能攒下七八块就不错了。这样的日子,她已经过了十七年。
天渐渐暗下来,金玉莲终于洗完了最后一件工装。她直起酸痛的腰,将衣服一件件拧干,晾在院子里的铁丝上。北风一吹,湿衣服立刻冻得硬邦邦的,像一排站岗的士兵。
屋里已经飘出玉米糊糊的香味。小丽生好了炉子,煮好了晚饭——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配一小碟咸菜疙瘩。这就是母女俩的晚饭。
“妈,手又裂了。”小丽握住母亲的手,眼睛红了。
金玉莲抽回手,笑了笑:“不碍事,抹点蛤蜊油就好了。快吃饭,吃完你看书,妈收拾。”
母女俩对坐在炕桌旁,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喝糊糊。屋子里除了咀嚼声,只剩下窗外呼啸的风声。
“妈,”小丽突然开口,“任叔今天又来了,送了块肉。”
金玉莲的手顿了顿:“嗯,妈知道了。”
“他还说……下个月矿上招临时工,问我想不想去。”小丽的声音低了下去。
“不去!”金玉莲猛地抬头,声音尖锐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你好好读书,考大学,离开这儿。矿上的事你别管。”
小丽沉默了。她知道母亲为什么反应这么大。金家沟煤矿是个男人堆,女人少得可怜。她从小在这里长大,听得懂那些矿工看她母亲的眼神,也隐约明白为什么总有男人半夜来敲门。
她不是不懂事的孩子了。
吃完饭,小丽收拾碗筷,金玉莲从炕柜底层摸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她这些年攒下的钱。她数了又数:八十七块六毛四。离小丽考上大学还有一年多,学费、路费、生活费……这些钱远远不够。
夜深了,小丽在里屋睡着了。金玉莲坐在外屋的炕沿上,就着煤油灯缝补小丽的棉袄袖口。灯光映着她依然姣好的侧脸,三十六岁的年纪,眼角已经有了细纹,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鼻子挺翘,嘴唇丰润。即使穿着臃肿的棉袄,也掩不住她高挑的身段和曲线。
她想起十七年前的那个冬天,也是这样的风雪夜。那时她才十九岁,从山东逃荒到东北,跟家人走散了,晕倒在金家沟的雪地里。是矿上的老矿工金老憨救了她,把她背回了家。
金老憨是个好人,比她大二十岁,老婆早逝,无儿无女。他收留了她,给她吃喝,给她治病。她感激他,在他提出要娶她时,她点了头。虽然谈不上爱情,但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可婚后第二年,金老憨就在矿难中死了。那时她已经怀了小丽,六个月的身孕。矿上赔了一百二十块钱,就再没人管这对孤儿寡母。
为了活下来,她开始给矿工洗衣服。一开始只是洗,后来有些光棍汉子看她年轻,动了心思,半夜来敲门。她赶过,骂过,可有一次小丽发高烧,她没钱买药,是任强送来了退烧药和两块钱。那晚,任强没走。
从那以后,她就走上了这条路。用身子换一口吃的,换一点钱,换小丽能活下去的希望。
窗外传来猫叫声,三声短,两声长。
金玉莲的手一抖,针扎进了手指,渗出一颗血珠。她舔掉血珠,放下针线,轻手轻脚走到门边。
门开了一条缝,任强闪身进来,带着一身寒气。
“嫂子。”他低声唤道,胡子拉碴的脸上带着局促。
任强四十出头,是个老光棍,在矿上干了二十年,攒不下钱娶媳妇。他长得高大壮实,心眼不坏,对玉莲母女也照顾。
金玉莲没说话,转身走回炕边,脱了棉袄,只穿着一件洗得发薄的小背心钻进被窝。被窝里还残留着她身体的温热和一丝淡淡的皂角香。
任强搓搓手,哈着气,等身上暖和些了,才脱了外衣上炕。他看着背对他的玉莲,月光从窗纸透进来,照在她裸露的肩膀和脖子上——那皮肤白得像雪,在月光下泛着瓷一般的光泽。
“小丽睡了?”任强小声问。
“嗯。”玉莲应了一声,声音低得像叹息。
任强的手小心翼翼地从背后环住她的腰。那腰肢纤细,隔着薄薄的背心能感受到肌肤的温热和柔软。他的呼吸粗重起来,嘴巴带着硬硬的胡茬在她后颈上蹭。
玉莲的身体微微一颤。十七年了,她还是不习惯这样的亲密,可身体却已经有了自己的记忆。任强的气息喷在她耳后,粗糙的手掌从腰间往上移,覆上她胸前的柔软。
“强子……”她轻唤一声,说不清是抗拒还是邀请。
任强却像得到了许可,动作大胆起来。他扳过她的身子,面对面看着她。玉莲闭着眼,睫毛在眼睑上投下浅浅的阴影。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呼出的气息温热湿润。
他低头吻住她的唇,一开始是小心翼翼的试探,很快便变成了贪婪的索取。玉莲没有回应,也没有拒绝,只是任由他吻着。任强的舌头撬开她的牙关,在她口中探索,吮吸。他的手从背心下摆探进去,直接抚上她光滑的背,然后绕到前面,握住一边的柔软。
玉莲的身体开始发热。她告诉自己,这是交易,是为了小丽。可身体却背叛了理智,在任强的抚摸下渐渐酥软。她的呼吸急促起来,胸口起伏,顶端的蓓蕾在任强掌中硬挺。
任强离开她的唇,沿着下巴一路吻到脖子。玉莲的脖子修长白皙,像天鹅颈,此刻仰起,露出脆弱的弧度。任强的胡茬刮过细嫩的皮肤,留下浅浅的红痕。他贪婪地吮吸着,在那片雪白上留下一个又一个印记,仿佛这样就能证明这个女人属于他,哪怕只是一夜。
“玉莲……”他喃喃唤着她的名字,不再是“嫂子”,而是她的名字。
玉莲睁开眼,看着头顶黑黢黢的房梁。房梁上结着蛛网,在月光下像一层薄纱。她的手抬起来,环住任强的头,手指插进他粗硬的头发里。
任强得到鼓励,更加激动。他扯开她的背心,让一对雪白的乳峰弹跳出来。月光下,那对乳峰饱满挺翘,顶端的樱桃早已硬挺发红。他像饿极了的婴孩,一口含住一边,用力吮吸,舌头绕着乳头打转。
“啊……”玉莲忍不住呻吟出声,那声音压抑而破碎,带着十七年的委屈和欲望。
任强的另一只手也没闲着,抚摸着她的腰肢、小腹,然后向下探去。玉莲今天只穿了条宽松的棉裤,里面空荡荡的。任强的手轻易就探了进去,摸到那片茂密的丛林和已经湿润的沟壑。
“玉莲,你湿了……”他在她耳边喘着粗气说,声音里带着得意和欲望。
玉莲的脸烧得厉害。她恨自己的身体这么容易就有反应,恨自己在这种时候还能感受到快感。可当任强的手指找到那颗敏感的珍珠,轻轻揉捏时,她还是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别……别碰那里……”她咬着唇说,可身体却诚实地拱起,将更多送入他手中。
任强低笑一声,手指更加灵活地动作。另一只手继续揉捏着她的乳房,时而轻柔时而用力,留下浅浅的指痕。玉莲的身体像一张被拉满的弓,绷得紧紧的,渴望被释放。
“强子……给我……”她终于忍不住,低声乞求。
任强却故意折磨她,手指在她体内浅浅探索,就是不给她满足。玉莲难耐地扭动腰肢,双腿缠上他的腰。
“求你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
任强这才褪下自己的裤子,放出早已坚硬如铁的欲望。他分开玉莲的腿,抵上那片湿热的花园入口。
“看着我,玉莲。”他命令道。
玉莲睁开迷蒙的双眼,看着他。任强的脸在月光下半明半暗,眼中燃烧着欲望的火。
“说你要我。”他固执地说。
玉莲咬唇,不肯说。这最后的一点尊严,她不想丢。
任强叹了口气,腰身一挺,猛地进入了她。两人同时发出一声闷哼——他是满足的叹息,她是被填满的呻吟。
开始了,又是一场交易,又是一次出卖。玉莲这样想着,可身体却自动迎合着任强的冲刺。任强很懂得取悦她,知道什么样的角度和力度能让她颤抖。他时而快速抽插,时而深深埋入缓缓研磨,每一次都顶到最深处。
“强子……慢点……啊……”玉莲断断续续地呻吟,手指在他背上抓出红痕。
任强却像发了疯的野兽,动作越来越快,撞击越来越重。炕板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混合着肉体碰撞的啪啪声和压抑的喘息呻吟。
“玉莲……你好紧……好热……”任强在她耳边喘着粗气,汗水滴落在她胸口。
玉莲已经说不出话,只能随着他的节奏摆动腰肢。快感像潮水一样一波波涌来,冲刷着她的理智。她忘了自己是谁,忘了为什么在这里,只知道这一刻的身体是快乐的,是活着的。
就在她即将到达顶点时,任强突然抽身离开。
玉莲茫然地睁开眼,看见任强跪在她双腿间,俯身下去,将头埋进她的腿心。
“不……脏……”她惊惶地想并拢双腿,却被任强牢牢按住。
温热的舌头舔上那片湿热,找到那颗敏感的珍珠,轻轻吮吸。玉莲像被电击一样弓起身子,双手死死抓住身下的褥子。那感觉太强烈,太羞耻,却又太美妙。她从未被这样对待过,那些男人只是索取,从不顾她的感受。
“啊……不要……停……”她语无伦次,身体却诚实地颤抖着。
任强的舌头灵活地探索着她的每一寸秘密,时而轻柔如羽毛,时而用力吮吸。玉莲感觉自己要疯了,快感堆积到顶点,终于在一阵剧烈的颤抖中爆发出来。她咬住自己的手腕,防止叫声太大吵醒里屋的小丽,身体却不受控制地痉挛,一股热流涌出,被任强全部吞下。
任强这才重新进入她,这次的动作温柔了许多。他搂着她,轻轻抽插,吻去她眼角的泪。
“玉莲,跟我过吧。”他在她耳边低声说,“我攒了点钱,够咱仨过日子。小丽就是我亲闺女。”
玉莲的身体僵了僵。这样的话,她听过不止一次。任强说过,呈刚说过,李达也说过。可她知道,这些男人说要娶她,不过是想要个长期免费的暖炕人。真娶回家了,小丽怎么办?她能带着女儿嫁人吗?就算嫁了,人家会对小丽好吗?
“别说胡话。”她淡淡地说,声音里透着疲惫。
任强不再说话,只是动作渐渐加快,最后在她体内释放。结束后,他趴在她身上喘气,久久不愿离开。
玉莲推了推他:“该走了,天快亮了。”
任强这才不情愿地起身,穿好衣服。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放在炕沿上:“里面有两块钱,还有半斤肉票。快过年了,给小丽包顿饺子。”
玉莲看着那个布包,心里五味杂陈。她需要这些,可每接受一次,自尊就碎掉一片。
“谢谢。”她低声说。
任强走到门边,又回头看她。月光下,玉莲裹着被子坐在炕上,头发凌乱,脖子和胸口布满红痕,美得惊心动魄,又脆弱得让人心疼。
“玉莲,”他犹豫了一下,“矿上不安全,你……少接点活。呈刚那人……不地道。”
玉莲点点头:“知道了。”
任强这才开门,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玉莲坐在炕上,许久没动。直到第一缕晨光照进窗棂,她才起身,穿好衣服,将任强留下的布包收进炕柜底层,和那个装着八十七块六毛四的小布包放在一起。
然后她开始生火,烧水,准备做早饭。新的一天开始了,她又是那个为了女儿拼命活着的母亲金玉莲,不是任何人的玉莲。
里屋传来响动,小丽醒了。
“妈,我帮你烧火。”小丽穿着单衣走出来,看到母亲脖子上的红痕,眼神暗了暗,却没说什么。
“不用,你去念书。”玉莲推她回屋,“妈今天要去矿上送衣服,中午不回来,锅里给你留了饭。”
“妈……”小丽欲言又止。
“快去。”玉莲背过身,往灶膛里添柴火。
小丽站了一会儿,默默回屋了。玉莲听见里屋传来压抑的啜泣声,心里像刀割一样疼。她知道女儿懂,什么都懂。可她能怎么办?一个没文化没技术的寡妇,在这男人堆里拉扯大一个孩子,除了这副身子,她还有什么?
水烧开了,玉米糊糊在锅里咕嘟咕嘟冒泡。玉莲盛了两碗,叫小丽出来吃饭。母女俩对坐,安静地喝糊糊,谁也不说话。
吃完饭,小丽背上书包去上学。玉莲站在门口看她走远,直到那瘦削的背影消失在矿区的晨雾中,才转身回屋。
她将昨天洗好的衣服叠整齐,用布包好,背在背上,锁上门,往矿上去。
一路上,遇见的矿工都跟她打招呼。
“金嫂子,送衣服啊?”
“玉莲,今天气色不错。”
“嫂子,我那件工装洗好了吗?”
玉莲一一应着,脸上挂着温顺的笑。她知道这些男人看她时眼里的光是什么意思,也听得懂那些暧昧话语背后的暗示。在这个女人稀缺的矿区,她就像一块肥肉,谁都想咬一口。
到了矿工宿舍区,她挨家挨户送衣服、收钱、接新活。有些人家多给一两分,她默默收下,记在心里;有些男人趁机摸她的手,她不动声色地抽回,脸上笑容不变。
最后一家是呈刚。呈刚是矿上的小班长,有点小权,也有点小钱。他老婆去年病死了,一直想续弦。
“玉莲来了。”呈刚开门让她进去,眼神在她身上打量,“衣服洗得真干净。”
玉莲把洗好的衣服递给他:“呈班长,这是您的,一共三件,一毛五。”
呈刚没接钱,反而握住她的手:“玉莲,跟你说个事。”
玉莲抽手,没抽动:“您说。”
“矿上要招几个临时工,在食堂帮忙。活不累,一个月二十五块。”呈刚看着她,“我给你留了个名额。”
玉莲心一动。二十五块,是她洗衣服收入的两倍还多。
“有什么条件?”她冷静地问。
呈刚笑了:“玉莲,你是个明白人。我啥条件,你不知道?”他的手顺着她的手腕往上摸。
玉莲后退一步:“呈班长,我还有事,先走了。”
“别急啊。”呈刚拦住她,“玉莲,我是真心想跟你好。你跟了我,不用再洗衣服,小丽我也供她上学。怎么样?”
玉莲看着他。呈刚四十多岁,长得还算周正,条件确实不错。可她知道这人脾气暴,前妻就是被他打跑的。跟了他,她和女儿的日子未必好过。
“呈班长,我配不上您。”她低声说,“您找别人吧。”
呈刚脸色一沉:“金玉莲,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是什么金枝玉叶?一个靠身子换饭吃的寡妇,我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这话像刀子一样扎进玉莲心里。她脸色苍白,嘴唇颤抖,却倔强地抬起头:“呈班长,钱给我,我要走了。”
呈刚盯着她看了半晌,突然笑了:“行,你有骨气。”他从兜里掏出一张五块的票子,拍在桌上,“今晚来拿剩下的,我等你。”
玉莲没接那五块钱,转身就走。
“金玉莲!”呈刚在身后喊,“你早晚是我的人!”
玉莲跑出呈刚家,一直跑到矿区的煤矸石山后面才停下来。她蹲在地上,抱着膝盖,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为什么?她只是想活着,想养大女儿,为什么这么难?
哭够了,她擦干眼泪,站起身。生活还得继续,小丽还在等她。
那天晚上,呈刚没等来玉莲,却等来了任强。两个男人在矿区的空地上打了一架,都挂了彩。这事很快传遍了矿区,自然也传到了玉莲耳朵里。
“妈,咱们走吧。”小丽那晚突然说,“离开这儿,去哪儿都行。”
玉莲看着女儿坚定的眼神,心里某个地方动了。是啊,该走了。小丽长大了,不能再让她活在这种环境里。她要带女儿离开这个羞耻的故土,去一个没人认识她们的地方,重新开始。
从那天起,玉莲开始更加拼命地攒钱。她接了更多的衣服洗,甚至开始在矿区的食堂帮工,虽然要忍受一些男人的骚扰,但工钱确实高了些。
而那几个男人——任强、呈刚、李达——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轮流来“帮衬”她。玉莲不再拒绝,她需要钱,需要尽快攒够离开的路费。
只是每个男人来的夜晚,她都会在事后独自坐在炕上,看着窗外的月亮,直到天亮。她的身体在交易中麻木,心却越来越清醒:她要带女儿离开,一定要离开。
时间一天天过去,小丽高中毕业了,考上了广州的一所大学。通知书来的那天,玉莲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她把攒了十八年的钱全拿出来,数了一遍又一遍:三百六十七块八毛二。
够路费了,够第一学期的学费了。
“妈,咱们一起去。”小丽握着她的手,“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儿。”
玉莲点头。她当然要去。女儿去哪儿,她就去哪儿。
临走前一夜,任强来了。他没像往常那样急切,只是坐在炕沿上,看着玉莲收拾行李。
“真要走了?”他问。
“嗯。”玉莲没回头。
“广州远啊。”
“远才好。”
任强沉默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这个你拿着,路上用。”
玉莲打开,里面是五十块钱。这对任强来说,是一笔巨款。
“我不能要。”她推回去。
“拿着!”任强硬塞给她,“小丽是个好孩子,有出息。你……你也好好的。”
玉莲的眼眶红了:“强子,谢谢你这些年……”
“别说这些。”任强摆摆手,“走吧,走了就别回来了。这地方,配不上你们娘俩。”
那天晚上,任强没碰她,只是坐了一会儿就走了。玉莲站在门口看他消失在夜色中,心里空落落的。
第二天天还没亮,母女俩就背着简单的行李,悄悄离开了金家沟。玉莲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这个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低矮的土房,蜿蜒的煤渣路,远处黑黢黢的煤矸石山。
再见了,羞耻的过去。
再见了,金玉莲。
从今往后,她要做一个全新的自己,和女儿一起,在南方的阳光下重新开始。
火车轰鸣着驶向南方,窗外的景色从冰天雪地渐渐变成青山绿水。小丽靠在母亲肩上睡着了,玉莲轻轻搂着女儿,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心里既忐忑又充满希望。
广州,那个只在广播里听说过的城市,会有她们母女的容身之处吗?
她不知道。但她知道,无论前路多难,她都要走下去。为了小丽,也为了自己。
窗玻璃上,映出她依然美丽的脸庞,和眼中从未熄灭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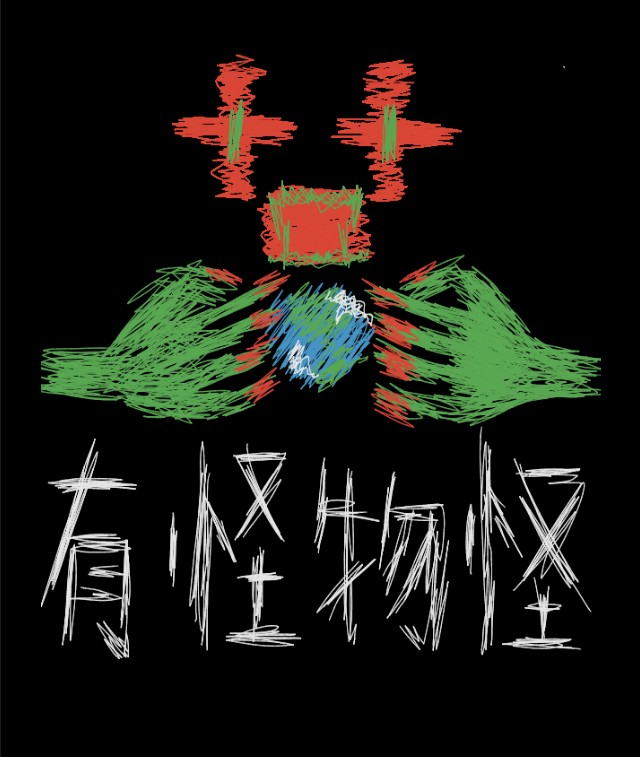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