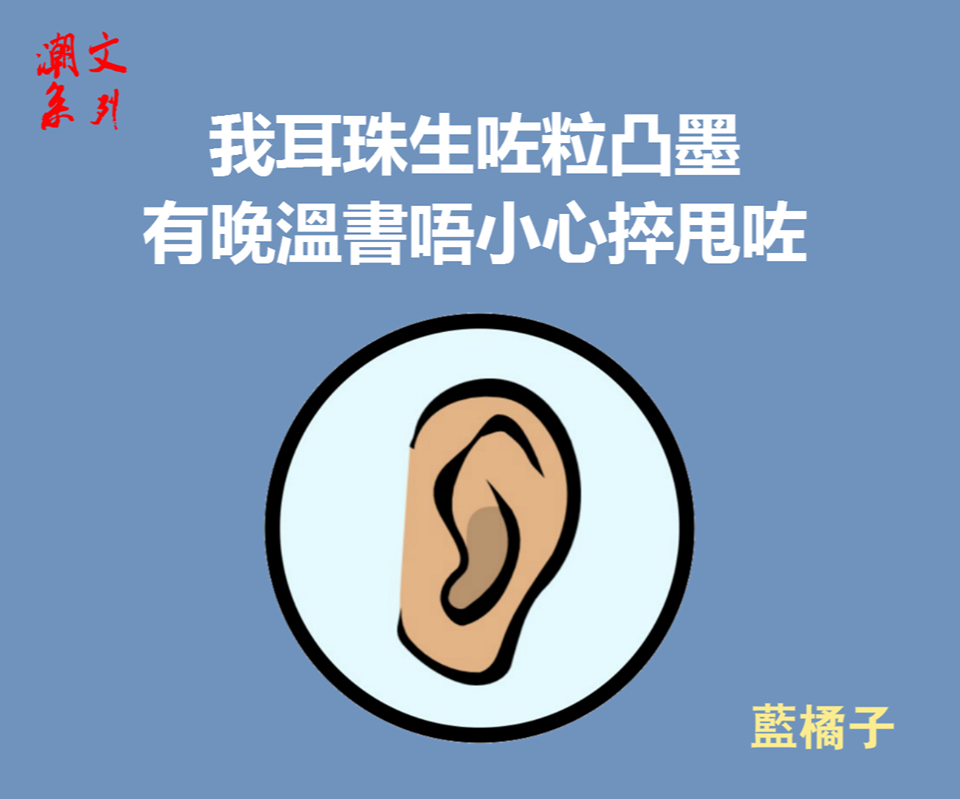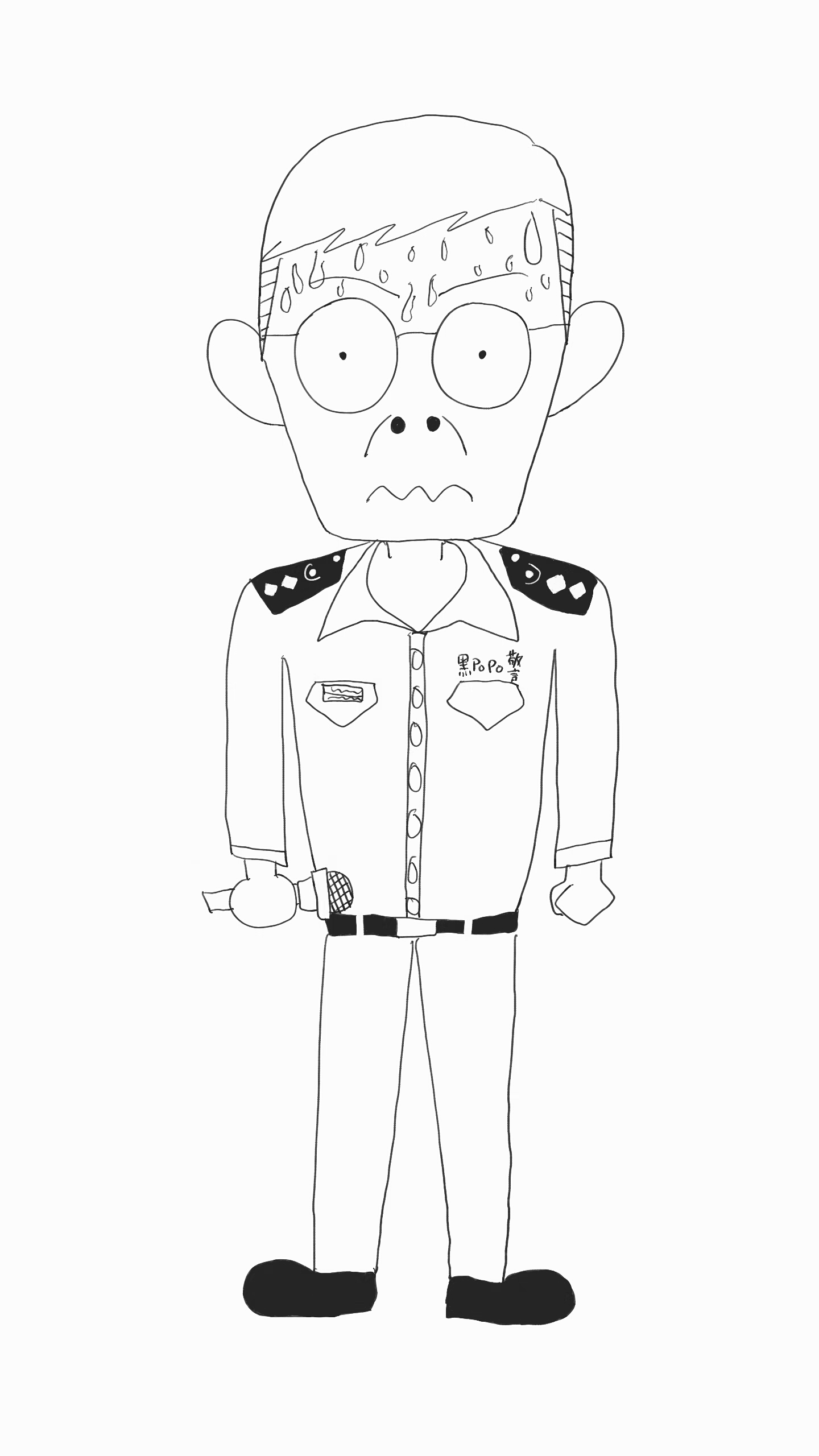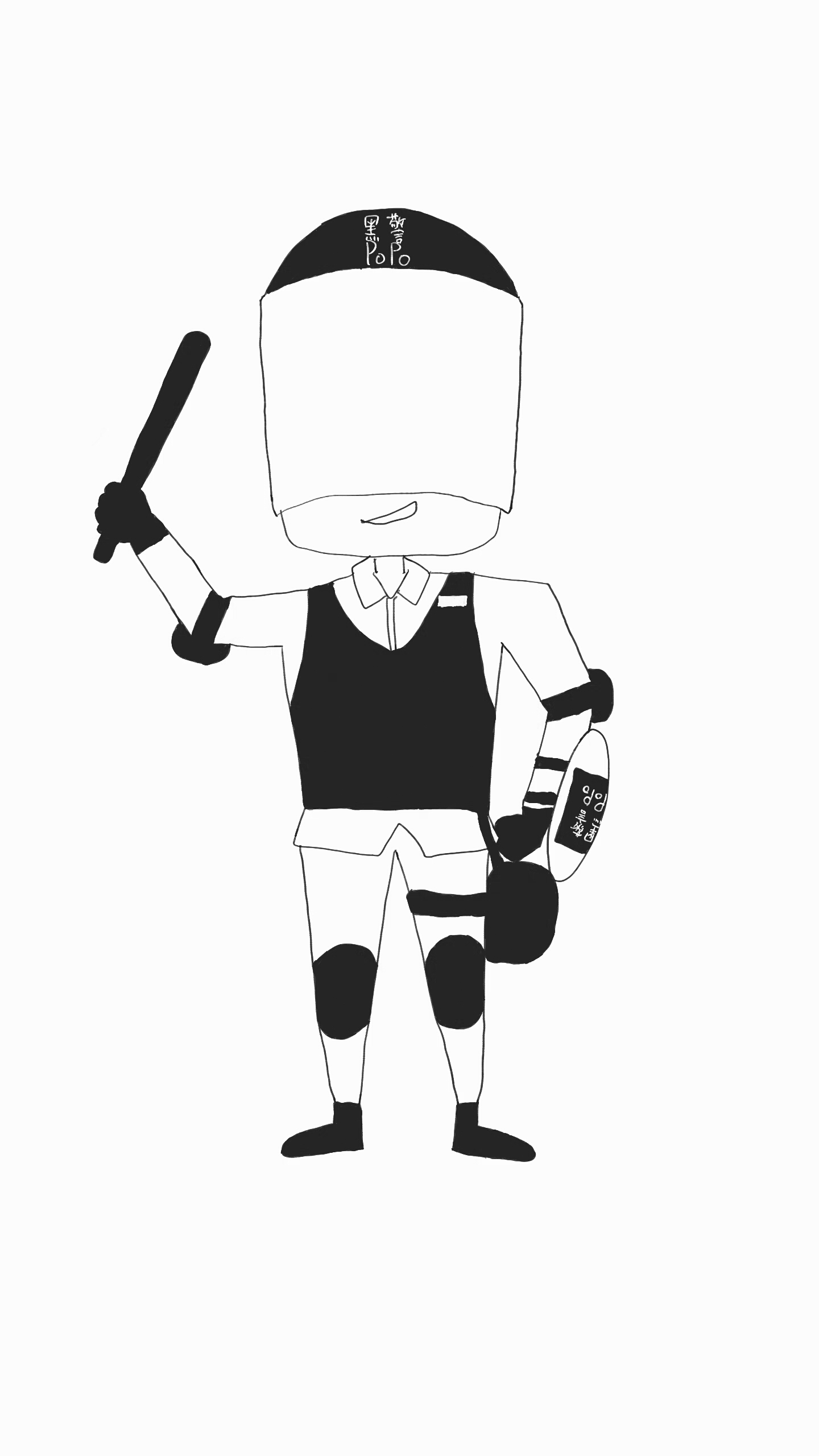現場凌亂一片,這裡是一棟只有五層高的舊式唐樓,想要到達位於四樓的案發現場,就要乘坐那部看起來隨時都會墜毀的升降機,後樓梯也只容許一人通過,還充滿著不知放了多久的雜物和垃圾。大廈的體積很小,每層只有一個單位,兩邊的大廈已經被政府重建過,而它就像一個肩膀縮起的小孩子被夾在中間。現場的相機的閃光燈忽明忽滅地閃爍著,幸好他們不是記者,而是在現場採集證據的警員,現場已經被警方用黃色的膠帶封鎖著,十幾個警員都案發單位來進進出出,每個人手上都拿著有用的證據帶回去化驗,以現場的情況來看,調查進度已經到達中段了,但某個人還沒有出現,那個「應該最早到達現場」的人還沒有出現。
在現場每個人都忙得不可開交,唯獨一個人站在案發單位的門外,阿齊。他尷尬地向每個進入的警員微微點頭打招呼,臉上掛著歉疚的笑容,每隔幾秒就看一下腕上的手錶,「為什麼那個人還沒來啊...」,心裡不停冒出這個問題,在阿齊接到警方的電話,這案件需要他們「岸峰偵探社」提供專業的意見時,他就一直在心裡祈求著,那個人千萬不要再遲到了...結果,現實跟他的願望似乎還有一大段距離。
「呵欠~~~真早啊~阿齊!守時是偵探必要條件,非常好啊~」突然一名男子從升降機裡走出來,笨拙地跨過黃色膠帶,搔著頭皮來到現場。
「是、是的,辛苦了。」阿齊再次微微點頭,心裡暗罵著「這裡最不守時的人是你吧...」
「情況怎麼樣?」這名男子就是「岸峰偵探社」的偵探,他叫陳岸峰,在這個年頭還用自己的名字當偵探社名稱的大概只有他吧,真是囂張的男人...而阿齊是他的助手,這家偵探社就只有他兩人雙依為命,真是孽緣啊~
「喔?你終於來了,快過來看看吧。」其中一名警員揮手示意岸峰過去。
「阿齊~工作了,小心別碰到現場的證物喔~」岸峰大叫。
「你才要小心嘛...」阿齊跟在他後面輕聲罵他,嘖嘖!眼前這個男人連直路都走不好,眼角還稠著一大垞眼屎,有資格叫人小心點嗎?
岸峰和阿齊進入現場大廳,也許是舊式樓宇還是個人喜好的關係,整個單位是一個正方形的大廳,左邊是睡房,近門口的是洗手間,隔壁是廚房,除了大廳看上去很寬敞,所有房間都小得可憐,而廳裡只有一張梳化、電視、雪櫃和一張褶合式木桌子,房間沒有任何裝飾之餘,絕對可以稱得上為簡陋有餘。
屍體正位於大廳的中央,屁股朝天地趴在地上。進入屋子後阿齊就一直摀住鼻子,因為在場一陣極之嗆鼻的化學液體味道,但岸峰似乎沒有察覺到,一定是因為他身上散發著能完全遮蓋住化學液臭味的酒氣有關。這單案件需要「岸峰偵探社」出現的原因,是因為這屍體的死法太過特殊,不像一般的兇殺案,奇怪的地方就在於那屍體某幾個部位被溶化成一灘血水。在梳化背後的牆壁有一道窗戶,外面的陽光能夠直接射進大廳,現在是正午時分,猛烈的太陽斜斜的把整個房間都照亮了,而光線剛好照在屍體的小腿以下和腰間,那正正就是屍體被溶解的部分,現場看起來,那屍體就像是被陽光溶解致死一樣。
「怎樣?有什麼資料需要嗎?」跟著岸峰進入現場的警員手上拿著一大堆資料,看著岸峰在東張西望了很久,所以才開口問他。
「這裡怎樣住人啊...真簡陋...」岸峰一開口就說出這些連屍體都會氣到彈跳起來的話。
「咦?」警員似乎不敢相信自己聽進去的。
「喔,請問有死者的相關資料嗎?」阿齊趕緊發問。
「根據調查的資料,死者是位六十五歲的老先生,名叫江方全,獨居,是這棟大廈的業主,一至三層都是外租給其他住客,而第五層頂樓和天台都是用來擺放雜物的,應該是被樓下的店舖租用來當貨倉了。初步調查所知,死者生前並沒有跟任何人結怨,也許在香港沒有家人,所以跟租客都很合得來,很多年都沒有加過租了。也因為這個原因,雖然是業主但家景沒有很富裕,所以也不像為了偷竊而殺人的案件,死者的財物都沒有遺失。而且大概是老人家的壞習慣,死者將所有錢和值錢的東西都放在床底下的餅乾罐了,不像是熟人的所為。」
「查案太快下定論是很大問題的喔~警員先生~」岸峰豎起食指左右搖晃,否定警員所說的結論。
「.....」阿齊皺起眉頭,岸峰的老毛病又來了。他自己也一定對案件還沒有頭緒吧,但卻總是否決別人的論點,打沉別人的士氣,好像現場只有他一個可以思考案情一樣...
「我說你滿身酒氣來當偵探才是大問題吧!」那警員反駁,岸峰的言論又成功惹事生非了。
「你說什麼啊,那是我的體味好不好...」岸峰還在辯駁。
「那有體氣是這種味道的!你是在酒瓶裡出世啊?!」警員愈罵愈怒。
「體味這種東西是你發明的嗎?」岸峰。
「吓?」警員。
「你確定自己嗅過全世界的體味嗎?」岸峰。
「你有資格評論我整個人生所發散出來的氣味嗎?你是體味博士啊?」岸峰。
「.......」警員。
「.....」阿齊望著岸峰那副得了辯論大賽的得戚樣搖頭嘆息。
阿齊不知該用惱怒還是憐憫的眼神來看待這個名叫岸峰男人。除非是對方道歉或轉移話題,否則這場對案件毫無用處的爭辯會一直延續下去。但很可惜,阿齊很清楚岸峰這個人不會有任何羞恥之心,簡單點說就是他能夠除時將內部完全放空,像抽水馬桶一樣,把無謂的或者重要的事在一瞬間忘得一乾二淨。阿齊就試過多次跟他去吃飯,當開始進食時,他總會像吃了毒藥一樣咒罵「哎呀!這裡的牛肉真難吃!」,下一瞬間他又會說「算了~下次記著不要再吃這裡的牛肉就好~」,別以為事情已經結束了,到下次跟他去同一家餐廳吃飯,他又會點有牛肉的菜色,然後重演上一次的戲碼...
在阿齊心目中的偵探,理應是具備超乎常人的洞悉力、分析力,還有心思細密但行事大膽的人。但陳岸峰先生,卻跟以上所有元素背道而馳,還兼備凌駕於白痴級數的目光短淺和輕率無腦...
縱使如此,警方還是對他非常重用,因為岸峰曾經多次協助警方,破解多宗難搞的殺人案件並找出兇手。但破案的真的是他嗎?當然不是~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有一個比他聰明百倍的嘍囉跟著,阿齊一直跟在這個爛透的男人身後。阿齊在讀大學時主修犯罪心理學,並獲得非常好的成績,也曾被大學教授推薦給警方,作為日後協助破案之用,他也曾被測試出128的超強IQ數值,在大學裡被籲為「明日破案之星」,本來是個自途無可限量的年青人,竟然蜷縮在這條懶蟲背後,到底是為什麼呢?連阿齊自己都不知道,也許是自己的性格太過優柔寡斷,每次想向岸峰提出辭去助力的職務,都被他用招牌的推卸技巧給矇混過去,也許在「行事輕率」方面,自己倒應該向岸峰學習一下。
「鈴鈴鈴~~」室內突然傳出卡通的主題曲鈴聲,但他的主人似乎毫不知情。
「岸峰先生,你的電話在響。」阿齊噘著嘴戳了戳他的背,那個人一定又是在「放空」狀態了。
「喔?我知道!我當然知道啊阿齊~這些小事你不用提醒我~」岸峰從遊離狀態驚醒過來。
「喂喂~我是岸峰偵探社的大偵探岸峰先生,請問有什麼事呢~?」連自我介紹都囂張臭屁,真是令人討厭到極。
「請問偵探先生查到什麼了嗎?」阿齊站在背後,隱約聽到電話裡的內容,看來是警方之類的打電話來催促,想要趕在對媒體公開前,掌握到破案的重要資訊。
「喔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大致上現場的情況我已經完全掌握了。如果不是有人對我的體味有意見的話,我早就能破案了!」岸峰故意大聲地說,氣得那個警員的臉漲紅起來,別過臉就走開了。
「請務必在對媒體公開前,找出破案的線索,有勞了~」
「當然。」岸峰把電話關掉,然後不知從那裡拿出電動鬚刨,放在長滿鬚渣的臉上,發出「滋滋滋」的聲音。
喂喂,你是搞笑藝人嗎?幹嗎在這種場合拿出這種東西...等等!那、那不是剛才放在大廳的桌子上,死者家裡的東西嗎?岸峰大偵探啊!你是決心想把那老翁氣到彈跳起來跟你說誰是兇手嗎?拜託你停手吧~~阿齊在身旁作出無用的祈求,那些滋擾聲音開始吸引到其他人的注意了。
「請、請問還有什麼資料可以提供?」阿齊用更大的嗓子問身邊的警員,遮蓋住鬍刨的滋滋聲,希望岸峰可以快點完結。
「喔,初步推判死亡時間是早上六時至八時,剛好就是天亮的時間。致死原因是在腰部被強烈的化學溶劑,把肌肉和骨骼都撤底溶解。相信兇手是想塑造一個「吸血鬼」被太陽光照射而死的假象,在警員到場時,在腰間和大腿遮蓋住一件死者的外套,相信是在掙扎時巧合地扔在自己身上的,這兩個部位沒有被陽光射到,所以也沒有被溶解成血水,由於外套很有可能藏有兇手的指紋,所以被拿回去化驗了。」
「現場還有什麼兇手留下的線索嗎?」阿齊。
「沒有了,地板上只留下一道從門外進入大廳的鞋印,大小剛好是死者的尺寸,而鞋印的軌跡剛好消失在死者的腳下,也就是說那鞋印是死者進入屋內時留下的。」
「死者進入屋內、剛好是天亮時間、被陽光照射到的部位全被溶掉...」阿齊在腦海中分析著案情。
就跟那警員之前所說的一樣,現場所有的線索,都是在塑造出死者是一名吸血鬼,因來不及在天亮前回家掩住窗簾,所以慘被陽光溶解...那當然不能將案件列為「吸血鬼意外死亡」了結事情,這全都是兇手的把戲,這是連小學生都清楚的事。可是也太奇怪了,如果死者的致命原因是肚子整個被溶解的話,除非那溶劑非常強烈,可以在一瞬間內把人的肌肉和骨骼全都溶掉,不然的話死者一定會在死前痛苦地掙扎,那就不可能不偏不倚地死在陽光照射進來的位置了...但死者身上確實沒有跟人打鬥過的痕跡,而且鞋印又只得一道...
阿齊在腦海裡不斷推敲尋找兇手的破綻,此時電動鬚刨的嘈音已經停下來了,岸峰剛才也一直有在旁聽著。阿齊瞟了他一眼,赫然地瞪目結舌起來。岸峰那副見到鬼的驚愕表情,還有顫抖過不停的牙齒,簡直就像小學生去露營聽到鬼故事時的表情一樣,看樣子岸峰已經將思緒完全偏向「死者是吸血鬼」的一方了。
「該不會死者就是吸血鬼吧...?!」那警員望著屍體補了一句。
「哈哈哈~單看就知道這全都是兇手的把戲,是連小學生都清楚的事吧,你這樣還去當保護市民的警察,真的沒問題嗎?!」岸峰聽見那警員的話,又下意識地否認別人的論點了...
多得岸峰再次惹怒警員,「嗤」了一聲走開了之後,阿齊才可以安靜的繼續思考案情。雖然法醫初步估計令這名比大廈更老的老業主致死原因,是令整個腰部溶解的化學溶液。但死者在死前並沒有任何掙扎過的痕跡,相信也沒有令人體在一瞬間溶解的東西,所以由此能夠推斷,雖然被溶解的腰部是「令他致命原因」,但卻並不是「令他致命的武器」。兇手想這樣做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要毀滅真正致命的傷口。那就是說,如果得知兇手使用的武器,就一定能抓到兇手了!但是,為什麼兇手要多此一舉溶掉他的腳呢?難道真的是為了形象「吸血鬼」的假象嗎?
「喂喂!阿齊,你一定是被這種場面就嚇傻了吧?難道你到現在還發現不到嗎?」岸峰敲了一下阿齊的頭殼,打斷了他的思緒。
「什、什麼?」阿齊摸摸後腦,難道他已經發現殺人的兇器了嗎?!
「被人用強烈的溶液灑中,就算是過百歲的人瑞,也會哎呀哎啊地掙扎吧?可是那個老伯根本沒有掙扎,所以在他被溶解之前,就已經死掉了!但這樣做是什麼原因呢?我就想不通了...」岸峰樣子得意忘形得令人反感。
「....是、是的。」雖然想法被搶先一步說出口了,但阿齊還是點了點頭表示同意。至於「就是為了隱藏令死者致命的傷口啊!」這句說話,阿齊也咕嚕一聲吞進肚子裡,避免又再發生不必要的爭辯。
有了初步的推斷,接下來就要縮小疑兇的範圍了,畢竟這個世上的瘋子很多,喜歡玩吸血鬼這種變態玩意的一定也不少。現場所有有用的證物都被警方拿走了,想要再擠出什麼蛛絲馬跡也不太可能了,是時候開始詢問目擊證人和有可疑的人了。雖然岸峰還在苦惱著「兇手為什麼要用溶液把死掉的老伯溶掉」的問題,阿齊就提議說不如去問問其他人,看有什麼新發現吧,岸峰就呼一聲將問題拋到腦後,重拾心情離開案發現場了,真是個頭腦簡單的男人。
「等一下盤問疑犯的時候,記得要全權交由我發問!」岸峰一邊走出單位,一邊回頭吩咐阿齊。
「是,知道了...」阿齊點點頭。
「哎啊!~~~是誰暗算我。」岸峰突然發出叫嗥,「咚」一聲向前仆倒在地上。
「......」阿齊低頭一看,原來是岸峰剛才因回頭跟他說話,沒注意到門外擺放著的鞋子,看款式應該是那老業主的鞋子了,現在被岸峰踢到亂成一團,老伯死後也一定不得安寧吧...阿齊一邊這樣想著,一邊雙手合十拜拜。
「可惡,竟然將鞋子都放在門外。阿齊,我們拿掉他一隻鞋子然後扔到別處去~」岸峰正想彎腰,被阿齊喝止了。
「這樣對死者太不敬了吧!況且他已經死了,你這樣做也沒意思吧...」阿齊。
「我只是開開玩笑嘛,你這個人真是沒幽默感~」岸峰噘著嘴進入升降機。
岸峰和阿齊兩人乘坐升降機到地下,這棟唐樓雖然殘舊,但卻有地下大堂和保安在看守著,但話雖如此,實際上這裡只是一條狹窄的走廊,牆壁掛著每層的信箱,和一張簡單的桌子和椅子,看著一個比死者更老的老伯,可以說是保安設備極差,對強盜來說是一塊只要張開口就可以放進去的肥肉。
第一個要問的人是第一個發現死者然後報警,住在一樓的陳伯,他也兼任著這棟大廈的看更。陳伯一臉愁眉苦臉的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岸峰走到他面前連招呼都沒打,就開口問他。
「我是岸峰偵探社的偵探,我的名字就是岸峰。看樣子你很傷心吧?你跟死者是什麼關係?」岸峰。
「我跟江叔已經認識二十多年了,當年我失掉了工作,也找不到地方落腳。就是他把一樓的地方讓我住下來,也沒跟我收取過一分一毛的租金,只是要我在這裡當看更。」陳伯一邊說,一邊強忍著淚。
「江叔?江叔是誰?」岸峰。
「是死者的名字啦...」阿齊輕聲在岸峰的耳邊說,連死者的名字也不知道,當然嘛,他直到警方搜集證據中段才到達現場。
「喔喔~沒人告訴我,哈哈哈。你是怎樣發現死者的?」岸峰以笑遮醜,繼續問問題。
「我每天都會在早上七時上班,到差不多八時江叔就會下來跟我聊一聊,然後他就會去喝早茶了,天天如是風雨不改。但今天一直等到九時他都沒有出現,所以我便走上去敲他的門。我看見沒人應門,所以便報警了。警察到場後把門破開,便看見...」陳伯。
「唔~警方提供的資料死亡時間初步推斷為六時至八時,大概是沒錯。」岸峰。
「那麼,請問這位保衛大廈安全的老伯!昨晚凌晨時分直到發現死者之間,你在做什麼?」岸峰突然嚴厲起來。
「聽你的語氣是把我當成疑犯嗎?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啊!」陳伯激動得大叫。
「你不回答我的問題!你就是疑犯!」岸峰的老毛病又開始了...
「我每天下班的時間是凌晨一點,雖然工作時間很長,但我這麼多年來都是自願的。下班之後我就獨自回到一樓的房間睡覺了,我並沒有什麼不在場的證據,但我絕對不會殺死我的大恩人!」阿伯幾乎用吼的回答岸峰的問題。
「非常好,我問完了!」岸峰。
「抱、抱歉,請問一下,在你昨晚下班之前,還有今天7時上班後,有什麼陌生的人進入過這樣嗎?」陳齊細聲的問。
「晚上大概十二時的時候,住二樓、三樓的四仔達和小鵑一起回來了,除此以外沒有看過其他人進出這裡了。」陳伯也有禮貌地回答。
「你這個疑犯!這麼重要的事剛才竟然不告訴我!!」岸峰暴怒,用手褶起衣袖作勢要打人。
「你又沒問!」阿伯也站了起來。
「我們問完了,謝謝、謝謝!」阿齊把岸峰扯進升降機,下一個要問的人就是住二樓的四仔達了。
「好了,我們去三樓!」升降機一關門,岸峰就用姆指連續猛按著三字按鈕,彷彿可以令升降機加速一樣。
「為、為什麼突然上三樓,二樓呢?」阿齊問。
「........」岸峰擺出一副聽不到說話的樣子,雙眼飆向上望著升降機顯示層數的位置。
「你一定是因為聽見三樓是女生就想跑上去吧?!這樣是不行的!」阿齊飛快地按下二樓。
「剛才全靠我才能問出關鍵的線索啊!現在卻對我的判斷有意見?!好丫!接下來你來問好了...」岸峰雙手交叉擺在胸前。
「.....」到底剛才是誰說要全權交由他發問的呢...
「什麼嘛~我是想給你發揮的機會啦,小學生被老師委派做班務時,不是都應該很雀躍地跳舞嗎?」岸峰。
「知道了...」阿齊想不通,到底剛才的情況是小學生被老師委任,還是主人把骨頭拋出去,然後叫我扮狗去叼回來呢?
升降機門打開了,二樓跟一樓從外表看來沒有什麼大分別,左邊是樓梯,面前就是二樓的單位。岸峰一副看戲的樣子靠在牆壁,阿齊只好上前按下門鈴,按了數十下,才聽到門後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跑出來應門,打開門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一身邋遢打扮,頭髮凌亂,還在一邊揉著眼睛,「有什麼事?」足以嗆死人的氣味從這男士的口腔傳出,阿齊的臉撲個正著,不禁臉有難色。
「咳咳,請問你就是四仔達先生嗎?」阿齊把食指湊在節前掩著。
「嗯,什麼事?」四仔達似乎還沒睡醒。
於是,阿齊就跟四仔達簡單講述一下事情的始末,四仔達聽見之後好像觸了電一樣,瞪大那雙因睡眠不足而充滿紅筋的眼。阿齊一直都有注視著的反應,發現當說到有關「遇光的部位全被溶解,就像吸血鬼一樣」這部分,四仔達就立刻警戒起來,每次問到有關死者的事,他都說「不清楚」「跟他不熟」「不知道」,還多次有意無意地把敝開的的門稍稍閉上,這些小動作阿齊全都注意得到。所以,他就大膽地提出請求。
「四仔達先生,我們並不是懷疑你,實際上只是有些問題想弄清楚,能讓我們進去嗎?」阿齊頭探頭望進屋內,現在已差不多是下午時分了,房間內竟然漆黑一片,令阿齊更加好奇了。
「我跟江叔根本就不熟啦,只是普通業主跟租客的關係...」四仔達。
「別跟他說這麼多,如果他不肯讓我們進去的話,就把他當成重量級的嫌疑犯,把他直接鎖進監獄,再慢慢問吧!看他那副賊眉賊眼的樣子,就知道不是好人了,依我來看他是兇手的機率達到99%。」岸峰突然加入戰團。
「好好好,你們警察都喜歡來硬的,進來吧,反正你說的那個死亡時間,大廈裡又沒有裝閉路電視,這裡所有人都應該沒有不在場證據吧?!」四仔達「砰」一聲打開門,屋內的酸臭味瞬間湧出來。
「謝謝你的協助。」阿齊鬆了一口氣,如果剛才不是岸峰的幫助,自己大概對這種粗魯的人最沒輒了。
「做得好,你一定是想用同樣的方法,進去三樓那個小鵑的房間,這樣別人就不會說我們濫用權力了,想不到你這麼聰明啊~值得嘉獎!」岸峰拍了拍阿齊的肩。
「謝謝...」阿齊無奈地點頭接受嘉許,但他根本就不是這個意思啦...
二人進入四仔達的單位內,阿齊覺得整個人都彷彿被惡臭籠罩著一樣,這裡的臭味比起案發現場還要臭。即使說這裡收藏著幾十具屍體也不誇張,阿齊由衷佩服四仔達能夠在這個空間裡睡覺。其後,三人隨便找了個地方坐下來,因為整個房間都漆黑一片,只聽見四仔達把一大堆雜物掃在地上,然後勉強把梳化騰空出來。
「請問,能把燈開著嗎?」阿齊覺得這個單位和四仔達都肯定有古怪。
「可以是可以,但你們答應我要先冷靜,事情並不是你們所想的...」四仔達這句說出口,阿齊就更加對他懷疑了。
「你放心!我們很冷靜!」岸峰大聲回答,其實在場最不冷靜的人是你吧...
「咔嚓」一聲,終於能看見單位的情況,阿齊和岸峰二人罕有地有默契從梳化裡彈跳起來!
「嘩!來人!來人!抓住這個兇手!!」兇岸尖叫得像一個看見蟑螂,跳上梳化上大叫的女生。
「我早就叫你們冷靜嘛,這就是我一直不想你們進來的原因!」四仔達搖搖頭。
阿齊鎮定下來後,掃視一下整個單位,對比起屋裡擺放的東西,那肢不知從何傳來的臭味實在小巫見大巫。先不談地上放了很多不知名的書藉和經文,牆壁上還掛滿了十字架、六角星的巨型畫報、泰國的佛牌。天花板還用紅色的油漆塗滿了詭譎的符號,最誇張是阿齊瞄到房間裡放著一副打開了的棺材,看樣子四仔達就是從裡面走出來應門的了。簡單來說,將這個世界所有詭異的東西集合在一起,就足以形容四仔達的房間了!
「請、請問你從事那個行業?」阿齊。
「別說那麼多啦~阿齊!抓住他!」岸峰還沒從驚恐中冷靜過來。
「四仔達只是我的花名啦,我是在附近的商場賣色情光碟的,屋子裡收集的東西只是我的興趣,至於那棺材,只是我找人改裝的啦,其實他是床...」四仔達聳聳背。
「所以你聽到江叔的死法,就害怕被我們看見這些東西了是吧?!請問昨天凌晨時分,你在那裡,正在做什麼?」阿齊點點頭。
「我大約在晚上十二點跟小鵑一起下班回到這裡的,回家之後就開始清理那些佛牌和唸經書,這是我每天的程序。唸到大約凌晨三點,就進去睡覺直到剛才被你們吵醒了,所以我就說根本沒可能有不在場的證據啦...」四仔達。
「明白了,那請問回家的時候,在大堂有看見陳伯嗎?」阿齊。
「有啊~雖然找他來當保安是沒什麼作用啦。因為我工作的關係,每天都差不多這個時間回來的,但陳伯他從來沒試過在工作時打睏,真是佩服他呢!」四仔達。
「嗯...另外,小鵑每天都跟你一起回來的嗎?」阿齊心裡將四仔達跟陳伯的口述綜合在一起。
「下班的時候碰見的話就會一起回家囉,她都是在附近上班的,但詳細的你自己問她好了...」四仔達眼睛不停瞟向房間裡那副棺材。
「嗯,暫時沒有問題了,抱歉打擾你休息,再有問題的話我們會隨時找你的。」
「我早就說我跟那江叔根本不熟,我也沒有殺他的理由啦。」四仔達再次強調。
「我們明白,謝謝。」阿齊站了起來,岸峰知道已經查問完畢,就飛快地衝出單位。
接下來,阿齊和岸峰向第三層進發。阿齊用手指執住衣服的領口,晃了晃想甩走四仔達家裡的酸臭味,這種奇怪的味道,吸太多也許會帶來霉運吧?!古老又殘舊的升降機關門時發出聽起來很痛苦的悲嗚,不仔細感覺的話根本不知道它是停在原地還是在上升。阿齊趁著這個空檔細嚼四仔達的證詞,如果他跟陳伯沒有串謀提供假證詞的話,那麼在時間上陳伯所提供的時間就吻合了。現在最頭痛的是,案發的唐樓根本沒有任何閉路電視可以提供到確實的證據,只能靠著各人的證詞來分析真諦。再加上事發的時間在剛天亮的早上,或者更加早的時間,在這棟只得四個住戶的大廈裡,根本不太可能提供到有力的不在場證據,所以這次的案件不能靠「不在場證據」來追查誰是兇手。從陳伯的證詞聽起來,他確實沒有殺人的動機,如果是他殺了江叔,更會使他扔了寶貴的工作。而另外一個人,四仔達的行為和證詞都讓人覺得很有可疑...
「你有覺得剛才四仔達的說話有古怪的地方嗎?」阿齊開口問。
「你是指他的口很臭的事?」岸峰打了一個像河馬的呵欠。
「首先,這次的殺人手法,很明顯就是指向四仔達他的古怪嗜好,就連他本人也立刻發覺到了。」阿齊。
「單看樣子我就知道他是兇手了,如果是有人想嫁禍給他,也證明他並不是一個好人...」岸峰剛才在眾多警察面前,都會搶著說一些沒意義的推理見解,但現在只剩下他跟阿齊兩個人,岸峰就乾脆把大腦關掉了。
「我是指四仔達回答問題的時候...」作為一個偵探以外表來判斷誰是兇手不會有問題嗎?阿齊有這樣的想法,但又不敢說出口。
「呃!我剛才沒專心聽到...」岸峰。
「....」還是算了,剛才自己開口問岸峰意見的時候,好像顯得太過多餘了...
這個時候,升降機轟隆地搖晃了一下,嚇得阿齊緊抓著扶手,岸峰不知那來的敏捷身手,竟然一下子跳上扶手上分開雙腳撐著身體了。兩人像電視節目完結時一樣定格,升降機也停住了,沒有絲毫想要開口的跡象,有種快要咚一聲直墜地面的感覺。「混蛋!混蛋!混蛋!竟然讓我出醜!」岸峰猛力踹向升降機門洩忿,升降機又大幅度地搖了幾下,這次阿齊失去平衡跌倒了。
「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升降機門慢慢打開了。
「唔唔~我早就叫你平時要好好鍛鍊身體了,看我剛才的平衡力配合英勇的膽色,也許這就是天生當偵探的材料吧。」岸峰眉飛色舞地踏出升降機。
「是、是的...」阿齊好不容易站穩住腳,也急步走出來了。
「對了!我想到了!」阿齊突然大叫。
「嘩~~想嚇死人啊?」岸峰被嚇得彈跳起來,剛才英勇的氣勢一下子被撲滅了。
「平衡!是平衡啊!這就是四仔達的問題所在了!」阿齊。
「你是說四仔達的心理不平衡啊?」岸峰。
「不是,你還記得嗎?他為了證明自己是清白,不停慌張地解釋自己家裡的棺材和佛牌,還多次說到自己幾乎不認識江叔一樣。」阿齊。
「然後呢?」岸峰。
「一個這麼害怕變成疑犯的人,把證詞說成對自己有利是正常不過啦。但是當我問到他跟小鵑的關係,你還記得他怎樣回答嗎?」
「別在賣關子了!四仔達所說的話我根本一個字都沒聽進去!我只想趕快去找小鵑啦!!」岸峰惱得把真相說出來了。
「他只是一副想逃避的樣子說「你自己去問她吧...」,一個這麼慌張去解釋自己的人,怎麼會說得含糊不清呢?難道他不害怕小鵑會說一些對他不利的證供嗎?」阿齊愈說愈激動,還忘形得揪住了岸峰的肩膀。
「那就是說....」岸峰根本懶得去思考,他的腦袋大概只會在其他人面前,眩耀自己不知所謂的時候才會轉動吧。
「可能性只有幾個,四仔達跟小鵑有「不知道是否應該透露」的關係。或者「如果透露了,會對小鵑或者自己不利」。」
「嗯嗯~道理得很妙啊,我們快去問一下就知道囉~」岸峰根本沒聽進腦子。
「好了!嘿嘿...」岸峰向前三層的單位前進,他興奮得雙掌在磨擦,還加了幾聲意識不明的笑聲。
「一切的謎底應該就在裡面了!」阿齊也緊張得屏住呼吸。
「?!」岸峰看了看門牌,伸出去按門鈴的手硬生生停住了。
「怎麼了?」阿齊。
「呵欠欠欠欠欠欠欠~~~」岸峰把手收回來,然後舉高雙手伸展腰板,做出一個極之生硬的伸懶腰動作。
「沒、沒事吧?」阿齊。
「很累啊~阿齊啊~不如今天就到此為止了~」岸峰。
「到此為止?現在是最重要的時刻啊,況且現在才晚上七時咧!」阿齊遞出手錶抗議,他今早剛天亮時就到達現場了,但岸峰差不多下午才出現,加上綜合了各人所提供的線索,小鵑是最重要的人物,怎能...
「啊!我的頭!很痛!!啊~~不行了,看來我是患了不能再思考的病,就算再查下去,也、也...啊~」岸峰在地上抱著頭打滾...
「沒事吧?怎麼會突然...」自從在案發現場離開之後,你那有動過腦筋啊...阿齊心裡咒罵。
「你想看著我死嗎?!」岸峰的眼有淚光。
「那好吧...明早等到警方那邊的報告出來後,再繼續查吧。」阿齊先扶起岸峰,再跟他走進升降機裡。
「阿齊,我告訴你,身體是很重要的,千萬別待薄自己的身體啊,早點休息,頭腦才會靈活,知道嗎?」岸峰走出大廈,就推推阿齊的背像趕他回家似的。
「可是,你自己一個人回家真的可以嗎?」
「咦?丫~離開現場後頭痛又好像消失了,哈哈哈~」
「這就好,明天見。啊...可是明天早上報告就應該會出來了,請前輩早一點到場。」阿齊怯懦地低著頭說。
「啊啊~明天我會是最早一個到場的,晚安晚安~」岸峰。
岸峰一邊揮手,一邊看著阿齊的背影在逐漸縮小。一直揮擺的手垂下來了,再三確認周圍沒有認識的人,岸峰又竄回大廈內...
明天早上:
案發現場,死狀令人不忍卒睹的江叔昨天就被人搬走了,現場除了標示著「生人勿近」的黃色帶膠,地上還有用粉筆畫上一個人型圈圈,在場有用的證物也被警方全拿回去再更深入的調查,雖然可以拿走的都已經拿走了,但案發現場還是有一堆警員在進行地毯式搜索,希望能夠找出兇手留下的痕跡。以現今的科技,只要兇手留下像沙子般小的皮膚組織或指紋,就能靠著這丁點線索找出兇手。一旦鎖定了兇手是誰,即使他逃到天腳底,靠著太空上的人造衛星、電話記錄、信用卡記錄,兇手也一定逃不過。所以有人不禁會懷疑,又不是福爾摩斯的年代,這個世界還需要有偵探的存在嗎?
所以,現今能夠成為偵探的,那個人一定是天才,不然就是精英中的精英。他的頭腦必須比一般人清晰,判斷力也要比電腦更精確。但...凡事總有例外的...
「鈴鈴鈴~~鈴鈴鈴~~」
「嗚..唔?」岸峰像隻喪屍一樣接聽電話。
「報告出來了,在案發現場沒有任何兇手留下的痕跡,升降機內充滿著每個住客的腳印和指紋,根本不能作準,你有什麼解決的方法嗎?!我們已經擋不住那批媒傳了!」電話裡是從警察總部打來的,從聲音就能聽得出他焦急萬分。但,電話在接聽之後就被可憐地扔在地上了...
「呼...呼...」
「別再睡了!!給我醒來啊!!」電話裡的那個人大吼著,如果是在動畫裡,那人一定會從電話裡竄出來捏著岸峰的頸吧。
「我在聽啊!我沒有睡啊...」岸峰。
「你到底在那?如果你還不給我解決這案件的話,你就永不被警方錄用了,這那家偵探社也注定關門大吉吧!」
「我、我已經在現場了,嘻嘻嘻~我已經找到兇手了~呵呵呵~」岸峰從床上彈跳起來,七手八腳地拾起地上的衣服,一股勁地將手啊腳啊亂穿一通,然後一溜煙般走出門口。
「這麼快就走了嗎?」睡在岸峰身旁的女人被腳步聲驚醒了。
「對啊!我要去抓兇手了~再見~」岸峰頭也不回就離開了。
「噠噠噠噠噠~」鞋子發出怪聲,岸峰走路的姿勢也有點怪,但也不理得這麼多了,岸峰急忙地跑上一層樓梯,到達兇案現場,現場已經擠滿了大批警員,以及等候多時的阿齊,顯然他並不是最早一個到達現場。
「咦?現在才九時而已?!」阿齊看著站在門外的岸峰,對他在「早上」時分出現感到驚訝。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啊!」岸峰正想跨過黃色膠帶,突然失去平衡,整個人飛彈進屋子裡趴在地上,眾人看著這個情景都默不作聲,這種誇張的跌法不是在過時的搞笑喜劇才會出現嗎?怎麼會...
「嗚啊~!!」岸峰極速從地上彈起來,因為他發現自己趴在地上的位置,正好跟江叔死亡的位置一模一樣。
「呼...這樣做的話會觸怒死者的呢~」岸峰拍拍自己的胸腔。
「.....」不計現場,你觸怒死者的事都已經幹得太多了...阿齊心想。
「死者也有可能是這樣跌死的嘛...唔~」岸峰避開其他人的目光,假裝在思考著,實質他的腦海一片空白。
回想起剛才岸峰跌倒的情形,阿齊好像突然發現了問題的癥結。昨晚他回家後,花了一整個晚上將昨天所得到的線索綜合起來再分析一次。有部分的線索跟疑點都已經被解決了。雖然只憑推理沒有證據的話根本不能證實,但相信這些線索應該能從小鵑身上問得到。但剛才岸峰這樣一個羞臉之極的飛撲,好像把阿齊心裡那些解不開的謎團都解開了。
「我明白了!」阿齊大叫,彈響了手指。
「又想嚇人?!」岸峰。
「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真是謝謝你啊岸峰先生!~」阿齊歡喜地讚揚。
「呵呵,不客氣。」岸峰不知為何,但還是高興地搔搔頭。
「能請你解釋一下嗎?」其中一位警員說。
「岸峰先生多次跌倒,是因為江叔的習慣,將所有的鞋子擺放在門外。但現場卻發現了一對走進屋子裡的鞋印,一直從門外伸延到江叔死掉的位置。一個習慣將鞋子放在門外的人,又怎會突然穿著鞋走進屋呢?答案就是,那根本不是江叔的腳印!」
「那是誰的?」岸峰還是沒睡醒。
「是兇手的腳印!是兇手穿著江叔的鞋子,然後走進屋內進行溶解時留下的腳印。」阿齊。
「那為什麼兇手能夠使江叔乖乖地躺在陽光照射進來的位置,讓他慢慢溶解呢?」警員。
「因為江叔在進入屋內之前已經死掉了!」阿齊豎起食指。
「死掉了?!」
「沒錯,兇手一定是埋伏在門外,等到江叔回來之後,就用武器從背後令他致死,然後為了遮蓋著那武器造成的傷口,就索性用化學溶液將他溶解掉了。」阿齊。
「背後受到襲擊?那為什麼能剛好死在被陽光照射的位置呢?」
「這個問題本來我也一直想不通,但全靠岸峰先生剛才進來時剛好跌在死者的位置上,我就想通了!」阿齊。
「呵呵,不客氣。」岸峰還是搔搔頭接受不知為何的讚賞。
「兇手應該是因為某種原因,一時情急之下才對江叔起了殺心,事前根本沒有太多計劃的兇手,在單位外伏襲江叔後,才清醒過來意識到殺人的嚴重性,於是就想出這種臨時的解決辦法。不知從那裡找到溶液之後,就穿著江叔的鞋子走到屍體旁邊,用溶液將受到攻擊的部位亦即是腰間溶解。但當兇手想要離開現場時,就察覺到雖然自己留下的只是江叔的鞋印,但他卻是沒穿鞋子趴在地上的,警方發現到有鞋印但江叔卻沒穿著鞋子的話,一定會起疑,所以就索性把小腿和腳踝都溶掉,製造「鞋子被溶掉」的假象。」阿齊。
「但為何兇手要多此一舉?」警員。
「頭好痛...」岸峰想必是思考過度,所以坐在一旁按摩著太陽穴。
「如果剛才我的推理正確的話,就能夠得出幾個結論只要找到幾樣東西,就能找出兇手了!」阿齊。
「別賣關子了!快說!」警員。
「一.兇手所用的武器很特別,單看傷口就能知道誰是兇手了。二.江叔的死亡時間是剛好天光的時候,兇手塑造「吸血鬼見光死」的假象,就是為了明顯地嫁禍給某個人,這就證明了兇手也是這棟大廈的住客。三.當保安的陳伯說每天天亮時就會上班,除了不見江叔下來之外,也沒有看過任何人進出大廈。所以,兇手使用的武器和穿著的鞋子都一定還留在自己的家裡!我們都太著重案發現場的證物了,根本沒有認真去查其他人的家!」阿齊。
「說得也對,但兇手會是誰呢?」警員終於認同阿齊的推理,令阿齊有點得意而嘴角上揚。
「咦?~那是誰的鞋子?」岸峰一直坐在一旁低著頭打盹,但當他注意到腳上有點不熟悉的東西時,才抬起腳一看,發現他穿著的不是自己的鞋子,一定是剛才太過匆忙所以穿錯了其他人的鞋子。
「啊!那跟殘留在地上的鞋印一樣!」岸峰抬起腳時,警員發現到他的鞋底跟殘留在地上的鞋印一樣。
「我、我不是兇手啊!」岸峰連忙揮手。
「這雙鞋子是從那裡得來的?」阿齊問。
「小鵑的家!」岸峰驚慌地跳起。
在場的警員、阿齊、岸峰一同奔出單位跑向小鵑的家。沒錯,全靠岸峰突然坐著抬起雙腳,像嬰兒換尿片時的姿勢一樣,就發現了誰是這案件的兇手。一眾人圍在小鵑的單位外嚴陣以待,警員大力拍打木門。終於小鵑打開門了,還沒意識到自己已被鎖定為兇手的她,還裝作一副神色自若的表情慢慢把門打開。
「有什麼要問的啊?」小鵑撥弄頭髮之餘,還不忘向岸峰拋媚眼。
「現在懷疑妳跟一宗兇殺案有關,請跟我們回去協助調查!」警員像重覆百次一次說出例牌的台詞。
「吓?你們都還沒有查,就說我是兇手?!」小鵑。
「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請妳合作。」警員正想上前。
「站住!不準動!」小鵑突然拿出一個黑色的長方形盒子,前方發出啪啪聲之外還閃爍著藍色的電弧。
「小姐你冷靜點!」警員被嚇得退後了幾步。
「原來是你!你昨晚睡在我這裡就是為了查案!是不是?!我要告發他濫用職權!召妓不付錢!是他!是他!!」小鵑發狂地指著岸峰,一邊揮動手上的電擊器。
「我、我...妳別含血噴人!」岸峰作賊心虛地反駁,剛才情急之下他又穿回江叔的鞋,突然右腳突然拐了一下,畢直地撲向小鵑。
「啊啊呀~」小鵑尖叫。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岸峰也發出悽厲的叫聲。
這也許就是岸峰先生人生中最英勇的時間吧?!阿齊心想。這時岸峰的身體發出滋滋滋的聲音,身體抖了幾下就昏倒在地上了,觸碰到電擊器的手臂還被燒焦了一個小傷口。阿齊低頭看著那個正在冒煙的傷口,突然像靈機一動般用手握成拳頭鎚打自己的另一隻手掌。
「多得岸峰先生,我想到了!殺死江叔的,就是電擊器!」阿齊。
「謝、謝謝讚賞。」岸峰以嘶啞的微弱聲音在地上擺出勝利手勢。
「還不抓住她!!!」岸峰吐出最後一口氣便昏倒了。
終於,小鵑因殺人案被警察正式落案起訴了。而英勇的岸峰簡迷之後送往醫院檢查,睡了一整天才醒過來。當他張開眼睛,就看到阿齊和重案組的警長都站在床邊,岸峰本來還想繼續裝睡,但警長就先開口了。
「哈哈哈哈~大偵探岸峰果然利害,只花了一天就破案了!」警長仰腰大笑。
「這、這個當然嘛,這麼簡單的案件,一天也嫌太慢了~」岸峰聽到讚賞,立刻變得龍精虎猛。
「說得好說得好。可是,那個當妓女的兇手不斷說你假冒警察還濫用職權,到底是怎麼回事?」警長語氣一下子變了。
「我當然是為了查案嘛,濫用職權的事我是不會做的!哈哈哈!」岸峰生硬地笑。
「這樣我就放心了,好~你慢慢休息,我不打擾你了。」警長拍了拍岸峰的膀頭,就步出病房了。
「.........」岸峰跟阿齊沉默了好一陣子。
「小鵑已經承認了自己是殺死江叔的兇手,原因是江叔經常恃著自己是業主,常常就跑到小鵑的家裡跟她進行性行為,以不加租作為理由事後又不願支付肉金,小鵑忍無可忍才動了殺機。」阿齊。
「那四仔達呢?」岸峰問。
「四仔達跟小鵑以前是情侶,但當四仔達知道小鵑的職業後就跟她分手了。小鵑覺得他只是個賣色情光碟的又有什麼了不起,所以就嫁禍給他了。」阿齊。
「喔...原來是這樣嘛...」岸峰點點頭,望著自己手臂被繃帶牢牢包住,回想起自己竟然在兇手的房間裡睡了一整晚,有種死裡逃生的感覺。
「小鵑所用的超強力的電擊器,說是用來防衛用的,但由於殺傷力太強,直接就把年紀老邁的江叔電死了。幸好岸峰先生的身體壯健,只是昏迷了一天就醒過來呢。」阿齊。
「當然嘛,偵探除了頭腦之外,還需要強健的體魄呢~」岸峰舉起手臂,不慎刺激到傷口痛得哎呀呀大叫。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