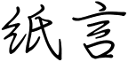我叫Fiona,朋友知道我是賣豆腐的,都以為我一定叫阿蓮或者阿蘭,現在是甚麼年代了,賣豆腐不可以有英文名?
我家三代賣豆腐,小時候覺得自己父母在街市工作,總比上其他同學父母在寫字樓或銀行這些地方上班高尚,曾經自卑了一段很長時間。即使升上中學後,同學問起我父母,我也只說他們做食品加工生意,他們一聽以為是即食麵或罐頭之類的工廠,總會一臉羨慕配搭「你爸了不起啊!」的神情望著我,又會問即食麵吃得多會生癌嗎?午餐肉究竟是不是老鼠肉等低級問題,難道李嘉誠會知道怎樣接駁屎渠?真替香港的教育制度擔心。
但後來我看過小津安二郎的「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之後,態度有所改變,驚覺原來賣豆腐也可以很文藝,可以很誠品,對自己的身份多了一種肯定。我稍作修改,變成:「我家是做豆腐的,所以我只賣豆腐」,這句話聽起來有一點世故,也帶一點年輕人的偏執,我認為很適合我。
這幾天,對面生果檔的肥仔聰經常借故過來找我,我是知道他喜歡我的,他從小學開始便喜歡我,但我對他沒感覺。他曾經在情人節送我九十九支玫瑰,但他是在我旁邊的花檔買的,送來的時候,就是從花檔搬過牆的另一邊,放了一整天,害我被三十二個人問我那些玫瑰賣多少錢,平白幫花檔增加了生意。
但他還是打動不了我,不為甚麼,可能就是欠緣份吧!加上他未滿三十歲便有四十吋的腰圍,我好說也是做素食生意的,怎受得了這種肥膩?
今天,他又無事找事的走過來,問:「Fifi,你想吾想睇軟硬呀?」。
這個肥仔就是懂得看穿我弱點,在「軟硬」面前,我變得只能軟,不能硬。
「是但啦!」我隨便應句,他歡天喜地走回去。
這時候,我想起王菲的一句歌詞:「歷史在重演,這麼煩囂城中⋯⋯」
完
賣豆腐 原來賣豆腐也可以很文藝,可以很誠品
熱門文章
「人唯有知悉世界的殘酷荒廢,才會修補自己的家園。何青眼裡的是充斥迷霧的青木原,寫的卻是嶄新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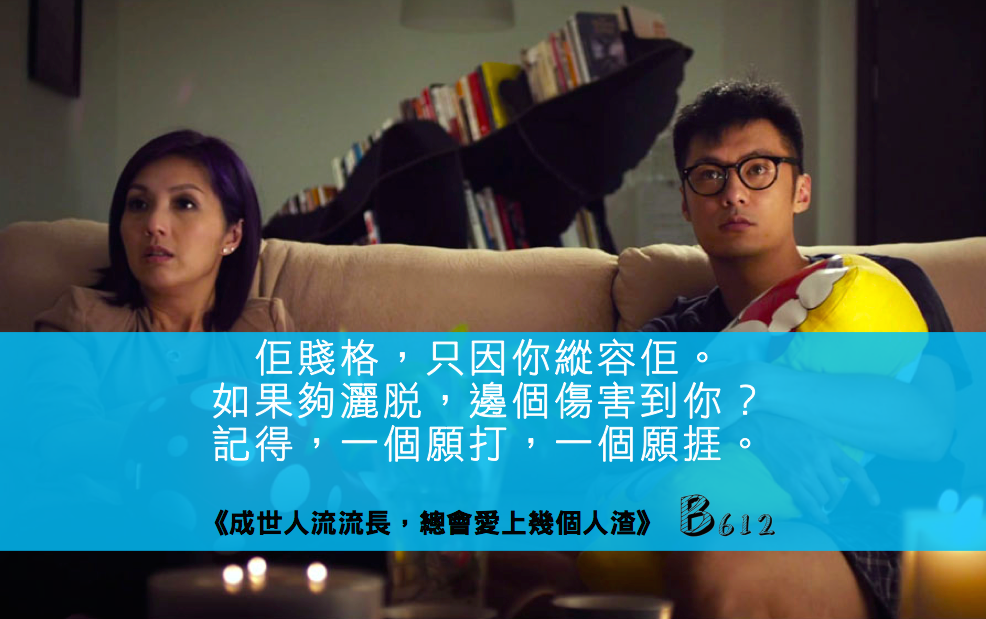
愛上人渣,似乎是物理定律一樣必然。不理你是陳女士還是張小姐,遇見人渣就跟中雀屎般普遍 —— 一生人總有幾次。 若然不幸遇上了,只好淡然說一句:嗯,來了嗎?
香港人生活節奏一向急速,連行路都唔會慢落嚟。但係正因為咁,我哋錯失咗好多生活中嘅美好。
紅塵之中,必有性情中人。 我很喜歡這一句說話。唯有將自身暴露在一片塵俗之地,才了解人間的現實虛偽,反思生命的真理,最終在情慾中大徹大悟,成為至情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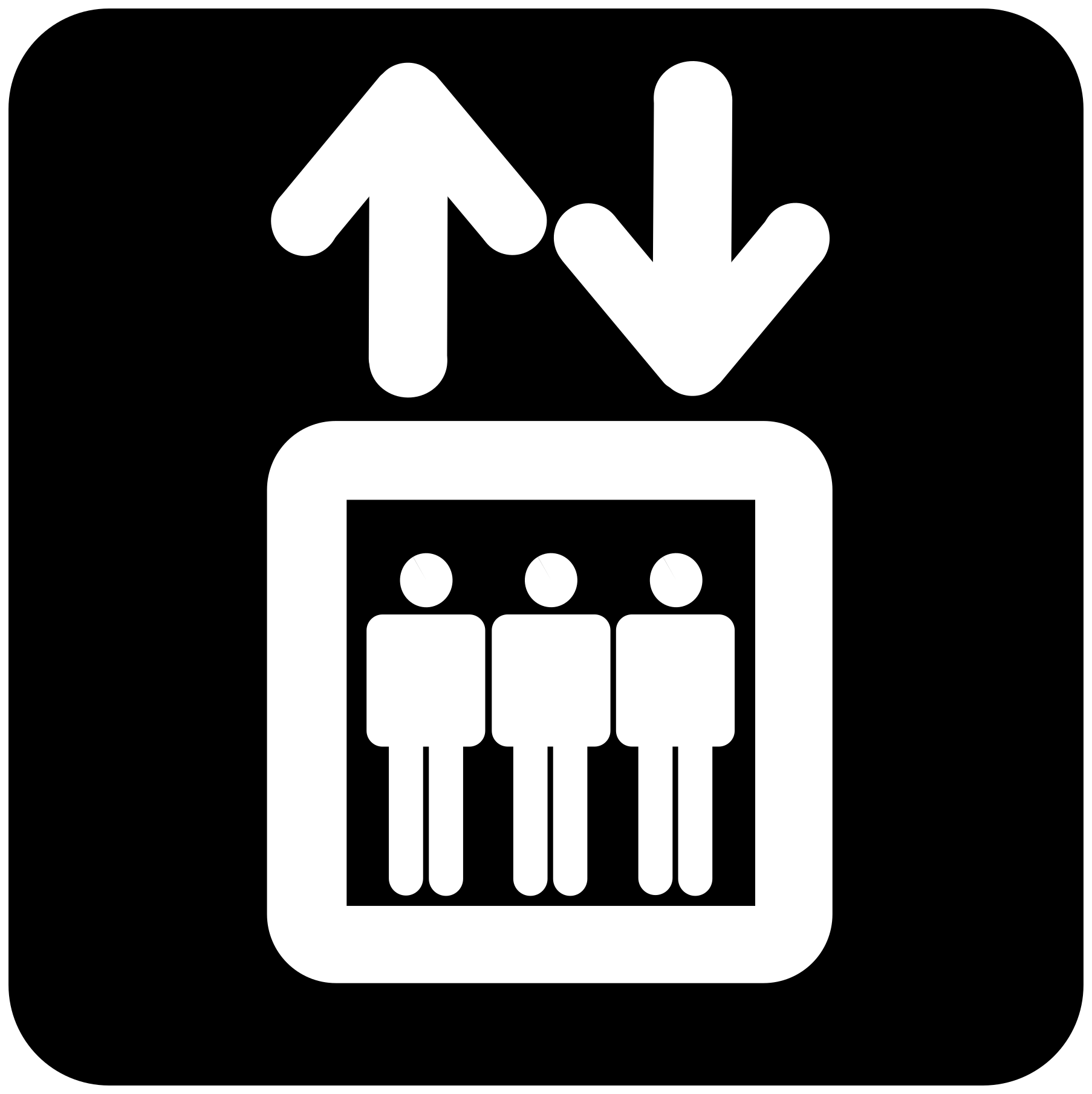
電梯中的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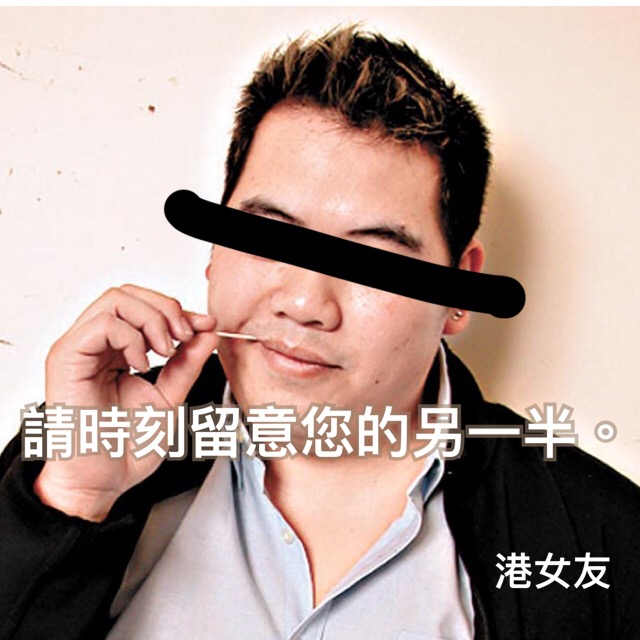
剛剛我見證到一場悲劇既誕生..
作者最新文章

我第一次看見她穿內衣的時候,是體育堂在更衣室換衣服時,我幾乎是看得目定口呆,我不知道原來一個女孩的身體會這樣好看的,害我立即自慚形穢,她是鮮花,我是泥。

在帶着鹹味的海風吹拂下,我們第一次接吻,就像『金枝玉葉』裡面的顧Sir與林子穎,我們旁若無人的吻了很久。

一晚我的肚痛得厲害,兩行血軌從下體一路流下來,我嚇得拍醒Steve,他送我到醫院後,醫生立即替我急救,但也救不了,BB沒有了!然後我整個人就像斷了線一樣,滿腦的齒輪像散了一樣!

她自殺的消息,是Steve在電話跟我說的,我英文不太好,只知道個大概是她這幾年有心理問題,因為之前曾經流產的事,一直有看心理醫生的,但早幾天當他回家時,發現她在浴缸割脈自殺。

他那隻張狂的手伸入我的上衣,鑽進我的胸圍內撫弄,乳房被他抓得很痛,我被他的舉動嚇怕了,想推開他............
相關文章
靈感來自喺東京食嘅一餐飯

金小麗與母親生活於80年代的東北農村,為了生活,母親苟且求存,待小麗成人,母女倆離開羞恥的故土南下求生,在做女裝生意創業過程中一次次的失敗,又靠出租肉身還債與偷生,然後再重生,創造出一個時代的輝煌,但在輪迴中又失去了一切⋯⋯。
故事發生在2023年的香港,一個繁華又充滿壓力的國際都市。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位於油尖旺區,真實反映香港警隊的運作——總區下設重案組,1A隊和1B隊負責調查嚴重罪案,高級督察通常領導小隊,處理兇殺、綁架等案件。這裡的辦公室充滿現代化設備,但氣氛緊張,案件堆積如山,同事間競爭激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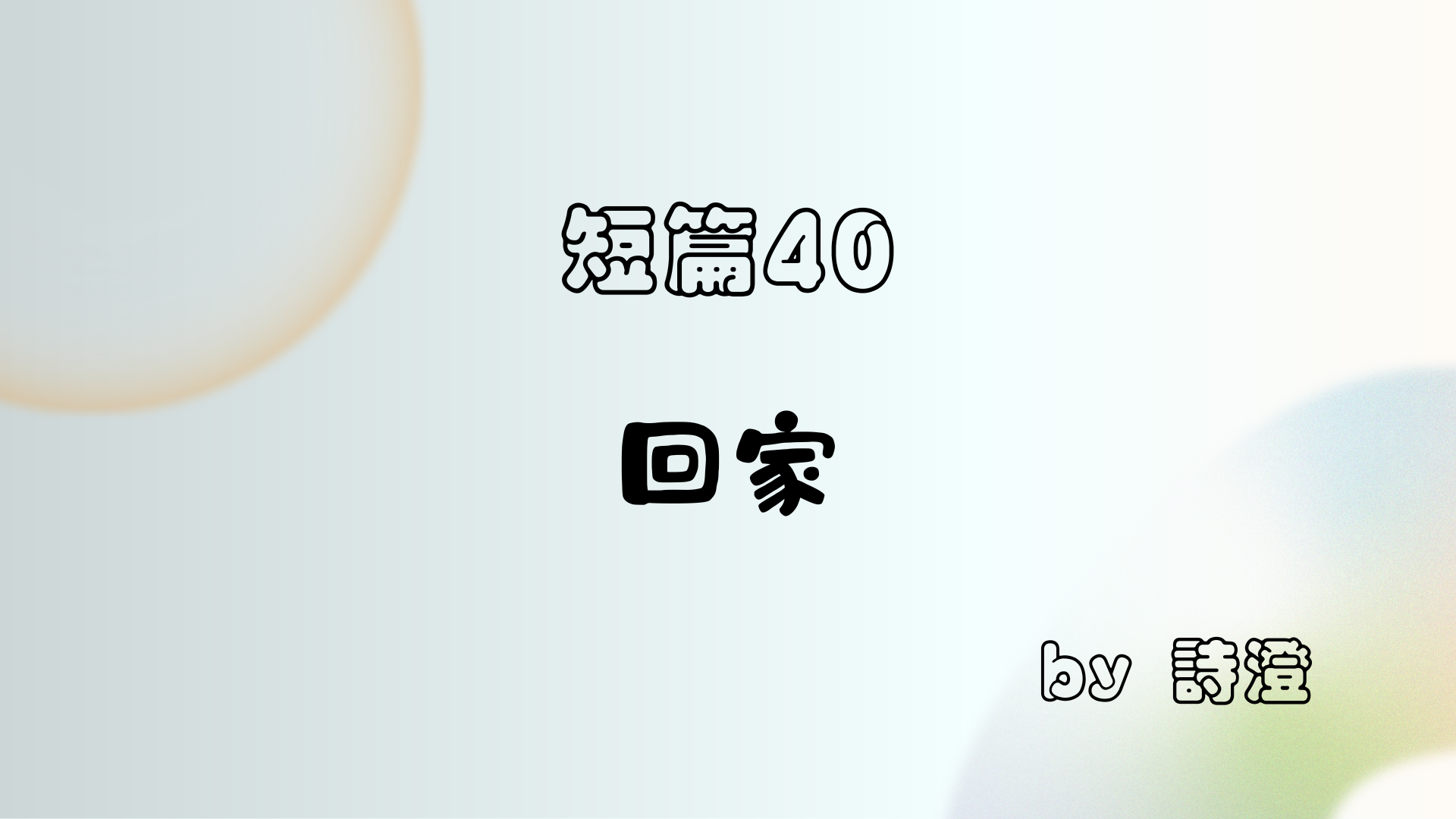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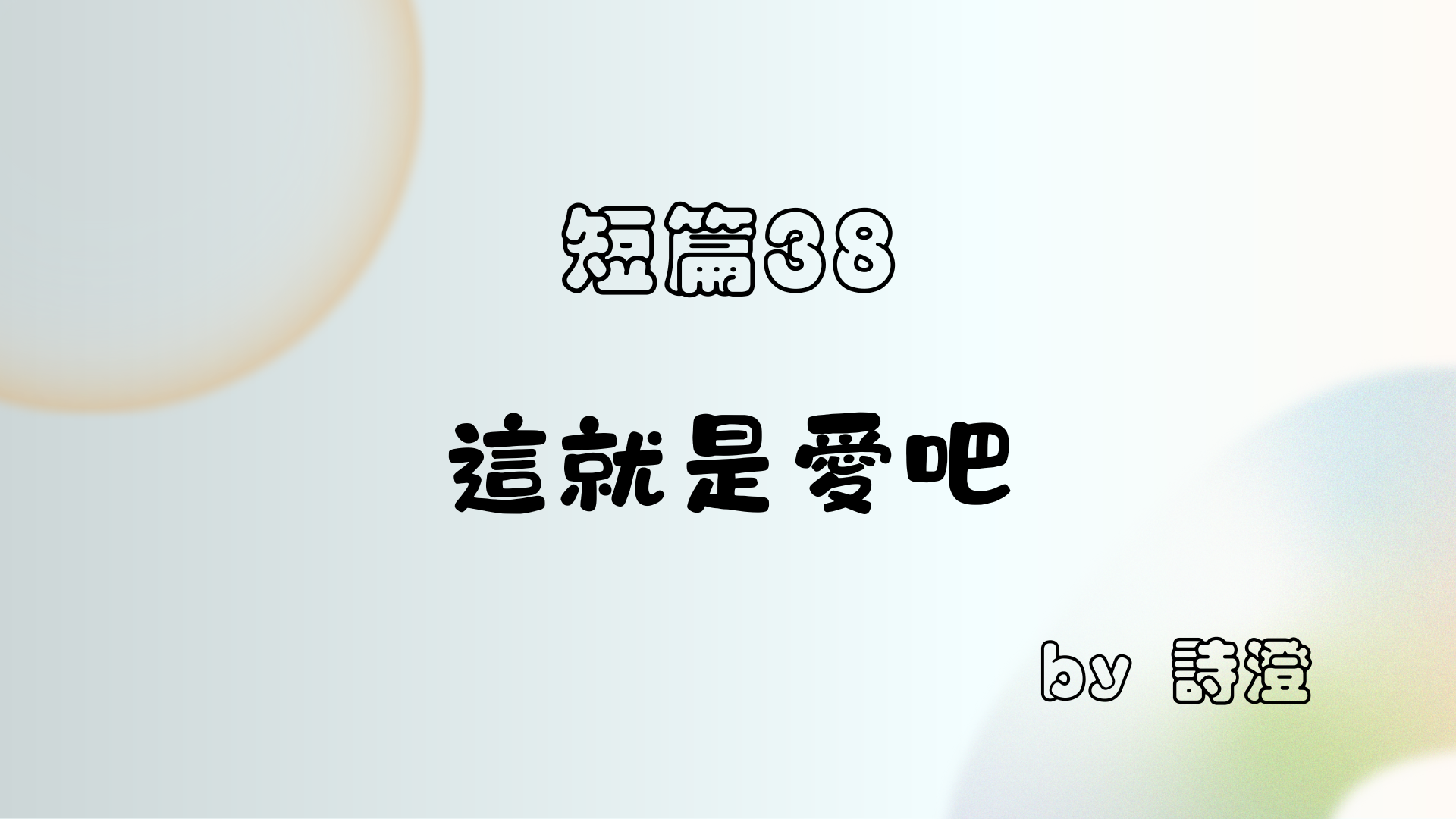
主題:微小說 字數:150字正

主題:小確幸 字數:10-3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