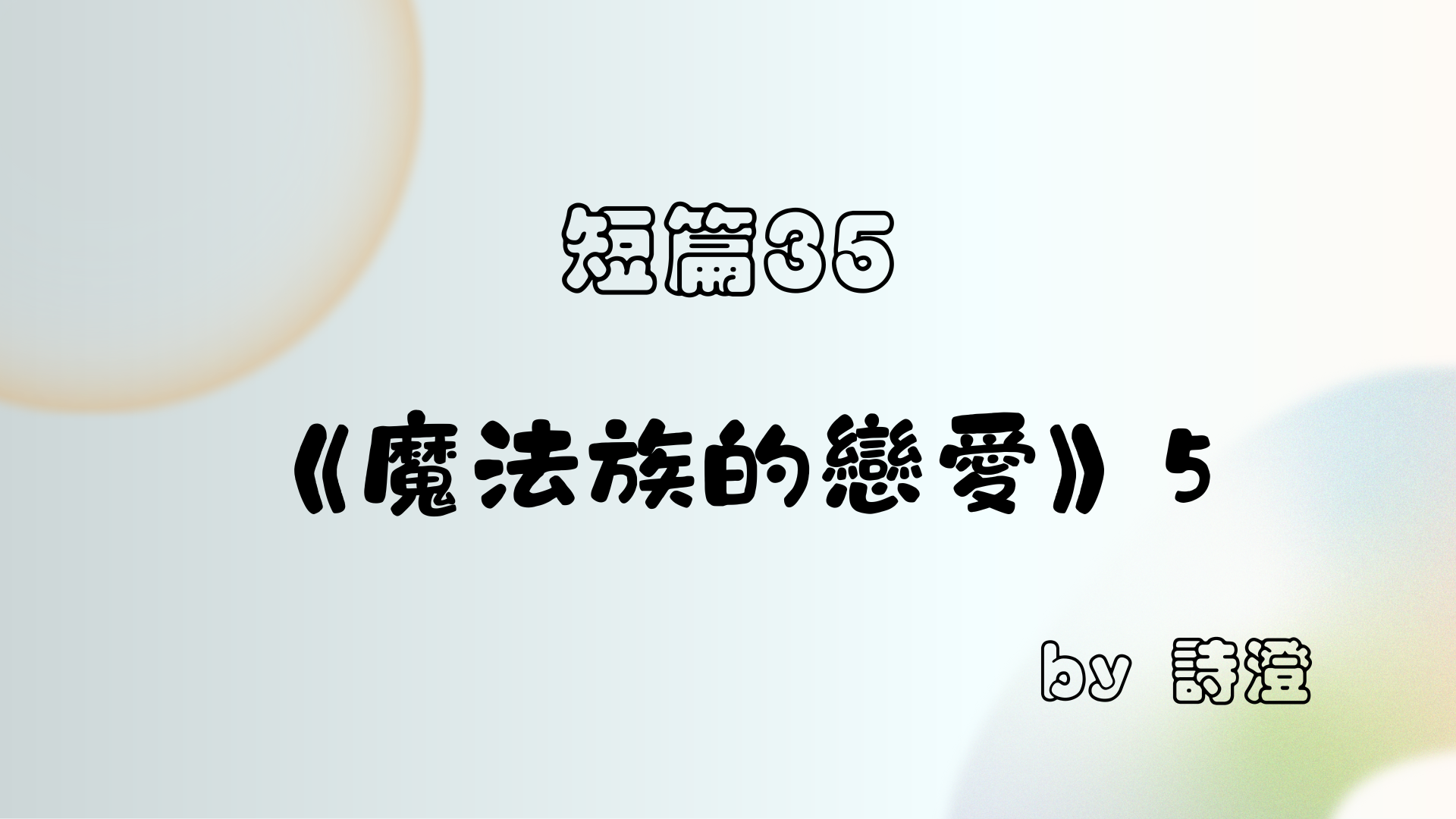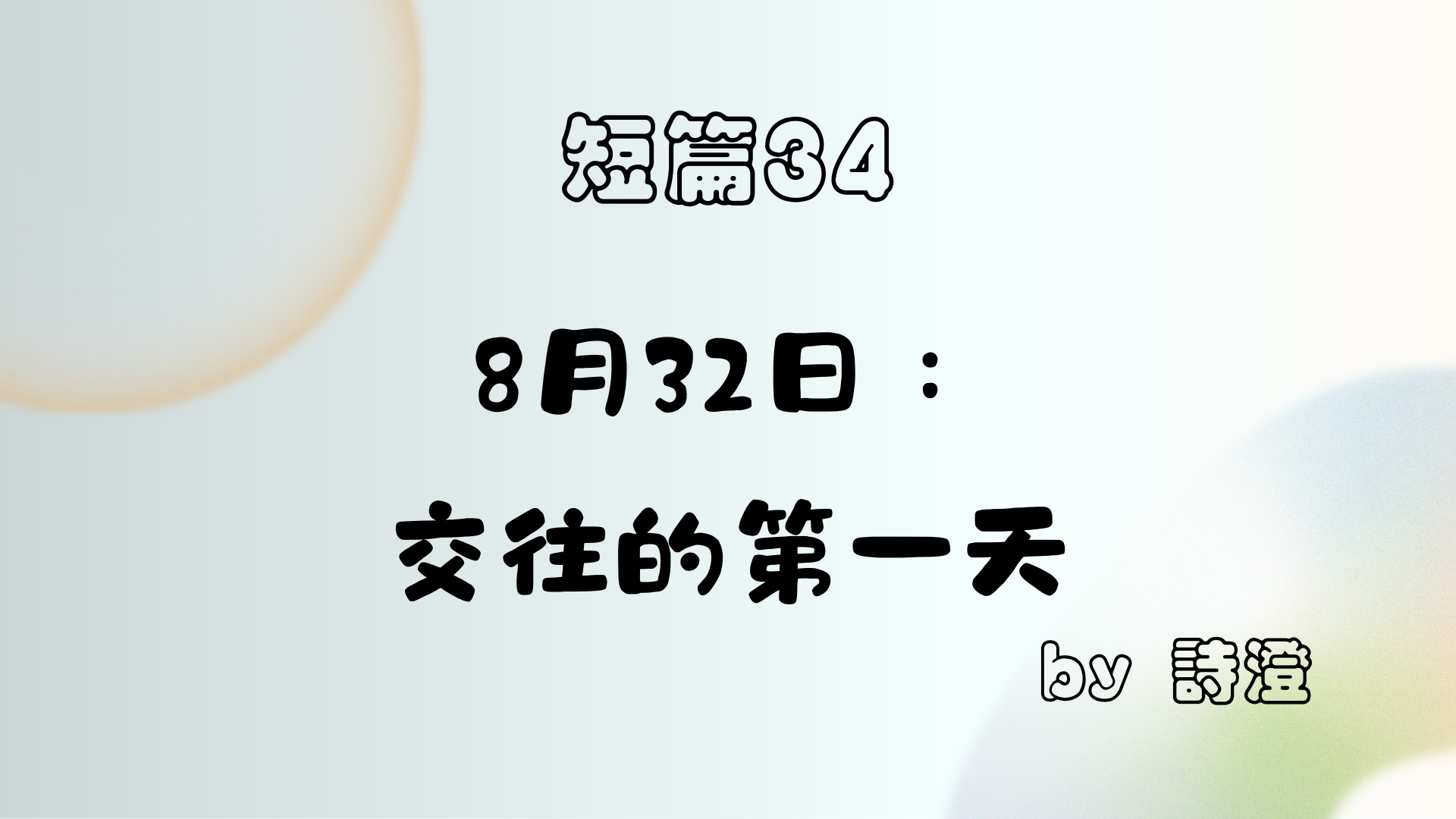我叫為常,家中排老么,當大哥出世時,父親想到以「平安歡樂」四字來替兒女取名字,到為樂這個四哥出世時,媽媽以為生了四個兒子都總算功德圓滿了,但那個年代不時興結紮,媽媽說是那一年跟父親返鄉下拜山有了我的,那時她已經四十六歲,大哥都已經結婚了,父親認為我是祖先要送給他的,待我剛滿一歲又特地帶我回鄉還神。
媽媽跟我說:「你阿爸話祖先有靈,可能仲有細路,喺鄉下間屋就話想要,我話我幾多歲啦!仲生?一腳就伸佢落床。」
我當時十五歲,笑到肚子痛。
其實父親或許沒錯,祖先保佑了他的生意,當年他在上海街與幾個朋友開一間的士車行,正值政府大力打擊白牌車,的士牌價開始水漲船高,父親看準時機大手買下很多的士牌,令他賺了人生第一桶金,我們一家由旺角道唐樓搬往太子道洋樓。人家說孻仔拉心肝,孻女拉五臟是沒錯的,父親可能覺得我腳頭好,對我萬般寵愛,我有父母疼之餘,還有四個哥哥給我呼喚,自少家裡沒有人給我難受,想要的東西不會得不到,生病了總有人給我餵藥餵粥。四哥大我七歲算跟我最接近,脾性也像我比較野喜歡玩,那年我四年班,同學中有個男生喜歡跟我過不去,有次他在我的書包上畫了隻烏龜,我回家對四哥說,四哥那時是個中學生,但頭髮長長的十足不良青年,隔天四哥便接我放學,我指出是誰畫我的書包,那個同學一見我四哥便嚇得要尿褲子,以後他一見我便逃到老遠,我成了學校的小霸王。
升上中學後,我根本沒心思放在書本上,終日與幾個女同學去東急、大丸、崇光等新商場買衫吃喝。有次在懷溜冰場認識了幾個男生,看樣子都是不讀書的材料,但打扮新潮,穿的都是新款時裝,其中一個樣子比較好看,我幾個朋友猛叫我問他名字,我偏不理睬他,對他冷冷淡淡。
就當我一個人在溜冰時,他走在我旁邊問:「喂,妳叫咩名?」
「關你咩事?」我張忍笑意。
「無……想妳對我講句嘢姐。」
「講乜嘢?」
「生日快樂,我今日生日,想第一個對我講嘅人係你。」
很快,我跟這個叫阿祖的男生拍拖,也沒有再上學,母親不喜歡我終日吃喝玩樂,她思想傳統,覺得我像飛女,好歹也要找份工作才像樣,於是要我在她一個朋友的時裝店上班,算是有個人可以看着我,但我可以看得住的嗎?做售貨員?我譚為常一條牛仔褲都貴過一日人工!這種工是我做的嗎?我上了半天便走了。母親說不過我便推出父親,我說只願意到的士行上班,因為在那裡我才是大小姐。
阿祖除了樣子好看,其實一無是處,沒錢就只懂問我要,但我沒所謂,因為錢都是父親的,我問他要他最多問幾句但不會拒絕。那時事道好,股票暢旺,的士牌價飛升,幾個哥哥在父親公司也賺了很多,個個住大屋坐Benz,除了四哥。
四哥自少心野,在中學識了黑社會之後就只懂玩和賭,父親替他還了幾次很大的賭債後,決心不理他。他後來還吸毒,有幾次我在家附近見到他瑟縮一角,他完全變了樣,不敢被父親與三個哥哥見到,他只敢問我要錢,有時幾百,有時幾千,我幫不了這麼多,有時也會裝作沒見到他便急急腳回家。直至很久之後,聽別人說他好像在澳門因為惹上一宗命案要坐監,我也從此沒見過他了。
有次和阿祖跟幾個朋友入長洲過夜,就這樣有了阿祖的BB,我問他怎樣辦,他支吾以對,只懂叫我找朋友想辦法。這個廢人,我當初是怎樣看上他的?肚子大了便瞞不了,我叫他跟我去註冊結婚,我約他在金鐘政府合署等,我等了三個小時都不見人,我走到他的家找他,開門的是他媽媽,她說阿祖不住這裡,叫我別找他,我說別騙我,等到死也要等到他出現。
他媽媽隔着鐵閘,冷言冷語:「好心做女仔就唔好咁賤啦!送上門都無人要就自量下,都唔知個醜字點寫嘅?」
我從沒試過這種委屈,眼淚哇啦哇啦直流,一路奔到樓下大街都沒停過,我發誓再見到這個賤男人一定要他好受。
有個叫阿堅的股票經紀跟我父親很熟,經常在車行出現,我知道他對我有意思,經常借故約我食飯。這個人油頭粉面,說話愛吹牛。我對他沒好感,但一個未婚大肚的女孩將來怎見人?那時候做股票賺到點快錢,我就當替BB找個便宜爸爸吧!跟他第一晚吃飯他便毛手毛腳,我說我家教嚴,不隨便跟男人出街,要是他真有意思便要跟我結婚。想不到他一口答應,父母見我肯安定下來也自然沒話說,婚禮很快便辦妥,七個月後兒子出世,叫信良。
信良出世後幾個月,世界變了樣。股市大瀉,市道很差,阿堅炒股蝕了一大筆,急需要錢周轉,叫我問父親借。幾個哥哥當然非常不滿,自然也有說話給我聽,他們覺得我既然已經結婚生仔,也不要經常打外家主意。我哭着求父親就當看在我倆母子份上,只幫這一次,父親從夾萬拿出兩個的士牌給我,說做父親的已經仁至義盡,以後各安天命。
阿堅變賣了兩個的士牌後,知道我沒有用處便原形畢露,說一早知道信良是個便宜仔,大家好來好去,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都給他取去,以後各不相欠。後來銀行追數追上門,我抱着信良躲在房內不敢出聲,那一刻我望向窗外就想跳下去算了,但信良一雙眼確實精靈,像他爸,我捨不得,一咬牙又活過來。
我別無辦法只好再求父親,大哥說車行生意很難做,父親也幫不了了我。
「香港地有手有腳唔死得嘅!仲有,阿媽喺醫院,可能唔得啦,可以見就見啦。」
我哭得一臉是淚抱着信良趕往醫院,母親是晚期胃癌,已經瘦剩一副骨,我後悔一路沒有好好看過她陪過她,母親最後的說話是問我信良呢?
「要養大佢呀!」母親一口氣回不過來便走了。
就是這句話,我要靠自己養大信良。
我記得有個親戚在花墟道有間花店,我硬着頭皮求他讓我打份工,起初他有點冷語,說我大小姐怎養我?我甚麼也不顧了,信良沒飯吃會死,我說就當看在母親份上吧!他說不過我就讓我在花店打工。
可能真有天生我材這回事!我記花種很在行,甚麼花來自那裡一學就會,特別是花束,女人心思我很在行,有些男人來買花追女仔,我教他們買甚麼就買甚麼,幾百幾百元的花束賣去很多,親戚看我賣力做事也沒有再單打我,一路做下來,親戚的花店成了花墟道做出名的一間,街坊都知道花墟有個叫阿常的阿姐。
阿偉也是做花的,但公司在舊金山,生意做很大,批發到全舊金山的超級市場。那年他本打算回來香港探親,其中一個是我的熟客,就帶他來介紹給我認識。
本來就是一場相識吧!但阿偉回美國一個月後竟然回來找我,他直接問我有交往的男人嗎?
「咩話?」我第一次聽人如此直接。
「我……我想帶妳到……美國行下……」這個人一時又那麼婉轉。
就這樣,我與信良跟阿偉去了美國,結婚後他找了間很好的學校給信良,而我則替他打理公司的業務。
這天,我坐在信良學校外的公園草地上等他下課,我望着面前幾個小學生一路走來,互相嬉鬧打交,想起很多年前,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學校小女霸王,她書包上有隻醜陋的烏龜。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