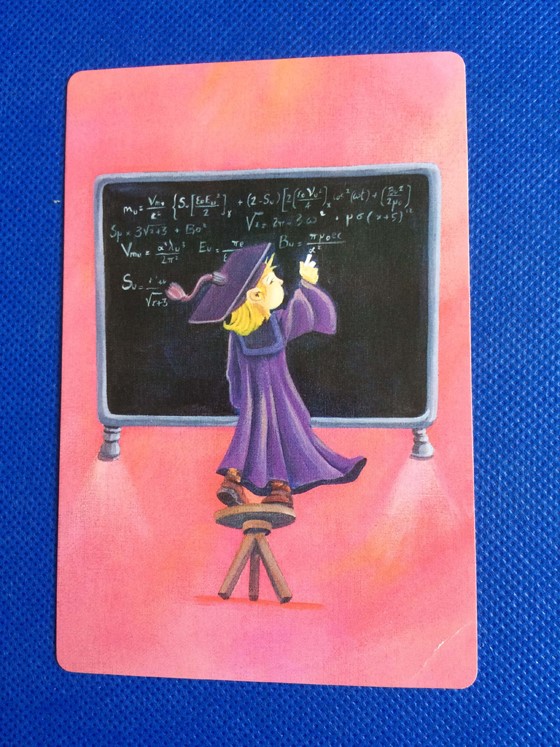我是一個的士司機,一個好色的男人。從小我就把婚姻視為負擔,成年後更把長期關系都納入伴脚石之列
填這個坑洞的方式,就是縱慾。找不同的女人,爬上不同的床;或者找不同的女人,爬上我的床。這種太多味道的生活在我24歲時終結了,我失去了味覺。成了無味的人,過無味的生活,靠幸福和美滿的劇本活下去。
味道没了,味蕾自然也無需要。他們都離開我了,連舌頭都委縮了,像杯麵片的脫水蔬菜。我没有看醫生,因為他們是治不好我的。
她死了,我的導師,我的啟蒙之母。没有她,我根本不懂何謂做愛。我不明白為何自己當初會和這個比自己年長十多年的女人斯混在一起,但她的香夭肯定是我失去味覺的主因。她死後我還在吃喝,但已經失了味,從打個八折到半價,到後來半點也没有了。再也没有味道了
我從没想過會如此重獲味覺,有一個修女上了我的車,拿了我的電話號碼,時常搭我的車。慢慢地,我不但想她上我的車,我還要她上我的床。終於,我們解下了安全帶,任由四輪跳舞。
她的衣服由我保管,上車是個西洋尼姑,下車是個花季少女。雖然我的尾箱成了她的衣櫃,但她可並非我的一切呢。我還有善變又可愛的Mary, 溫柔貼服的Sendy, 冰雪聰明的Lucy ...
我們除了在房間偷歡,就是到餐廳吃喝。我討厭大排檔,我討厭茶餐廳,我討厭酒樓。我生錯了階級,我喜歡貴夾唔飽的高檔餐廳,我喜歡烏燈黑火地進食。在桌下雙腿四脚盡情地犯罪。
「 這是一種有味道的生活,有鹽的日子。你若離開了修會,我倆間只有咸味。無法渡日」
「我當然知道,你以為我還是小女孩?我28歲了」
「哈哈,我只有25歲喔,姐姐」
「 這不是那些犯濫的言情小說,你以為我會想和你做人世?你以為自此以後我就會哭哭啼啼和你不相往來,覺得被你佔了便宜?不會囉。」
我們都笑了,細聲講大聲笑,笑得拍桌子,笑得整間餐廳狠瞪着我們
這是本小說,一本庸俗的小說。至此,劇情急轉直下。我原以為這個故事可以淡淡然,畢竟我雖然回復味覺,但已經大不如前。但原來不是,如果說那個老女人是我性愛啟蒙之母,這個修女就是我的基督。靠近她就靠近了烈火,遠離她就遠離了有味道的生活。
在這爛鬼劇本中,她始終離開了我。她去了羅馬留學,要去四年。我居然掛念她,我居然掛念她的味道,我居然掛念她念經的聲音,我居然掛念她享受時的呻吟。我居然掛念和她一起經過的每個音樂會
她離開後,我本以為根本没什麼大不了,直到感覺慢慢浮面,慢慢,慢慢,我花了很多時間,才能講一句:我掛念她。
妳是誰,妳有四本福音書,記錄關於妳一生的故事。
「瞓啦柒頭」
這本福音書把描述成mk妹,粗鄙好玩,穿着熱褲在坐在花槽,邊抽煙邊狠吞熱狗。還有啤酒和一群mk仔。每月都更换紋身紙。
「你要清醒點,別給喵星人迷惑!」
後來,在別的福音書中卻把妳寫成充滿文藝氣質的女子。妳的左眼滿有貓的魅惑,右眼則滿懷未知的慈愛。
「我說,你我所以偷歡,一定是在前世,在浩瀚太陽前,有個靈魂刻意把自己分成兩半,讓自己在下界不至於孤獨,還能順道玩尋尋覓覓的遊戲」
但唯有這本福音書才寫下了最真實的妳,藏有妳最直白深沉的思想。有妳的自白,妳是一個深藍色的女子
「我所以做受洗,完全出於貪玩。我所以做修女,完全出於教會缺人,待遇又好。」
偏偏這才是最寫實的福音書。說妳不過是個普通的香港女子,帶着香港人的座右銘去打份工。
妳到底是什麼人,妳到底是誰;四福音書中的妳,是我的演繹還是真實的妳?我要去羅馬,我要去找妳。我與妳原為一。
飲食男女,人之大存?不,還有洗澡。人到此去,這是要洗澡的。人可以不食,可以不婚,可以居無定所,可以無所作為;但切忌不洗澡。
我從來没到過歐洲,但到埗首件事,就是洗澡。在浴室一切都歸於虛無,時空於此處重疊。天堂和地獄都在這裏展現,在浴室中的時光都是無聊時光 ... 呀 ... 我就是無法去表達哪種感覺。那麼不絕重複的似曾相識,對未來的幻想不絕地逐個破滅。但唯有浴室的風光於腦海中流傳。實在我能寫到這裏已經很了不起,因為我那壞父母總是在打壓我的表達,毫無用處的家教,還不如留下千斤家產實際。
她給我念過四本福音書,整整四本,我喜歡她的聲音,她讀字時所噴出的口氣。都是我那瀆神的父親所無法享受的。那個糟老豆於我腦中留下多少褻瀆,妳都報以無量神聖。
「為什麼路加,瑪竇,瑪爾谷的背景那麼朦朧,他們到底是誰」
「他們都是講故事的人。可是你這聽故事的人又是誰?快講出來,免得過多兩千年,又有偷歡的男人問我:為什麼那偷歡的男人背景那麼朦朧?他到底是誰?」
我是誰,為什麼我不像旁人一樣有段正常的婚姻關系?為什麼我要跟十日談斯混?我又該從何說起?
家庭,超級英雄片都從他們的家庭講起,反英雄片則由他們轉化講起。那麼一個凡人的故事該由何講起?這個充滿壓抑的故事又該從何講起?
就由他的壓抑講起。終日把揾食放在咀邊的父親,易怒的父親,無為的父親,幼稚的父親。還有終日瘋瘋癲癲的母親,終日口齒不清的的母親,終日言之無物但又不絕發言的母親。
家庭和婚姻,就是這個墮落的團體和他們扭曲的關系把此人給毀了。
我並無如電影般衝進修院與之擁吻。生活不是電影,電影如夢,都是願望的達成。
我用另一種方式去解決這個願望: 掀起她的蓋頭來, 架好望遠鏡,仔細觀察她的每一天。
我要了解她。她的喜好,她的興趣,她的日常習慣:她會於幾點鐘起床,用多少牙膏,會否摺被,梳洗後做什麼樣的早操,或者根本没有做早操。她喜歡吃什麼早餐,她一個修女的工作是如何的?她通常幾點吃中午飯?她晚上又會作什麼活動,習慣幾點晚飯,又會於幾點洗澡,又於何時進睡。她的生活如何,她就是如何。食物構成了她,而生活譜寫了她。
我無法置信鮮活的她過如斯樣的僧侶生活,原來她面對我是此鮮活,皆因日常是那麼壓抑。我終於明白她時時掛在口邊的非人化是什麼意思:就是像她那麼鮮活的一個女子,給裝進了一式一樣的制服,在一樣的時間起床,進食同樣的早餐。在每餐之間作相同的宗教儀式,於相同時間洗澡,於相同時間進睡。没有內容,没有texture的生活。
仔細思索就如每個香港人的生活一樣:充斥規範,没有味道,謹謹足以維生。而且那個社會的去人化歪風這愈發猖狂,都市流行一句話:此地無人睡得足夠。與之不同是常人生活為了自己,而他們則時刻為了神聖。
我把她領出來了,別問如何,總之我把她領出來了。看着這個她如同看一個出身保守家庭的兒童:壓抑,沉鬱。好似兒時的我。
我記得在香港時,妳曾經和我碎碎念過妳的信仰。妳說那信仰的核心:就是天主與人類同在,與我同行。我問妳,那麼心中有神就行,何故要信基督?妳不說話,但妳觀望苦像,好像那人與妳共情同苦。我不認識他,但他的弟子把改造到像個機械娃娃
但我要問妳,要是妳真的信有主宰,妳又確實於祂旨意下出生,為何祂把妳生之為人而非其他物種?我的答案就是祂要妳感受一下生之為人的感覺。飲食男女,人之大存,把之視為污穢,壓抑之,非有違天意嗎?
我把她領到海邊去了,我要和她一起回復人性
「A for apple」
「B for boy」
「C for cat」
「D for dog」
「E for et」
由歡笑到憤怒,一切情感都要從頭感受。更重要的是鼓勵她去盡情感受。好像我倆都有機會重新做人,重拾那些被現實重壓的情感,那些好東西。【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