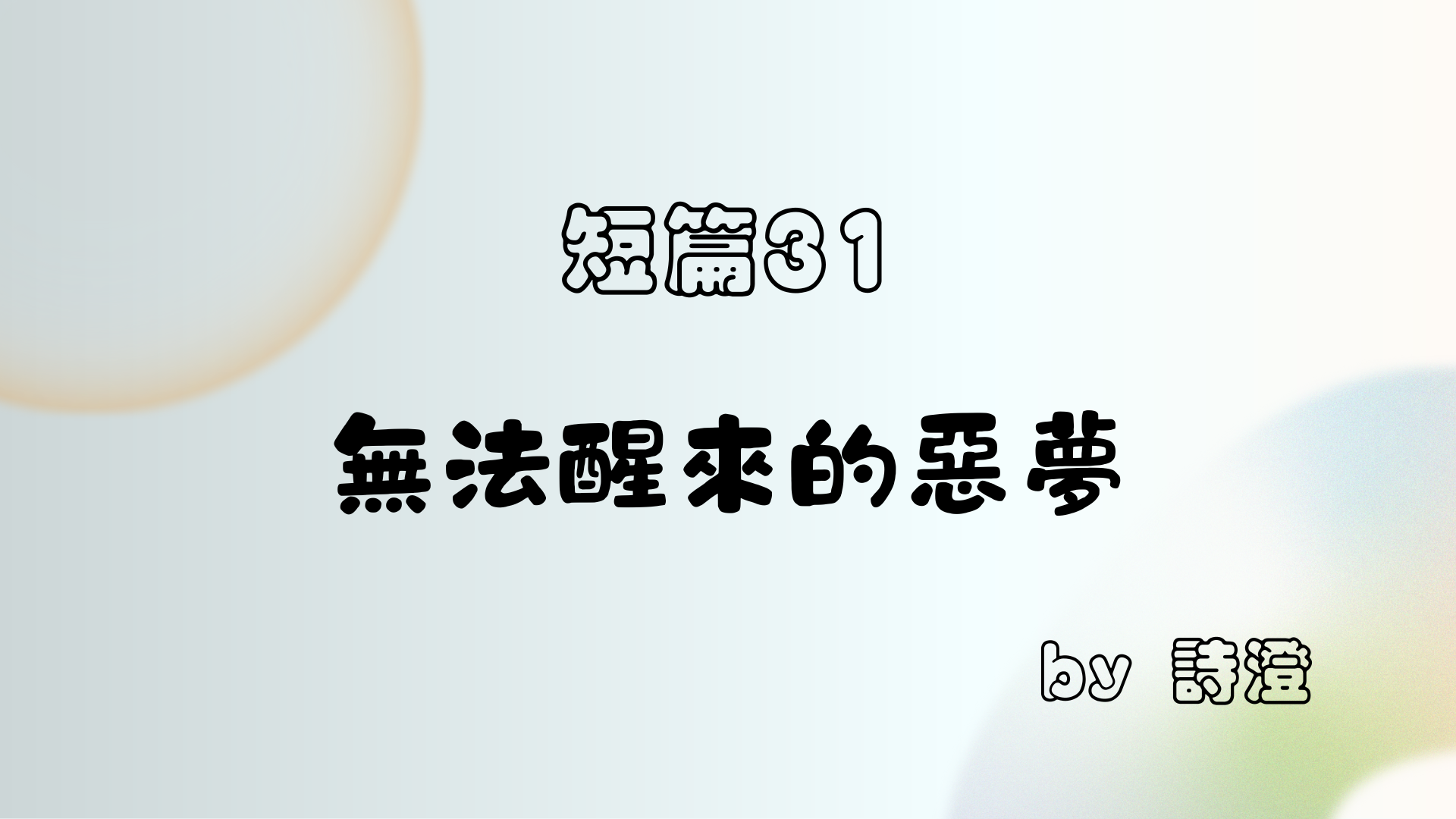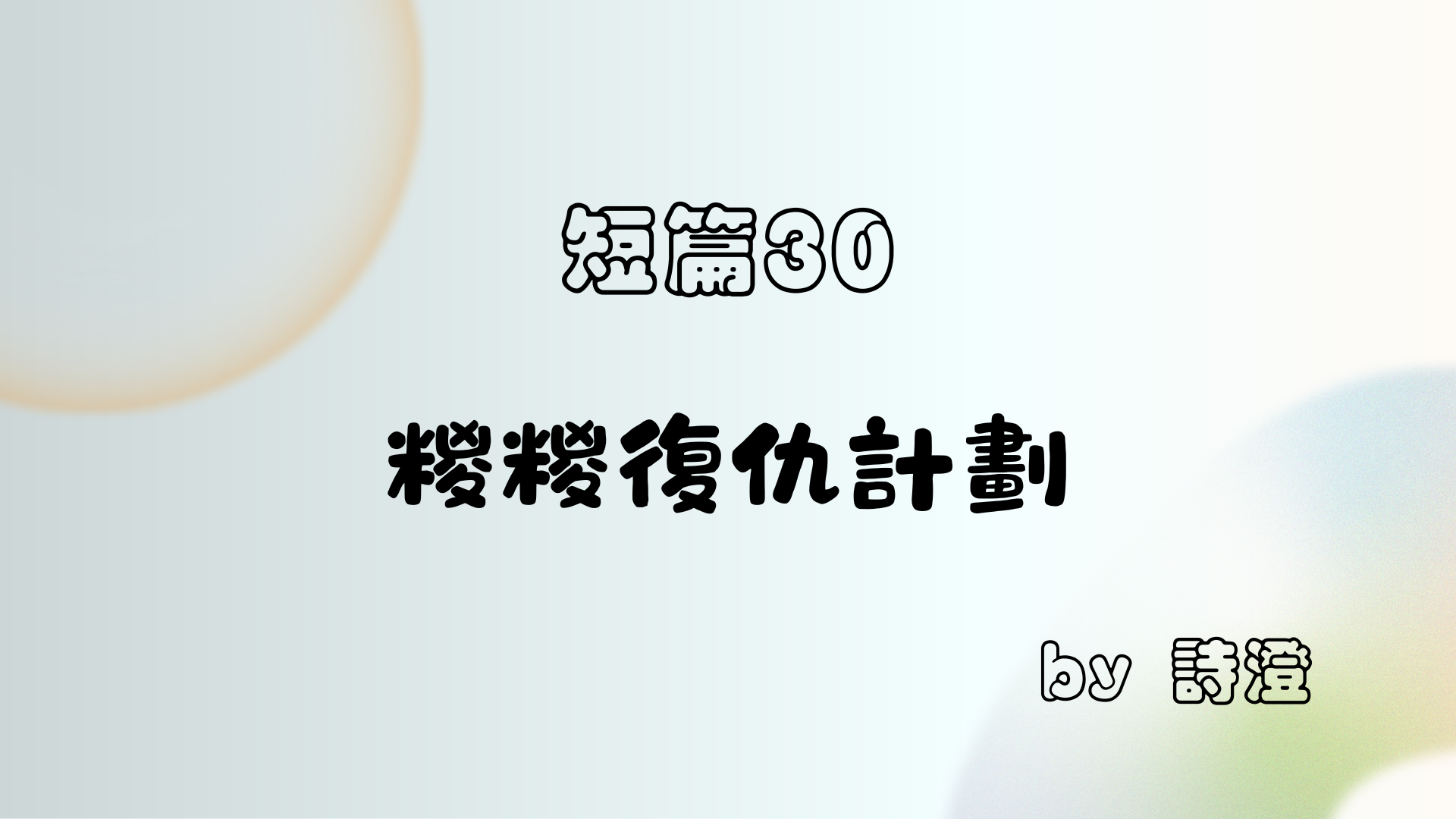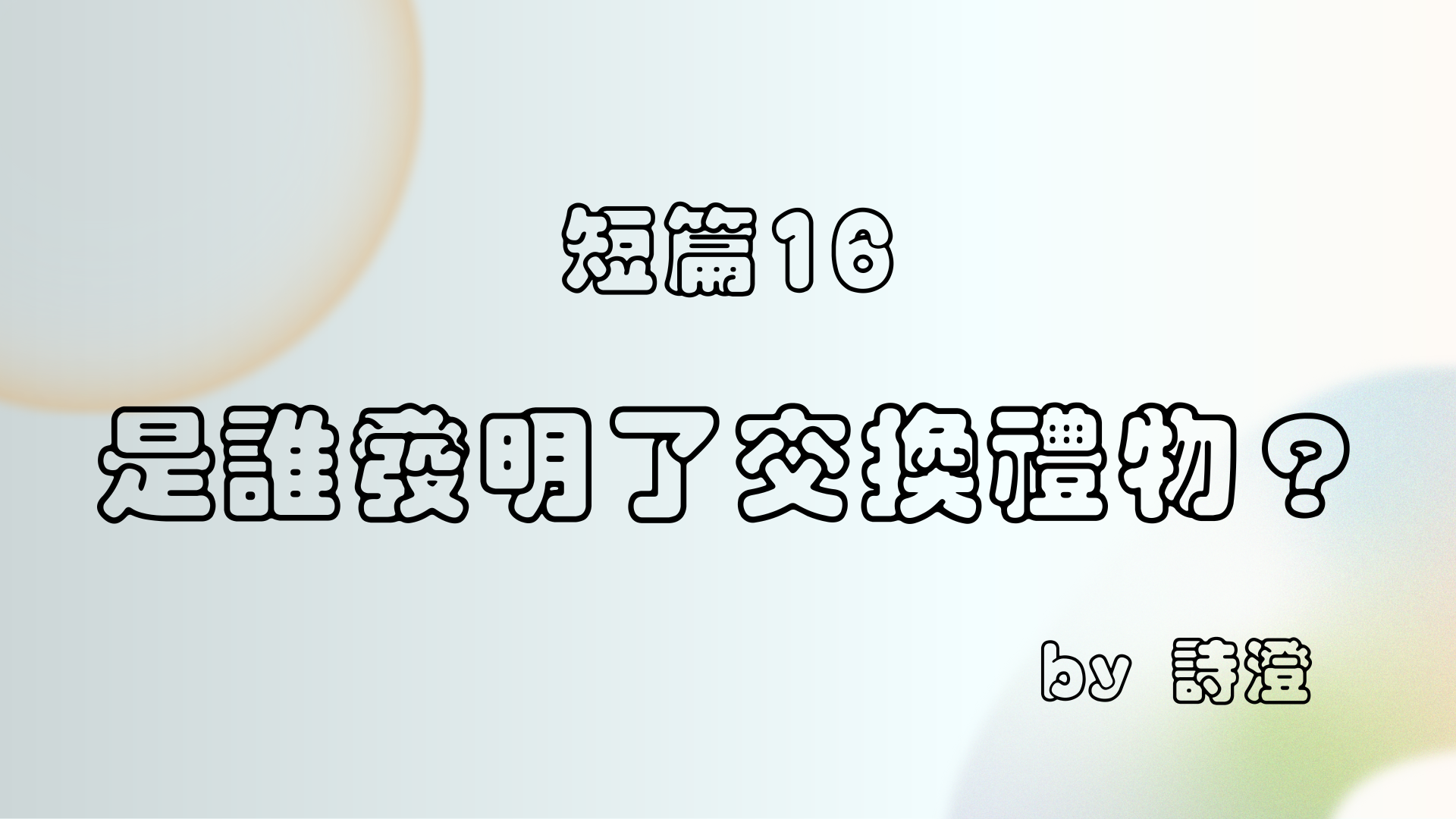在開始講故事前,有些事必需澄清:作為常人口中之吸血鬼。千年以來有許多關於我們的傳說,但這些鬼話都純屬虛構。
首先是「我們」,其實由始至終只有一個;我非但沒有同類,也無法藉由傳說中的種種方法把人類轉化為同伴。
第二,我接受的稱號就只有「夜行者」;至於「吸血鬼」和「吸血殭屍」之類稱呼均屬物種歧視!對此我沒有進一步回應。
第三:我不會見光死,也不怕十字架和蒜頭;更不會於故土中補充元氣。至於變成蝙蝠於夜間飛翔尋找可吞食之人;老實講,我渴求擁有此能力。
最初以我為藍本發揮想像力的應該是天主教士。他們把其信仰中的至苦境界盡書於我身上:惡人面對天主聖容的無限痛苦﹑無法與人建立和諧圓融的關系﹑依靠他人血汗維生,還有孤寂和放逐等無聊教理,
通通於我身上具體表現出來:見光死﹑怕十字架﹑飲血﹑渴求同伴 … ...
雖然教士們鬼話連編,把我這個大好姑娘寫成一頭妖獸(畢竟我是非常注重形像的) ,但有件事並沒有講錯:從前,在許久許久以前,我確曾飲血維生。但現在我脱離了那階段,我已能像常人般進食﹑像常人般在日光下盡情遊戲。我還能享受獨處的自在,於此我自覺超越了許多常人。
這寧靜給打破了,許久沒有感受過的渴和困乏又再湧現;我知道,他要回來了。那個鬼鬼崇崇的傢伙﹑那個原是奉命要捕獵我的傢伙﹑那個與我相愛相憎但最終難逃一死的傢伙。
原來這渴不是我的渴,這困乏不是我的困乏;乾涸出於他的舌頭﹑困乏來自他久睡剛起的肉身。我要去找他,我倆間有個結。
在我心底時時壓着一件憾事;我知道你也一樣。就是我倆始終未能在一起,始終未能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在漫山遍野月橘盛放的季節,你沿着我的足跡步入山谷。花香隱約蓋過你身上的酒氣,但我還是能隨風細味你的暴戾,你怠倦的思緒。我知道,你不會殺我的。
於是我倆間展開了迷離的捉迷藏:你跟隨﹑我停步;我轉身,你暴露。
我帶着勝利者的風姿邀請你到咖啡廳;直到今天,我這記得那兒的模樣。後來你也給我建了一座,說這是領我步進人類世界的前廊。
你說:我受委托要捉拿你,但我累了。叫我不如收手,好教我倆可以成全。作為勝利者,我冷冷地拒絕:藝術是不能止息的。但你可以作為我的俘虜,伴着我活下去。
於是,你看着我殺人﹑看着我抽乾他們的骨髓﹑看着我把他們的臉皮剥下再套於精緻的頭雕上。我把他們的臉皮割破,好教當中藏着的寶石能祼露出來;在血腥和暴力中藏有無限祥和。我深信這魅惑能使你完全臣服於我;所以每天我都會邀請你步進我裏頭。我相信你在其中待久了就會懂得去欣賞它,就能跨越那相隔我倆的深淵。
可是你死死釘在對岸,堅定地散發一道命令﹑一股誘惑;不絕地挑逗我往你前行。我失陷了,像許多勝利者被殖民地所張開的柔軟唇舌所吞沒;連骨頭也給吃個乾淨。我戰敗了,在你的魅惑之下給吞沒;連半點也留不下。
於是我倆間展開了互相撕磨的脱癮療程:我看着你一天比一天教人憎惡;你看着我終日歇斯底里,一天比一天難受。我們間不再擁有當初的美好。
然後有一天,你死了,我忘了你是如何死去的﹑也忘了你的形相﹑你的外貌,但我始終記得你的味道。你的血一次足以贖永遠。
我把你妥善安葬,待肉身的復活,我們就能天天在一起了。
我想念你。我知道你蟄伏於我内。
在晚間貪婪地呼吸月橘的香氣﹑為了你克制吸血慾望的掙扎﹑在你懷中嗅着比我更為親近你的酒氣;沒有你共行,我根本不會走近的菜市場。你革新了我的體驗,帶給我雖歷漫長時光,但許許多多沒有做過的事:在夜間遊巴士河﹑隨處和路人搭訕﹑混入節慶的遊行偽裝成人類,去體驗他們那莫名其妙但擠在一起就很快樂的感覺。
有一天,你把我牢牢夾在懷中﹑邀請我進入人類的時間表:開半吋窗簾,讓日光照射進衣櫃,我們就靜靜地欣賞這些從未如此清晰的細緻:布料上的縱橫交錯﹑一朵朵浮在格網上的暗花﹑別忘了申手去感受它們被日光烤得和暖的質感 … …
你走了,我的血癮也忽然斷了,斷得撤底;就連同對日光的驚恐也消失了。原來血是那麼腥臭,日光是何其令人享受。我終於能像你一樣,每到下午坐在落地玻璃前欣賞我們一同拼湊的風光,你我一起挖的池塘;細察於其中棲息的錦鯉,聽着蛙鳴。還有我們一起搭建的竹製水車。
這株月橘,這株月橘是在十五夜我們一起去林間深處把她移植到這小天地的;你我一起埋首於她的秀髮,暢吸她的香氣;一同迷醉於其中,縱然你我是兩個物種,卻因她的香氣而走近:她的味道,她的盛放,蓋過了你的酒氣,蓋過了我的血腥體味。因着她的香氣,教你我暫且忘記那深淵。
可惜我還是無法像你一樣欣賞這個樂園,無法像你一樣投身其中:日光和園境就似我和你;沒有日光,再別緻的園林也無從欣賞。沒了你,我就陷入了荒園;但要是你親臨,要是你日夜和我在一起,我就失卻了自己。現在我才能看清:原來你是多麼努力把我領進這美好的世界,引我走進你的世界。諷刺在於,唯有你的離去,你的死,你不屑地離座才能教我自在地享受這片光景,去回味我倆間的時光。
你走了,回憶於我腦海中千迴百轉。何其弄化的一場戲:你伴在身旁,我就置身地獄,片刻不欲留;可是,當你離去了,當你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建更多花園﹑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去挖月橘﹑再也不能一起混進人群中呼吸;此時,那些日夜相伴的日子,那些在一起互相撕磨的時光卻教人回味無窮。
夜深了,又是一個刺激的時分;味道在五内紛陳。每晚都是無眠夜,就讓思緒在腦海中衝浪;在未曾有你的日子,性慾和食慾常於寂夜交纏互咬,要是在月色下漫遊碰上可口的姑娘;我們不需要言語,雙唇就會自顧自地碰撞去尋求愉悅質感,這質感就像你和我的每一夜。
滿月在牽引體液:血液湧上頭腦,湧向你。汽車翻起浪聲﹑沙井傳出蛙嗚﹑蟬叫,還有空洞的滋聲;所有聲音都在向我訴說你。
一切感官為你而展開,喉間的乾涸,髗內莫名的興奮,空氣中最細碎的甜味和充血的眼目;派生而出慾望和濕潤。一切都在吹促我與你連成一體,一切都在推我跨越那個深淵。 深淵在於,你對我的維生之道有無理的憎惡;你明明知道我吸血是必須的。但你就是不喜歡,你就是不悅於此、你就是憎惡;不過如同撲火的飛蛾,寧可擺脫自己也只為與你在一起,單單的在一起、每天在一起。
你愈發臨近,你的形象,你的神髓,和你一起的回憶就愈發鮮活。
如果和你永遠分隔是至苦,看來和你朝夕共對也未必是極樂。你我間痛苦扭曲的關系活脱脱應現了那些教士們對我咀咒:既於天主聖容下無限痛苦,又無法與人建立圓融和平的關系。
你蟄伏於我內蠢蠢作動
教我又想起那些教士的荒謬信理,縱然他們的權勢已過去了很久很久;久遠得連同我對他們的憎恨和捕獵﹑他們對我的恐懼和浪漫幻想,兩者要不成為歷史檔案,要不就被視為迷信笑話;充其量提供電影和文化創作題材。可是那些教士的一言一語,他們的信理和儀式﹑他們公式化的藝術和思維卻深深烙於我腦海;他們是構成我的重要部份,他們的形像當在我思緒中閃現。
他們說,他們的基督是天主的羔羊;他來到世間就是為了讓人類歸向天主。以他的名作洗禮非但能抹去人類得罪過,這能洗去原罪。
一派胡言!我不吃他們那一套!原罪是種傾向,是他們人類背離那位天主的傾向:人要吃喝,人要交合,人就是要居於肉體之內且尋求滿足它的快慰;我的食糧是人血,我的歡樂緊扣血腥,我生來就是獵食者且居於晚間。我與你背道而馳。
你是誰,在守候你的期間;我不絕重復描繪你的形相﹑你的性格﹑尋找明明該永遠隔絕的我倆,何故曾經在一起﹑勉強且撕磨地在一起。
曾經你是無比微小的,不動聲色不絕愛撫我。我的唇,你曾挑逗過﹑我的牙齒﹑我的舌頭﹑我身上每一方吋都有你的痕跡。滋養我的每一個細胞,在不經意的滲透給我許多快慰。
後來你愈來愈宏大,愈發澎漲;你的思緒在我體內每個細胞都孽生腫瘤,你渴望佔有我,渴望支配我每個舉動,渴望我倆合而為一:在我每個念頭你都烙上印記,不絕給我重寫你的狂亂宣言: 你與我原為一體
你是個控制狂,在一次又一次重温記憶;一次又一次否認這個現實,達到上百遍後,我屈服了,現實就是:你是個控制狂,你承受不了計劃外的詩意;在無數次罔圖把我重構的工程紛告圖勞後,你爆發了,你發了瘋,毀了我們一起製作的花瓶﹑毁了我們一起拼湊的彩色玻璃窗﹑毁了合照﹑毀了廚房﹑毀了月橘。
你還毁了咖啡廳:你建造給我用以進入人類世界的前廊。你毀了我們一起營造的小世界,你推倒了所有美好;就是為了宣泄現實不如人意的憤怒,宣泄我無法成為你心中理想配偶的失落。
我還記得於此渡過的每一夜﹑那個我很欣賞,覺得聘對了人的小姑娘。那些高談革命與文化的稚氣青年﹑覺得於咖啡廳泡上好幾個下午就能顯得自己有品味的中年人;終日呻窮但有閒錢來坐上一整天﹑摟着畫板但什麼都畫不出來的插畫家﹑更不消說那位百發百中的保險之王 … … 我從他們氣息間所沾染的人性遠超於上千年來所吸的血:我精心挑選的獵物居然比不上隨意上門的座上客。
每天在廚房準備小甜餅﹑芝士蛋糕﹑牛角包﹑西蘭花批;重復不絕的猜面粉,打蛋,開糖漿。你在身旁偏執地調控咖啡烘培的温度和時間,嚷嚷着什麼水粉比﹑萃取﹑衝煮等等我聽不懂卻又好像很科學專業術語。每每我看見滿頭大汗的你在歡呼又或罵娘,你總是不耐性的給我一句:咖啡這東西,你是講不明白的!
但這一切美好都敵不過你的畸形癖好:這一切都只是為了改造我的工程而草草搭建。雖是如此美好,但要是無法達到你的目標;就是空無一物,就是不值一題。你冷冷地吐出毀掉一切的火陷,不留餘力。這就是你對我畸形的愛:你一邊鄙視我,一邊狠狠把我訴說成錯誤。另一邊則傾盡心力為我建造這美好的一切,但到頭來於你眼中,我還是錯誤的;我還是被你所放逐,你還是離我而去。好像是早就計算好能投入的心力,要是於時限已到還未能獲利就抽身而去。
教士們時時推銷一個觀念:「存在出於天主,萬物在起初圓融成一體。」然後他們就會以基督之名要求信眾與萬事萬物修和。因為存在所以分崩離析,都是因為人類背棄天主。
但當初果真如此美好嗎?看來不是:由野蠻到文明﹑由醜到美﹑由無到有 … …看來一切都與教士們的說法相反。
就像我渴望和你享受圓融和諧的關系;可惜現實殘破不堪。但為了步向那美好的境地,我不自覺間把記憶篡改得一片光明。
怎麼辦?那麼該怎麼辦?只好不放手,唯有不放手,全心全意在一起。在相愛相憎﹑彼此痛苦撕磨間再不分離。
【全文完】




-01.png)
.jpeg)
.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