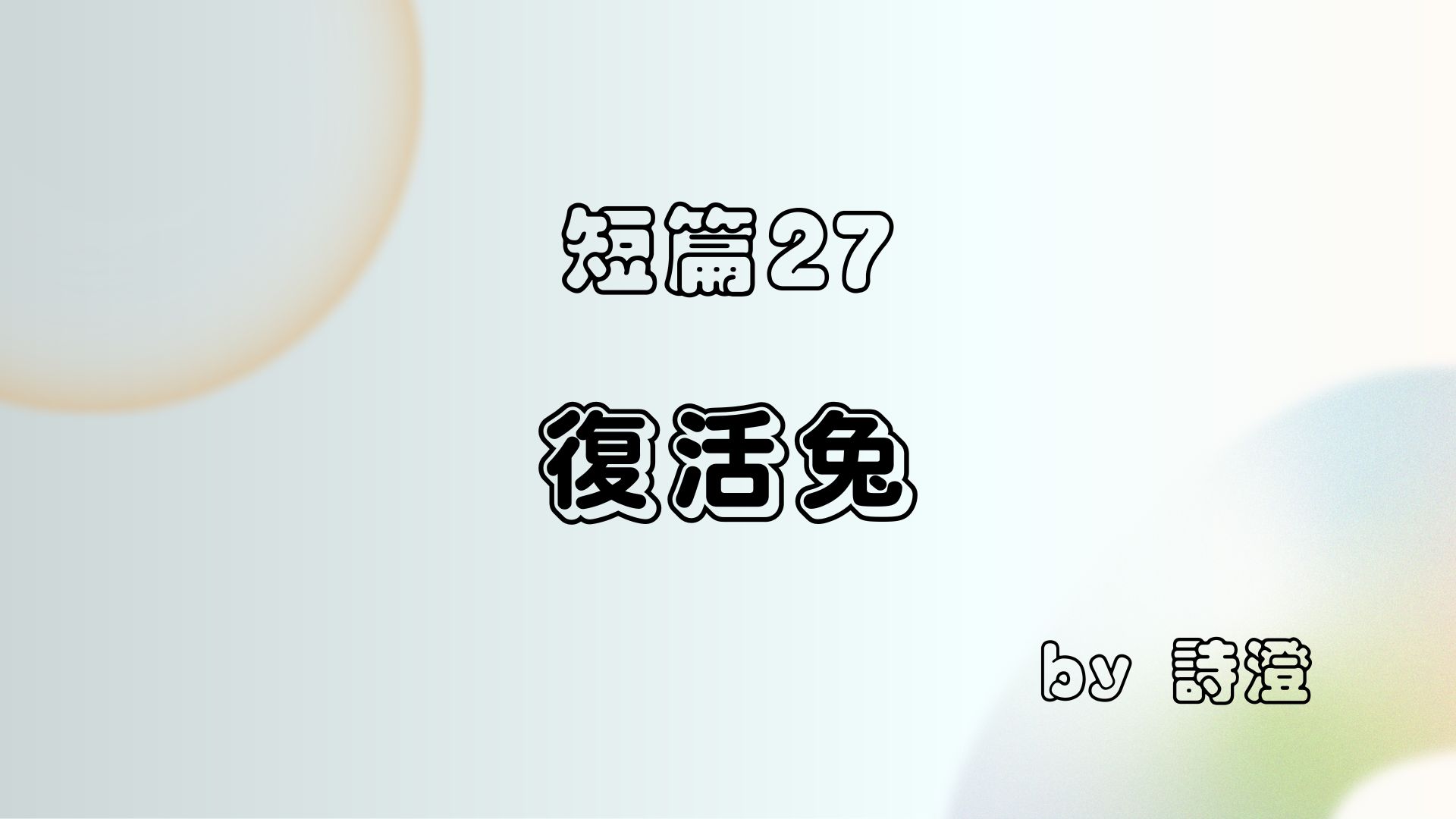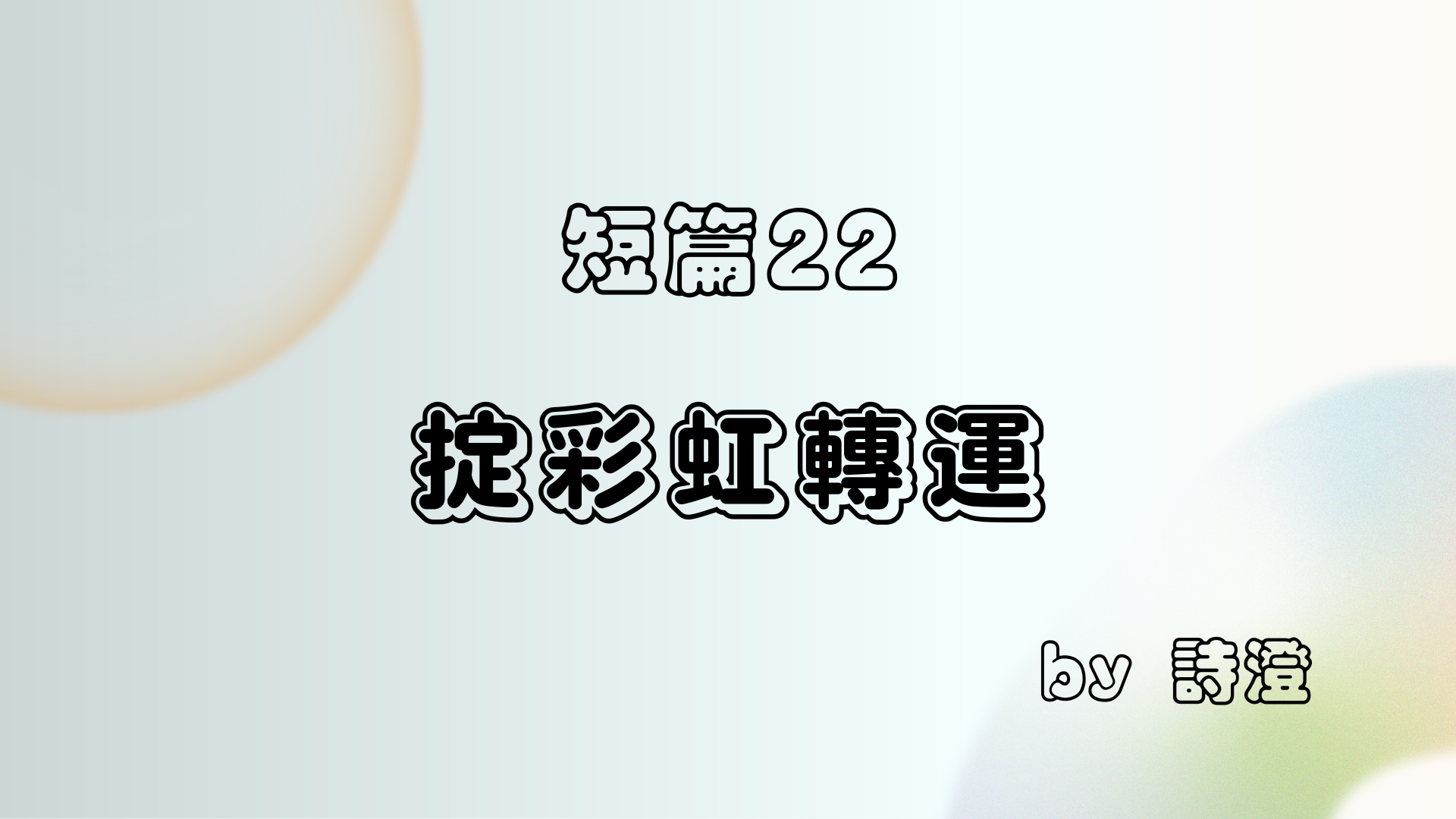人要活得不平凡,其中一個途徑,是做一份特別的工作。那是化妝師梁天一說的對白,他是少數到內地進修專業化妝課程並取得證書的香港人,他說的特別工作,是為逝去的人,進行人生最後一次的化妝工作。
那是叫大部分香港人撒手擰頭的工作,即使收入很高,卻又不是每人都能夠勝任。透過電視節目畫面,他一步一步地從理論學起,諸如要如何設計一張比較好看的臉,破爛了的要縫針,若屍體冷藏得久了,亦影響化妝的決定。
他的工作不是安慰死者家屬,而是讓每個人生的最後一段路,走得有尊嚴,走得漂亮。曾有傳媒訪問了他爸爸,他爸爸很支持這份工作,還很實牙實齒地說,若有一天他走了,一定要由兒子化妝。
日本電影《禮儀師之奏鳴曲》讓人看得笑中有淚,主角最後要化妝的人,的確是他的爸爸。在香港,願意投身這個行業的年輕人不容易找,也許正式工作後,也會受到一定冷言冷語。天一也有這種經歷,他喜歡放工後去超市買紅酒,因為飲了酒會比較醉,醉醺醺時會較容易入睡。
我沒法想像那種與不會答話的對象化妝的景象,不過若然化了妝後,那些對象會抬起頭來說聲「謝謝」,那大概更刺激。那些妝容化了後就永不會卸去,伴隨屍體化作輕煙,意義重大,家屬會心存感激。
醉心屍體研究的人,我的確認識了一個。她是很多年前的一個女性朋友,與其說是醉心屍體的人,正確一點是法醫人類學家。面對屍體的方式和目的都不同,而鑽研骨頭也是重點工作,能夠替死者沉冤得雪,從骨頭裡找到重要破案線索;亦會接觸新鮮的屍體,曾與屍蟲共侍,亦能解因種死因,那當然是一份特別的工作。她的與眾不同,讓人學懂許多法醫知識,亦受到傳媒和出版社愛戴和支持,為香港人爭光不少。
我無法了解和進行他們的工作,一來沒有那份勇氣,二來沒有那份學識。但不知怎地,總被這種獨特的工作吸引着,會去看他的節目,會深入地閱讀她的文章,在腦海裡有概念,卻又很難用文字寫出來。
沒有人可以避免死亡,也許有些人不會得到化妝機會(諸如被炸得粉身碎骨或被燒成炭),但他們的骨頭,比較大機會被法醫研究。中方有化妝師,西方有法醫,工作層面當然不同,只是我的聯想,把他們歸納為特別的工作。
註:畫面攝自港台電視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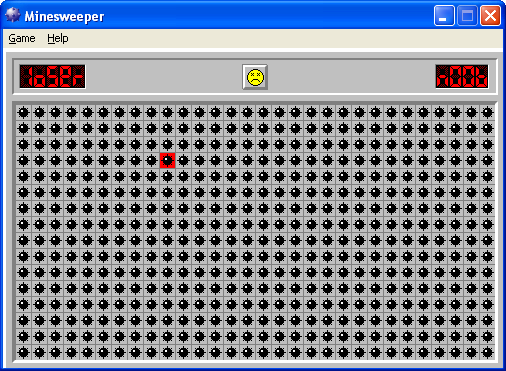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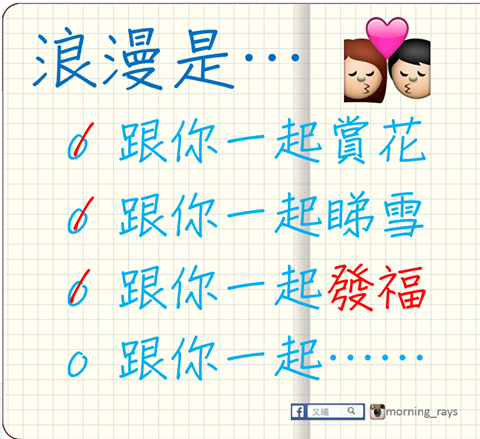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