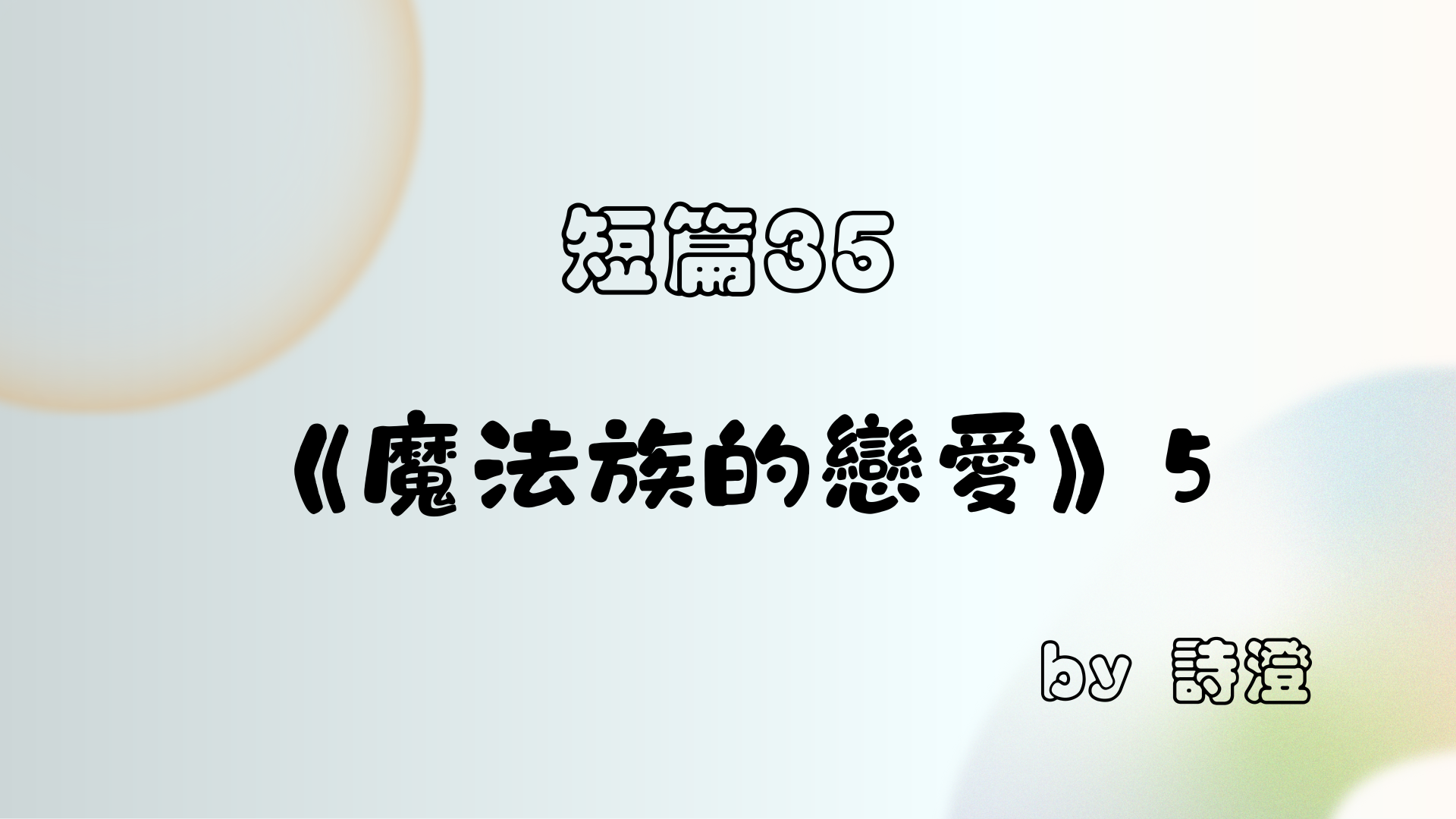然後別了依然相信,以後有緣再聚。那是二OO九年的事了,Y仰望着天空,雖然沒有吸煙,但仿似看到一團煙圈就在他頭頂飄起來,一直一直上升着,直至融入空氣之中。Y很喜歡說然後,仿似然後是他的口頭禪,然而,他那一晚很感慨地說,已經十年沒有拍拖了,大概在愛情上,沒有了然後。
Y是個樂天的男生,在群體活動裡,他總是起領導者的作用。最記得那年迎新營,他就在一班認識不到十小時的同學圍內,說了不下十個鬼故。鬼故的原材料不來自網絡或傳說,而是他的靈感,害許多女同學記下了,許多年以後想起還是會害怕。例如那個會在每晚十二時陪伴住客搭升降機的小女孩,只要一搭入十二時,走進升降機的一刻,她就會跟着,會模仿按樓層的動作,人按了十樓,她就會按九樓,而且是會亮燈的。
那年,他很明瞭女生的心思,當其他男生還在呆呆滯滯在跳營火舞時,他已鎖定了一個女生,然後就展開攻勢,不消數個月就看到他們牽手了。在校園的每一個角落,都沾有他們的戀愛氣息。他說過,與他拍拖的女生,每一刻每一秒都不會感到沉悶,一來他不允許,二來他總是說個不停。
戀愛生活不像補習社那樣既明愛又暗戀,也不像近期糖妹與智叔的「糖廖」效應,他們二人就是糖粘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糖。糖的角色就是帶給別人甜味,就如拍拖時喝凍奶茶,走甜也還是很甜。
不知道從何開始,已經習慣了甜蜜的兩個人,漸行漸遠。Y失戀的那年,世界沒有大災難,香港也平靜如昔,最多只是維多利亞港的白頭浪較平日稍多。Y是這樣形容的,他也不相信自己失戀,也不相信原來這樣深愛的愛戀,失戀後的平靜,竟只如維多利亞港多出的白頭浪。
Y依然樂天愛笑,笑起來可看到牙齒很白。Y的髮型也保持得很好,每逢十周歲的年份,他都會寫一段字。剛過去的三十週歲生日,就寫了十年沒有再拍拖,好像戀愛沒有了然後。
雖然沒有與女生拍拖,但Y的女生緣是不絕的。許多時候看到他和女生單獨吃飯,臉貼着臉自拍,笑起上來,兩個人的牙齒都很亮白,驟眼看是很合襯的,但他卻總會否認,女生是名花有主的。
Y喜歡寫一些小文章,也會看書,有時候會把書帶到離島去,一邊看着沙灘一邊閱讀。他的皮膚變得黝黑,顯得他的牙齒更白,因他總是開懷大笑,每一張相片如是。
在最近的日子裡,Y也會穿起黑衣。許多個晚上,他都會到金鐘那條有多條行車線的道路安靜地坐下來,有時候望望天空,有時候看看書本。他沒有衝到最前,只是默默地留守,會由天黑坐到天亮。
那晚,Y如常一個人坐在馬路上,凌晨二時了,身邊只有零散的數十人,坐得很開很開。Y坐得累了,沒有理會瀝青路的冰冷與堅硬,躺了下來,雙手托着頭,眼巴巴地看着天空。
不遠處,有一個一襲黑衣,長長頭髮,戴着口罩的女生,也學着Y那樣躺下,一起望着天空。Y留意到那個她,但他沒有發揮自己的看家本領,只是一直看着天。
原來,在這瞬間,金鐘的天空沒有星星。也許,再過一段時間,Y看到了星星後,或者就可以延續那個然後。
註:圖片取自互聯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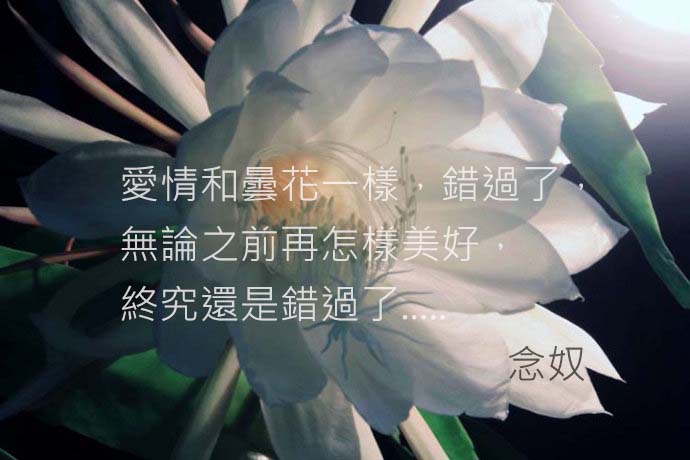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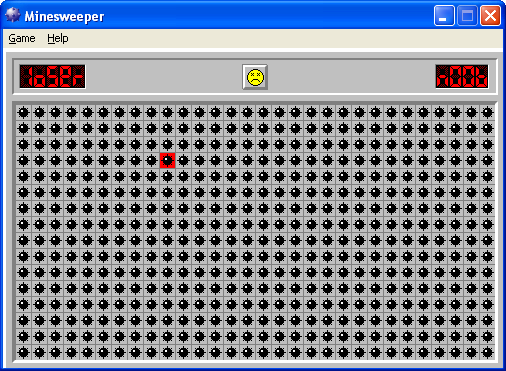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