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樣,到麥當勞點餐時,恆常的套餐是豬柳蛋漢堡餐。每一次到麥當勞,無論是自己一個,抑或是帶同願意陪我吃麥記的不如,我都慣例點豬柳蛋漢堡餐,就喜歡那豬柳被蛋壓着,下層再有一塊溶了一半的芝士的味道。然而,一口咬下去後,回憶卻有點模糊起來。
記憶中,第一次自己一個人買麥當勞也接近十歲了。下午放學後,我拿着一張二十元紙幣,到堅尼地城士美菲路那家麥當勞去,在櫃台前惆悵了一會,不知道要點些什麼,那時候櫃台前的姐姐看到我,就主動地對我微笑(微笑的確是免費),然後問我想吃點甚麼。
我無言以對,她就拿出一張Menu,細心地向我介紹着各種套餐,而我只顧看着她,並沒有任何主意時,她主動地叫我信任她一次,讓她為我選一個套餐。我點了點頭,她就收了我二十元,然後向我說,她給我點的是煙肉蛋漢堡餐。
原來,我第一次點的麥當勞餐,不是豬柳蛋漢堡餐,而是煙肉蛋漢堡。姐姐快速轉過身去準備食物及飲品,她建議我喝可樂,那也是正常不過的配搭。
我捧着載有那個煙肉蛋漢堡餐的黑色餐盤,走到二樓的座位找個位置坐下來,然後剝開黃色的包紙,頓時傳來陣陣煙肉夾雜芝士的香味。我二話不說地一口咬下去,那種味道就烙進我記憶裡,現時記起仍能幻想得到一個煙肉蛋漢堡在面前浮現的畫面。
我慢慢咀嚼,發覺此包的包皮是白色的,和其他麥色的包皮不同,咬口比較粗糙,像有着一份男人的粗獷。煙肉的煙燻味滲入包皮當中,再加上半融化的芝士,美味得讓我把包包的黃色紙也舔着,把粘在紙上的芝士吃乾淨。
自那次之後,我每一次去麥當勞點餐時,都會跟櫃台的姐姐(同一個)說:「我要一個煙肉蛋漢堡餐,飲可樂,謝謝。」姐姐都會認得我,然後很甜地對着我微笑,說要弄一份比較大的薯條予我,我總覺得這個姐姐有暗戀我的意思,可惜當年的我是個浪子。
不知不覺間,吃了數年的煙肉蛋漢堡餐,每一次都是下午放學後去吃,有時一個人,有時一班人。有一天我興高采烈地再去買餐時,發覺櫃台的姐姐不見了,而負責招待我的變了一個大嬸,她向我說煙肉蛋漢堡餐已取消了,只會在早餐時供應,下午只有豬柳蛋漢堡餐。
我猶疑了一會,發覺這個大嬸的說話不可靠,她一定是殺了那個姐姐再取代她的位置,還要欺騙我沒有煙肉蛋漢堡賣,要強迫我吃豬柳蛋漢堡。我沒有妥協,但我還是有禮貌地向嬸嬸說:「我今日不吃麥當勞了,突然想吃粥,不好意思。」
大嬸的奸計沒有得逞,但我已很掛念煙肉蛋漢堡的味道。我沒有刻意早上去測試有沒有煙肉蛋漢堡餐賣,而是連續很多次放學後買不到煙肉蛋後,都垂頭喪氣地改買皮蛋瘦肉粥去。
當我升上中學後,有一次不甘心地再去那家麥當勞碰運氣,雖然還是不能買到煙肉蛋,但我卻重遇那個以為被大嬸殺了的姐姐,而姐姐也認得我,我們的重遇甚至有着心跳回憶。
「姐姐,可不可以賣個煙肉蛋漢堡餐給我?」我懇求着,眼神充滿希望。
「煙肉蛋取消了,不如日後吃豬柳蛋吧,只要你不停吃着豬柳蛋,很快就會忘記煙肉蛋的味道了。」姐姐也誠實地告知我煙肉蛋沒有了,但她也學着大嬸那樣勸我改吃豬柳蛋。
「煙肉還煙肉,豬柳是豬柳,怎會吃得多豬柳就會忘記煙肉的味道呢?」我大惑不解地反問她,對她沒有了當初推薦我吃煙肉蛋的那份堅持感到失望。
她笑了一下,卻沒有理會我是否要點餐,轉身拿了一份豬柳蛋漢堡餐放在我面前的餐盤上,然後對我說:「這個餐我請你吃,吃過這次後,你日後也要記得買它。」
我不理解她的用意,但想起當初的煙肉蛋餐也是她為我點的,我接受了她再一次建議,沒有要她在工作期間付錢請我,我堅持付了錢,捧走那個盛有豬柳蛋漢堡餐的餐盤。
我看在姐姐的份上咬了那個豬柳蛋漢堡包一口,發覺沒有吃煙肉蛋幾個月後,這次吃豬柳蛋的感覺相當美好,包皮和芝士的味道都存在,而且也有粘着包紙的芝士,我也同樣吃光了。
下一次我再去點餐時,姐姐又消失了,取代她的大嬸竟然對我說,那個姐姐要到外國升讀大學辭職了,還交托她告訴我,不要再記掛着煙肉蛋漢堡餐了,日後只要點豬柳蛋漢堡就好。
那刻年少氣盛的我胡思亂想了一通,原來姐姐心中的確有我,她為了讓我忘記煙肉蛋漢堡,竟然用豬柳蛋漢堡來取代。
那個姐姐,已經在記憶裡變得愈來愈模糊了。雖然此刻的我會恆常地點豬柳蛋漢堡餐,但若然有一天,超值套餐當中重現煙肉蛋漢堡餐的話,我想我會再點一次。
(不要問我為何不早餐時去買煙肉蛋,我吃早餐時不會吃麥當勞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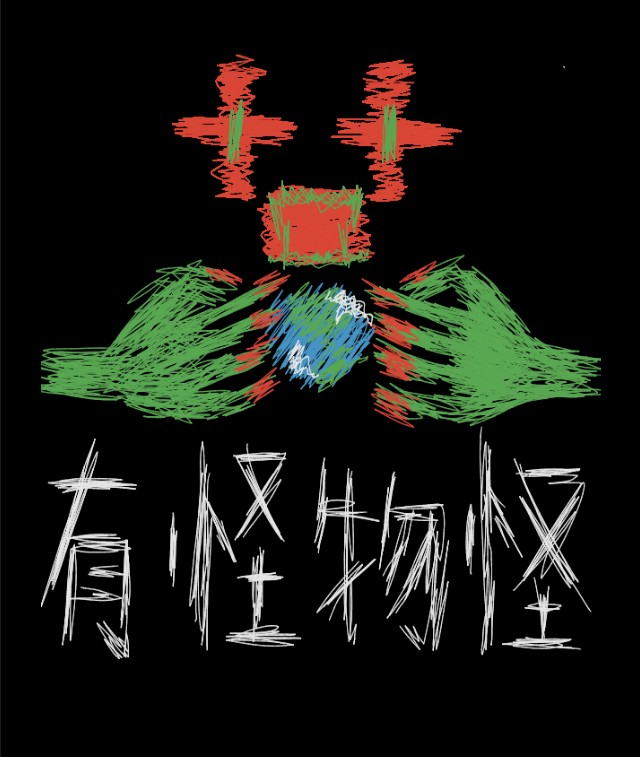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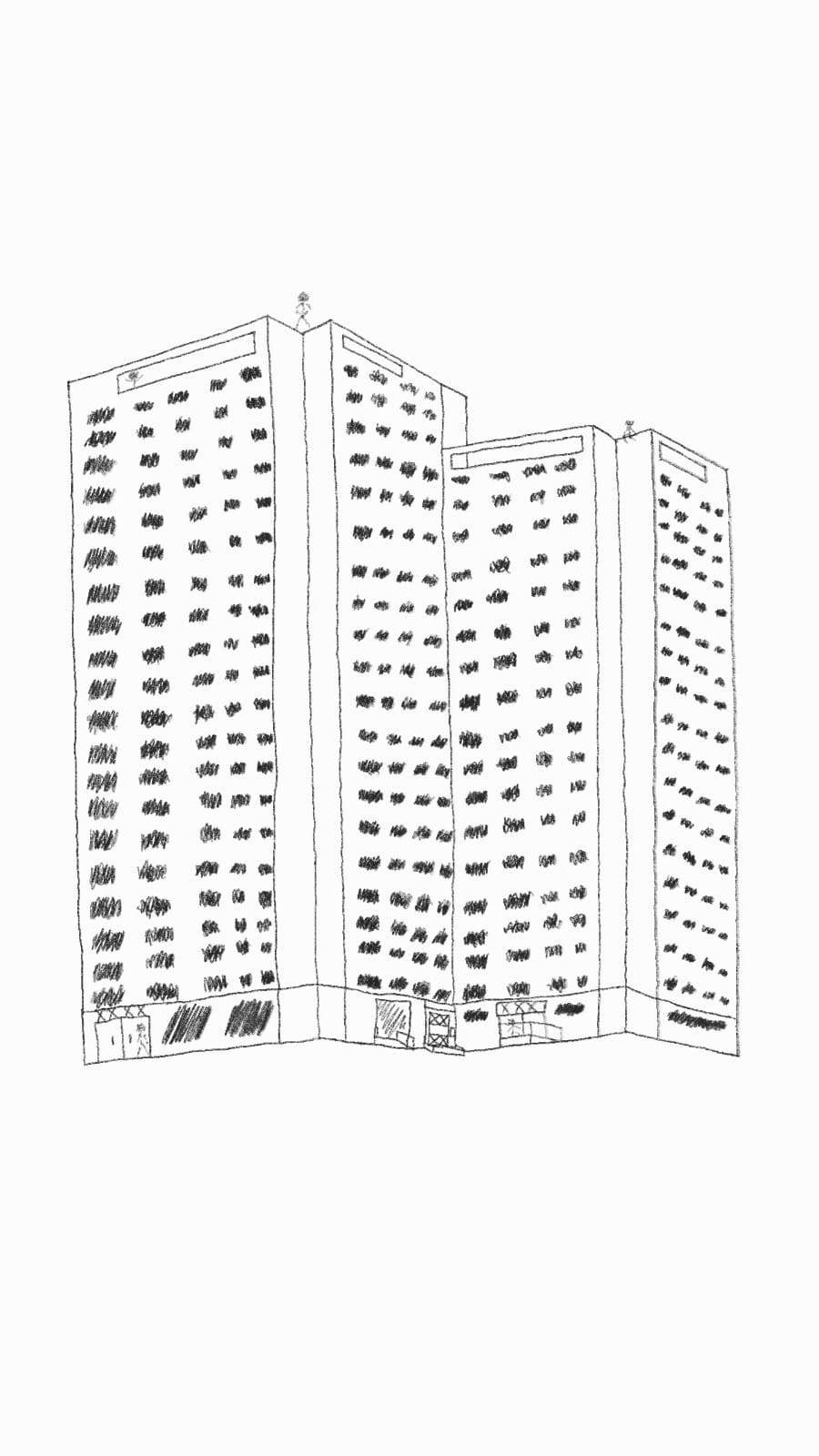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