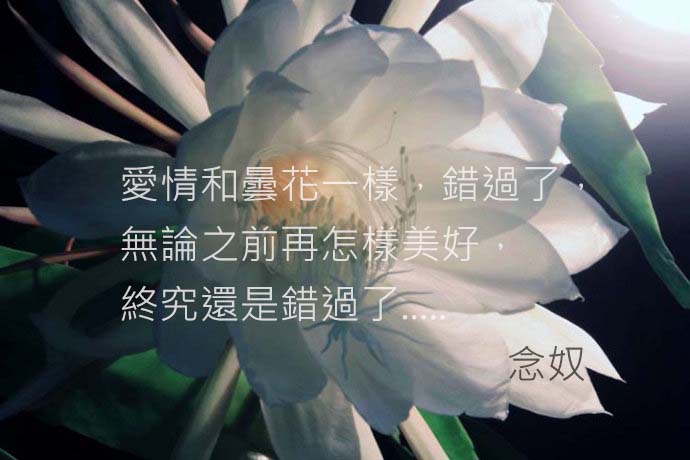她今天走下樓梯的腳步分外輕快,幾乎腳不沾地。一位在樓道中與她相遇的鄰居也驚喜地發現,她竟然主動對他點頭問候。雖然兩人平日甚少碰面,但他對這位女子的印像一向都是一副眉頭深鎖,形色沉重的模樣,即便狹路相逢,她也只會低頭耷腦,踮起腳尖悄悄溜過。因此鄰居不但對她今天態度上的轉變感到驚訝,更覺得她臉上那不自覺地流露出來的梨渦淺笑格外可愛。就連街上與她擦肩而過的路人,也都會覺得這位女子走起路來身姿輕盈,分花拂柳,使得自己也分享了她的一份如沐春風的喜悅。最先發現她的轉變的是女孩的家人。她平日說話一向半吐半露,多番咀嚼,總是一句起兩句止,但這幾天她明顯比往日活潑開朗,說話直截了當,甚至對家中瑣事也多了幾分主見。女孩並未意會到自己的轉變,她的日子也與往日別無二致,但外人卻對她的變化一目了然。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這位一向拘謹內向的女子悄然蛻變成一朵嬌豔欲滴的蓓蕾?這還得由前幾天的一個下午說起,或者,還有必要由更早的時候說起。
雖然這個女孩出身自一個並不富裕的家庭,但也不愁溫飽,教育當然亦不能太過失禮。她成長於傳統教會女校,一直按照淑女的要求來培養,因此她自小就是個安份守己,循規蹈矩的人。在理應最熱情奔放的荳蔻年華裡,她也從未對任何人產生過什麼情愫,一方面是因為沒有遇上能勾起心潮的對象,另一方面也因為理性的限制。她喜歡浸淫於思想之中,她的思維邏輯清晰,條理分明,但唯獨對感情缺乏想像力。她的家人平日總說她是個沉悶的人,身上缺少少女應有的甜美,眼見她身邊那些早熟的昔日好友要么早已嫁作人婦,要么一頭沉浸於熱烈的愛戀情當中,然而轉眼間女孩這個夏天就要二十六歲了,還一直是孑然一身,就實在很難不為她感到憂心。
女孩自己倒是從容不迫,不緊不要的。她一股腦兒專注於學問,目前仍在像牙塔內研讀哲學。她喜歡理性的思辯、書卷的馥鬱、智慧的潤澤,總之就是陶醉在一切思想層面的愉悅。由於未嘗辛勤工作,也未在社會上吃過苦頭,歲月在她臉上沒有留下太多痕跡。她的雙瞳還映照出孩童的純真和爛漫,眉色淺薄,平淡的五官安立在小巧玲瓏的圓臉上,絕不能使人一見傾心,但確有幾分秀氣可人。柔順的肢體線條,胸乳菽髮的體態,也使她看起來敏捷靈巧。正是外表上種種巧妙的和合佈置將她的稚嫩完整地保留了下來,令她由內至外都是如此的質樸無偽,使大多數人在知道她的實際年齡後都會感到驚訝不已。然而,她對此至終也沒有多在意,因為她對這可感的物質的現象世界的興趣絕不比那個不可感的觀念世界高。
她另有一項鍾情的活動,就是散步,並非因為有益於身體,而是因為有益於思維。尤當遇上值得思考的問題時,她散步的次數就會更為頻繁,時間也更長。當她試圖重新推演笛卡爾的六個沉思時,腳步會變得特別沉重謹慎;當她在腦海中演奏華格納的交響曲時,步伐就會不自覺地加快;當她重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時,雙腳就彷彿踩在舊魯薩的一條小路上。平日的大部分下午時光,她都是在河畔公園的行人路上度過的。這條步道以一片嫩綠的草地為中心,外邊流著一條護城河,全長約八百公尺。她沒有對此進行過精細的量度,而是靠日復一日的踱步推敲出來的,至於踱步一圈需時多久,則完全取決於思維的快慢,她經常圈復一圈地走至思緒暢快淋漓為止。對於這個時間出沒在公園裡的人,她都認識,並且可以說是了然於心,並不是說大家互通過姓名或是愉快地聊過天,而是她習慣在相同的時間相同的地點見到他們,並將他們的臉孔設置成思考背景。雖然當中大多是婦人或退休老漢,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涉及一些季節性變化。當夏天或假期來臨時,孩子們會結伴到公園來享受課餘時光,他們像一輛輛有無限燃料的小火車,可永無休止地狂奔下去,所以散步時得小心不要讓他們一頭栽到自己身上。至於身穿罩袍和長衫的外來移民則多在陰天或涼風初起時光臨,他們熱衷於交流,且語速飛快,像發了鏈條似的一直嘀嘀咕咕個不停。寒風凜烈之時,大多只有清潔工還在盡忠盡職地收拾步道,偶爾可見寥寥無幾的幾個人零散地在向陽處打發時間。而她則特別享受風雨過後的散步時光,雨水蕩滌的空氣有一絲莫名的蒼涼之感,總能安定她的思維和情緒。
那天午後,她一如既往地出現在河畔公園,腦袋裡裝著大衛•休謨的自我同一性問題,沿路的白雪花護送著她漫步。住在護城河對岸的白髮婆婆在護工的攙扶下進行康復運動,她前不久因不小心踩到碎石子堆里而崴了腳,連續兩個星期沒有參與到公園的下午時光。女孩原本還擔心老婆子會從她的思想拼圖中缺席更久,但現在看來老人家的腳傷已經痊癒得差不多了。禿頭的矮個子老伯照舊坐在樓梯口處的長椅上聽廣播,一聽到喜歡的音樂就會閉起雙目,翹起二郎腿,跟著節拍輕搖身子。另外還有幾位熟悉的慢跑者,他們的跑姿會告訴女孩這些人最近過得愉快抑或疲憊,心情舒暢者跑起步來眉目舒展,身姿堅定,勞累憋悶者則曲肩駝背,愁眉苦臉地跑跑停停。一路上,她允許這些迎面而來的人在她的思緒中略過,並在心底跟他們一一打招呼。她也留意到有兩名外裔少年在草地上踢球,年紀較小的一位初中模樣,一臉稚氣,較大的一位應該不足二十歲,個頭不高,正是英氣初現之時,肌肉在灰色襯衫上勾勒出雛形,黑色運動短褲下方是一對矯正有力的長腿。二人正在進行盤球練習,時而狂奔衝刺,時而急停或繞過同伴,較小的一位從未成功地在他哥哥腳下搶過球權。她以前從沒見過這對兄弟,其實青年人在這個時段是頗為罕見的,因為他們現時理應大多都在課堂上打午後瞌睡,但轉念一想,當今青年移民在學校或工作中待不下去,亦非什麼新奇事了。於是,她又轉頭繼續投入人格同一性的沉思。
當她在腦海中重溫到論尊敬和鄙視時,已在步道上漫步了好幾圈了。太陽的傲氣已消退了幾分,陽光穿過白樺樹婆娑的枝葉,在步道上撒下跳躍的金光。微風一起,春天的甘露便乘機滲透進鎮上的每一條小巷子,落在每個人的心頭,悄悄埋下一顆春意盎然的種子。白髮婆婆和護工暫且坐在長凳上休息,老人的臉孔在綠蔭下忽明忽暗,枝影與皺紋交融,垂老的眼角似乎又亮起了生機。來得稍早的一位慢跑者已經喘著氣,但跑姿依然堅挺,步履小而緊密。行至彎道時,她悄悄讓出內道讓對方經過。草地上的兩位少年此時正有來有往地踢著球,足球在他們腳下回了數個回合,然後年紀較小者腳下一滑,一下子踢歪了,球便偏離了原來的路線,往步道旁的灌木叢滾去。年紀較大者一個箭步上前,連三跨五,乾脆利落地把球帶回自己腳邊。她轉念繼續沉思,並由以上章節聯想到一向放任的瑪麗安•達殊活竟以理性的選擇為最終歸宿,那麼她的同一性又該如何論證呢?在故事設定的條件下,認知主體與情感的關係又如何構成知識呢?她又繼續繞了好幾圈。當思考到驕傲與憎恨如何使靈魂振奮,而愛與謙虛又如何使靈魂變得軟弱時,高枝已化於春暮,落日快要掉進護城河了。老伯裹緊了風衣準備離座,幾個慢跑者正在做最後的伸展運動,兩位少年亦早已停止踢球了,年輕的一位正坐在草地上休息,其兄長則在隧道口徘徊。女孩一點點收起心思,像剛領薪水的工人小心翼翼地將信封安置口袋一樣,準備打道回府了。
當她經過隧道時,少年出乎意料地叫住了她,「不好意思……」她下意識以為年輕人是要問路,便停住了腳步扭過頭來,然後驚訝地發現對方離自己非常之近,似乎是緊追著她的腳步而來,「小姐,請原諒我的唐突!剛才您在若有所思地散步,似乎是在想什麼艱鉅的問題,我實在不忍心上前打擾。我留意您好一陣子了,甚至可以說今天整個下午都受到了您的吸引,您的可愛、您的沉思、您的一舉一動都牽引著我。請問能允許我知道您的名字嗎? 」
少年一口氣吐出來的話宛如一串驚雷,將她震懾住了,這是她不曾設想過的情境。她一時間只能張口結舌地盯著對方,大腦一片空白,不能思考,整條隧道都落入了無垠的虛空之中,就連眼前的臉孔都是如此的虛無縹緲。在她還沒反應過來之際,年輕人突然一步踏前,捉住了她的右手,掌間的溫暖瞬間轉移到了她的手臂,直擊著她的心靈。她感受到了眼前這位男子的力量,那是一股難以抗拒的震撼力。
「對不起,請原諒我!」少年感覺到女子指間的震顫,意識到自己嚇到了她,於是再一次道歉,但雙手卻握得更緊更小心,像握住一隻受傷的小鳥,「雖然我倆素不相識,但懇請您相信我別無惡意,或許我是在說一些愚蠢的話,還請您見諒,因為事實上我也同您一樣受到了驚嚇。」
年輕男子無意識地將握著的手拉近至自己的胸膛,她觸到他被汗水浸濕的運動上衣,隔著衣服感覺到他心臟跳著狂熱的節拍,沸騰的血液彷彿要流進她的指尖,傾注到她每一條血管。熾熱的血流頃刻湧上大腦,在她的思想曠野裡燃起了一點星火,並瞬間漫延至腦海中的每個角落,使她一時心亂如麻,頭昏腦脹,混身打顫。
「噢,親愛的,請不要驚怕!這個下午我曾多次嘗試捕捉您的視線,但遺憾地總是與您擦肩,我只希求您能施捨我一記溫柔的目光。」他說著把緊握著的手提到了嘴邊,輕輕吻了一下。她實在驚慌得動彈不能,就如此輕易地被眼前這位男子撩動得面紅耳赤,不能言語,不知所措。年輕人見狀便更覺她可憐可愛。
她滾燙的臉頰被少年柔情地抬起,她直觀地感知到對方目光中的灼熱和真誠,二人深刻地直視著對方的雙眼,彷彿要看穿彼此的靈魂。少年趨步向前,進一步拉近了雙方的距離。她聞到了對方身上汗水蒸發的氣味,竟是那麼的濃重、剛烈、迷惑,簡直使人心醉神迷,神魂顛倒。年輕人在她腮邊低下頭來,氣息吹進了她的耳邊,然後在她前頸上溫情脈脈地獻上一吻。那一刻,她最後的一絲理智幾乎要被這衝車般的一擊給粉碎殆盡,她知道自己若再不離開的話,必定要暈倒在他懷裡,任由對方支配。她調動全身的力氣,慌亂地抽出了手,推開他厚實的胸膛。 「不好意思,請讓開……」她的聲音略帶沙啞,語氣比平常更為冷漠,自己也被嚇了一跳,但顧不上體面了,馬上頭也不回地朝出口大步流星走去,甚至可以說是落慌而逃。
她不敢回頭,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直到安全地隱身於家附近的一處胡同之中,靠著牆費了很大的力氣才穩得住身子。她的胸脯誇張地上下起伏著,彷彿所有的情感都要瞬間從肋間一湧而出,傾瀉千里,匯合河水流向大海。她頭靠著冰冷的石牆,閉目收拾心神,大口捕捉晚間空氣。她不知道到底過了多久,也許只有幾分鐘,也許有一個多小時,因為她暫且失去了感知和推算的能力。等到她平住呼吸以後,才發覺深不見底的夜幕已覆蓋城市,虛空消融於夜色之中,知覺終於再次落地,思想又可立足於一磚一瓦。她聽到自己爽朗的笑聲在空巷中迴盪,她從來不曾笑得如此放肆。天啊!剛才的一幕是多麼的滑稽可笑!她清醒過來後扶牆走出胡同,慢慢地朝家的方向走去,她雙腿沉重,彷彿剛完成一場劇烈的賽跑。離家的路明明是那麼熟悉、清晰、短近,但她似乎要走上足足一整晚。當她置身自己熟悉的被窩時,早已筋疲力盡,馬上就酣然入夢了。這個晚上是個特別安靜、平穩、深邃的夜晚,孤星倚月照長河,才子佳人夢輝映。
翌日清早,女孩從深沉的睡眠中甦醒,感到神清氣爽,混身舒暢,但依然緊閉雙眼,不願動身,任由敞開的窗戶多情地招攬庭園春色,讓和藹的晨光和微風愛撫眼皮。昨午那位少年的身影像已癒的高熱,已從她額上悄然退去,只剩下一抹殘雲。她試著回憶起對方的樣子,卻如霧裡看花,水中撈月,似乎她從來不曾捕捉到對方的外貌,但她依然真真切切地感到被他的氣息和力量所包圍。她的手腕彷彿仍然被那雙自穹蒼而來,強而有力,蘊含無限溫柔的手握住,並一手將她從理性的廢墟中拉出來。她不怪年輕人的荒唐無禮,對方的勇敢、真誠和坦率贏得了她由衷的敬佩,而她驚惶失措,窘迫盡露之態倒是令自己感到羞愧不已。她很想對男子說句寬慰的說話,但她心裡有個地方確信這位只有一面之緣的男子不會再出現在她眼前了。雖然她不知道這個信念的根源,也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證據,但她就是肯定他們不會再相見。這個念頭讓她頓感安心,長舒了一口氣,平淡的面容上亮出了一絲淺笑,一抹紅暈又悄然爬上了額頭。
或許現在,白日已叫年輕男子將昨午所受的屈辱通通拋諸腦後,並再次勇闖生活激流。雖然兩人在背過身去的一刻,就終將注定不會再有任何交集,但對女子來說一刻相遇仿歷百年。那位少年或許會在往後的日子裡,在她某一個進行了激烈思考的午後,突如其來地闖進她的思緒中。每當他的身影閃現時都會是約翰•威洛比的形象,而她會像幻想家愛著納斯金卡那樣祝福他。她願意把多年後的男子想像成一位氣宇軒昂,風骨偉岸的紳士,她希望他能為自己心愛的女人採摘山野間的櫻花草,在她耳邊輕哼莎翁的第一百一十六首十四行詩,並在一個繁星燦爛的晚上向對方許下浪漫的白色誓言。他的生活必定到處充滿浪漫與熱情。另一方面,她的生活則是可預視的。她會在一個適當的時候,經過仔細的考量,與一位門當戶對的儒雅之士結合,安穩地活過一生。然而在此之前,她將繼續重複著往日的生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她心靈中某個不能被感知的隱匿處,發生了一些本質上的異動,並外顯在經驗世界中,使她會踩著輕快的腳步上街,臉掛微笑向那些熟悉的面孔一一打招呼,並學會欣賞目光所及的一切風光。或許,我們可以浪漫地解讀成,女子的血液中將永遠流淌著那位少年最美好的青春,每當回憶湧動之時都會在她心裡吹起一陣春風。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