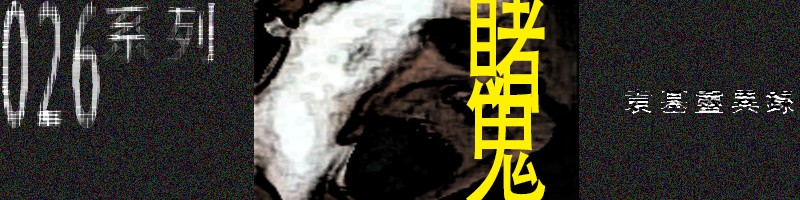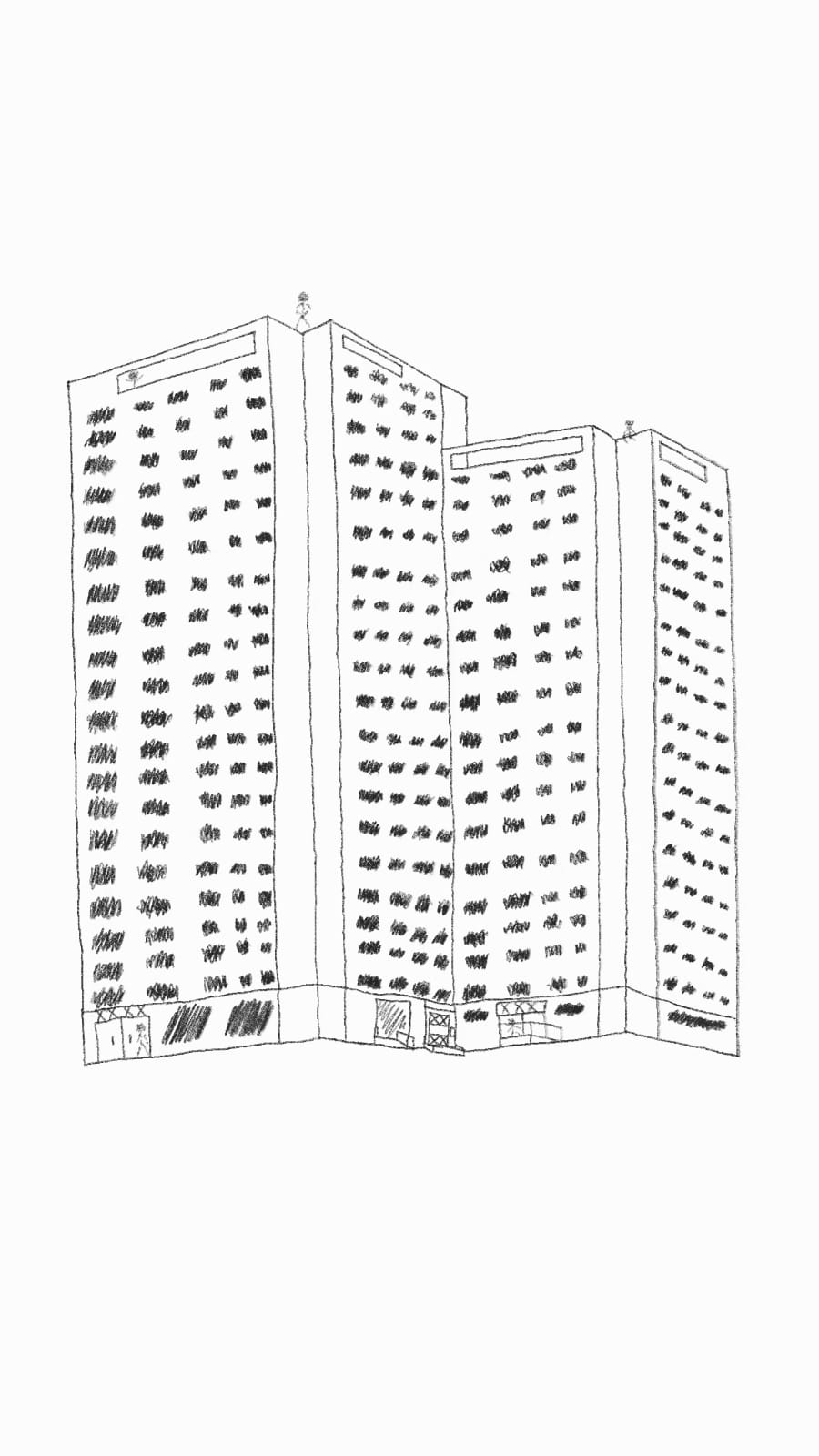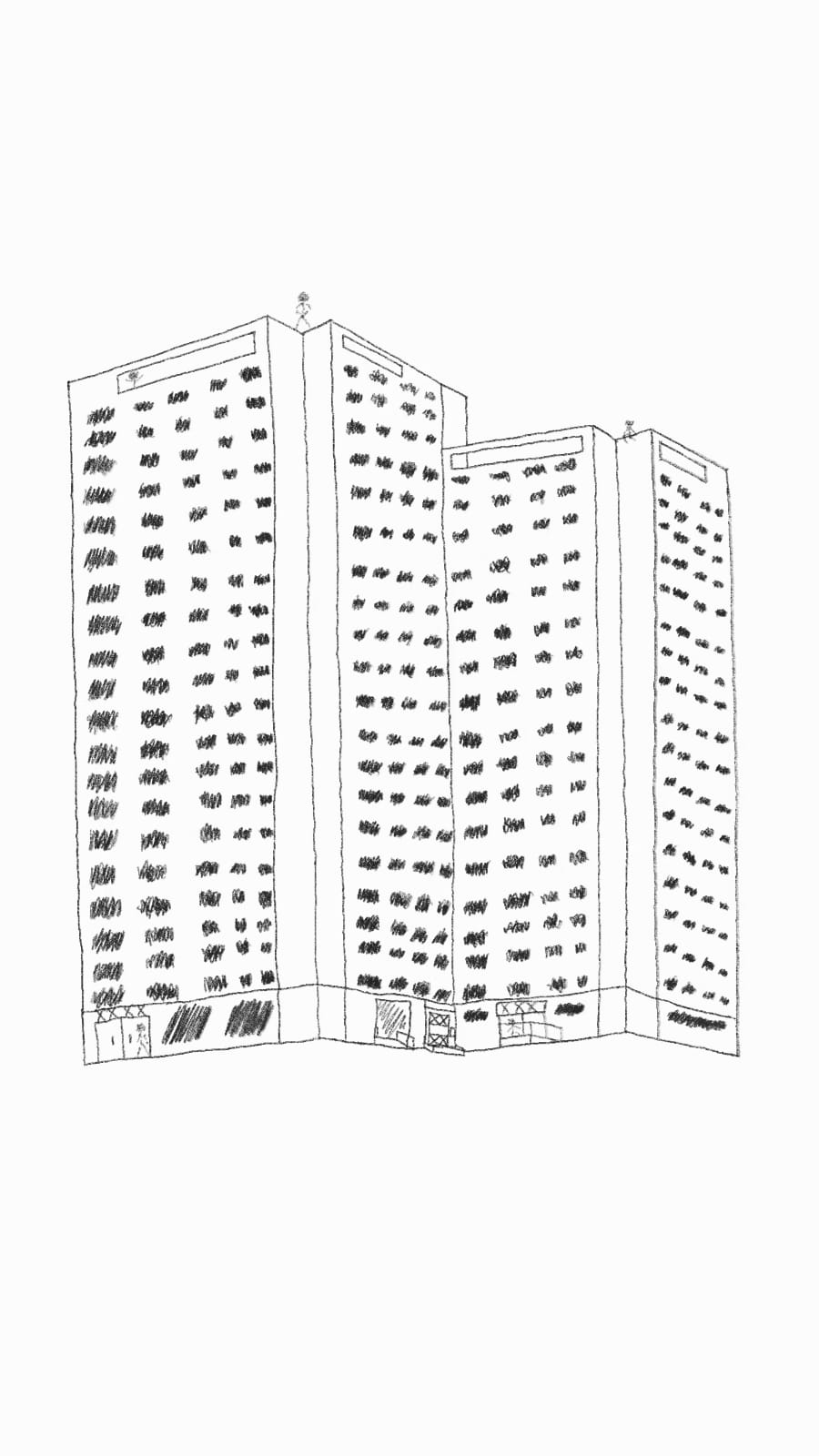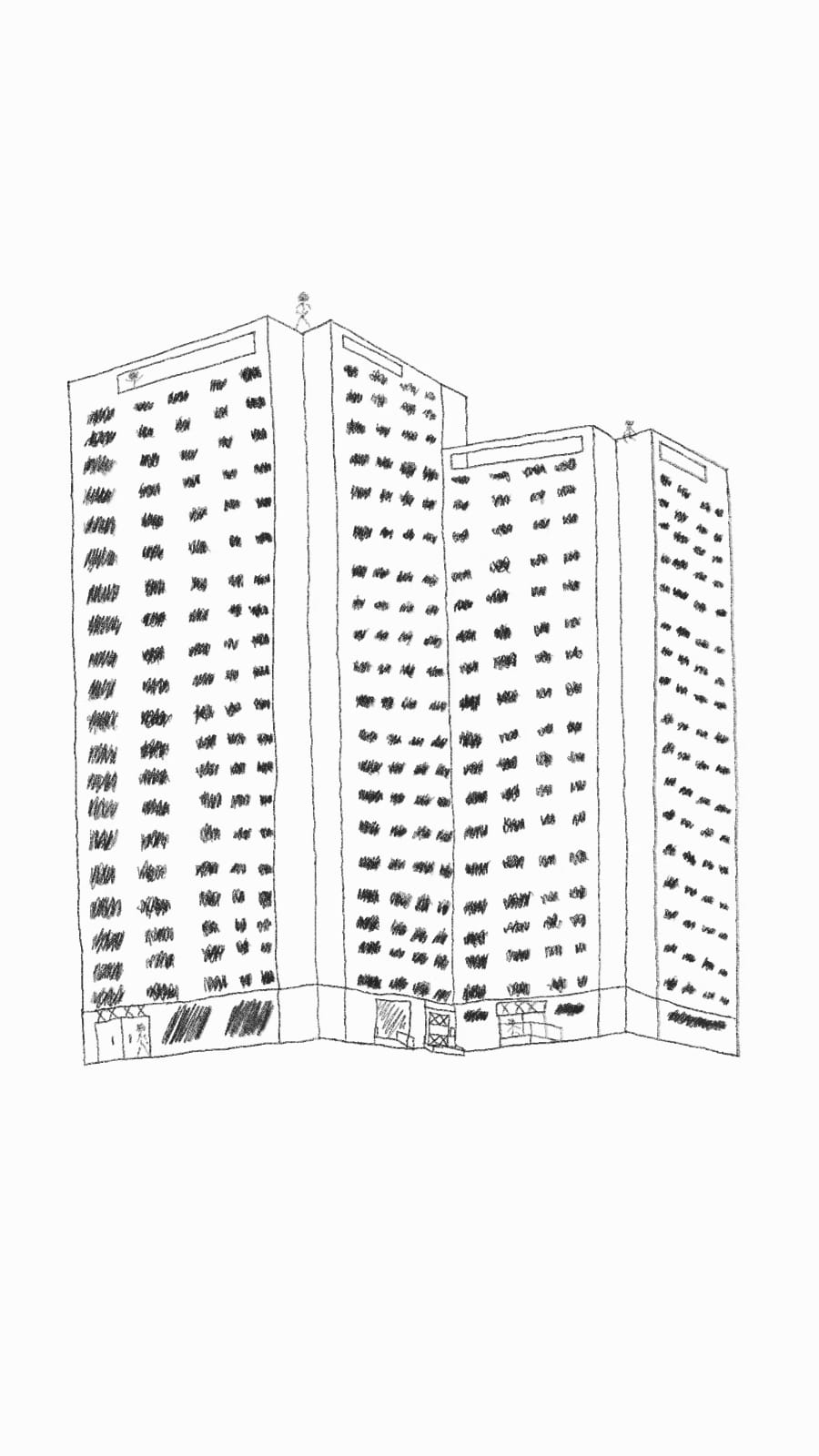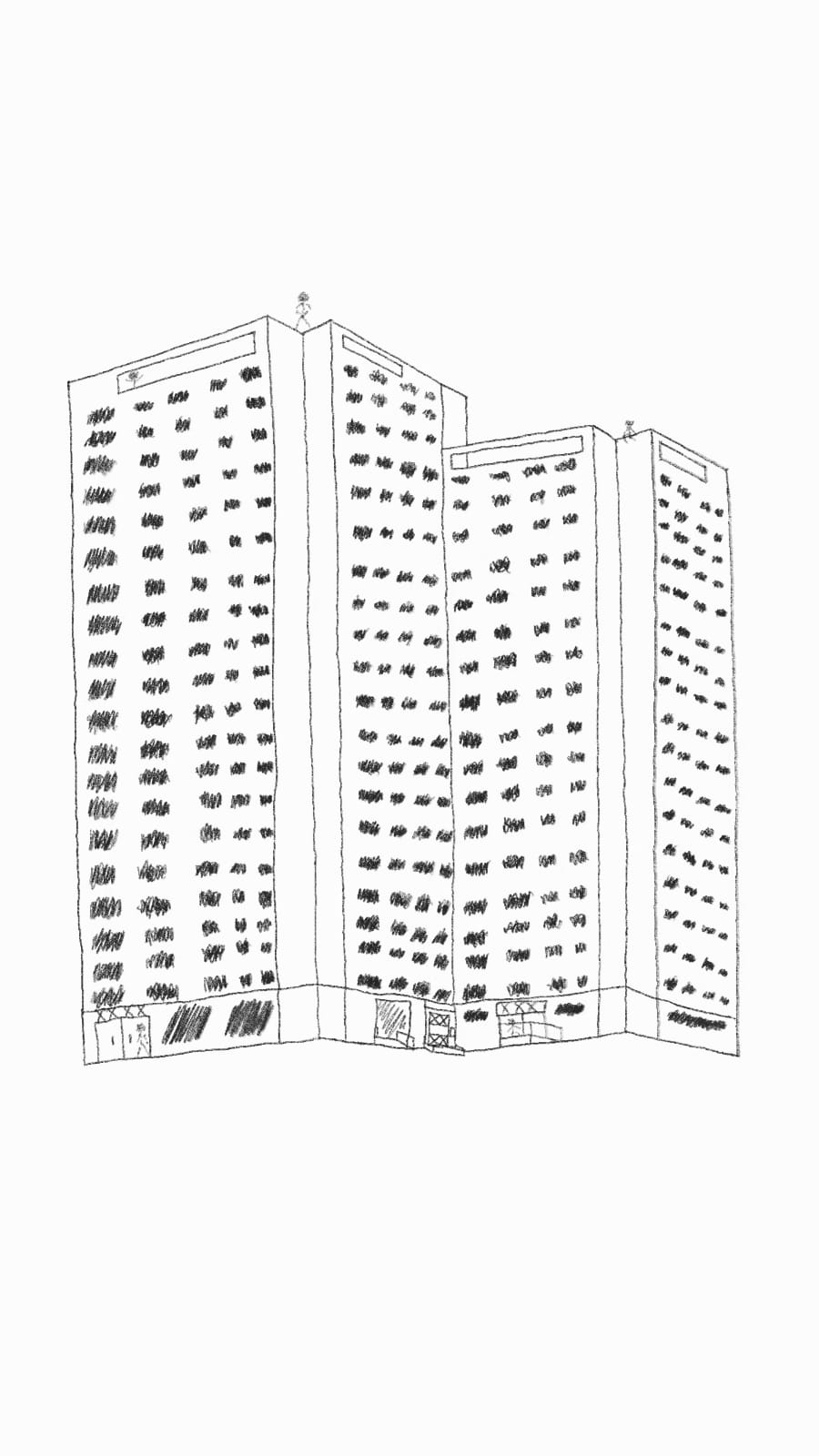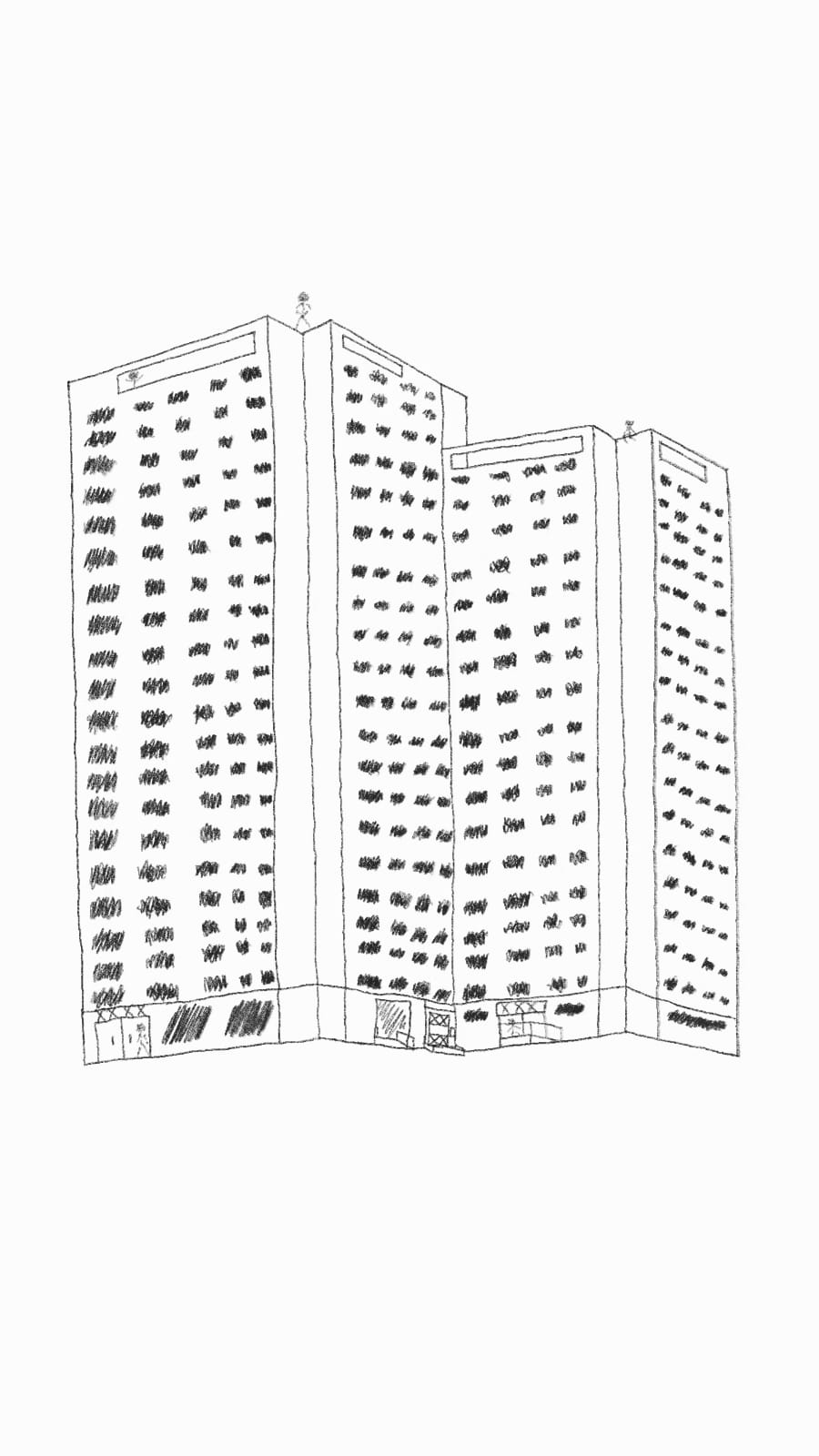001《屍承》
諸君好,能以這形式與大家會見,實屬有幸。先自我介紹,本名袁基,是典型地球人,為人好奇,就是如此。喜歡周遊列國,但稱不上為旅遊家,反而自我套上冒險家的身份,更覺恰當。之所以敢充當冒險家,因為早就把尋幽探秘,蒐羅奇聞,融為生活的一部份,這或許有一點奇怪,但在大學選讀考古學亦是這個原故。
提起大學時代,就令我憶起一件頗為驚險的事……
說話,大三那年,我無意間,參加了由湘西辰溪文化機構舉辦的「文物考察團」;當時,一心想只圖到外面逛逛,剛好為期五天的考察,正好符合一個小假期。隨團還有當地著名的地質學家──柳坤洪教授,聽講,柳教授很少參加這類活動,難得一同參與,也算緣分。
教授雖然年過五十,但臉色仍然神采飛揚,瀟灑不覊,而且頭上還紮有一條灰白色的稀短小馬尾,更顯個人風格。我和柳教授初次見面,即有一見如故之感,所以天南地北,無所不談。這份忘年之交,來得奇妙。如果信有輪迴之說,說不定我倆早在某時代已經相識。
來到考察第二天,我們經已到達形影不離的地步,感情尤如叔侄,之所以關係可如此「進展」神速,全因大家都是「同途中人」。原來,柳教授亦是一個喜歡獵趣蒐奇的人,加上當我知道他的家族背景後,感覺就如活生生的一件「奇聞」站於面前。
關於柳氏家族的生意,就是教人忌諱的「趕屍」工作。這門工種,是一種把客死他鄉的人的遺體運送回鄉的技法。當然,時移世易,早就令這門技術失傳,但當中的秘聞,仍然是令人津津樂道;可惜,由於考察團裡,有部份是國家官員,加上柳教授的身份,話題上就只能限於學術,所以我們的「交流」亦只可點到即止。
直到考察的最後一天,整個行程總算順利,當晚,主辦單位還特設款宴;中國人就是這樣,只要有酒的地方,懶理是何時何地,氣氛總如過節一樣熱鬧。至於我跟柳教授,固然就自成一角,小酌一番。
那時,一眾團友都已喝得酩酊大醉,柳教授見狀,便向我提出一個小玩意,道着:「小子,有興趣要看我的家傳之寶嗎?」
他口中的家傳之寶,不禁令我把他的家族生意聯想起來,自然莞爾而笑,隨之跟教授打了一個眼色,然後便啞聲問津:「跟趕屍的有關?」柳教授笑而不答,只一邊拿起椅背上的外套,一邊說着:「跟上來吧。」
離開酒家後,沿途上,我們沒有並肩而行,只一直跟隨教授的步伐,因為由酒家到柳教授的家,必需穿山走徑,四曲五彎,加上月黑風高,雜草繁生,舉步為艱。
大概用上廿五分鐘的路程,終於到達教授的住所,這是一座獨立式的古宅。古宅旁邊,除了有幾顆大榕樹環圍之外,四周荒野無物,暗透心悸。
據教授所講,古宅至少已有一百八十年歷史,是柳氏家族世代相傳的祖屋;就連那個富有歷史價值的銅制瑞獸頭門環,也不敵歲月沖刷,而變得銹迹斑斑;而庭中掛上幾顆微弱的小燈泡,令宅內處處,更顯神秘。
其實,這座古宅每一磚一瓦,都可為尤如家珍,基本上不能逐一細數。柳教授繼續帶我到在大廳旁的祠堂,然而,先為列祖送上清香一炷,之後柳教授便閉起雙眼一言不發。
雖然教授回來之後,就未有再提過所謂的家傳之寶,但難得可參觀這座古宅,可叫榮幸。而我環顧四周,發現祠堂的屋頂上,吊了一塊平放的木板,木板的四角都被穿上大麻繩拉着半空,感覺該有東西放在板的上面,但我沒有發問,因為教授好像在冥想什麼,唯有自己仰天猜想。
此時,教授自語說着:「那木板上,就是放了我們柳家的家傳之寶。」教授話出突然,似乎已留意到我的注視,我見生趣,笑着回應:「如此重貴,就只放在這裡?這算是三十六計其中一計策嗎?」
柳教授苦笑幾聲,仰望一眼,說着:「這件家寶,估計要有膽識之士才能目賞。」
我沒有再追問原因,只顯出一副尷尬的笑容,之所謂「尷尬」,明顯就是受到教授所講「膽識」兩字有關,雖然尋幽探秘,我也算是經驗老到,可是在沒有心理準備下,我承認也有一點心跳加快。
教授拉着一條在靠牆的麻繩,我沿着去看這條繩,是帶動着一組組的齒輪,逐漸轉動,組件原理,令懸吊的木板開始慢慢由上至下降落,這種不順暢的聲音,應聲刺耳,「畫面加上聲效」,成功把我雙臂的毛管都豎直起來。
當那塊木板差不多降到我的身高時,我緩緩退後讓它繼續,直至它滑到我的視綫,我不敢相信,放在上面,居然有一個躺着的人型被白布蓋住。現場除了剛才嘈耳的齒輪聲,就還有我的心跳聲,我瞄了教授一眼,但他沒有回望我,只一直看着板上的「東西」。
板木順利平放到地上,齒輪聲亦因此停下來,但我的心跳聲仍然如鑼鼓般響。我迫得不已大力吸了一口氣,好讓自己冷靜過來,效果算為有效,但是,教授接着又說:「先把布拉開吧。」
柳教授輕聲一笑,然後回我:「情況並非想像中。」
說到底,我也是好事之徒,我對着教授點點頭,繼至蹲下,一邊不由自主地用手掩鼻,一邊快速拉開白布。
結果,躺在我面前的,是一具呈墨綠偏紫色的男性屍首。
眼前的屍體,以腐化程度來看,出奇地完整,那種乾巴巴的表面,或許受過什麼特殊防腐也說不定。柳教授捲起衫袖,打量這屍體一會後,便向我說著:「別呆望著,先幫忙把它豎起來。」
說實話,我的接受能力已到頂了,而視覺神經亦早就達至飽和,現在還要再挑戰其他感官,確在情難以堪。我緩緩呼了一口氣,認真問津:「這位『前輩』就是柳氏的家傳之寶?借問典故由來?」
教授依舊沒有回我,只心急道:「要快一點著手,因為這傢伙不能沾有地氣。」他沒有解釋下去,便動起手來,而我只好硬著頭皮,幫他一把。
合二人之力,算是輕易。但看它的外面,沒想到會有一種濕綿綿的感覺,一想到這種手感,指尖就莫明其妙的震個不停。
雖然,它個子不高大,約莫只得一米六的高度,可是比想像中重,怪難教授也有一點氣喘。
我先不作聲,好讓教授回回氣來,而他歎息一聲,拍一拍它的肩膀,說著:「老朋友,我們很久沒見面了。」
從教授那雙婉惜的眼神,背後肯定有著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正如推測一樣,柳教授就向我說了一段小時候的經歷。
話說,柳氏家族為湘西著名經營趕屍生意,柳氏的趕屍技法,別樹一格,安全可靠;然而獨門技倆不傳外姓,只能世襲繼承。所以柳家每一男丁,都必須要學懂,避免流失真傳。
而家規說明,凡年滿十四歲的男丁,就都必須通過測試,但如果在十八歲之前,都未通過測試話,屬天資有別,無須受傳,但就必須留有一條小辮子以作識別,所以辮子算是柳家男丁的一個恥辱的記號。
那時,我看著柳教授的辮子,起初還以為是個人風格,殊不知,令是一個痛苦的回憶。
柳教授摸摸辮子,悠然一笑:「是的,這辮子由十四歲開始,就一直跟著我至今。」
「而令我不能通關的,就是這位『老朋友』。」他再次輕拍旁邊的屍體。
我驚訝追問:「這屍首就是一直用來測試柳家男丁的工具?這會否對此『先人』不敬?」
教授沉默一會,然後就忍不住偷笑一下:「我家的技法果然是鬼斧神工,實不相瞞,這傢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屍體,它這只是一件木雕製品。」
我徹底傻眼,暗覺好笑又生氣,當知道是一件仿真度極高的贗品,心情自然緩和不少。隨之,好奇心再次欲動,不禁近靠幾步,細看一番。
其實不管紋理以及形態,簡直與真正的無異,甚至乎,我在想,會否是教授存心騙我的藉口。
教授見我看得聚精會神,反而就提醒我要小心一點,雖然這傢伙是木制品,但由於經過柳家的「獨門秘方」,除了物質上,與真正不同之外,大概它已經練成與正常屍體本質無誤,還是生人勿近較安全。
聽到這番鬼神之說,我沒有質疑,所謂「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況且,柳氏貴為著名的趕屍家族,當中肯定有他「秘方」,才能獨佔鼇頭。而我的好奇神經亦早已啟動著。接下來,就繼續安心聽教授,逐述典故。
而柳氏男丁,就必須向這傢伙誠心念出獨門口訣,對它發號施令,方能透過測試;這時教授緬懷自語起來:
「兩眉閒三寸,神聚上丹田,氣呼五口換,雙眼敞開烱,意透鬼人間。」
這句就只柳氏的獨門口訣;教授又說,咒語用途甚廣,悟領高的話,甚至可以與靈界溝通。
那時,這傢伙果然向前跳了一步。害得柳教授嚇了一嚇,而我當然只是隨意的在內裡念了一念,教授驚訝追問著我,這情況,祠堂只得我倆,我根本不得不認,唯有尷尬點一點頭。
殊知,教授即時變得雙眼通紅,而眼眶的淚水,亦隨著眼角,傾倒而下,說著:「先父臨終時,就希望我能夠用上咒語,把這傢伙帶到後山的家墳,好好安葬,如今袁弟,有緣成事,還助完先父遺願。」說後頓時跪下來。
這種請求,我自問受不起來,現場畫面,也弄得我手足無措,唯有急快扶起教授:「晚輩不才,起來再說。」可是,此刻的教授已哭不成聲。
我明白,這遺願在他內心,肯定抑壓多年,如今終有機會釋懷出來,也算好事一樁;之不過,剛才的一跳,只是無心插柳,老實說,我繼續在心裡念出多一次咒語,但傢伙依然無動於衷,毫無反應。
這時,我正打算向教授說過明白,忽然,這傢伙有再次一跳,而且一步一步,朝著外面跳出去,而且還越跳越急,教授猶疑望我,當然非我所為,而教授立即收起傷感,緊張說著:「快追。」
那具木製的屍體,在沒受任何指令下,突然由祠堂裡跳了出去;而柳教授亦收拾悲傷心情,聯同我一起追上。我走過祠堂入口的時候,看到門檻旁邊有一束麻繩,下意識地覺得有必要「順手牽羊」,以作不時之用。
教授隨之登上一台腳踏車,並連聲叫我趕來就坐,我好不意思問起:「跑步應該比這個快捷。」但教授像有所應對,答著:「我們先跟著他就可以了。」
雖然我不明白箇中意思,但堂堂兩個男人坐在一台單薄得很的腳踏車上,難免有點古怪;然而以我年輕力壯,也不該由教授費力踩車,所以我倆快速調換位子後,緊貼追隨。
跟隨期間,我們發現到這傢伙,好像朝著某一方向走去,沿途中,教授就說起曾聽先父提過,如這木製的傢伙突然自發跳動,很可能是家墳出現問題。
我應聲追問:「即是說它具有靈性?」教授不能肯定,始終家族裡沒有深入提及,也從未發生過,不論如何,現在唯一就是要知道這傢伙的去向。
果然,這傢伙的確溜到柳氏家墳,便停了下來;這裡杳無人煙,加上陣陣陰風,更不時飄來陣陣霧氣,絕對媲美港式的僵屍電影。
柳教授拿出手機,開啟內置照明系統,細心檢查每一個墳墓,而我則在附近看看有沒其他可疑,就在此時,柳教授有所發現,隨即驚訝一叫:「手呀!」
深夜時分,傳來一聲驚叫,儘管膽量不小,也防不勝防地嚇了一跳,原來,教授那邊,居然發現有一墳頭的混凝土無故裂開,而且縫隙中伸出一隻手來。
我急忙前去會合教授,而他已經蹲在地上,已開始調查什麼似的。
「我認得手上的戒指,是家母…」教授沉住氣說著,與此同時,他亦好像在「母親的手」裡發現一些東西;原來是一張小字條,由於光源不足,很難細讀,所以我亦隨之拿出手機,補光一下,紙上寫著:「愛子坤洪,母親知孩兒從小喜歡當研究工作,但家規難違,為保洪兒夢想,愚母唯有私下下咒,令家寶(即木製屍)不受命令,以讓兒子通關敗北。只望兒子能導從志向。可惜換掉兒子的尊嚴,留下辮子記印,成同輩笑柄,使洪兒飽受恥辱;吾其死有不甘,決意臨終之時,重振家譽及孩子名聲,再向家寶下咒,如他朝家寶再能受令,引帶前來,留字揭真相。賤妾知罪,願等候不化土,一紙作證,求愛兒見諒,走出霾影,棄辱辮,重生活。」
柳教授得知真相,忍住落淚,搬出笑容,回先親一句:「娘,孩子沒未委屈,生活也好,請安心入土吧。」
此時,縫隙中的手緩緩向下,就好像聽到教授的心聲。至於一直站在不動的傢伙,也突然應聲倒地,或許,已完成任務,功德圓滿;教授亦為了圓先父遺願,也將把這「傢伙」安葬起來,從此長眠於此。
翌日,我隨團離開,與教授的經歷也告一段落。之後,我與教授也不時書信往來,交換蒐奇,樂趣無窮。
大約在一年後,無意看到柳教授的電視台訪問,主持人問到他辮子的典故,教授自豪回應是母親給他的一份禮物,主持人當然聽得糊裡糊塗,但知情的,例如我,就明白到這是一位慈母對愛兒的見證,回想起來,實在暖在心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