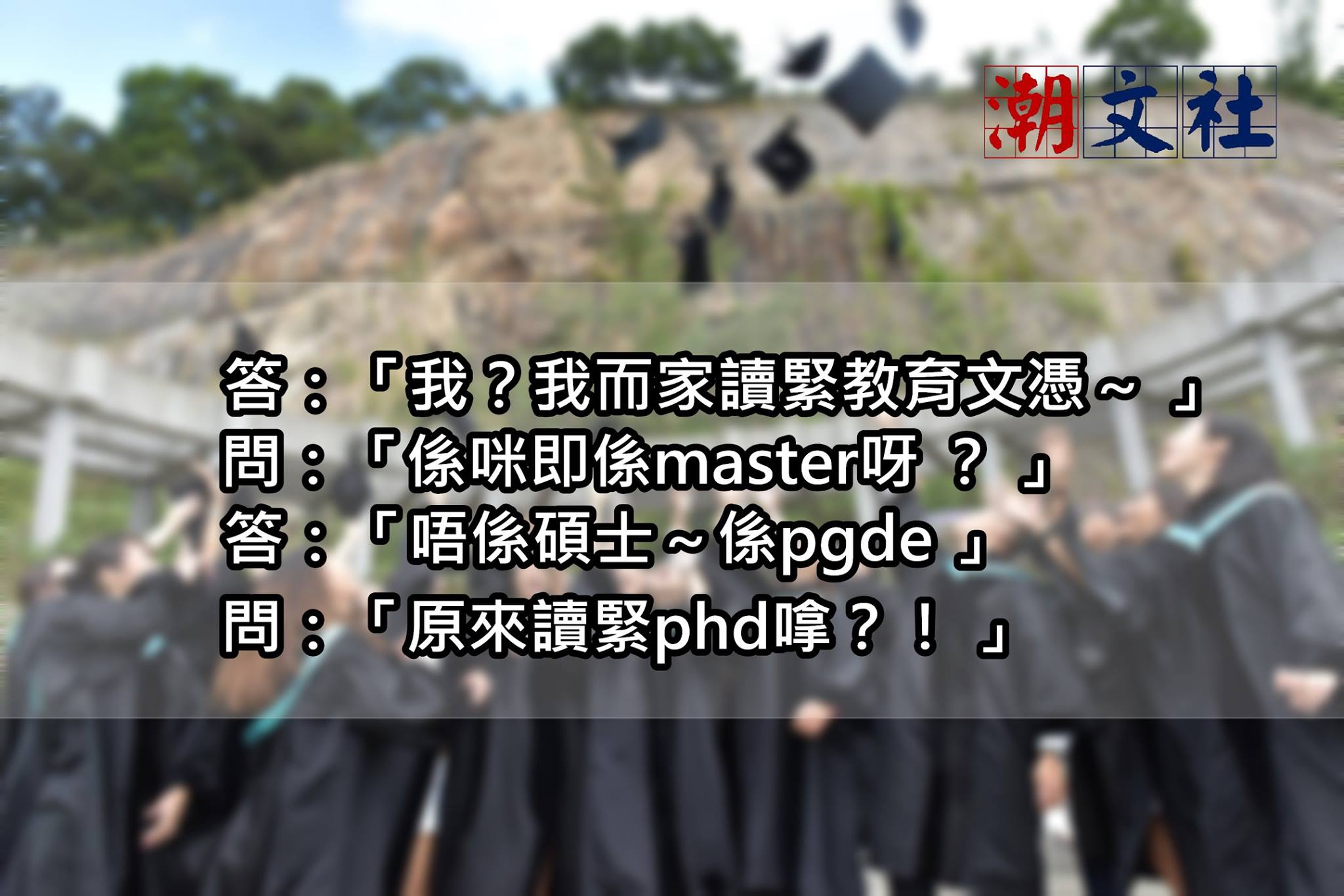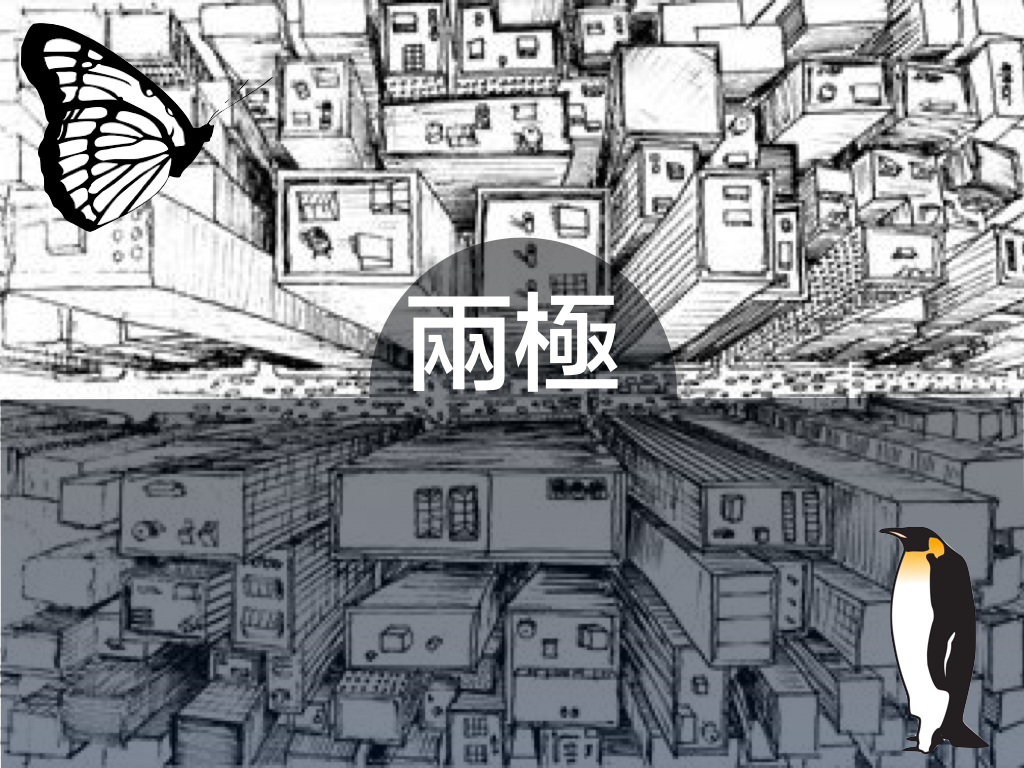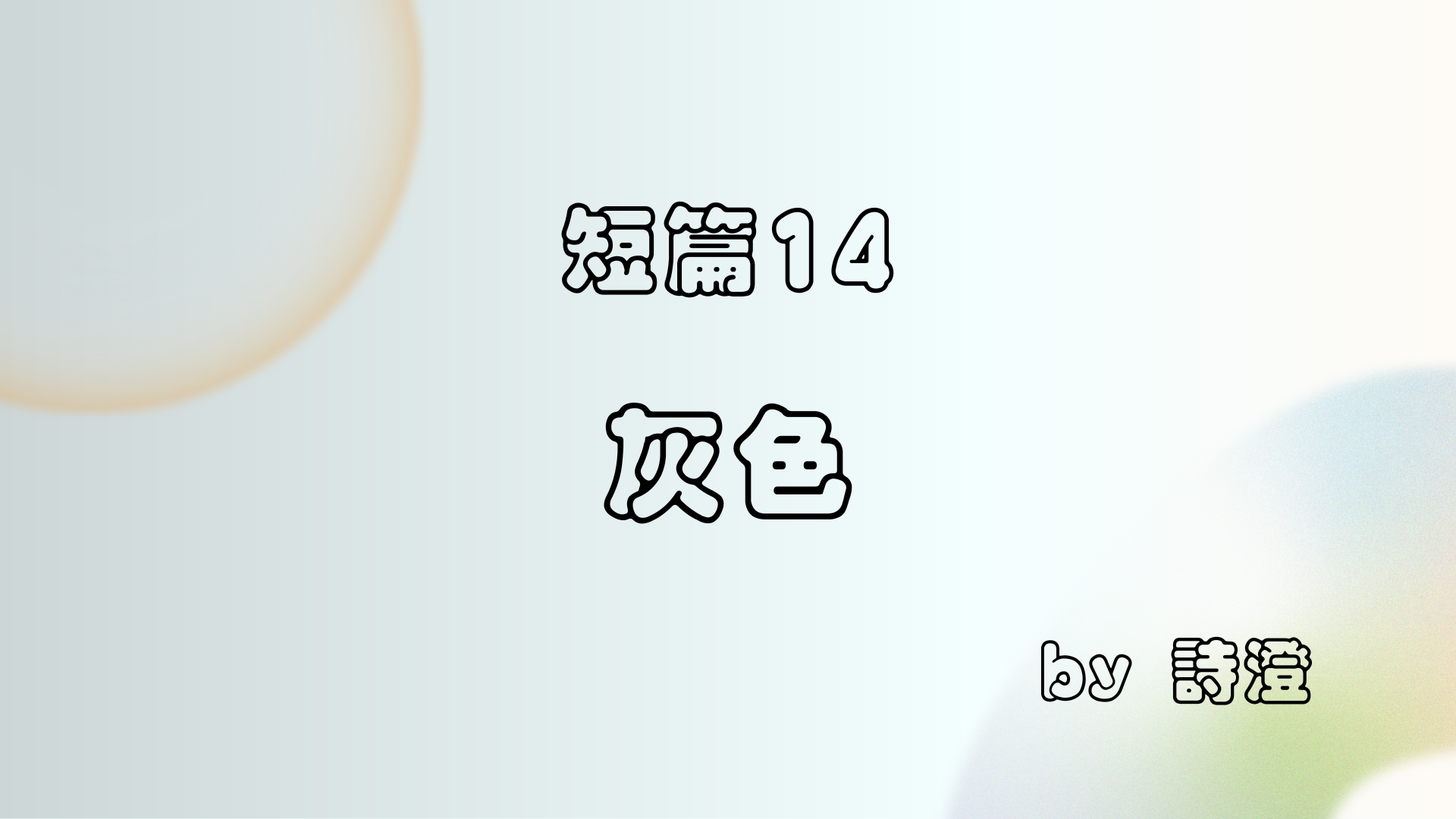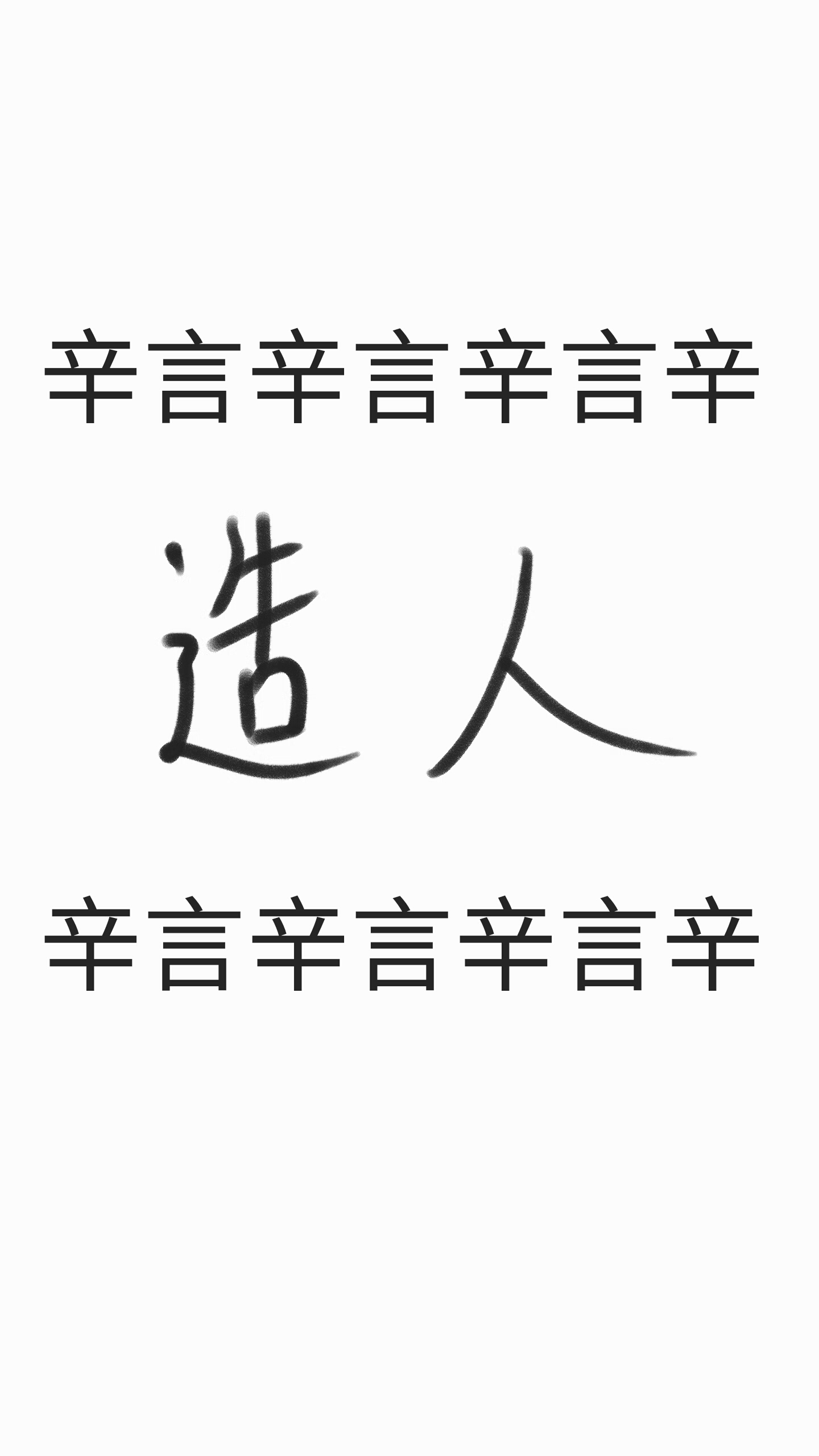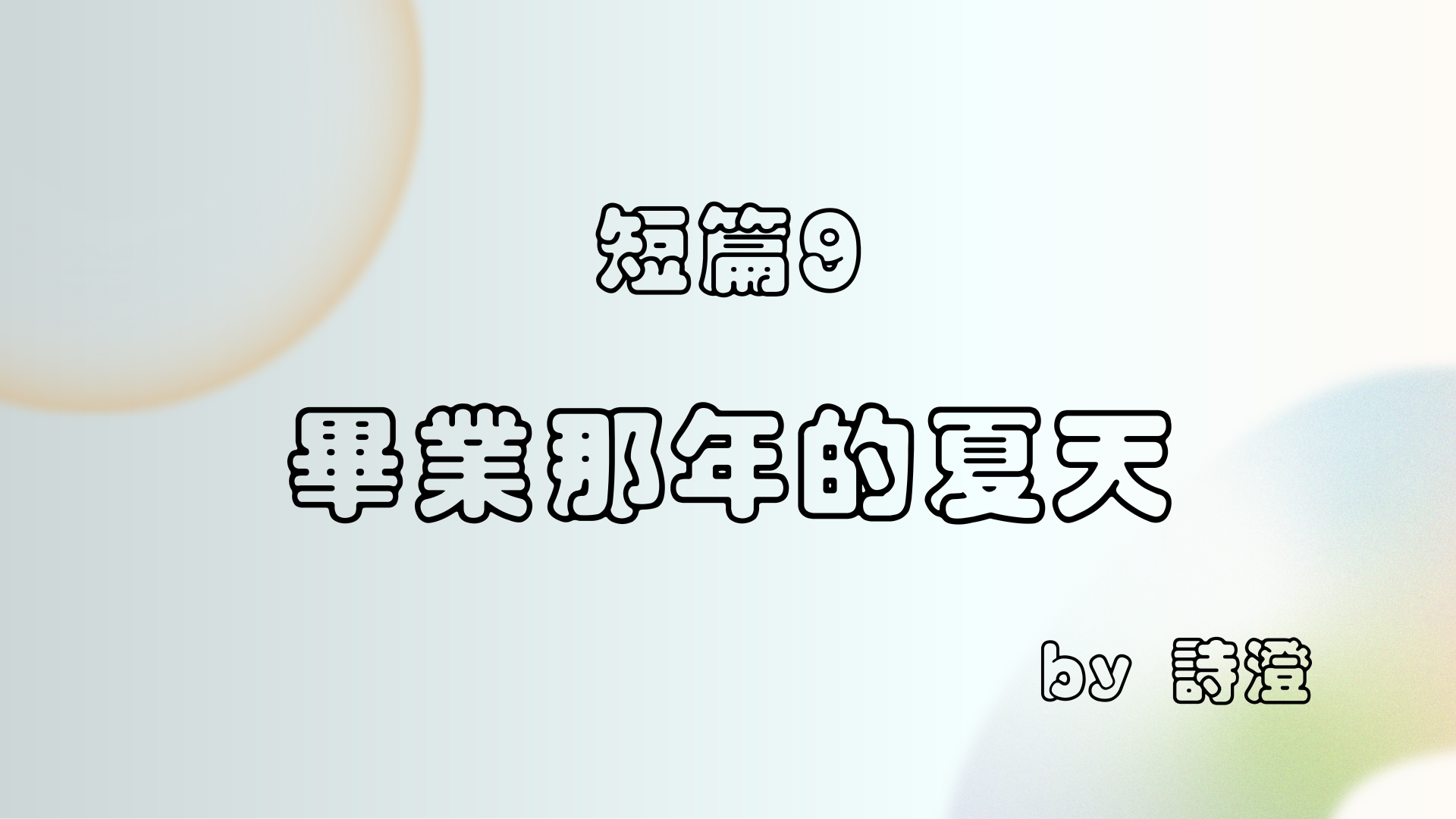下班,列車上,聽著陳奕迅的《浮誇》,心裡罵起七個髒話,但我知道這不能怪神,即便怪,也只可怪他唱得過份美麗,把一個又一個的高音飆得精準細緻,讓我聽出過多耳油,把左邊的耳筒浸壞了。最後,我只好故作若無其事,掛起單邊耳筒,抵著那只得一邊的享受,與我愛的廣東歌結伴走畢餘下的回家路。
家中,狹房內,翻箱倒籠找著那舊耳筒,終於讓我在一個塵封的NIKE鞋盒內找到了,它就平和地被綑在那個已不知何故珍藏起來的橙色乒乓球上,連忘把舊耳筒插進手機,檢查狀況,當黃貫中一曲《這是我姿勢》的結他前奏響起,這次我再按捺不了,呼天搶地般衝口拋出了一句「俾返個BEAT我!」,方想起,舊耳筒之所以淪為舊耳筒,是因它早在大半年前已失去了右邊的聲音。
看著手上的耳筒,想像到沒有它的明天會是如斯的難熬,我跌進了絕望的深淵中。生存在這紛擾都市裡,一對耳筒能把你隔絕所有不必要的溝通,擋過一切煩人的喧鬧,讓你隨時隨地搭建出私人空間,浸淫於靜謐的安全感中,而這自設空間你更可選用強勁的Hip Hop、撩人的K-Pop、迷幻的電音又或是憤慨的搖滾來建構,而我則只會選擇我愛的廣東歌。對於耳筒那份徹底的倚賴,我不懂怎樣具象化形容,或許,若然在街上,不幸遇上悍匪脅持,著我要留下耳筒還是內褲,我會選擇前者,應該會。
在惶恐與失落的交戰下,我從褲袋中抽出那左邊失聲的耳筒,凝視手上這一對傷痕纍纍的知己,突然靈光一閃,心中浮現出八大字:「一左一右,仲有得救!」
當然,對於一個既怕麻煩且沒能耐的獨男而言,若想要它們結合起來,絕對是天方夜譚,所以,我只是再次的翻箱倒籠,從那塵封的NIKE鞋盒內找出一部舊手機來,然後把現用手機內的歌曲播放清單一式一樣的抄進舊手機內,接著,每部手機分別插上耳筒,雙耳掛上完好的一左一右,再從兩部手機中同步按下播放放鍵,奇妙的事發生了,阿Paul的《紅黑紅紅黑》奏起,沸騰的結他聲順暢地左右急竄,澎湃的節奏縈迴耳際,而阿Paul那略帶沙啞的歌聲則分別沿著兩條獨立的耳筒線向左走向右走,最後穿透雙耳的鼓膜,匯合到意識中:「就係咁簡單。」
接下來的六天,每每出外,我就如攜著雙槍的西部牛仔般,左右褲袋各插著一支手機,拉出四個耳筒,再把兩個掛上耳邊,合拍性地按下播放鍵,重建出我的私人空間。而這雙機播歌法更讓我發掘出個玩意來,在個多小時的車程裡,我試著自行混音,左邊一曲右邊另一曲,一次過滿足兩個願望,胡亂的混搭著,讓我無意間發現偉大的廣東歌大多有著類似的曲式旋律,組合起來,往往很容易便能混出首首不大礙耳的新曲,感覺新鮮。
下班,列車上,雙手忙於嘗試歌曲的配對,這次我左手選了麥浚龍跟莫文蔚的《瑕疵》,右手則從選單中滑至李克勤與容祖兒的《世界真細小》,貪婪地嘗試來個磅礴的四聲大合唱,然後,我後悔了。當兩曲雙雙進入激昂的副歌時,兩耳分別傳來男女重疊的澎湃歌聲,剛與柔,左與右,不住交替,是一片無止盡的喋喋不休,突然,一陣壓倒性的寧靜把雄渾有力的節奏打斷,耳根先是落得前所未有的清靜,慢慢地,周遭環境的人聲車聲風聲經由耳筒邊細密的狹縫鑽進耳內,我開始聽到身旁一對婦人的對話,僅餘的兩雙耳筒宣告壽終正寢。
然而,我並沒有把耳筒脫下,決定就這樣,任由不再發聲的耳筒掛在耳邊,伴著它們走這最後一程。回到家,我把它們綑在一起,拍下一張黑白照,然後,為左邊的舊耳筒倒了一小杯珍藏已久的單一純麥威士忌,又為右邊那剛撤手人寰的耳筒泡了一杯沸騰的單品咖啡,藉以向它們這些年頭為我播過無數的廣東歌致敬。
順滑馥郁且易於入口的單一威士忌,暖和了心頭,香濃回甘的單品咖啡,則為心添上絲絲苦澀,一酒一啡,單調而珍貴,混出了最錯綜複雜的情感。喝罷,我珍而重之地拿起兩對纏在一起的耳筒,把它們放回那NIKE鞋盒內。然後,便開始擔憂著,明天,沒有歌,怎敢說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