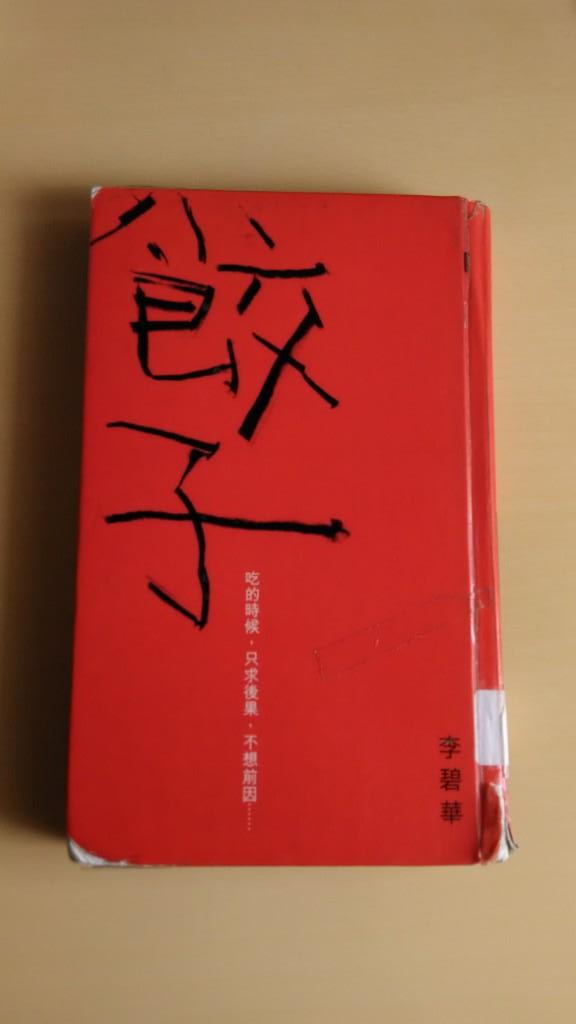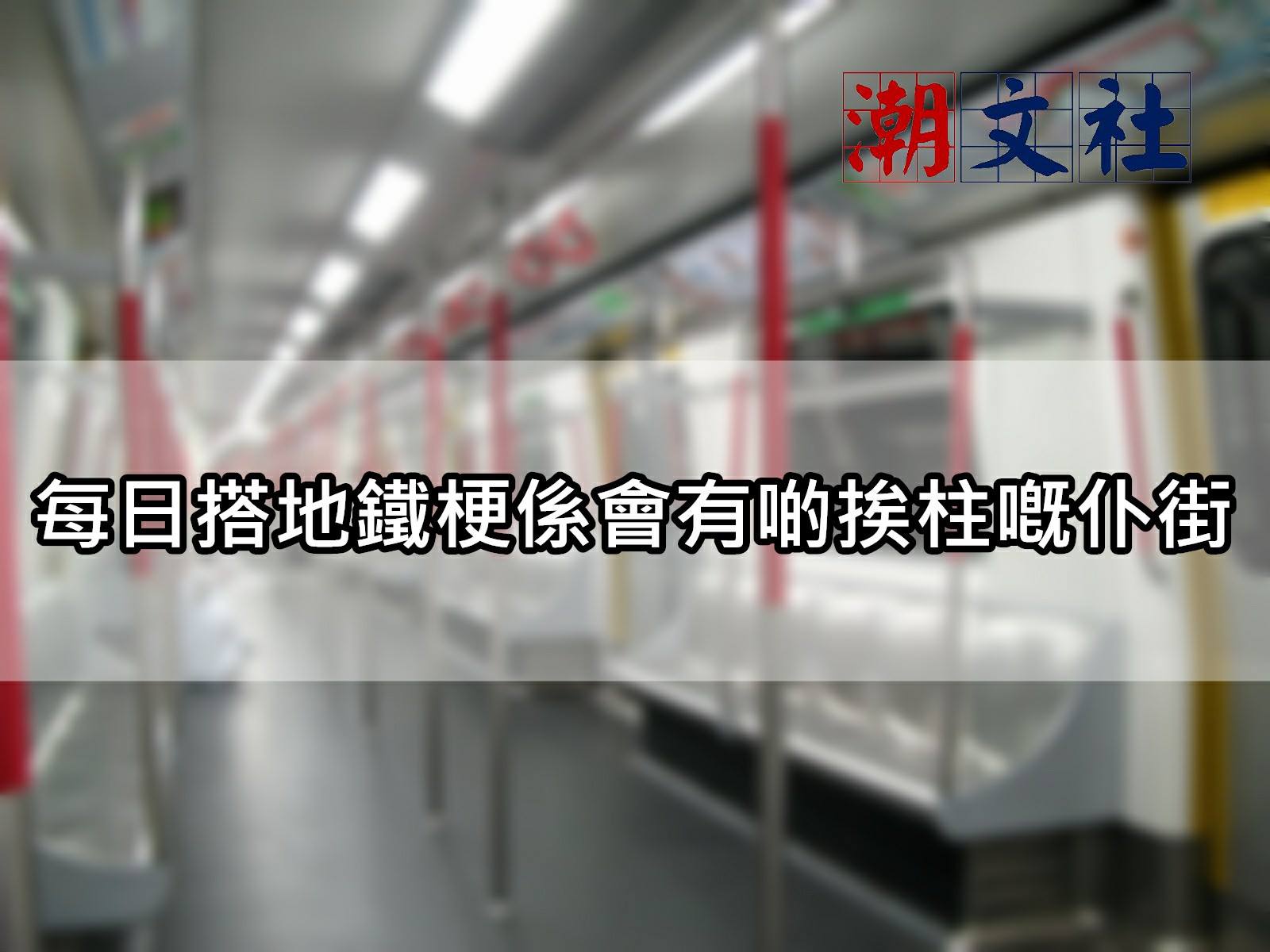二零一六年五月,西環的午後悶熱得像一場退不掉的高燒。德輔道西一帶充斥著鹹魚乾與老舊海味店混合的腥燥氣息。黃信陵扯了扯那條洗得略顯發白卻依然平整的藏青色領帶。身為司法機構的助理執達主任,他深知在這種老舊唐樓執行任務,形象就是法治的最後一道防線。他從西裝長褲口袋掏出那部屏幕已有裂紋的手機,按亮。
兩點二十八分。
阿信不愛戴手錶,皮膚上多出一層金屬壓迫感只會提醒他時間正無情流逝。何況,他那雙視力達1.5的眼睛,即便在光線昏暗的唐樓後樓梯,也能清晰捕捉到法律文書最末端的細則。
「黃生,差人到咗。」隨行的收樓外判領班阿強指了指後方。兩名軍裝警員按例隨行。這類針對武館的清盤案,警署通常派兩個體格魁梧的人員。阿信點點頭,領頭踏入這棟外牆剝落的唐六樓。
「六合體育會」的門戶是一對厚重的坤甸木大門,門楣上掛著「精武魂」橫匾。武館採前舖後居式間隔:前廳約四百呎,正中供奉關帝,兩側擺放兵器架與練功木樁;前廳後方有一道屏風,屏風後則是館主的起居內室。此時,前廳站著四名神色不善的壯漢,雖然穿著武館汗衫,但那種站沒站相、眼神閃縮的模樣,阿信一看便知是臨時找來「撐場」的臨時演員。真正練拳的人,下盤不會浮成那樣。
館主趙國強年近六十,腰間紮著褪色紅綢帶,正對著關帝像上香。兩名警員與三名外判工人呈半圓形散開,站在大門處警戒。
「趙國強先生。」阿信拿出證件,語速如機關槍般穩定,「我係執達主任黃信陵。根據法庭判令,今日我會對呢處物業進行查封。如果你對債務有異議,麻煩你同你個律師講,我份糧唔包聽你訴苦。依家,請無關人等即刻離開。」
「黃主任,你哋唔使咁盡下話?」趙國強回頭,眼神裡透著困獸般的瘋狂,「我喺呢度四十幾年……」
「趙生,如果你守法嘅程度有你守舊咁堅持,我諗你今日應該係去緊匯豐收息,而唔係喺度等我貼封條。」阿信毫不留情地切斷對方的感性攻勢,「大家都係搵食,你唔好難為我,我亦唔想搞到你上電視。依家清場。」趙國強突然冷笑一聲,指了指屏風後的內室,「黃主任,我老婆啲遺物同珠寶清單喺入面。你入去點清楚,費事轉頭話我老屈你哋手腳唔乾淨。」警員正要跟進,阿信擺了擺手。他知道這類老派武人最重「密室談判」,若在警員面前硬闖,這幾個臨時演員一旦激動起來,場面就會失控。他將手機收好,踏入內室。
內室僅百來呎,四壁堆滿木箱,只有一盞昏黃的吊燈。阿信剛跨入,趙國強猛地轉身,右手一拉,沉重的木門栓「喀嚓」一聲鎖死,將警員的喝止聲隔絕在外。「黃主任,你叫佢哋走,如果唔係我今日同你一齊交代喺度!」趙國強身形下沉,一記六合拳的「斜行撩手」蓄勢待發。
「趙生,襲擊公職人員加非法禁錮,刑期夠你老人家坐到全港都換晒電動車。」阿信背著手,眼神冷得像冰,「你話間武館係你老婆留低最後嘅嘢?佢如果見到你用佢個名嚟犯法,佢可能會後悔當年無揀隔壁街個賣菜強,起碼人哋輸咗份糧唔會輸埋人格。」
「你找死!」趙國強怒吼,腳步一蹬,「進步衝拳」直取阿信中路。阿信眼神一凝,並未後退。在西裝襯衫的包裹下,他的肌肉如緊繃的弓弦。當重拳迫近胸口一吋時,阿信左手化掌為「掤」,使出一招太極散手的「攬雀尾」。他並非硬碰,而是以掌緣貼住對方前臂,身形微側,腰胯一轉。趙國強那股足以打碎木板的衝力,被阿信這記旋轉的勁力輕巧地帶偏。緊接著,阿信右手如蛇信,順著對方的力道「捋」下,左腳踏入趙國強的襠中,一記「搬攔揰」以肩膊為撞擊點,精準撞在趙國強失去重心的胸口。
趙國強悶哼一聲,整個人被這股綿密的橫勁撞得倒退,後背重重撞在兵器架上。紅纓槍亂顫,發出刺耳的鳴響。「六合拳講究『內三合、外三合』,你氣浮於上,力散於外,除咗嚇親啲細路之外,連隻雞都打唔死。」阿信步法緊隨,不給對方喘息機會。趙國強老羞成怒,雙手變掌為爪,試圖抓取阿信手腕。阿信冷哼一聲,使出「肘底揰」。他右手下沉,左肘由下而上斜斜切入,正中趙國強的腋下神經叢,力道收在皮肉之下。
趙國強半邊身子瞬間發麻,動彈不得。阿信反手一扣,將這位館主死死鎖在牆邊。「趙生,你話想守住老婆啲嘢?你依家喺度同我玩摔角,外面班後生仔就喺度諗緊點樣趁亂偷走你關公像前面嗰對銅燭台。」阿信湊近他的耳邊,語速飛快,「你請嗰班『弟子』,收咗錢就係戲子,你一坐監,佢哋就係老鼠。你保住間武館幾十年,最後就係想將佢變成一個笑話?」趙國強頹然垂手,那股不甘的氣勢徹底散掉,「佢走咗五年……我連佢最後呢間屋都保唔住……」
「五年?你算好命啦。」阿信鬆開手,開始冷言冷語,「我老婆走咗五年,我連間屋個房契係邊個名都未有時間搞。你要守嘅係個『名』,唔係呢幾塊發霉嘅磚頭。你依家乖乖出去簽名,起碼仲可以留返個宗師嘅款,如果你想試下警署啲飯盒係咪好食過大快活,我可以成全你。」阿信掃視四周,看見兵器架縫隙處掉落一個殘舊的紅絲絨盒。他低頭,快速撿起。裡面是一枚磨得發亮的金戒指。
他背對著木門,趁外面的人還在拍門,壓低聲音:「趙生,我個名單入面,無記載呢件動產。我份人好懶,唔想寫多份證物報失報告。如果你有啲『完全無拍賣價值』嘅私人垃圾,最好依家就塞入你個褲袋。」趙國強愣住了,看著黃信陵那隻指骨分明的手。戒指遞到了他眼前。
「……點解幫我?」
「幫你?你諗多咗。」阿信重新擺出那副債權人的死魚臉,「我係唔想因為你呢粒垃圾戒指,搞到我五點鐘收唔到工。我仲要返去服侍另一個小祖宗。趙生,你啲戲好屎,下次要威脅人,記得搵個無負債嘅人,我呢種人連命都賣咗畀銀行,你憑咩同我鬥?」阿信轉身,拉開木門。外面的警員差點衝了進來。
「無事,入面太焗,趙生血壓高暈一暈,依家清醒返。阿強,入嚟搬嘢!」查封工作進行了四個小時。黃信陵看著封條一張張貼在牌匾上。他面無表情地記錄進度,直到夕陽將西環的街頭染紅。
走出唐樓,汗水浸透了背後的襯衫。他拿出手機,屏幕牆紙是一個小女孩背著校服包懶床的照片,背景隱約能見到一個雜亂的龜缸。
五點零三分。
「阿信,收工未?澄澄話想食麥炸雞,你唔好又去買涼茶。」短訊來自「阿珊」。阿信看著屏幕,嘴角抽動了一下,像是想罵人,卻又露出一個疲憊的弧度。
「買麥炸雞?你以為你理財概念好過我?食完熱氣又要我煲涼茶,你真係當我係開藥材舖。」他自言自語地碎念,卻快速回覆了一個「OK」的符號。他大步走向地鐵站。在法理與人情之間,他今天找到了一道縫隙。雖然他依然是那個在現實中掙扎的社畜,但在那個昏暗的武館裡,他短暫地變回了那個四歲就在父親掌下練習推手的武者。
法律是冷的,但指尖觸碰過的那枚戒指,餘溫猶在。
【字數統計:2,965字】
【編輯吐槽】
趙館主真的選錯了對象。要脅持一個每天被銀行本金、利息和女兒學費追著跑的「極致社畜」,難度比對付警察還高。畢竟對阿信來說,坐牢可能比還房貸輕鬆,這種「無慾則剛」的毒舌邏輯非常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