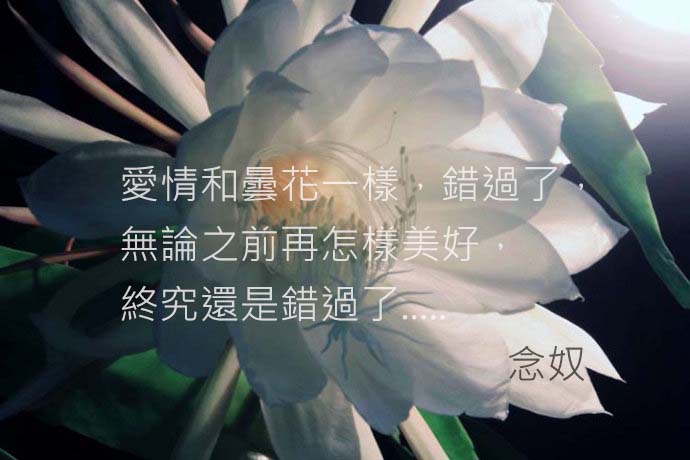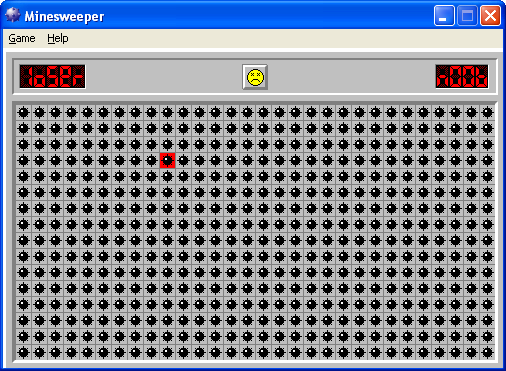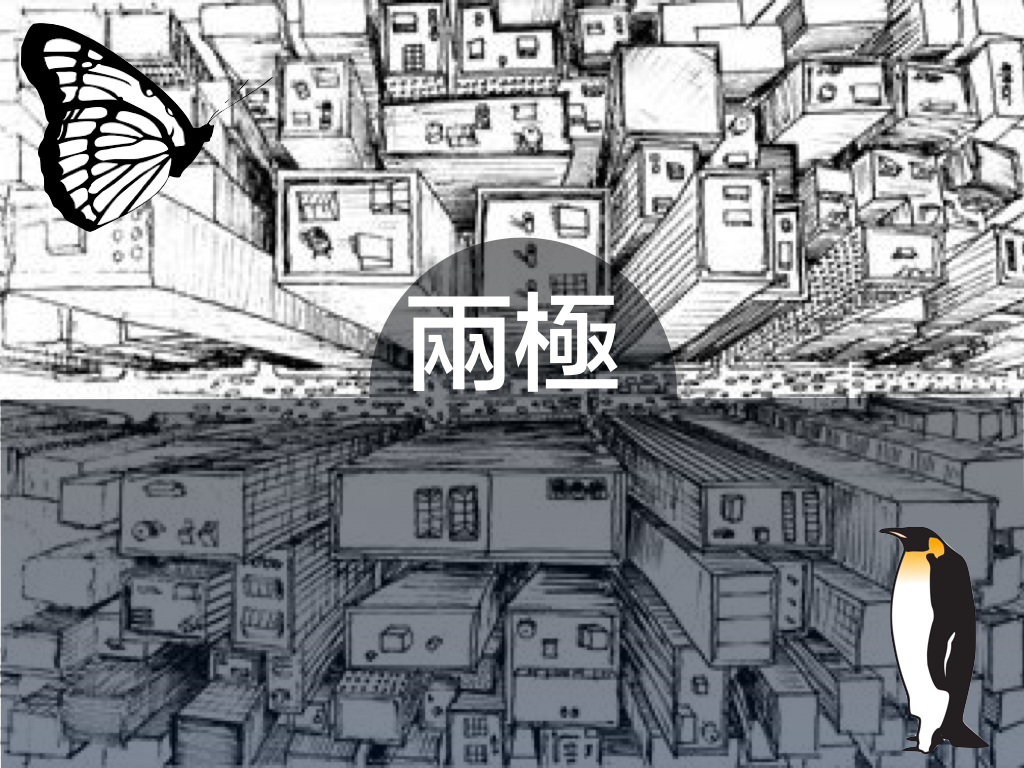三月,正值步入明媚之春,他,順著心的引領,走到泳池邊,二話不說的便躍身跳進池中,然後,整個人便一直的藏於水底內,久久沒有把頭仰出水面,於氧氣欠奉的水中,憋著氣的抵受著水底中那份叫天不應,喊地不聞的靜謐。
就這樣,整個泳池,自他跳進水中的那一刻,便再沒有任何動靜,只有一股幾近時間停頓,映象定格般的死寂,莫說浪花,就連丁點柔和的漣漪也沒有。他,雖談不上享受,卻未及抗拒,只因在這獨佔的泳池中,他仍有一定的控制或選擇權,靜了,便踢出一腳浪花,悶了,便撥來兩片漩窩,累了,便定下來全然浸泡於水的流動中。在這裡,唯一的法則,就是他終究不能把頭浮於水面。
七月,仲夏伊始,她,順著心的律動,走到一房子內,二話不說便把內裡的所有門窗都緊緊鎖上,然後,便抱著一副世界與我再不相干的態度,匿藏其中,於這與外間隔絕的空間內,伴著心的紊亂與思想的迷惘,享受著那份自製的安寧。
就這樣,整個房子,在她的進駐後,便再沒有任何的動靜,確切點說,是再沒有任何對外的動靜。她,全然的感受著這份近乎絕對的自在,沒任何磯絆,無丁點枷鎖,靜了,便到琴前奏出段段樂章;悶了,便在爐頭前弄廚為樂;累了,便倚著床前翻開書本隨意的看兩頁直至安然酣睡。在這裡,唯一的法則,就是她終究未能擺脫由情緒牽動周遭氣旋所產生出的壓力,那是一股惶恐房子門窗有天終要被再度打開的憂慮,一份對外未知的憂慮。
泳池,就置於房子前端的不遠處;
他倆,就平行地生活著或生存著。
一天,他得到了驚世發現,就是每每當他奮力在池中游泳時,整個泳池都會向房子移近一點。得悉這現象後,他便開始在池中拼命地游,渴望一天能把泳游挪置房子旁,為的就只是能清晰點聽到那偶爾從房子裡奏鳴出的琴音。
日復日,泳池與房子拉近了,但,還是隔下了七步的距離,勿論他怎樣努力的在水中划腳撥手,終無法再讓泳池前行,這七步之遙,既近且遠。
他,急於為所謂的將來打拼
她,樂於享受當刻最後恬靜
七步,能撰出一闕後現代唯美情詩,
七步,卻總離不開二人的潛藏自私。
九月,夏末秋至,泳池中的他無力再游下去了,漸漸,放棄的念頭縈繞腦際,心裡不住迴響出句句教人洩氣的魔鬼告誡:
累了,就這樣算了
算了,無力更好了
好了,滿足不夠了
夠了,真的夠累了。
隨著池水對身體造成的搖晃及至心房,他始被動搖了,於是,用上最後的一股勁兒,撥開前方的水,讓身子往前一步,手指觸及池邊,冀盼作出最後的嘗試能修得正果,但,泳池依舊絲毫不動,倏地,他那將近半年沒仰於水面外的雙眸,不知怎地,溢出了淚水來,無聲的沿著臉頰流淌,然後,與那堆帶著氯的池水混和了,無聲也無息地。
他,只想好好的唞一口氣。
*credit: displayed photo is a painting from David Hockney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