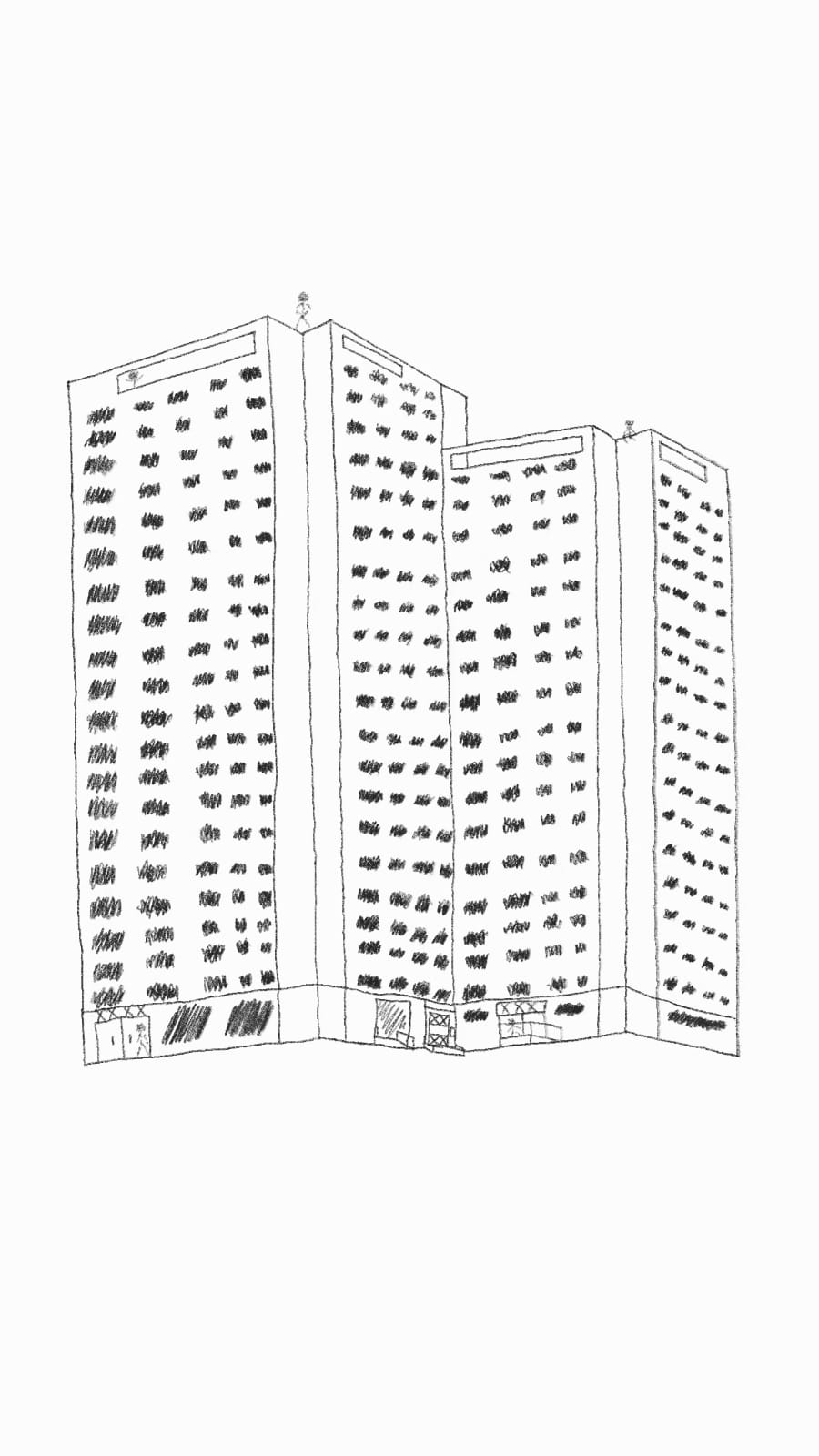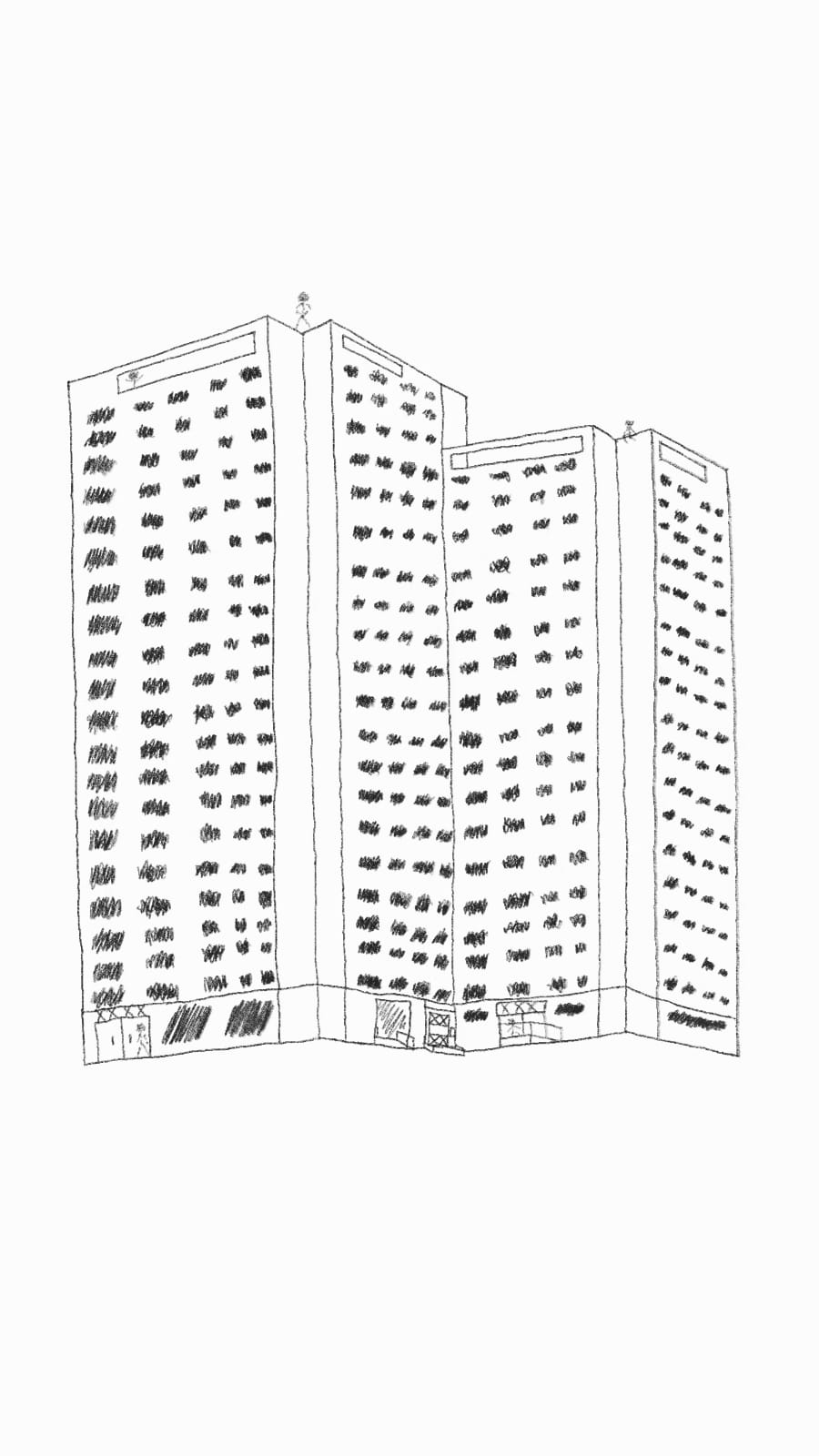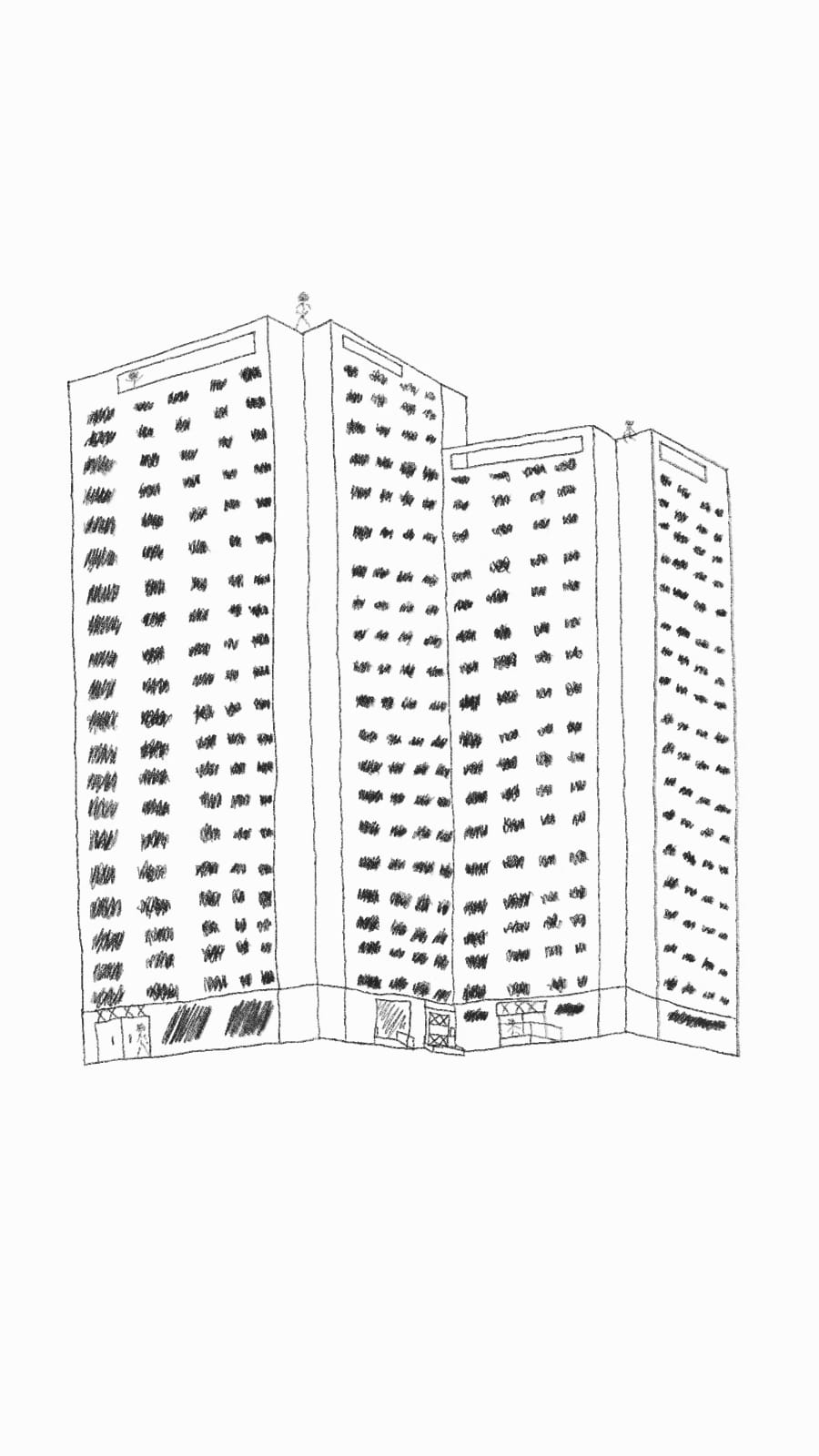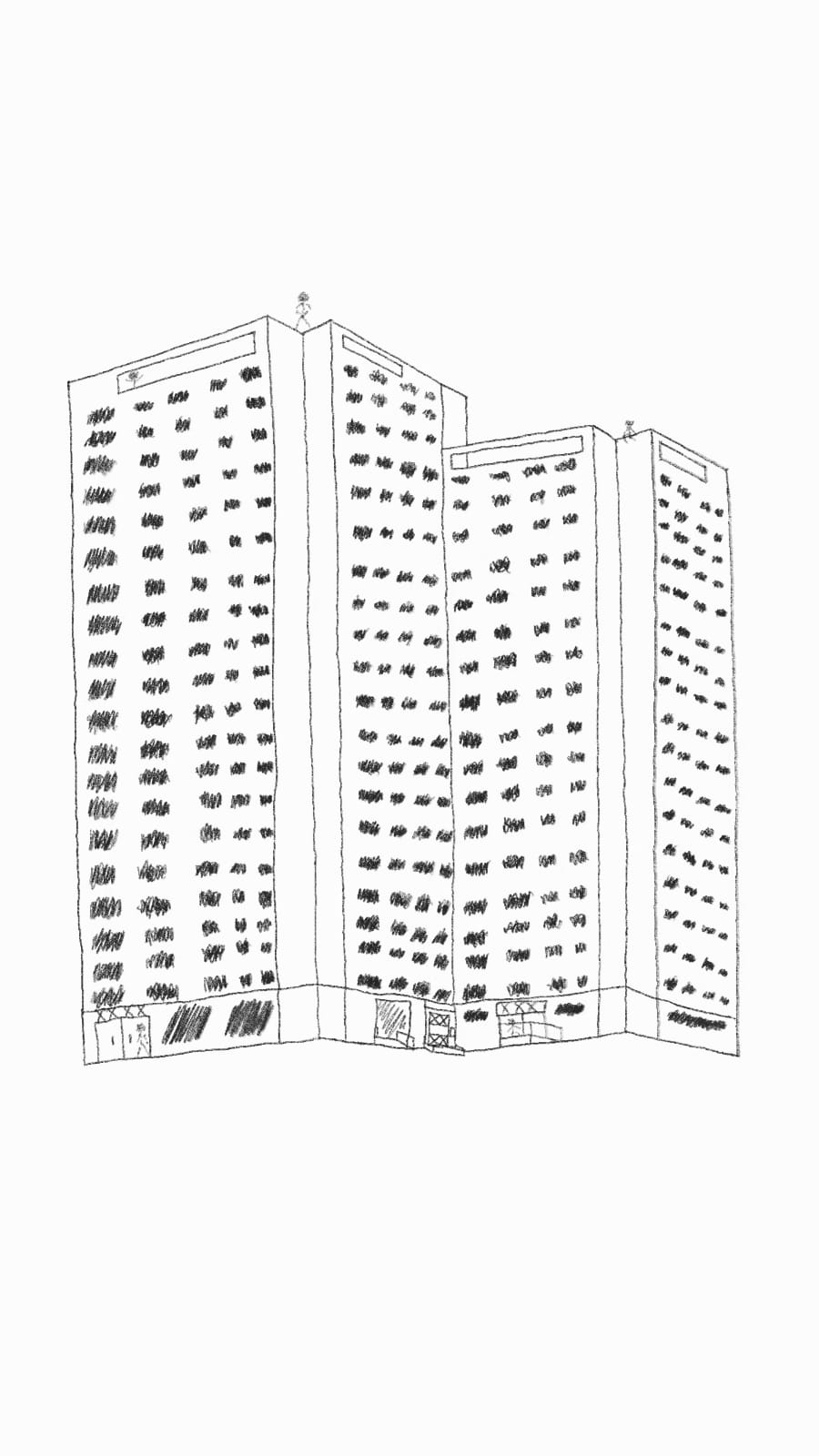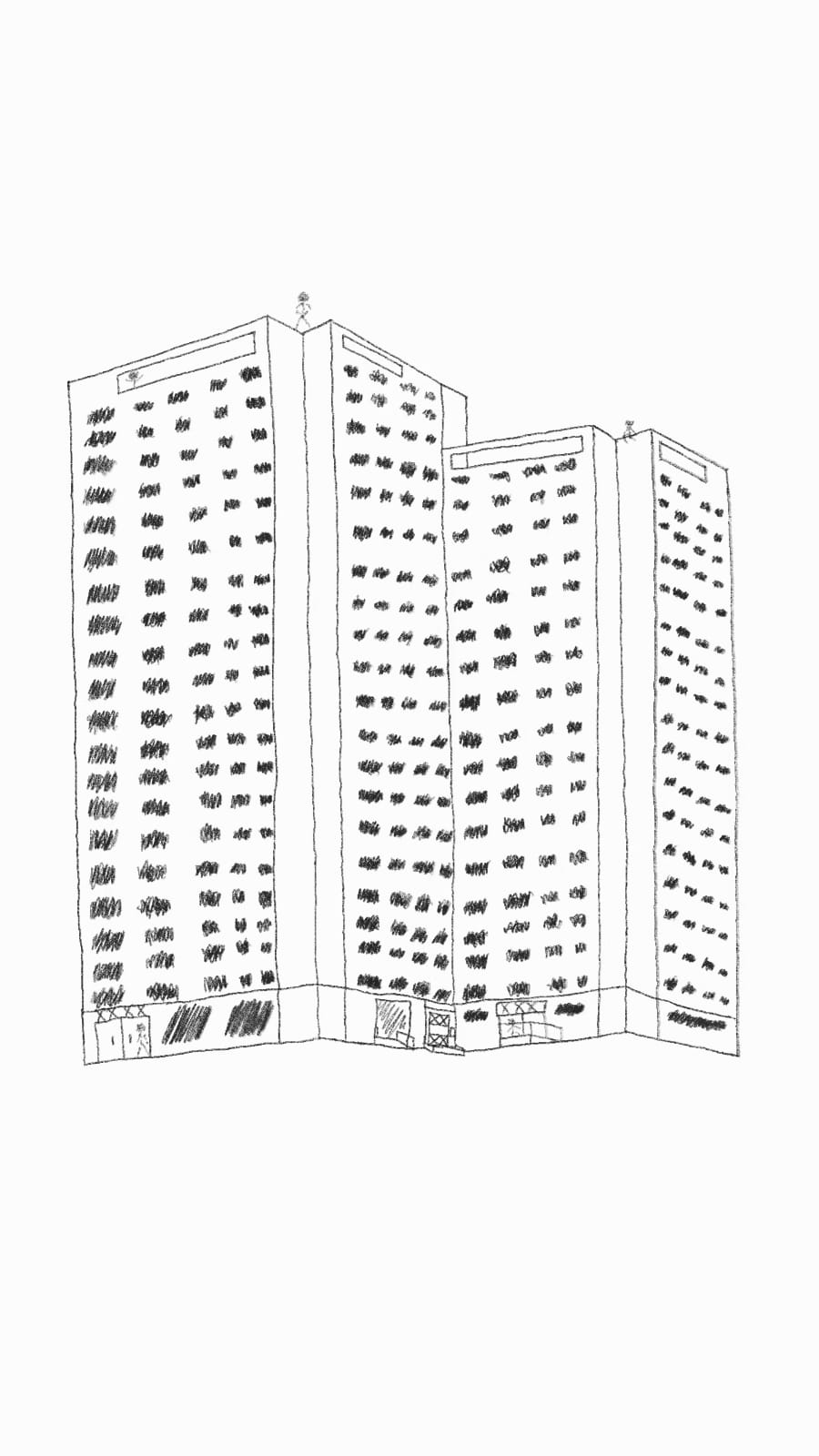蔡明恩是一名孤女,十八歲那年找到工作後便從孤兒院搬到北角。房子很小很舊,但總算是自己一片天地。
十八歲的她有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戀愛,第一次失戀。
還有第一次聽見別人腦裡想的東西。她對這新的感覺有點害怕,所以沒有告訴任何人。
她在中環的議員辦工室當秘書,工作很繁忙,每天都很晚下班。今天星期五也不例外,她打好文件後正想回家,見老闆不斷朝她這邊看。明恩感應到「逃」不了,低聲對自己說:「去暍杯酒嗎?」
老闆順了順筆挺的西裝,來到她桌前, 道:「去暍杯酒嗎?」
他們一起行到蘭貴坊的一間酒吧。老闆幾乎每個星期五下班後都找她去暍酒,講一些她年紀都聽不懂的話題。
感應力常令明恩很不自在,好像今天,他們在酒吧坐下才一盞茶的時間,四方八面的腦電波已紛然襲來。
「四十二吋美腿,正!」右邊幾名青年邊暍咖啡,邊定睛朝這邊看。
「雪白的肌膚像牛奶!」後面一個中年漢老實不客氣地盯著明恩吊帶裙下露出的背。 明恩心中發毛,真想起身罵他一頓:「沒見過女人嗎!」
「這老頭子可以當她爸了!」一個女人瞟他們一眼。
午夜,老闆開平治送明恩回家。她在大廈門口回頭時老闆仍站在車旁目送她。
夜裡,她又夢見家雄。早上醒來時滿臉淚水,頭痛欲爆裂。這半年她常頭痛,看了幾次醫生,都說她可能工作太累。
家雄曾和她訂婚,但後來卻分手了。她對自己說,也許一生再找不到深愛的人。
她沖了杯咖啡,打開電視,看了一會後掩面驚叫:「天啊!」
午間新聞:今晨七時,李輝議員從住所四十樓墮下身亡,遺下母親,妻子和兒子三人。李議員一生為國為民,本台上下員工向他的家人表示深切慰問。
晚上,明恩和其他同事應警方要求到警局記錄口供。
「議員不可能自殺的。他昨天才訂了蛋糕,預備和母親慶祝生日。」明恩對短髮的警官說。
「妳怎麼知道?」
「我是他祕書嘛。」明恩略猶豫道。其實她是從感應知曉的。
「今早一時到八時,妳在哪裡?」
「在家睡覺。」
「有時間證人嗎?」
「我一個人住,你知道的。」
「妳和議員每星期五都去喝酒嗎?」
「對。」
「你們有性關係嗎?」
明恩再也按捺不住,哇一聲眼淚奪眶而出:「家雄,我是這樣的人嗎?」
家雄警官喜怒不形於色,道:「謝謝妳和警方合作。妳可以回家了。」
家雄是這案件的領隊。他回指揮室再看黑板上的資料,腦內重組案情。半年內第三宗離奇「自殺」案,表面毫無疑點。第一宗是史密夫教授年初在西貢行山時跳崖身亡,跟著富商陳福健在中環國金墮樓,他的員工還聽到他跳下去前大呼:「都是我的錯。我不是好人,不是。」。李議員五歲的兒子很早起床。他說爸爸跳出陽台前曾喃喃哭到:「我是壞人,我是壞人。」
其他隊員都嘆道,這城市的壓力太大了,很多人患了情緒病也不知道。
但壓力大也不是今年才有的事情,家雄心道。
他打開電腦重看議員家附近的交通監察錄影帶,希望找到新的線索。不知不覺,天色發白,已是次日五點。家雄突然趨近螢幕,倒抽了一口涼氣。
明恩心情很低落,整晚沒睡。每次想到老闆,忍不住下淚。
天台曬衣架上的衣服在微弱的晨光下隨風飄揚。明恩站在天台邊,張開雙臂,俯瞰街上如螞蟻的車輛。老闆就是這樣跳進空氣中嗎?她想。 沒可能的,他是那麼樂觀的人。
「生存比死需要更大勇氣。」一把男聲從後傳來。
明恩回頭,見家雄剛站在她右邊,望著天空出神。
「你也睡不著?」明恩道。
「我記得妳說過妳有個雙生的姊姊的。妳有她的消息嗎?」
「都失散了那麼多年。為什突然問起她?」
家雄從袋裡拿出三張照片遞給明恩,道:「我剛從交通監察錄影帶發現的。」
第一張印著「2014-1-28 7am 西貢公車站」,第二張「2014-5-12 6:50am 國金入口」,最後一張「2014-9-1 7:05am 跑馬地議員家對面的711」。照片明顯用電腦放大過,有些矇矓,但三張照片中都有一個頭戴白帽的少女,看上去有九成像明恩。
「我沒去過這些地方呀!」明恩訝異地說。
「我相信妳,所以並沒有告知我上司。」
「那不怕影嚮你的事業嗎!」明恩語帶諷刺說。
家雄低頭不語,然後道:「現在最重要是要找到這女子,然後了解她為何會出現在這三個地方。」
「瑪利亞修女可能幫到我們。」
他們吃過早餐後,便馬上開車去孤兒院。
修女一見到明恩,便一把擁抱著她,道:「My dear,我聽到你老闆的事,妳一定很傷心。」
明恩講述詳情後,修女便答道:「我沒有見過妳姊姊明詩,但你們可以問問劉大賢醫生。」
「他是誰呢?」明恩問。
「英國腦外科最權威的教授。」家雄說。
「小恩,其實妳也認識他呢。他就是鬍子叔叔。他剛巧叫我通知妳,說下星期會來香港開會,想跟我們吃飯,到時妳便可親自問他了。」修女道。
「啊!太好了。」明恩大叫一聲,雙目發出喜悅的光芒。鬍子叔叔就是每年都寄聖誕禮物給她的助養人。
回市區時,家雄邊開車邊說:「假設妳姊姊和這案件真的有關係,那究竟受害者有什麼連繫呢?一個醫生,一個商人,一個議員。且慢!」他把車草草泊在一旁,然後拿出手提電腦看了一會。
「妳的鬍子叔叔有危險。」
明恩面色一沉。家雄把螢幕給她看,續道:「史密夫教授,陳福健和李議員二十年前都是腦外科醫生,是當年替妳和妳姊姊做切割手術的四位醫生其中三位。而第四位就是劉大賢!」
家雄的上司覺得自殺案便是自殺案,無須浪費警力,但家雄堅持親自保護劉大賢。
劉大賢抵港的前一晚,明恩既驚且喜,整晚睡得不好。
深夜,電話鈴聲響起。明恩摸黑拿起聽筒。
「喂。」
「阿妹,你們不要再跟姊作對。」
「姐姐,真是妳嗎?我好想妳。這麼多年妳在哪?」
「多得這些臭男人,令我們分開了十六年。他們都該死!」
「姐,妳不要嚇我。家雄說他們的死和妳有關,我都不信。」
「他們罪有應得。」
「他們是好人啊。」
「這叫內疚!當年,由於手術的切割角度,我得到的腦組織比較小,四肢失去了活動能力,但他們發現我們有很強的心靈感應力。於是,他們用實驗藥物刺激我的腦部生長。最初,療程好像很有效,我的腦細胞增加了三培,手指開始有活動能力。後來他們又發現我們即使一個在香港,一個在九龍,也能有同步的感應和對話。他們叫這做量子腦電波。可是,四歲那年,我對新藥產生了過敏,成了植物人!妳的感應力也像枯萎的花一夜間消失了。不久之後,我們便遭遺棄了。可是他們做夢也沒想到,十六年後我會醒過來!」
「不是這樣的。」明恩激動的說。
「妳要看看我這些年來住的地方嗎?」
矇矓中,明恩覺得自己飄上了夜空,四周滿天星斗,然後飛到一個小島上的一棟大廈。一陣消毒藥水氣味撲鼻而來,然後她穿過一條陰暗的長廊,兩旁的病房傳來哀號聲。明恩掩著耳朵,大叫:夠了夠了。
家雄和手下納蘭芝從機場護送劉大賢到旅館後,在他的房間外站崗到天亮。家雄心底一直覺得虧欠了明恩,很想為她做點事。他不會讓她的鬍子叔叔出事。
「組長,我買杯咖啡給你好嗎?」納蘭芝看著家雄滿臉的鬚根,笑道。
「你聽到嗎?」家雄把耳貼近門口,問道。
納蘭芝搖搖頭。
「有打鬥聲。」家雄說。
「聽不到啊。」
「Action!」家雄拔出手槍,破門而入,只見一名魁梧的印度人手持軍刀,和劉大賢在地上掙扎著。家雄用英語命令道:「警察,放下武器!」
「組長!」納蘭芝尖叫。
印度人揮刀欲割劉大賢喉嚨,家雄砰砰連開兩槍。
納蘭芝雙手拿槍指著家雄,喝道:「組長,放下你的槍!我要拘捕你。」
「阿芝,妳玩什麼,快放下槍?」
「把雙手放在頭後!」
家雄回頭一看,原本倒斃在血泊中的印度人不知所縱,只見劉大賢兩眼翻白,胸膛血如泉湧。
十數名報紙送貨員離開中環地鐡站不久,上班的人群逐漸出現在大街小巷。旅館外的警車在灰色的天空下閃著藍色的警號燈。家雄被兩名軍裝警員戴上手銬,押上車時,回頭在湊熱鬧的人群中彷彿看見一張熟悉的少女面孔。
晨光從窗口射進來,明恩張開眼睛,發覺自己躺在一間陌生的房間內。一陳難聞的消毒藥水氣味撲鼻而來,令她有些作嘔的感覺。她想下床看過究竟,但手腳都不聽使。手臂插了吊鹽水的針筒,但一點感覺也沒有,就好像四肢不屬於她一樣。鐵床扶手的反影裡是一個長髮披肩,面部發漲的人。發生什麼事?明恩的雙唇不由自主地抖震起來。
一把聲音驀地在她腦海中響起:
「阿妹,多謝妳。沒有妳,我的計畫不會這麼成功。
「當妳意志鬆懈時,譬如睡覺,失落,我的量子腦電波便可完全控制妳的身體。
「妳可能自己也不曉得,妳擁有的特殊感應力能輕易把幻象投射進任何視線範圍內的人。我便是借助妳的力量,把那些醫生一個一個推向絕路。
「還有,小說裡講的元神,其實是腦神經元的網絡而已。
「我住厭了這房間,所以索性把我們的神經元網絡對調了。
「暫借妳的身體用用,不對,如果不是那些壞人,這身體根本也是我的。
「啊,今晚穿哪對高跟鞋去吃飯好呢?」
----------
九七年的舊報紙:
單親母親蔡太誕下香港第一對共用一腦的連體雙胞胎。當妹妹吃奶時,姊姊會露出滿足的表情;而姊姊睡醒時,妹妹也會馬上張開眼。英國來的專家打算三個月後替嬰兒做極危險的切割手術。
三個月後聖誕日報紙:
單親母親蔡太積勞成疾,一病不起。醫生決定把手術延期三個月...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