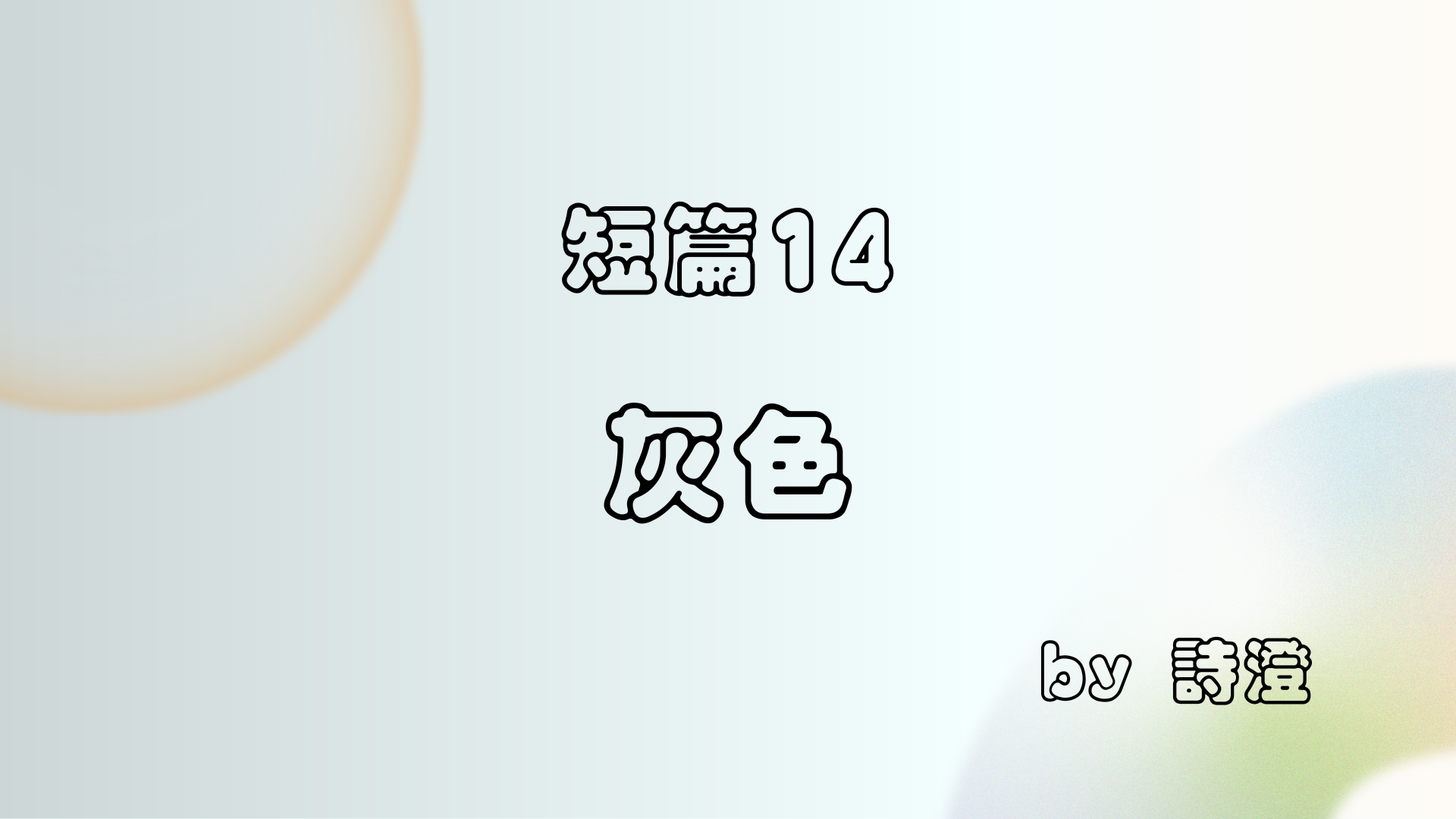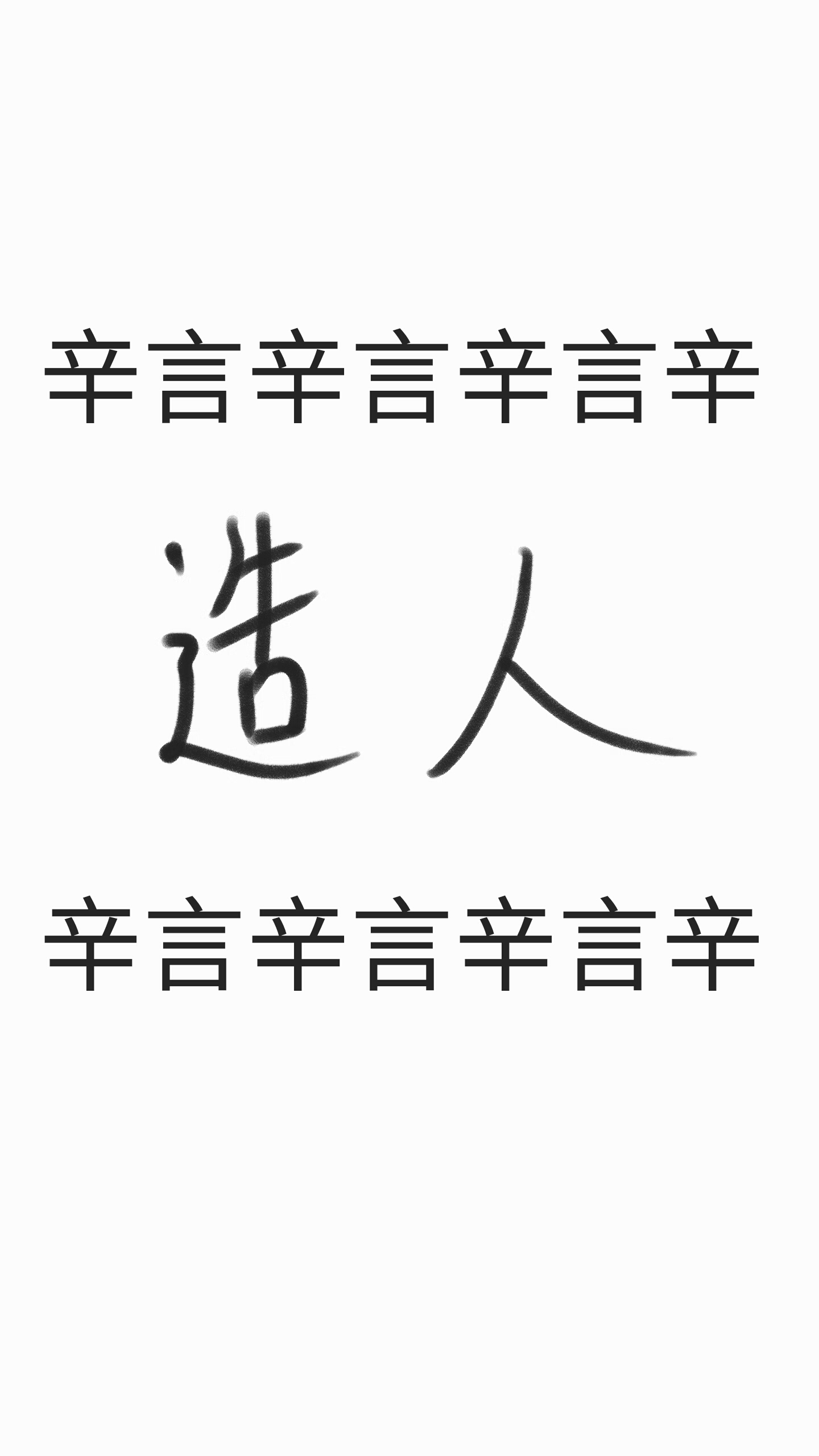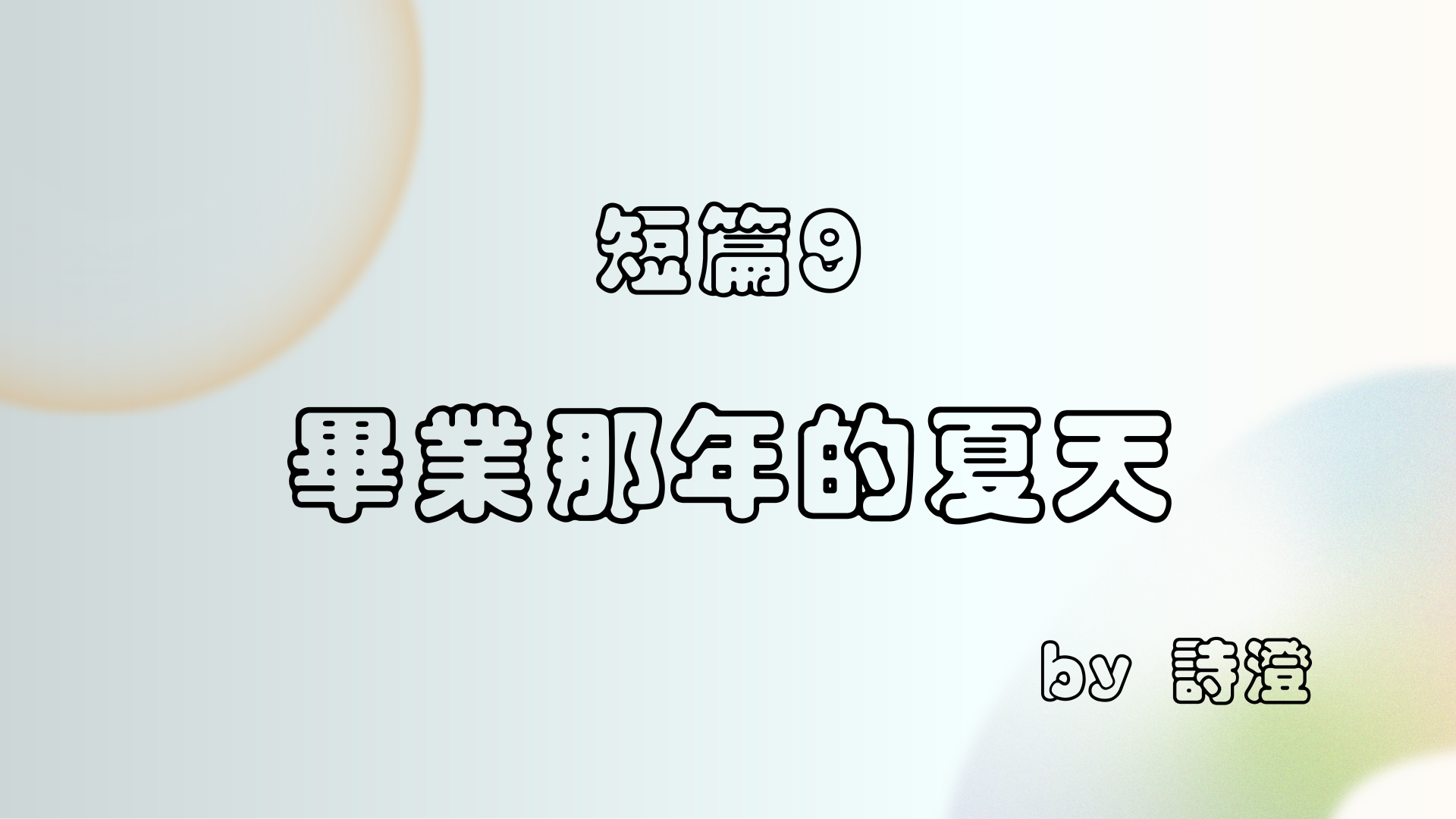上學路上
由天水圍到香港大學
鬧鐘在俊軒醒了之後才響起,被吵醒的滋味並不好受,俊軒在自己腦中設置了一個閙鐘,不像現實中的鬧鐘,那東西不會響,但會在適當的時候敲了敲負責的腦神筋,提醒俊軒: 該醒了哦,忙碌的一天要開始了。於是俊軒跟從腦海中某個位置的指令,睜開了眼睛,等待現實中的鬧鐘響起。
鬧鐘鈴聲是手機內置的,大概是哪個充滿偉大志向的音樂家作的吧,如今變成香港的某個普通大學生的閙鐘鈴聲,而且還沒能起到鬧鐘的作用,那感覺應該不好受吧。
俊軒從床上坐了起來,拿起手機,也不管原作者的感受,把設在7點30分的閙鐘無情地關掉。看了看家裏的情況,確認和昨晚睡覺時沒甚麽兩樣,哥哥還睡在對面的床墊上,姐姐的房門緊閉着,爸爸已經去上班了,媽媽聽着收音機,不知道睡了沒。對,和昨天睡覺時沒有變化。
俊軒從客廰的床墊上站起來,躡手躡脚地走到廁所,畢竟家裏還有兩至三人在睡覺,打擾到他們是不禮貌的。
廁所的木門卻不爭氣地發出聲音,那是天氣還沒回暖的訊號。俊軒關上廁所門,用冷水刷了個牙,本想再洗個臉的,想起剛才的冷水要刺激到自己的臉,也就打消了這個念頭。今天沒有重要的約會,頭髪長甚麽樣也不要緊了。
走進厨房,媽媽已經煮好粥了,還有一隻熟了的蛋。早餐在家裏吃,就省去了幾十塊錢。這是俊軒一家的家訓之一。但不能不吃早餐,收音機裏的專家說的。
穿起衣服後,時間只過了20分鐘。本來計劃8點出門的,10分鐘的空白也做不了甚麽。還是早點出去吧。
走進電梯後,俊軒拿出了剛才的手機,是個不太起眼的台灣牌子。當初因為錢的關係才買了這部,是那牌子裏不起眼的型號。把耳機插進手機,再把兩根尾巴塞進耳朵。音樂響起時,電梯已經到地面了。音樂播的是昨天回家時還沒聽完的卡農。
車站已經大排長龍,那是一輛只停五個站的巴士,俊軒的站是第三個。有幾輛巴士經過卻沒停下,看來已經在頭兩個站就已經人滿為患了。巴士公司經常要安排一輛空的直接到第三站。今天卻有點慢,等了十分鐘還沒有空的巴士過來。
排隊的人已經開始鼓譟,也有人跑去搭輕鐡,速度是比巴士慢的,但一旦上了車心理會舒服一點,那些人應該是這樣感覺的吧。排在前幾個位置的一位女性像是打了個電話去投訴了,俊軒聽着音樂,但還是能隠約聽到她的聲音。於是他把音樂調大聲,現在播的是謝安琪的囍帖街,那條街在灣仔,不是在天水圍。
「但霎眼,全街的單位,快要住滿烏鴉。」
俊軒嘗試想像那畫面,眼前又一輛裝滿人的巴士經過,若那些人變成烏鴉,應該就接近了。
空巴士到來,人龍的頭進入巴士後,身體也搖擺着前進,如果從天上看的話,龍應該是被巴士吃掉了。
現在到我變成烏鴉了,俊軒想着。
俊軒要在下一個站下車,基本上全車的人都要下車。第四個站和第五個站都是在天水圍西鐡站下方,差別在於第五站有電梯可以上去。在電梯和樓梯之間,大多數人選擇了樓梯。俊軒選擇樓梯的原因是做運動,平時雖然不忙,但就是沒有做運動。或許這是個契機。
說是做運動,俊軒並沒有跑上去,倒是有些穿着西服的男士,拐着高跟鞋的女士在跑着。俊軒聽着古巨基的愛得太遅,小心注意着眼前的樓梯級,在這麽多人面前跌倒是很丟臉的事。
「最心痛是,愛得太遲。」
「天水圍根本是一個國家。」俊軒聽過別人這樣開玩笑,原因在於人多。一輛空空的列車從屯門方向開過來,在天水圍站滿滿地離開,還有一些人在月台上痴痴地羡慕着。俊軒很幸運,他總能找到個適當的位置上車。俊軒想拿本書出來看看,那是幾天前剛買的村上春樹的書,很厚,也不便宜,但書是俊軒唯一捨得花錢的東西,從不會心疼。但車廂裏沒有足够的空間讓俊軒那樣做,左左右右都擠滿了烏鴉。若不小心碰到他們,會被啄吧。這時音樂切換,在一段沉寂之後,響起林亦匡的安徒生的錯。
「堅守的雋永 亂世之中哪個細心欣賞」
那天是星期五,是俊軒最忙碌的一天,有四個小時的日文課,兩個小時的化學課,還有一個小時的common core tutorial,由9點半開始,在7點半完結,那是在學校要呆的時間。想起當時選日文課的原因是為了更好的了解日本的小說,現在卻等不及了,那本小說正安靜地站在俊軒的背包裏,因為車廂的烏鴉太多而不能拿出來看。
天水圍的顏色是黃色,不知道是甚麽原因。從天水圍出發,不同車站,不同顏色。到南昌時顏色也是黃色,鮮艷的黃色,不同於天水圍那種土土的黃色。南昌對俊軒來說是個被利用的車站,只供中轉,不留下任何痕跡。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這是俊軒手機裏唯一一首英文歌曲。
在西鐡上並沒有甚麽可以讓俊軒記住的情景,從黃色到黃色,俊軒還是俊軒,一切還沒有發生變化。不值得被儲存在腦海的角落裏。
上學的路只剩下一半,俊軒已經進入香港的核心地區。接下來要到達的地方,叫香港。
從鮮艷的黃色出來,走出西鐡時已經8點40分,俊軒從來沒試過坐過站,在車廂裏沒有甚麽東西或家伙能夠讓他分心,看着手機熒幕傻笑的短髪女孩,站着睡覺的高大男人,拖着行李的非本地人,偶爾可以一見的穿着制服的空姐,一切都在腦袋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內。俊軒的生活不會再改變了,在大學畢業之前。
在南昌搭上前往香港的車廂中,俊軒聞不到不同的味道,像是把整個西鐡車廂都搬了過來。這時響起了宋冬野-斑馬斑馬的前奏。俊軒正在自學吉他,從女朋友的朋友處弄來的吉他,從網上下載的教學短片,並不是興趣,也不是為表演,只想在平時的空閒中多一項活動來殺掉多餘的時間。
「班馬班馬,你不要睡着了,我只是個匆忙的旅人啊。」
香港站是個比南昌更有利用價值的中轉站,許多人,包括俊軒,都借此站前往香港島各處,從香港月台上來,多了穿西裝的人,多了點國際的味道。當然最多的還是俊軒這樣的本地人。
那是一支軍隊,從香港浩浩蕩蕩出現,俊軒則是偷懶的士兵。在別人加速前進的時候,俊軒放慢了脚步。他看到了一些東西。不像軍隊的東西。
在香港去中環的路上,黑壓壓的一群人,在不用迷路問路的情況下走着同樣的路,那是意識告訴我這麽做的。這些人應該是這麽想着。
不,俊軒知道,那是身體告訴他們這麽做,眼睛告訴你,我要打開了哦。脚告訴你,我要站着。身體告訴你,我要穿那黑色的東西。嘴巴告訴你,我要說那句話了,快把嘴動起來。他們的腦子在休息,他們的腦子放棄了擔當,放棄了主人,他們只想休息。「腦子動久了會累的,要記得休息」,那是聰明的人對沒那麽聰明的人說的話。
「若被傷害夠,就用一對手,痛快地割開,昨日詛咒。」
俊軒想起來了,自己為甚麽會走在這條路上,今天的日文課在9點30分開始,每個星期五他都要在7點30分起床,8點出門,在9點半之前到學校。現在已經是9點05分,他在一群腦子在休息的烏鴉中間動了腦子,他想停下來,但不知何處來的風把俊軒的翅膀控制,讓牠們繼續擺動着,反正在港鐡空間裏,誰也飛不高。
腦子想站起來,其他神筋在壓制着,烏鴉已經飛進最後一個月台,還有最後三個站就到香港大學站,時間在被殺。
人一生只用到了大腦的5%,其餘是多餘的存在,但5%可以做到其餘95%做不到的。一次,一次站立,就可以擺脫烏鴉的存在,那5%摧毁了95%,為自己騰出空間,一次站立,可以飛出黃色的規範,那5%剪斷了阻撓的神筋,一次站立,可以飛出限制的空間,那5%跳進腦海,進入別的東西進入不到的世界,沒有不值一提的東西在腦海裏,在腦海裏沐浴,在腦海裏重生。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不起眼的手機透過便宜耳機線把剛才播過的歌重新播一次,俊軒揮動着翅膀,跟着歌詞哼了一遍。
「turn away and slam the door」
到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