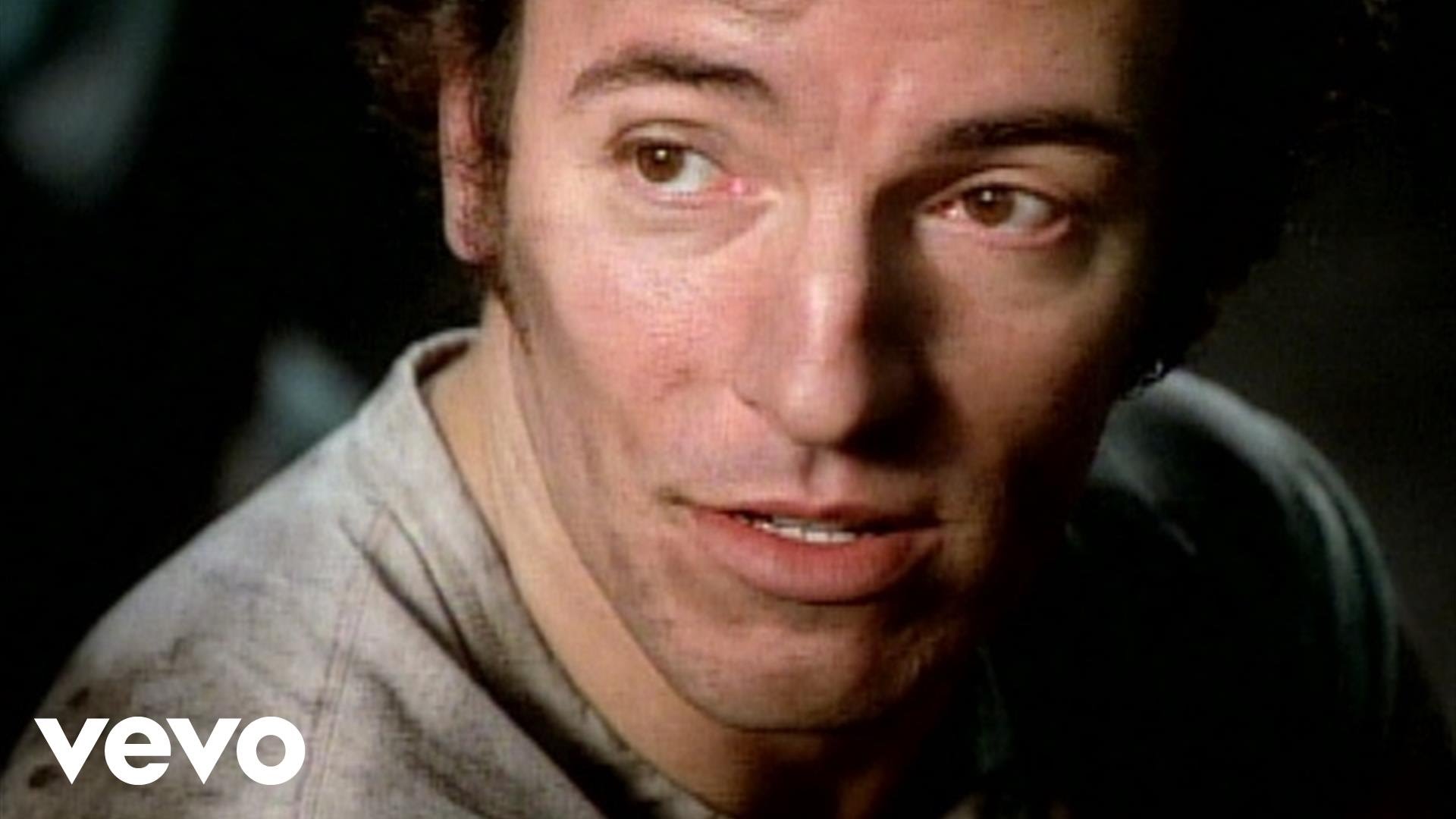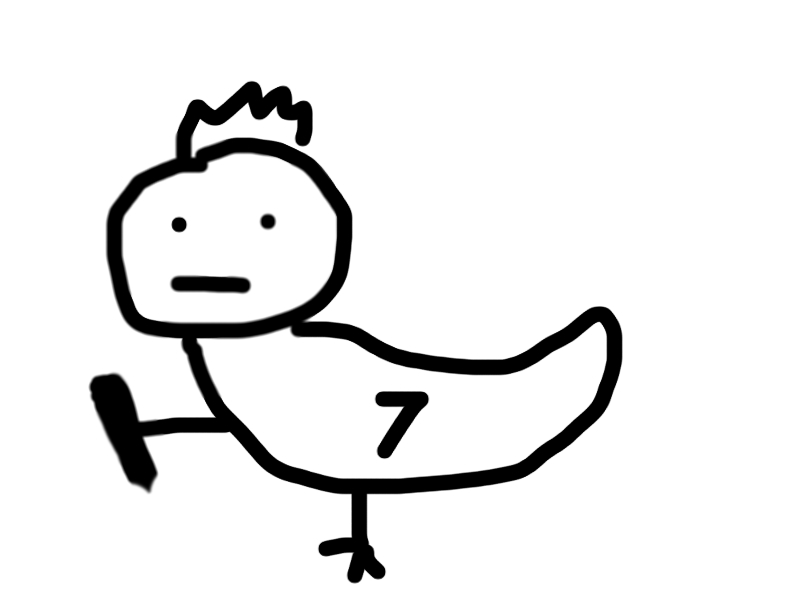我抬頭望著眼前的酒吧,沒有想到它有一點像Elgin大街的酒吧有點相似。不過想到自己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去買酒飲就是在這大街。以前修讀電視廣播,每逢期末考結束,大伙兒就相約到這兒的酒吧開懷暢飲。加上日後我在市中心工作的日子不少,這街也成了我工作範圍之中。
無怪乎這酒吧與那大街的酒吧相似。
我信步踱入。年紀跟我相約,高大,說不上是壯漢,但身型結實,卻又有幾分書卷氣的酒保一見到我進來,就堆上一個熱情的笑容歡迎我。
「你好!許久不見!」
我掛上一個從容的笑容,行到吧臺坐下來。
「沒錯!都有一段時間沒有飲酒--一要駕車或上班,我都滴酒不沾。」
「想點甚麼飲?」
我懶洋洋地望著酒保身後的酒架--思緒沒有一個焦點。
「你有沒有響(ひびき)?」
「之前老闆入貨,有買入這個。」
「就給我一杯!唔該!」
「好!」
酒保接著將一個杯墊放在我的面前,然後拿出酒杯來,將兩粒冰塊放進去。
淳棕色的液體從精緻的酒瓶落進酒杯,與冰塊交融。這個過程看來十分普通,卻令我看得入迷。
酒保將酒放在杯墊上,又為自己倒酒,然後他舉起酒杯來。
「飲勝!」
我也舉起杯來:「飲勝!」
由於這是我第一次飲威士忌,所以我不像平時飲啤酒或已習慣的酒那般豪快地灌進喉嚨之中;而是慢慢流進口中,先享受當中的甘淳,然後用舌頭慢慢引入咽喉之中細心回味。
「好酒!」酒保滿足道:「你果然識貨!」
「我是第一次飲威士忌。只是胡亂去點。」我淺然一笑:「對了!世佑叔今日會不會來這兒?」
「阿正!」
「一講曹操,曹操就到。」酒保揚起手來:「世佑叔!」
「給我準備啤酒!另外給我一個香草白汁青口意粉!」
來者五十來歲,西裝骨骨,頭髮是黑白滲半。他雖有發福的跡象,不過看來挺結實。歲月在他的臉上留下不少痕跡,但是他那張爽朗的笑容告訴世界:「沒有甚麼事情可以將我打倒。」
他這一個模樣令我想起香港實力派演員曾江在二三十年前的模樣--眼前的大叔和曾江當年的模樣十分像。
「你的意粉,仁仔已經準備好!」
說時快,那時遲,侍應已經將意粉拿來。
「世佑叔,」酒保指著我:「看看誰到來。」
世佑叔望過來,哈了一聲,伸手過來跟我握手。
「寫稿佬!許久沒見!近來如何?」
「不過不失。」我愜意回道:「為生活而忙...其實我想找一份比較好的工作。...」
「你有沒有考慮過法律行政工作?」世佑用叉子扭著意粉:「我看你寫組織條文挺有板有眼。」
「這又要花錢花時間去進修。雖然是實際,不過我寧願去修讀一個創意寫作的碩士課程。日後都可以申請做劇本分析。以前有本領沒學歷時候,就不知道如何好。現在有本領有學歷,經驗卻欠一點。真不知道那幫天殺的人力資源如何選擇人...人總要有一個地方開始才可以累積經驗...」
「也許人家有他們理由...」
「有些甚麼理由?老子見過一些不知所謂,生活智慧全無的自大狂拿著人家的求職信回家在家人面前嘲笑人家。那是哪門子的道理?」然後我將杯中的威士忌乾掉,狠狠地將酒杯敲在臺上――差點將它敲碎。
酒保見我情緒激動起來,就揚揚手,向世佑叔示意不要說下去。他接著向侍應招手,在他耳邊耳語幾句。侍應點點頭就回到工作。
「給我再添一杯,唔該!」我有一點負氣,也有點歉意:「剛才...對不起。」
「不打緊!不打緊!」世佑叔嬉笑著:「有心未怕遲。你之前也十分努力。」
「也問自己不少回為何要回大學完成學業...真是為一口氣。之後又是如何?」我自嘲著。
「你不應該慶幸因為你仍幹著這『技能與學歷不相乎的工作』,否則你可能不會在街上增長智慧及有機會讓自己的思想沉澱及提鍊。」
「的確。」我掛上笑容,向世佑叔舉杯,感謝他給我的安慰。
這時,侍應將一碟漢堡包,番薯薯條及青菜沙律放在我面前。
「我沒有點東西吃...」
「是我吩咐廚房做。」酒保插嘴:「我請客!這個,你應該明白的。」
我輕笑一聲,說來自己也有點肚子餓,於是我老實不客氣抓起漢堡包來。
「謝謝你!」
「別客氣!」酒保溫柔回道。
「對了,世佑叔...」我邊吃邊說:「關於你的故事,我有可能會拖一拖。」
「除了『沒靈感』﹑『不知道如何寫下去』﹑﹑『趕功課』,你要給我一個可以說服我的理由!」
這時候,有兩個年輕人進入酒吧。
比較年輕的一個擁有一張少年人臉孔。天真瀾漫的笑容看來對前路滿有憧憬--應該是剛入大學的。
至於年長的一個:他也有一張令女生心動的臉孔,與年少的有幾分相似。可是,他的眼神落漠,又有對周遭的懷疑――像是剛經歷震懾身心的事。
他手插褲袋,目光滿載蹣踹張望四周。
「哥哥,過來罷。」年少的輕聲喚著年長的。
兩人就坐在吧臺近門口的坐位。
酒保過去,以他平常的熱情去歡迎來客。
「歡迎光臨!想要些甚麼飲品?」
「你有沒有生力生啤?」
「有!」
「就兩杯生力生啤。」
「馬上來!」
酒保轉身去雪櫃拿出兩罐特大生力生啤。之後他拿出兩個長型大口的啤酒杯,將啤酒倒進去,放在兩兄弟的前面。
弟弟拿起酒杯,微微轉向哥哥,想與他碰杯。
「哥哥...」
可是哥哥垂著頭,雙手扣起來,對弟弟的動作沒有反應過來。
弟弟卻耐心等待。
「多管閒事」的酒保湊起去,輕輕在哥哥面前晃晃手...
哥哥的動作看來比較遲緩――不過,我知道他是正常。他過了好一會才見到酒保向他揮手。
酒保指一指弟弟,哥哥才轉過去看看弟弟――弟弟仍舉起酒杯。
我冷眼旁觀。世佑叔見我似乎知道一點內情,就湊過來輕聲問:「喂!你是不是認識這兩兄弟?」
「嗯!」我點點頭,喝著我之後點的黑啤:「他們也許是我的後代罷...」
世佑叔登時將下巴掉下來:「甚麼?真的假的?」
「視乎你如何看待我這一個回應。」我逕自飲酒,繼續故弄玄虛。
兩兄弟碰杯,喝了一口啤酒。
「你們要不要點些甚麼來吃?」酒保關切問。
他首先望望哥哥。
哥哥仍是有點遲緩。他想了好一會才開腔:「暫時給我兩片麵包。」
「要牛油及果醬嘛?」
哥哥搖搖頭:「不必,唔該。」
酒保轉向弟弟:「小兄弟,你又如何?」
弟弟見哥哥點異常簡單東西而拿不定主意。酒保將這矛盾心情看進眼裡,於是再一次多管閒事。
「就給你本酒吧的特式意大利粉罷!」
「謝謝你!」
「希望合你口味。」
酒保將侍應招過來,將單交給他,又跟他耳語幾句。侍應點點頭之後就走去廚房。
「朋友,」酒保拿著之前與我敬酒的威士忌:「不介意的話,我想向兩位敬酒。」
「好!」弟弟靦碘一笑。
酒保舉著酒杯:「慶祝你倆兄弟再度重聚!」
弟弟聽到酒保的說話,手如觸電一般抖動一下――動作輕得普通人是不會察覺到。
他舉杯的手停在空中。
「調酒師是一個需要洞悉人心的行業。」酒保自信一笑。
果然是一個銳利的人――我心道。
同時,我的嘴角也蹺著自豪的微笑。
世佑見狀,就湊過來。在想開口問我時,我立刻簡潔回道:「他們就是理由。」
侍應也將兄弟所點的食物奉上:哥哥的兩片多士,弟弟的卻是一碟超大分的白汁海鮮意粉。
哥哥甚麼都沒有塗在多士上,就將多士抓起來咀嚼。
弟弟望望世佑叔的意粉,感到奇怪。酒保在迅雷之間將兩隻碟及兩套餐具在兄弟倆前面,弟弟呆若木雞,酒保點點頭,溫柔一笑,務求讓弟弟安心。
弟弟以點頭答謝酒保的善意。然後,他拿起一隻碟,將意粉夾在碟子中,放在哥哥的旁邊。
「哥哥,仍然肚餓就吃點意粉。」
「可以?」
「可以!」
世佑叔對此感到奇怪――要了解更多,他覺得他需要主動出擊。
於是,他挨後,轉身過去問:「小兄弟,你們從哪兒來?」
「我們從香港來。」
「香港?好地方!」世佑叔曾經從我口中聽過有關香港的事。
「的確是一個美麗,充滿動力的地方。」弟弟含蓄一笑。
「不過我之前聽到那兒有年輕人因為政府施政不善而起來抗議...也有出版商因為敏感話題而被『邀請』到你們的宗主國『協助調查』...」
「那些事,是發生在我倆兄弟出生之前...」
世佑叔聽到這個答案滿感稀奇。
弟弟繼續說:「學校沒有人提,我和哥哥只是從書裡知道。那些『抗議』,學校就說是『亂港暴動』...」
「由這國家的人寫歷史,真是放屁。」我喃著。
酒保望著靜靜在吃意粉的哥哥。
他望一望弟弟,然後伸出手來。
「你好!我叫傲正。」
「我叫龍永汰。」
永汰跟傲正握手。驚鴻一瞥,永汰見到傲正手腕上的舊傷痕。
「你的傷痕...」
「都是不值一提的老傷痕。」傲正這一個微笑顯得老成――一種與他同齡的人沒可能有的老成。
接著。傲正轉向永汰的哥哥,想跟他握手。
哥哥只是低著頭吃意粉,對傲正的動作沒有反應過來。
永汰輕輕拍著哥哥的肩頭,才令哥哥從「吃東西」當中拉出來。
「我叫傲正。」
哥哥與傲正握著手。
「我...我...我叫...」
「他叫龍太軒。」弟弟插入。
「這真是我的名字嘛?」哥哥迷惘。
「沒錯!你的確叫龍永軒,而我確確實實是你的親弟弟永汰――並不是甚麼『託管人』!」
弟弟的態度頗為激動――看來他一直努力幫助哥哥去回想有關自己的一切。
世佑叔越來越感到奇怪,又湊到我的身旁問:「哥哥像是曾被囚在勞改營?」
「『那個國家』在千禧年代沒有『勞動教養』這玩意。」我懶洋洋回道。
「永軒曾經被囚禁?」傲正小心翼翼問。
永汰一臉無奈,望著埋頭吃東西的永軒。
「該如何說?我跟爸媽的確從赤柱監獄接哥哥回家。可是,他就一直在說許多莫名其妙的說話,說自己的家人應該全部離世。」
「甚麼?」世佑叔震驚:「我聽說,赤柱監獄是你們那兒的一所高設防監獄...但是我看你哥哥一點都不像...」
「世佑叔,你最初不也是以為我不是前僱傭兵,就是職業殺手麼?」傲正略作揶揄。
「你根本是一個無可救藥的行動派!」世佑嚷道。
傲正嬉笑著,轉過去對永汰說:「別要理會那醉鬼的說話!」
永汰因為傲正與世佑叔製造出來的滑稽氣氛而略為寬心,在臉上掛上笑容。
「哥哥是一個相信『行動勝於一切』的人。他為了改變社會,參與在大人眼中是『激進』,『反社會』的組織。不過,據我所知,他們只是派派傳單,偶爾發動罷課,靜坐--最『頑皮』的只是半夜三更在街上塗鴉,寫寫諷刺政府及親國派的字句。一點不暴力。」
傲正點著頭,示意永汰繼續。
「我知道哥哥和他的同伴都是為了爭取一個更公平,更令人安居樂業的社會。大人卻認為他們是破壞社會安寧的壞分子。三年前,哥哥出去跟同伴聚會就沒有回家...直到幾個月前,懲教處通知我們去赤柱監獄接哥哥。」
身為律師的世佑叔著急問:「他從來沒有被法庭審判?」
「我們根本不知道他被控甚麼罪名,也不知道他的刑期――我甚至懷疑哥哥根本不是被囚在赤柱,而是另一個地方。」
永汰帶著悲傷的眼神望著永軒:「我哥哥回來時,徹頭徹尾成了另一個人。」
這說話令世佑叔心痛。
「我真希望我能夠幫助你們!」世佑叔由衷道。
「我兄弟倆現在可以一起出外旅行已經算好。」
「你們有甚麼打算?」傲正問。
「會回去香港。」永汰堅定回道:「始終,那是我們的地方。」
我聽著永汰這說話,默默無言,繼續喝酒。
「而且,」永汰續道:「我知道我只可以在那個地方找到發生在哥哥身上的真相。」
傲正無言以對。這時,永軒將意粉吃完。
「哥哥,要添一點嘛?」
「不必了。」永軒望望永汰,才發現永汰因為之前與傲正聊天而未吃完意粉。
他略有惶恐。
「原來你仍未開始吃飯...」
「不打緊。」
此時,有一個女人牽著一個大約三歲大的男孩子進入酒吧。
傲正見狀,從酒吧走出來。
「爸爸!爸爸!」小男孩奔過去。
傲正將孩子抱起來,臉上堆上一個「有仔萬事足」的笑容。
「我的大傢伙!今天在學校愉快嘛?」
「好玩!我今天終於捉到一隻大蝸牛!」
「不像之前捉到的小蝸牛!」
小男孩重重地點頭。
「蝸牛...」這是永軒第一次主動說話。
他望著傲正懷中的男孩,笑了一下。
傲正將兒子放下來,說:「嗣揚,不如你將今天捉來的蝸牛給這位哥哥看。」
「嗯!」小男孩點點頭。
小男孩落地之後就奔去媽媽那兒。媽媽捧著他的書包,讓孩子將載著蝸牛的透明的罐子出來。
永軒從坐座下來,蹲下來。嗣揚行去拿著「戰利品」給永軒看看。
我乘著這一個空隙向孩子的母親打招呼:「嫂子好!」
「真是稀客!」嫂子見到我,就上前跟我擁抱:「甚麼風將你吹來?」
「沒啥特別。酒癮起,就來這兒買酒飲。」
那邊廂,永軒望著嗣揚手中的蝸牛,嘴角蹺著一個意義難明的微笑。
吃完意粉的永汰也下來,蹲下來去看嗣揚的蝸牛。
「我小時候,曾經為我的弟弟捉了一隻類似的...」
永汰聽到這個,正蹲下來的他突然止住。
「哥哥...你仍記得?」
「每一天,就望著下雨,望著雨後,去捉蝸牛...」
永汰強忍著淚水,慢慢蹲下來跟永軒看蝸牛。
世佑叔拉著我輕聲道:「雖然我以前曾經見過有人真是因為在獄中多年而真的犯瘋進入精神病院,可是...出來不能認人真是第一次見聞。」
「有時,當權者利用他們的想像力去折磨反對他們的人。」我說道:「他們知道將這些年輕人殺掉的話會惹來不滿――何況香港因為前宗主國的關係而沒有死刑。倒不如利用一個狂想及科技去毀掉本是他們最優秀的人。」
永軒著迷地望著蝸牛--也許這一隻蝸牛將深藏在他的腦海之中的童年回憶勾出來。
過程之中,嗣揚都顯得安靜,穩妥地拿起瓶子讓兩兄弟欣賞。畢竟是小孩子,時間一久,就會想動。
永汰察覺到這一點,就溫柔跟永軒說:「哥哥,我們要回酒店。」
「嗯。」永軒點點頭,接著起來。
「哥哥!」嗣揚叫道。
兩兄弟回頭望望孩子。
嗣揚將蝸牛捧起來。
「這個送給你們罷!」
傲正上前,向嗣揚解釋:「哥哥他們來自外地,不能將這一個帶回家。」
永汰也道:「沒錯,我們不可以將這一個帶回家。謝謝你!」
「小兄弟!」
世佑叔起來。他從懷中掏出一張名片出來,遞給永汰。
「這張名片只有我的聯絡方法,沒有將我的專業寫出來――我只是用來交朋友來。如果有需要談談,找我罷!」
永汰接過名片:「謝謝你,孫先生。」
「你跟他們叫我世佑叔。」
接著他向兩人伸手。
「有緣再見!」
永汰跟世佑握手。
「有緣再見!」
傲正和嫂子也過來。
「路上小心!下次再來時,記得再來這兒。」
「我們一定會!」
我們目送兩兄弟離開。
我聽到嫂子幽幽道:「老公,不知道為何...我從這兩兄弟身上嗅到你的氣味。」
「你何時成了獵犬?」
嫂子聽後輕拍傲正的胸膛啐道:「你說甚麼!」
「不不,我才是你高貴大小姐憐憫的流浪狗...」
世佑呼出滿帶感慨的嘆息。
「我以為一個無罪的人被法庭判為有罪入獄是最不幸。沒有想到有更加不幸。」
「世佑叔,如果你有能力去幫助他,你會如何幫助他們?」我再呷一口酒問道。
「不要問假設性問題――這是律師第一條要遵守的規則!」
「但是,作者的職責就是,一是作為時代的先知,將一個大眾沒有想過的未來告訴大家。或是作為時代的歷史教師,重述歷史,以此警告大家。」
「那麼,」傲正站在我們的中間:「你有甚麼打算?」
「我可是一個盡責的寫稿佬!」
「明白!」
他回到吧臺,拿出兩隻酒杯來。
「也給我一杯!」世佑叔要求。
傲正悶不作聲再拿出一隻酒杯來,然後拿出之前為我奉上的酒瓶來,乾淨俐落地倒了三杯酒來。
「好!咱們乾了它!」傲正首先舉杯。
「好!」世佑叔和應,然後他向我舉著酒杯。
「你一定好好將永軒永汰的故事寫出來。否則我不會放過你!」
「明白!雖然我仍是拿你的故事去作一場賭博。」
我們三人碰杯,一飲而盡。




-01.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