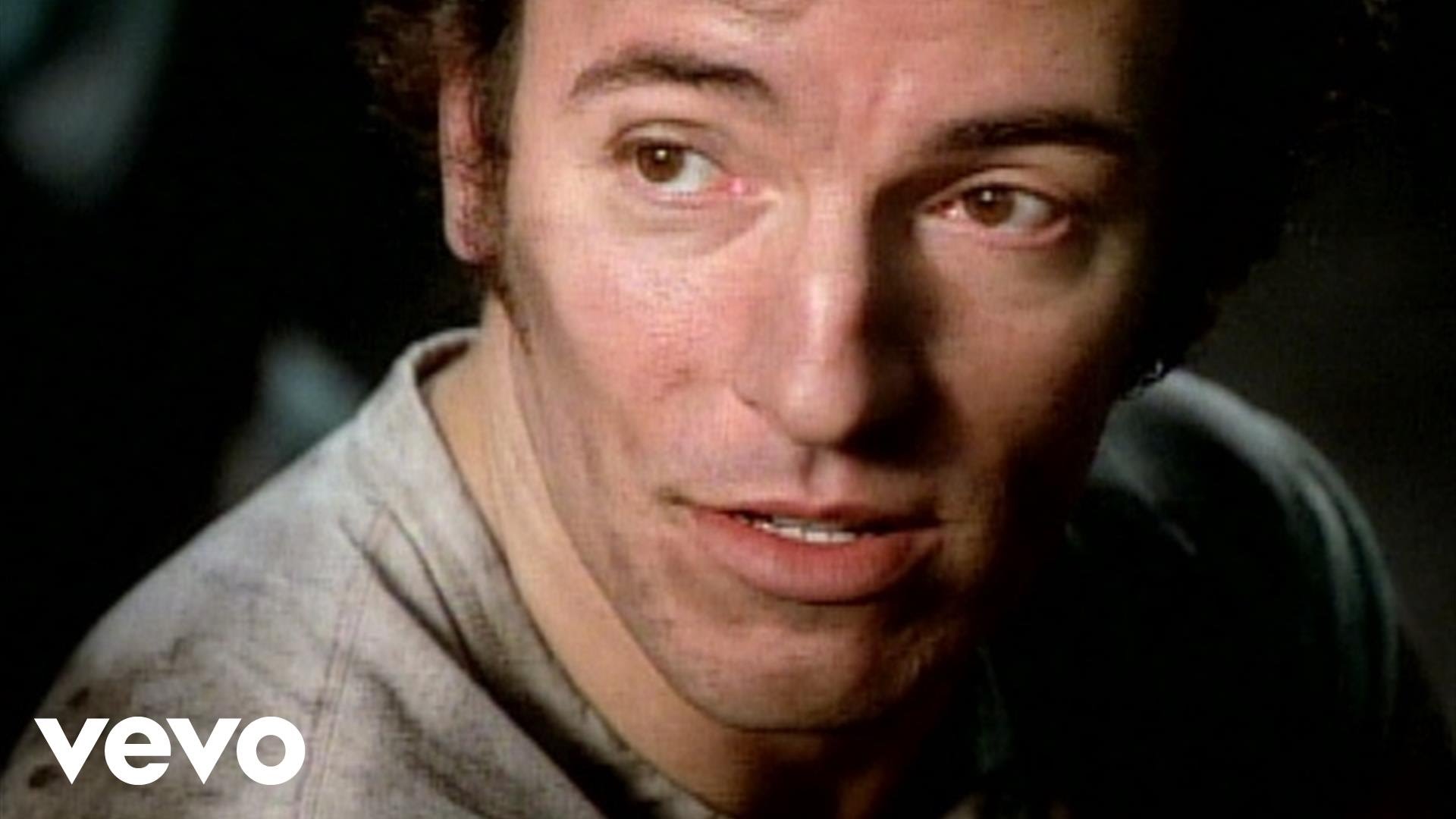將身上的衣服財物放進接收處人員準備的紙盒裡,接受全身檢查之後,我就穿上略大的橙色,一件式的拘留所囚衣。
這是我第二次穿上這囚衣――也沒有想過自己有機會再穿上這囚衣。
在獄警的指示之下,我到另一個櫃檯領取床墊、被舖、毛巾、替換衫褲、肥皂、牙刷、牙膏等日用品。
「跟我來。」
獄警領我到獨立囚室的一翼。這兒是一日二十四小時燈火通明――最主要的原因是方便獄警管理。但凡囚犯之間發生甚麼事情,或是自殘,獄警都可以迅速進來控制場面。
拘留所關押兩種犯人:一種是已被定罪,刑期少於一年的犯人。另一種是等待上法庭應訊的犯人。
而現在,我屬於第二種犯人。
「由於你屬於高危犯人,所以安排你獨立囚禁。每日有一小時活動時間,每兩日洗澡一次。每星期有人到來收集衣物去清洗。現在你是待審犯人,所以你可以在指定時間之內與你的代表律師見面。清楚沒有?」
「完全清楚,長官!」我站直道。
獄警按著通訊機:「將二三七號關上。」
機動閘門就徐徐關上。
我先將床墊放在床上,舖上床單;然後將其他的東西放在床尾的塑膠箱裡。我漫不經意望上鐵窗:今晚是月圓,所以可以在月光的照明之下見到雲霞的輪廓,令人可以放鬆下來。
此時,我才感到積聚在身上的疲累。
今天和昨晚,我到底睡了多少?
昨晚倩雲在下塌的小酒店之中出事,我費了一點氣力將她從那那酒店房間拉出來。回到房間,我需要好些時間才能安撫她入睡。我一直都是坐在旁邊守護著――我也許睡了一會,不過不到兩三個小時就醒來。之後我沖泡酒店提供的咖啡,將所有的咖啡喝掉。
雖然我已經決定會回去監獄,將倩雲交給獄長先生及自首,卻萬想不到會如此節外生枝!
我很懊惱――絕對不是為了自己身處的境況。
而是懊惱自己令倩雲遇上她不應該遇上的不幸!
昨晚,她表面上睡得十分熟。可是我擔心她內裡惡夢連連,沒有安寧。
即使獄長先生說要一槍將我打死,我不會有怨言。
這是我應得的。
我癱坐在床上,用手揉著臉上每條肌肉,重重地呼出一口氣去放鬆自己。
倩雲已經回到她父親的身旁,我的重擔應該要卸下來。只是這一分懊惱在我的心口上加上重量――令我仍有忐忑。
眼瞼越來越沉重,我也不得不向睡魔投降。
翌日早鐘響起來,我就起床梳洗,然後執拾床被。在閘門打開之時,我步出囚室,筆直地站在黃色界線之後。
一個四十來歲,略帶點胖的獄警主管到來――有兩個比較年輕的獄警跟隨在後。
主管拿著夾著該是囚犯名單的文件夾在點算人數。他一邊踱著,一邊打量我們,然後在文件上做記錄。
這一種枯燥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
在監獄,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點算人數。
獄警要確定囚犯應處的位置,會反覆地點算人數。而囚犯如何不願意都好,也要乖乖地站著,等待獄警將人數點算完畢才可以吃早飯。
上一回我被拘留於拘留所,曾被一個獄警利用這個時候下馬威。不過我上回在法庭上認罪,很快離開拘留所到監獄服刑,所以那人沒有機會在這兒「折騰」我。如果這一回讓他知道我回來,不知道他的反應會是如何。
可是,我不想在這一段時間惹麻煩——應該說,我任何時間都不想惹麻煩。
「好!以下被點名的人,吃完早飯之後就在走廊排隊!」
聽這說話,大概是有親友到來探訪。
胖主管開始唱名。
這是一個十分沉悶的過程。再者,我昨晚才被安頓在這兒——相信獄長先生現在也未必知道。所以這事應該與我無關。
而昨晚感到的疲累仍聚在我的身心上。於是我將頭腦裡的一切掏空,令自己可以專注在「站立」這動作。任憑胖主管如何單調,我應該不會倒下來。
我打算吃過早飯之後就躺下來休息一會——反正作為被拘留的犯人是不需要工作。除了指定的活動時間之外,一整天只可以待在囚室之中,我反而可以決定如何運用時間——真像在放悠長假期。
再加上這一回是「單獨囚禁」,除了監視的鏡頭,沒有囚犯可以騷擾我——這正是我需要的。
「傲正!」
啊?甚麼?為何胖主管將我的名字唱出來?
難道?難道是倩雲走來要見我?
昨日當我從獄長的辦公室被警察帶走時,倩雲真是走上來攔阻我們,不讓我們走。不過警察二話不說將她推開,我們才可以離開。
她到底是不是嫌我為她帶來的麻煩不夠多?還要來見我?
無論如何,一會兒跟她見面的時候一定要絕情!
食過早飯之後,我步出囚室排隊。
在號令之下,我們操到另一翼。
「停!」
胖主管走過來,打量著我。
「傲正?」
「是!長官!」
「你跟我來。」
「是!」
胖主管領我到另一邊的獨立會客室——似乎只有我一個人有如此待遇。
就在這一刻,我知道要見我的人不是倩雲。
獄長先生即使如何要保護我都好,也未必「濫權」到向這兒主管要求安排倩雲在這種獨立會客室跟我見面。
不知道為何,我對獄長有這種信心。
只是我在情況許可之下向他提及此事時,他回曰:「即使倩雲要走去見你,我也一定跟那拘留所所長要求安排你們在獨立的會客室見面——因為那在你身上的懸賞仍是有效!」
「進去吧!」
我依著指示進入會客室——在會客室的另一方坐著一個西裝骨骨,大約四十來歲的中等身裁的男人。
他見到我進來時,就站起來。
望著他的面孔——即使他掛上一個公務式的微笑——我想起獵鷹。
「傲正你好!我叫程逸東,是你的代表律師。」
得悉這男人的身分之後,我登時成了丈二金剛。
「我沒有委託律師。」
「是道宏老兄叫我來。」
甚麼?獄長先生?他的服務是不是過分貼心?
「道宏,即你之前被囚監獄的獄長,是我在士官學校的同學。」
接著,他坐下來——而我只是呆呆地站著,沒有坐下來的打算。
「坐吧!」程律師伸出手來,著我坐下來。
「我沒有錢聘請你的。」
「我也看著倩雲長大的!別婆婆媽媽!坐!」
見他一而再,再而三著我坐下來,我只好將椅子拉出,坐下來。
「昨日,道宏拜託醫護人員為倩雲做檢查;證實她被人強姦。而倩雲也將整件事告訴我。我打算利用這些...」
「程律師,」我打斷他的說話:「我打算認罪。」
「你該知道有刑期定讞這回事!無論如何,我也是利用這一點為你保命。倩雲也準備上法庭為你作證。」
聽他如此一說,意思是這一回我是犯下必死之罪。
死與不死,對於我來說已經不重要。
但是,我真是後悔那日監獄發生暴動時將倩雲帶走——本來以為是保護她,到頭來卻是傷害她!
傲正,你這弄巧成拙的大笨蛋,還是一死謝罪好了!
於是我打算回絕他:「程律師,勞煩你到這兒見我這笨蛋,真是不好意思...」
「你也是我的恩人!」這一回,輪到程律師打斷我說話:「我絕對不會放手不管!」
「那麼,律師費方面...」
「我是不收分毫去打這官司。」程律師飛快回道:「我只是一個單身寡佬,沒有家累。可以偶爾做這種義務活。」
我將放在檯面的雙手扣在一起,垂下頭來。
「你有沒有說話要我傳給倩雲?」
我用力扣緊雙手,抿著嘴,思想好一會。
「沒有。」我輕輕回道。
「咱們在法庭見!」
我點點頭,然後向門外的獄警示意要離開。
我是沒有想到我這個大笨蛋連「不」也不懂得說出來!
晚飯時候,我坐在門旁等待負責送餐的囚犯到來。順道看看走廊的情況。
我沒有解僱程律師――就是知道這是徒然。可是,從現實角度去看,我根本是不需要他。他跑來站在我的身旁,聽我說認罪,聽法官給我的裁判,有些甚麼用?
我反而覺得他去幫助世佑叔會更加好。
如果世佑叔有至少一個人幫助,也許他可以早日洗脫殺人犯之名而重獲自由。
「你就是那個『挫鷹人』嘛?」
「挫鷹人」是在監獄中別人在我背後改的外號――因為我之前將五個屬於黑幫組織「鷹揚會」的頭目殺掉而被判五次終身監禁。
事實上,我不太喜歡這外號――總感覺令外號會令我惹到麻煩。
我抬頭瞄一瞄門閘外――派飯的人額大目小,顴骨突出,身型瘦削的人。
他的鼻子高高,眼神有點在普通人看來感覺是鬼祟,但在曾經坐牢的人看來是警覺的閃爍。
「你就是那個『挫鷹人』嘛?」他再一次問道。
「嗯!」我點頭承認。
「好了!阿剛拜託我看看你的情況。」
一聽到剛哥的名字,我略彈起來。
「大家的情況如何?」
「你認識的人應該沒事――阿剛說小耀也沒事,乖乖地在囚室呆著。」
聽到這消息,我可以放下另一塊心頭大石!
「我沒有甚麼可以跟你交換。」
「阿剛的朋友也是我魚眼根的朋友。」魚眼根笑道:「再者,你是那個『挫鷹人』!」
「謝謝你。」我掛上一個客套的笑容。
「你有沒有說話傳回去?」
為何大家都要問我這一個問題?當真一字千金?
只是,這一回我有說話傳回去。
「請你告訴他們,我的情況很好。見過律師,不用擔心。」
「我看你多數會回去凌北繼續服刑。」
我靦腆一笑,點點頭。
「好了!好好吃飯!」
魚眼根離去之後,我打開飯盒――飯餸果然比第一次收柙於這兒時豐富許多:有魚有肉,飯底豐厚。我從來沒有跟其他人說我的喜好。大概是剛哥他們不知道我喜歡吃些甚麼,於是甚麼都要一些,務將飯盒塞滿。
我慢慢咀嚼每一口飯,感謝這些朋友的心意。
幾天之後,我被帶到法院應訊。
在法庭上,我只需要說一聲「認罪」,然後待法官定下一個日子去做刑期定讞,決定我的刑期。之後——直到下一次上法庭確立刑期之時——我只是待在拘留所之中「休息」。
仍是穿著橙色囚衣,雙手被手銬及鐵鍊扣在腰間的我在庭警的押解之下進入法庭。
程律師一見到我,就立法上前到辯護人的一旁。
在我站在他的身旁,庭警將手銬及鐵鍊解下。我立刻用手擦擦手腕舒緩之前的因為血液流暢不好而引來的不適。
「倩雲也到了,就在後面。」
「嗯!」我點頭示意,沒有轉身去看。
法庭書記就郎讀控訴狀:「現控告傲正,本為於凌北監獄服刑中囚犯,一,於X月X日,被告逃獄期間於明思鎮謀殺男子丁兆豐。二,於同月同日謀殺男子淩子健。三,於同月同日謀殺男子孫家煌。四,於同月同日謀殺男子袁志沖。」
「被告,你認罪還是不認罪?」
「認罪。」
法官在聽到我的認罪主張之後瞄一腦我,又看看文件。
「被告,上一次,你也是認罪?」
「沒錯。」我點頭道。
「你知不知道你認罪是意味著放棄在這一個法庭審訊的過程?」
「知道。」我再一次點頭回道:「法官大人,這不是我第一次如此做。」
法官維持一副撲克面孔,但良久沒有說話。
他用一個十分奇怪的目光望著我——像是感覺我說的不是真的。
「好。既然你認罪,本席定於Y月Y日作刑期定讞。由於被告本身是仍在服刑之中及曾經逃獄的犯人,被告還押監房看管。」
法官舉起木鎚,重敲一聲。我的事暫時告一段落。
由於我認罪,所以我只待了大約十數天就上法庭進行刑期定讞。
我仍是穿著橙色囚衣應訊。
這一回與上一回不同的是:我不單雙手被手銬鐵鍊扣在腰間,雙腳也被扣上腳鐐。所以我的步伐不可以急,也不可以大。
基本上,我的行動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真可以說是「想動」的自由都沒有。
我並不是第一回被扣上腳鐐——成為無期徒刑的罪犯時,我在離開拘留所時跟其他同行的犯人被獄警們「侍候」,披枷帶鎖,然後踏上失去自由的路途。
只是,我在押送中途犯睏,呼呼大睡。
而我沒有感到手銬腳鐐的束縛,睡得不錯。
「喂!傲正!要醒來喇!」在矇矓之中,我被人推了幾回。
由於不能用手,我在昂頭打呵欠之後,嘗試用肩頭擦擦面孔——卻做不了。
這時,我才意識到囚車是駛到法庭地牢的被關押嫌疑人的專用入口。
我的腦子仍有一點「混濁」的感覺,再打一個呵欠,本想再多睡一會。但是,現在我不得不抖摟精神,下車上庭應訊。
將我叫醒的獄警已經下車。
「別著急,我們仍有一點時間。」
我勉強自己將精神抖摟起來,轉身面向車門;然後小心翼翼地站起來。獄警同時捉住我的手臂,協助我下車。
他從口袋中抽出一包香煙出來。
「要一根嘛?」
我搖搖頭:「謝謝你!可是我不抽煙。」
「哦。」獄警從將香煙收起。
「一會兒帶你去洗手間。讓你洗洗臉。」
他瞄一瞄我。
「準備好了沒有?」
我點點頭:「嗯!」
獄警向他的同事示意。兩人就一左一右提著我的手臂,押送我進內。
到過洗手間洗洗臉,將之前小睡帶來的混沌感覺驅走,獄警們就像上次一樣,將我安頓在法庭外,非一般公眾能夠進入的休息間。
我坐在長木椅,將腦裡的一切雜念清除,讓自己的精神集中在接下來的刑期定讞。
此時,我意識到有一個人趨近。
一個不是獄警的人。
「阿正。」
倩雲!
我垂著頭,以避免與她對視。被扣在腰間的雙手在潛意識的驅使之下緊緊地握著拳頭來。
倩雲緩緩地蹲下來。她將手放在我的大腿上,一臉憂戚地望著我,希望能夠跟我有眼神接觸。
我極力地去逃避——我就是沒有心理準備去面對她!
我咬著牙,決意一句說話都不說。
見到我這副倔強模樣。倩雲的手緩緩地溜過來,想摸我的手。
按著本能,我的手往後退,避免身體接觸。
「啊!要上庭了!辛小姐,你也要離開。」
獄警已經開口說出來要逐客。可是倩雲蹲在我的面前,沒有離開的打算。
她知道我不想她摸我的手,再加上獄警的說話,她將手溜到我的膝蓋。而我坐起來,身體挨前。
我自顧自起來,一眼都沒有看她。兩個獄警一左一右押送我前行。
「起立!」
法庭裡所有人都站起來,恭迎法官進來。
在法官就座之後,大家也坐下來。
沒有銬鐐束縛著,我反而感到渾身不自在ーー正式賤骨頭。
穿著黑袍,斑白頭髮,留有素白色鬚子的法官托一托眼鏡,翻翻案上的文件。接著,他瞄一瞄我ーー表情不多。
「被告,請起立。」
我站起來,等待他下一步指示。
「你已於提訊時認罪,放棄於本法庭審理案件的程序。本席想你在本法庭敘述你的犯案經過。」
「遵命!」
我努力回憶那一夜的事...
我們由暴亂中的監獄逃出來之後,一直躲在一個樹林之中。那時我負責打獵,倩雲則負責將多出的獵物拿去附近的村莊賣給村民。及後,我考慮到倩雲未必可以長時間留在樹林之中,就決定到附近的小鎮落腳。待監獄暴動平息之後,就會將倩雲帶回獄長身旁及自首。
決定離開樹林時候,蓄了鬍鬚的我決定扮作倩雲的啞巴哥哥,希望混到我們回監獄為止。
可是,我們在吃晚飯的時候就出看來是微不足道,卻是事情起始的意外。
倩雲在餐廳遇到熟人——是她在音樂學院的同學。
這人——叫丁兆豐——一見到我們就坐在倩雲身旁。
我粗略看看他身上的衣著:是價錢高昂的名牌子。而他的語氣及舉止十分輕佻,該是那些只懂玩樂的二世祖。
他口裡說因為聽到監獄暴動而擔心倩雲的安危,可是他的舉止卻是不尊重倩雲。這丁兆豐借故去坐近倩雲,又乘機將手臂圍在她的肩膀——我更見到他的另一隻手在食桌之下有「其他動作」。倩雲總是掛上一個客套的笑容去「婉拒」他的侵入。可是空間狹窄,她無處可逃。
作為她「沒有血緣關係﹑不能說話卻聽覺正常﹑滿面于思﹑剛從外地回來」的哥哥,我狠狠地踢這油頭粉臉的二世祖一腳。
這二世祖果然痛得叫出來——像個女孩子!
二世祖知道是我踢他,就起來想跟我理論。
我怒目以對,落力扮演因為不能說話而情緒暴燥,護妹心切的哥哥,兇神惡煞地將這娘娘腔拉起來,扯著他的衣領,將他壓在牆上。但我沒有打算動手打他——絕不可以在公眾場合惹人注意。
可能我太投入「角色」,倩雲起來制止我。我才將那二世祖丟下來。
倩雲為我打圓場之後,二世祖落荒而逃。我跟倩雲才可以享用我們的晚餐。
我們回到下塌的小旅館。我先去洗澡,準備睡覺。
在我進浴室之前,倩雲告訴我:「我去拿冰。」
我點點頭。為免隔牆有耳,我以唇語回道:「速去速回。」
「嗯!」她嫣然一笑,就開門出去。
我洗澡之後,換上倩雲在進入這小鎮之前為我買的睡衣。
摸著電視遙控,我突然之間有一種莫名其妙的不安感覺——不過十分輕,只有腦裡閃一下。
我望一望門口——我剛才暗中估計,由我們的房間到自動販賣機及冰櫃只是不到一分鐘的腳程。倩雲應該在我洗完澡已經回來。
為何她還沒有回來?
冒著被人認出來的危險,我換上便服,走出去找她。
我先到冰箱及自動售賣機的角落看看。甫在入口時,我已經在地上見到倩雲拿來載冰的小桶。
望見那小桶及散在地上的冰塊,我不由自主握緊拳頭——同時整個身體也在震抖。
倩雲真是遇到情況!
我顧不得自己是逃犯的身份,行去走廊梯間,到處看看聽。。
我咬住嘴巴,不讓自己作聲,不放過空氣之中一絲動靜——希望抓到倩雲所在的一點提示。
這時,我望向遠處一間房間;心裡產生一種我不懂得形容的感覺——也許用「靈感」兩字比較適合。
我左顧右盼,看看走廊有沒有其他人。然後我將耳朵貼在門上,希望聽到房裡的動靜。
其實,我這樣做是沒有可能知道房裡的人在做甚麼。可是,我又希望從中得到一回線索。
「...乖乖地別掙扎...沒用...」
「哈哈...遇到...」
「幸好...」
「你們!」
那是倩雲聲音!
我立刻用敲打房門——敲了好幾回。
終於,有人開門。
「我們沒有...」
我甚麼都不理會就推進去,見到之前見過的二世祖俯臥在床上。在他之下是有一個人。
另外,有兩個男人按著那被二世祖壓在床上的人。
那人極力抗拒二世祖的淫吻,別過臉來——是倩雲!
我沒有一刻遲疑就衝進去,卻被開門的人從後攔住我。
我跟他扭打起來。即使我從來沒坐監,這紈褲子弟也不是我的對手。所以,我只用了兩三下拳腳功夫就將他擺平。
我咬緊牙,仍扮著不能作聲,立刻撲去那二世祖旁邊。
二世祖別過臉來看一看:「是倩雲的哥哥!」
我轉身往後。那本來跟我糾纏的人已經拔出刀衝過來。我抓住他,一起倒在隔鄰的床上。
我壓著那人,在床上角力好一會。在角力之中,我感到一點不對勁。於是我翻一翻,讓自己臥在床上。
「霍!」那人重重地壓在我身上,刀子掉在我左邊臉頰的旁邊。
「糟糕!」
我沒有浪費一分一秒,立刻將刀子拾起來,翻起來開始進攻。
我首先見到的是那姓丁的——他拿著高爾夫球棒,呆子一般站著。
乘著他沒有意識去攻擊我的優勢,我猛然地在他的頸上劃一刀。他還未反應過來就倒下來。
我迅速轉向他的同黨,衝向他的心臟刺下去。
眼見他最後一個同伴都被我幹掉,原本將倩雲按在床上的人放手。
他縮在一角,惶恐地舉起手來;繼而跪下來哀求:「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我拾起高爾夫球棒,望著這要嚇得要尿褲子的二世祖;又望望仍躺在床上的倩雲。
我想我在那一刻,已經沒有「放人一馬」的選擇。
我狠狠地揮著球棒,擊向那人的頭。
那人應該在我敲了兩三次之後已經死了。可是,我沒有停手--我一直敲到我感到沒有意義才停手。在我停手的時候,那人已經沒有生命氣息。
我隨意將球棒拋開,過去倩雲身旁。那時候的她已經不懂得反應過來。
我沒說一句,就靠近她,正想伸手將她抱起來時,倩雲輕躍起來,牢牢地摟著我。
我感到她的震抖。
就這樣,我將她抱起來,回去我們的房間。
「我的陳述就是如此。」
「被告,你可以坐下。」
我坐下來;高高在上的法官望一望文件。
接下來,就是檢控官的刑期建議。程律師早跟我說,他的目標是保住我的性命。
不過,這一刻,對作為罪犯坐在法庭的我,能不能保住性命根本不是重點。
我只是想求一個贖罪的方法,僅是如此。
太陽才升起來,兩個獄警已抵囚室門前。
剛洗臉的我起來,站在囚室的中間。
「轉身,面對牆壁,將雙手放在頭上,跪下。」
我按著指示,轉身背著他們,將手放在頭上,然後跪下來。
兩個獄警在閘門打開後進來:一人在我的腰間纏上手銬和鐵鍊,另一人為我扣上腳鐐。
「侍候」雙手的獄警將我的左手拉到我的腰間,扣上手扣。然後兩人將我拉起來。
步出拘留所,我望上晴朗的天空,吸了一口清新空氣。
雖然身體受到限定,但是在那一刻,我內心感到十分輕鬆。
「...被告本身已經是被判五次終身監禁的犯人。他乘著監獄暴動,脅持監獄獄長的女兒,偷取他的汽車逃走。他已經觸犯兩條罪。最後,他殺死四個人——而他也承認在殺死最後一人時,是『殺傷過多』。儘管他是另一宗罪行而再次殺人,但是殺人是最不能饒恕的罪行。被告之前就是謀殺罪成而入獄。而他這回是第二次殺人,可以說是重犯。我國法律對逃獄時間殺人是有明確的刑罰:就是死刑。之前我已經說過:被告是重犯。足以証明監禁對他沒有警戒的作用。我在此懇請法官閣下依照法例,判處被告死刑。」
檢控官坐下。法官望一望我身旁的程律師。
他站起來,開始他的陳詞。
「法官閣下,正如檢控官所說:我的當事人是第二次殺人。不過,檢控官也提過:他犯案的時候,有另一宗罪案進行之中——就是所謂被脅持的辛倩雲小姐被本案的其中一名死者丁兆豐強姦。當時,我的當事人只想到要將辛小姐救出來。另一方面,他的生命也受到威脅——不單另一名死者用刀意圖刺傷我的當事人,丁兆豐更拿起高爾夫球棒想擊殺我的當事人。他的行動第一個出發點,是救人心切;第二個出發點,才是自衛。」
接著,程律師拿起一封信。
「辛小姐為我的當事人寫了一封求情信。請容許我朗讀出來。」
法官點點頭:「請讀出來。」
程律師將信打開:「法官閣下,我的名字是辛倩雲,是傲正服刑監獄獄長辛道宏的獨女。在過去的兩年,我每週末都會為傲先生演奏音樂。每一次,他都是被扣上手銬。我就覺得他是一個明白自己處境,絕無打算討好別人的老實人。
在監獄發生暴動時候,他對三位同伴跑去家父辦公室所在尋找我ーー剛巧,我正前往那兒去看看家父幹甚麼仍未回宿舍。在他那三位同伴協助之下,我作為被脅持者與傲正離開監獄。我們在一個森林躲藏。期間,他沒有對我作出任何無禮的行為。
事發的一天,我們得悉監獄暴動已被平息。傲先生也打算帶我回去自首。可惜,我們就發生這個意外。
傲先生一切的行動都是為了保護我。是次犯案,情有可原,罪不至死。懇請法官閣下網開一面,不要判處傲先生死刑。求情信內容到此為止。」
程律師將信交給庭警,讓他遞給法官。
「我的當事人是承認所有罪名,而他在第一次犯下殺人罪也是認罪。顯然,他沒有逃避罪責的打算。鑑於這一點,我的當事人並非一個不知是非的喪心之狂。兩次殺人,他都是在殺死最後一人時是『殺傷過多』。這不是他的習慣,而是痛苦的表現。現在,我的當事人已經受到良心責備。我懇請法官閣下判處我的當事人無期徒刑。」
程律師坐下來。
法官拿著倩雲的信看一看,接著他望著我。
「被告,請站立。」
我跟程律師站起來ーー法官應該有決定了。
「聽過你的陳述,控辯雙方的刑期建議,以及辛倩雲小姐的求情,我看到你的坦率以為承擔。而我也看到你一切行動的原因。可是,法庭對殺人此等罪名是不可能無視它的嚴重性。你的處境,十分遺憾,只有一個結果...」
囚車再一次將我送回這所監獄。
只是,這一回的入口不是上次的一個。
我的身旁,沒有其他同行的囚犯,只有荷槍實彈的獄警。
囚車車門打開的時候,除了幾個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獄警之外,我也見到獄長。
雖然他仍是一張鐵面,但我在他的眉宇之間看到一絲哀傷。
我掛上一個微笑:「獄長先生,我回來了。」
他只是微微地點頭,沒有答腔。
我被押進囚舍。獄長將我身上的銬鐐解下,我就將身上的所有衣物脫下來,完全赤裸站在負責搜身的獄警之前。
獄警們沒有放過我身體的每一分每一吋,以確定我身上沒有違禁品。
他們派發一套灰色,無領,像是醫院技工制服的囚衣給我。
穿上囚衣,拍過檔案照片之後,獄長說:「面向牆壁,雙手舉在身旁,手板向後。」
我依著指示去做。接著,我感到一隻粗壯的手將手銬扣在我的手腕。
在我的雙手穩妥地扣好在我的身後。獄長拍拍我的肩頭。
「行吧!」
在獄長及一名年紀跟我相約無幾的獄警押送之下,我到了我的新囚室。
囚室的閘門打開。在號令之下,我進入囚室。囚室閘門關上之後,我才將仍被手銬扣在背後的手從閘門的小窗口伸出去,讓他們解開。
手銬解開之後,我行入一步,然後才轉身面對著獄長及那年輕獄警。
獄長從頭到腳,再從腳到頭打量我。
我抿一抿嘴。我跟他上一次見面就在他的辦公室——當時,我不單跟他說出那個壞消息,也向他承認罪行。
「傲正...」
我站直起來。
「作為一個死刑犯。你每天有一小時在外的活動時間。每兩天洗澡一次。每星期有人到來收集衣物清洗...」
聽起來跟之前在拘留所的生活沒有多大分別...
「...每次離開囚室,你都要扣上手銬...另外,你沒有探訪的限制。」
聽到這一個,我輕輕地昂一昂頭。
「意思是你的親屬及辯護律師可以隨時到來探望你。每次的探訪時候有兩個小時...」
我點點頭,示意明白。
「你,需要我們通知你的親友?」
我搖搖頭:「沒有需要。」
「真的沒有需要?」
「真是沒有。」
獄長緩緩地點點頭。接著他向我介紹那年輕獄警:「他叫于胤。雖然只是比你年長兩三年,不過在這裡工作十年。如果你有甚麼需要,就跟他說。」
「明白,獄長先生。」
獄長和于長官離開之後,我環顧我的周圍:床舖不需要我來整理。廁所,洗手盤...基本囚室會有的東西都有。
我留意到床舖有一張紙,就拾起來看。
「正:我知道你已經回來。雖然不是回到大樓...大家很好,放心。我有屬下在你那兒行走。如果你有甚麼需要,就跟那人說。他知道你的長相,會定期找你。剛」
我笑一笑:「剛哥,謝謝你!」
這囚室就成為我吐絲結繭之所;等待被抽絲——也就是被領去絞刑架受刑的一日。
懊悔?沒有。反而我覺得這是最好的結果。
唯有這樣,我才可以抵償我的罪。





-01.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