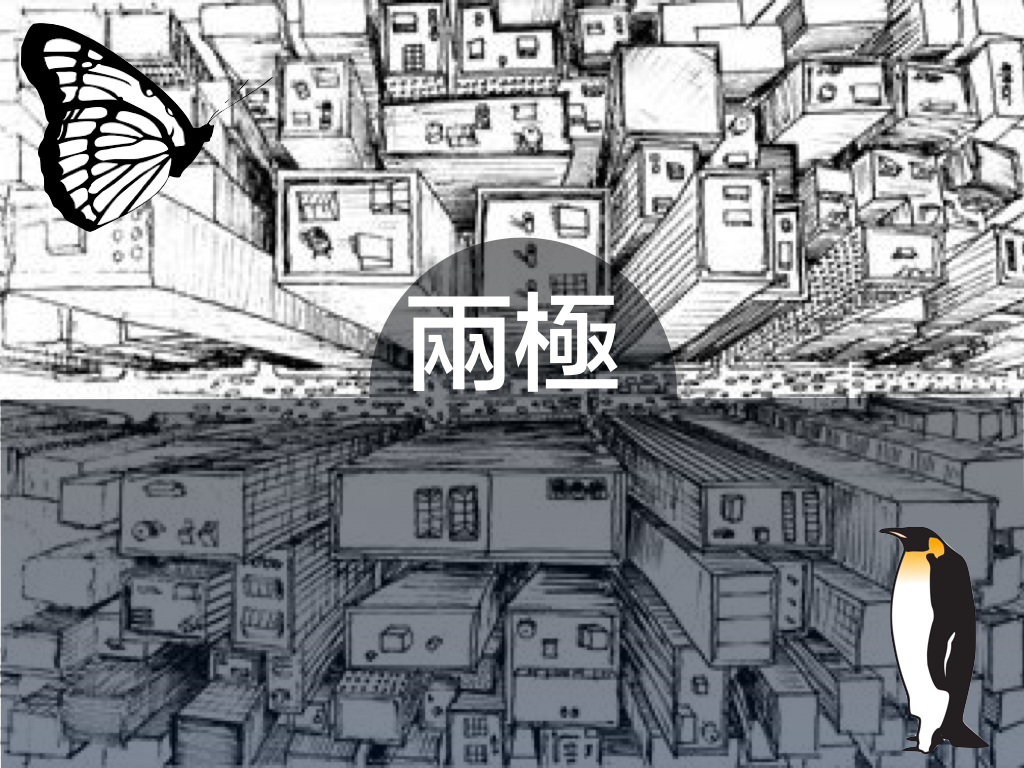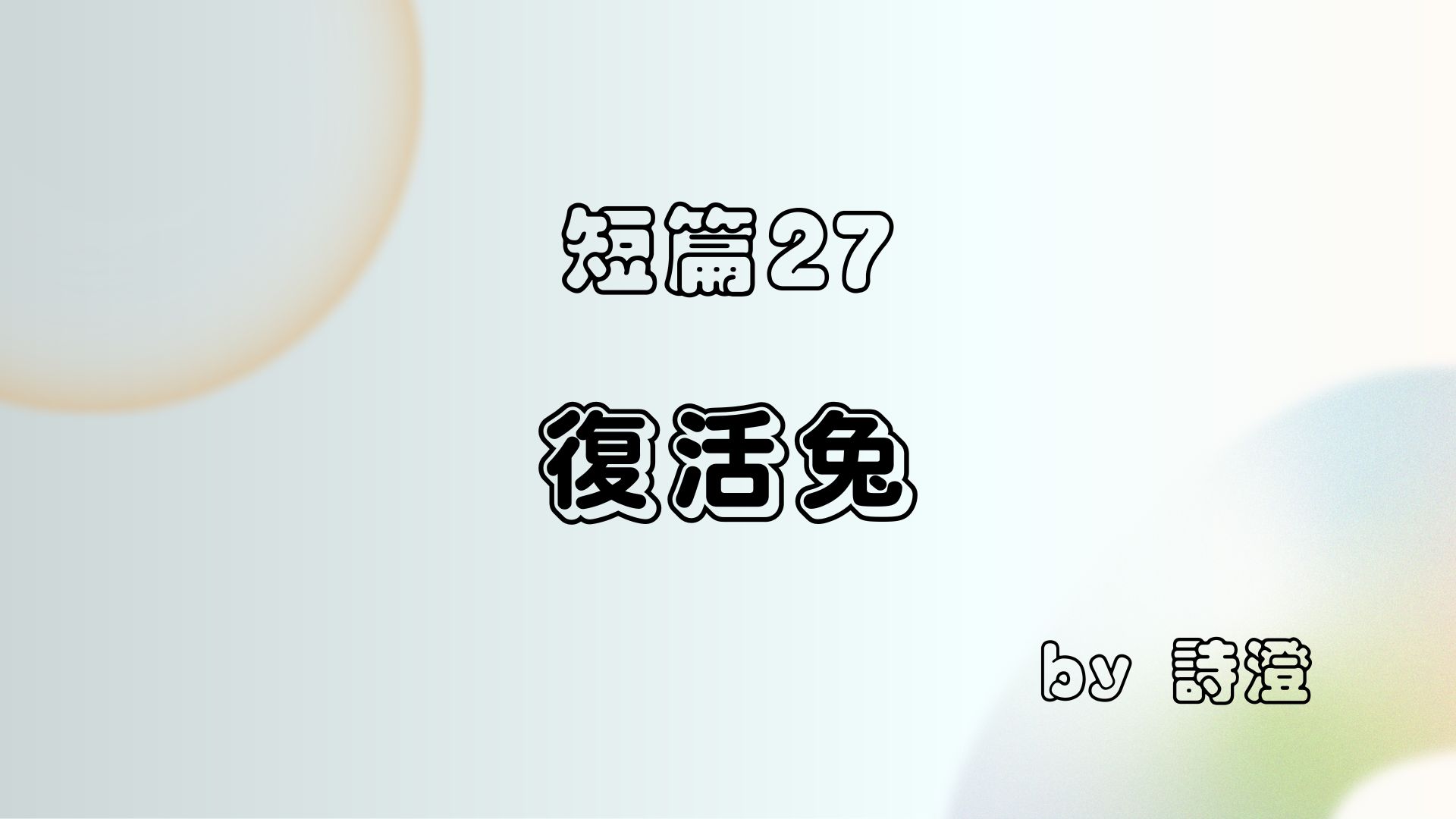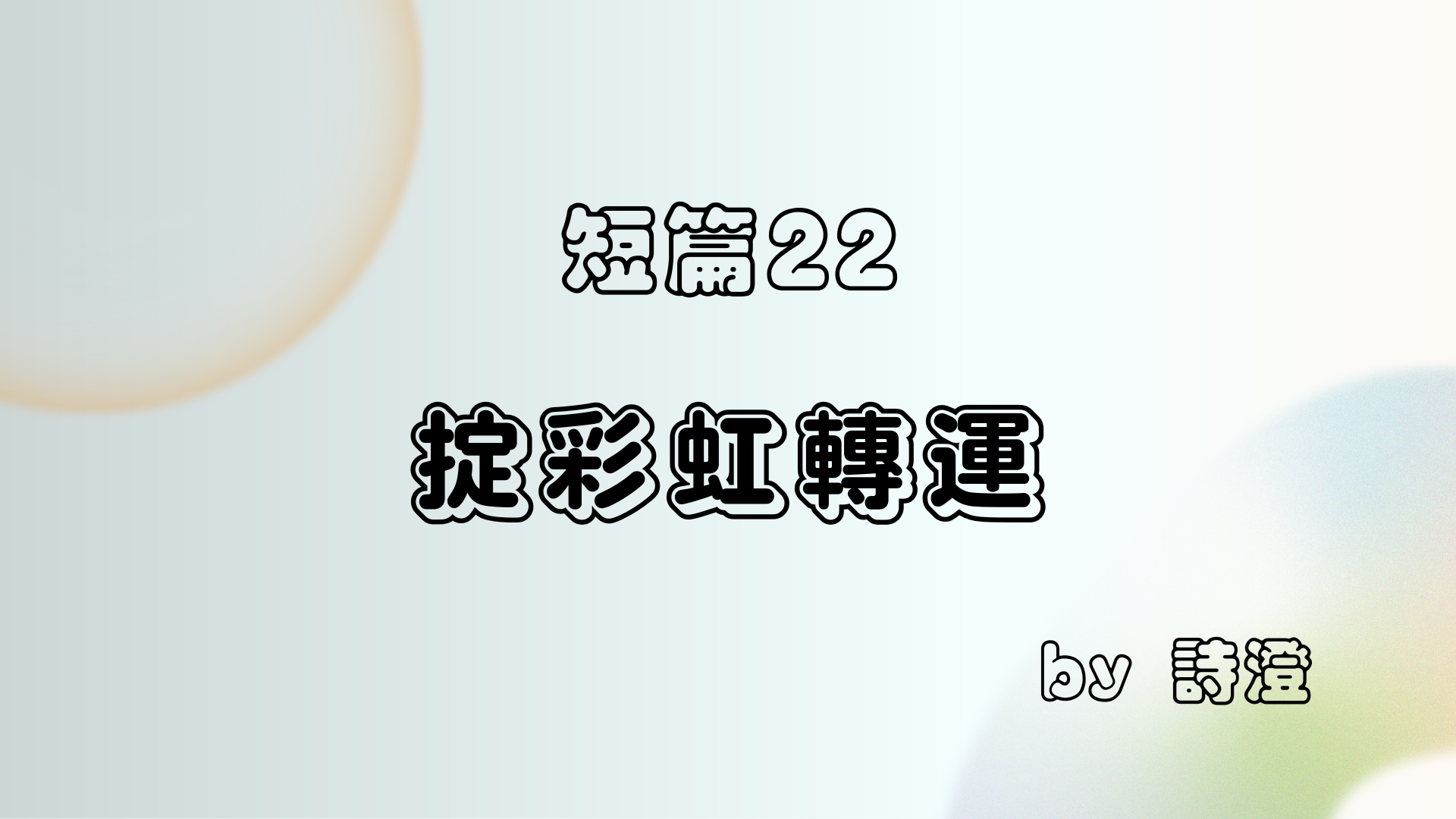我總認為對於充滿熱誠的東西,於人生中不能太多,畢竟,人生苦短,而熱誠的基本門檻就是時間,所以,一個人倘若戀上太多事物,這充其量也只能稱作興趣,談不上熱誠。
而我,於三十有一的這段人生中,便只曾對三件事報上真切的熱誠,從前是籃球,近來是咖啡,現在是與朋友到網吧打《Left 4 Dead》。我知道,就世俗眼光而言,首兩項絕對無傷不雅,至少,當你挺起胸膛大聲地向別人說自己對籃球與咖啡滿載熱誠的一剎,對方即便不報上七分佩服三分尊敬,也不至對你評頭品足,但若然是說到懷著一腔熱血與朋友到網吧打《Left 4 Dead》,那準會教人不敢恭維,換來三數聲的竊笑不在話下,極端點,更可能得到一對不屑的輕蔑眼神。
就此,我從沒怪責過旁人,因為於網吧內那髒透的洗手間裡頭,我都曾不下數十次看著鏡中的自己,然後狐疑著眼前這位三十出頭的男人在這裡幹甚麼。
無奈,我不能欺騙自己,這幾近過時的喪屍射擊遊戲,委實是會讓我體內流淌著的血液沸騰起來,但說得確切點,教我投之以誠的又並非單憑這遊戲的吸引力,還有網吧與戰友這兩項配套,所以,我決不會說自己對《Left 4 Dead》充滿熱誠,而是對於與朋友到網吧打《Left 4 Dead》這全套組合行徑,我帶上了一份熱誠。
至於,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遊戲,我沒打算作太多介紹,畢竟,話不投機半句多,總括的說,就是一個打喪屍的過關遊戲好了。而著實,我們亦已徹底地「打爆機」不下百次,只是我們於這遊戲中領悟出另一玩法來,所以,這份熱誠便被無止境的延續了。
新的玩法是一門對時間的挑戰,於收費為十二元一小時的網吧內,我們的目標便是於這有限的付費時間內「爆機」,遊戲的目的不再落於喪屍的殺戮,而是技術性的逃亡,從鐵閘打開的一瞬,便各自為政地頭也不回的向著那拯救車或飛機直奔,任憑喪屍們擦身而過,哪怕戰友被圍剿至不幸倒地,也絕不施以援手,亦因此,最後能成功登上救援之車的,往往都不會是一隊人,總有一兩位於跑道上壯烈犧牲,名正言順"left for dead",而重點是,大多數我都會淪為捐軀死侍,直直地躺於泥濘地上,一邊任由喪屍們的魚肉,一邊看著前頭隊友們的背影漸遠。
就這樣,於一趟趟的疾走中,我透徹的看到了人性,有時,可以比喪屍更恐怖。
今天,無聊地在網上看了《有樓萬事足》這節目,看著一位九十後有樓女生侃侃而談地述說著自己如何於這納米之都成功上車的經歷,不知怎地,我不禁聯想起《Left 4 Dead》這遊戲。委實,這年頭,多少人何嘗不是走過那畢業的大閘門後,便頭也不回的向著那輛車直奔,過程中放棄了多少也不過是過程,只要結局是車已上便於願足矣。
想到此,我有點恨自己,為何熱誠只能投於虛擬中,而更為氣憤的是,即便是虛擬中我也甚少能全身而退,成功上車。
思索著自己的失敗,嘆過一口氣,抖擻一下精神,我便拿起電話,於群組中發了個短訊給戰友們「今晚,我要上車!」
然後,便繼續播放下一集的《有樓萬事足》,並靜待他們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