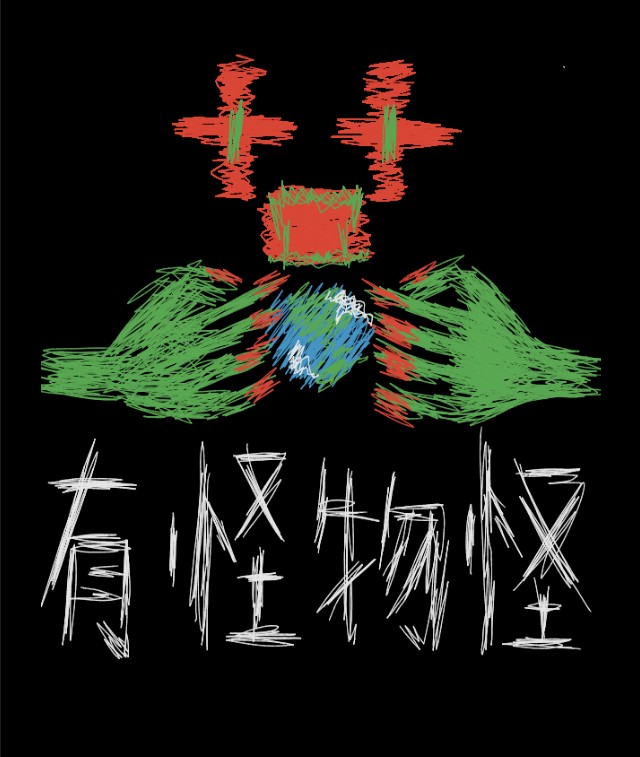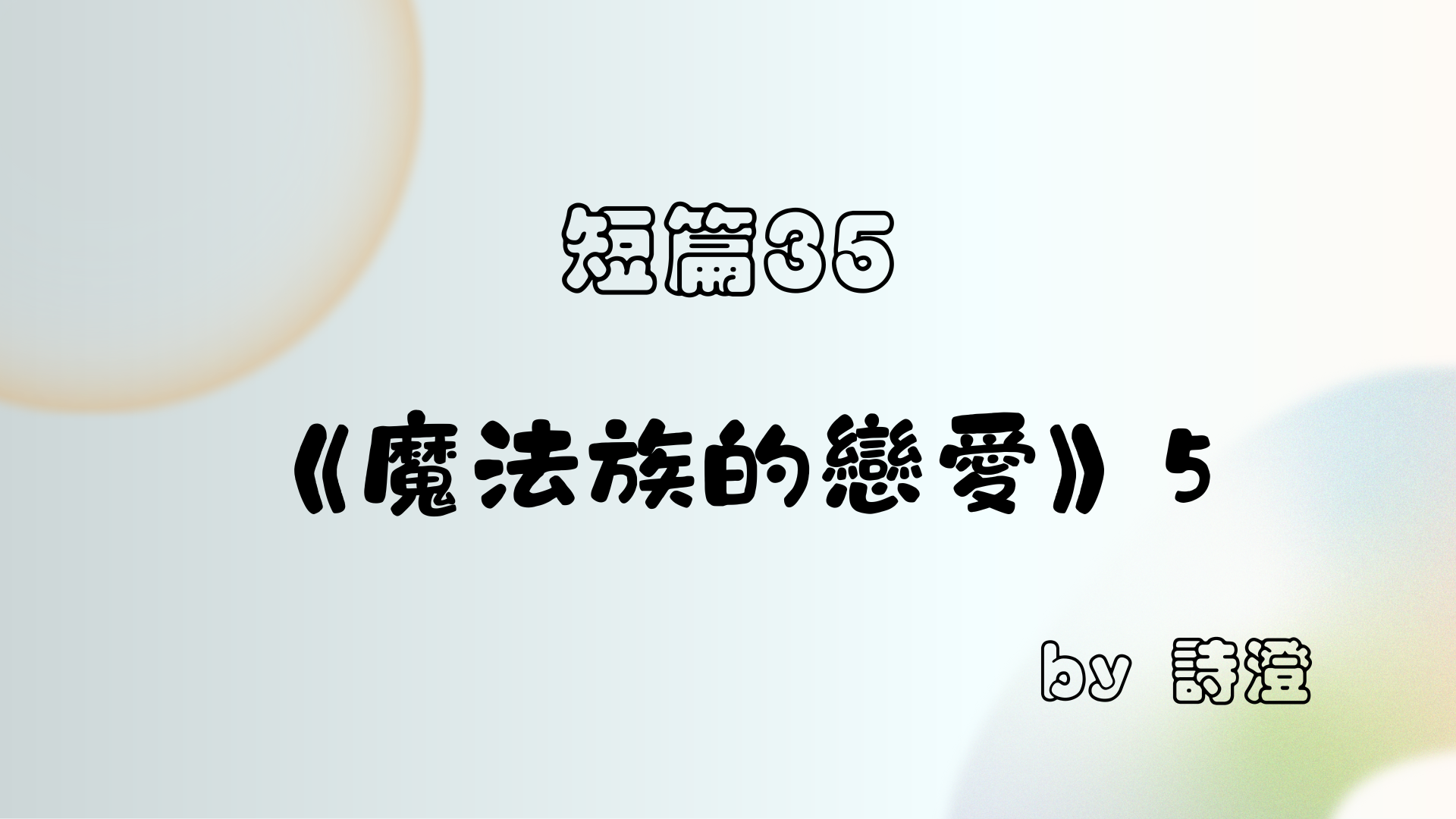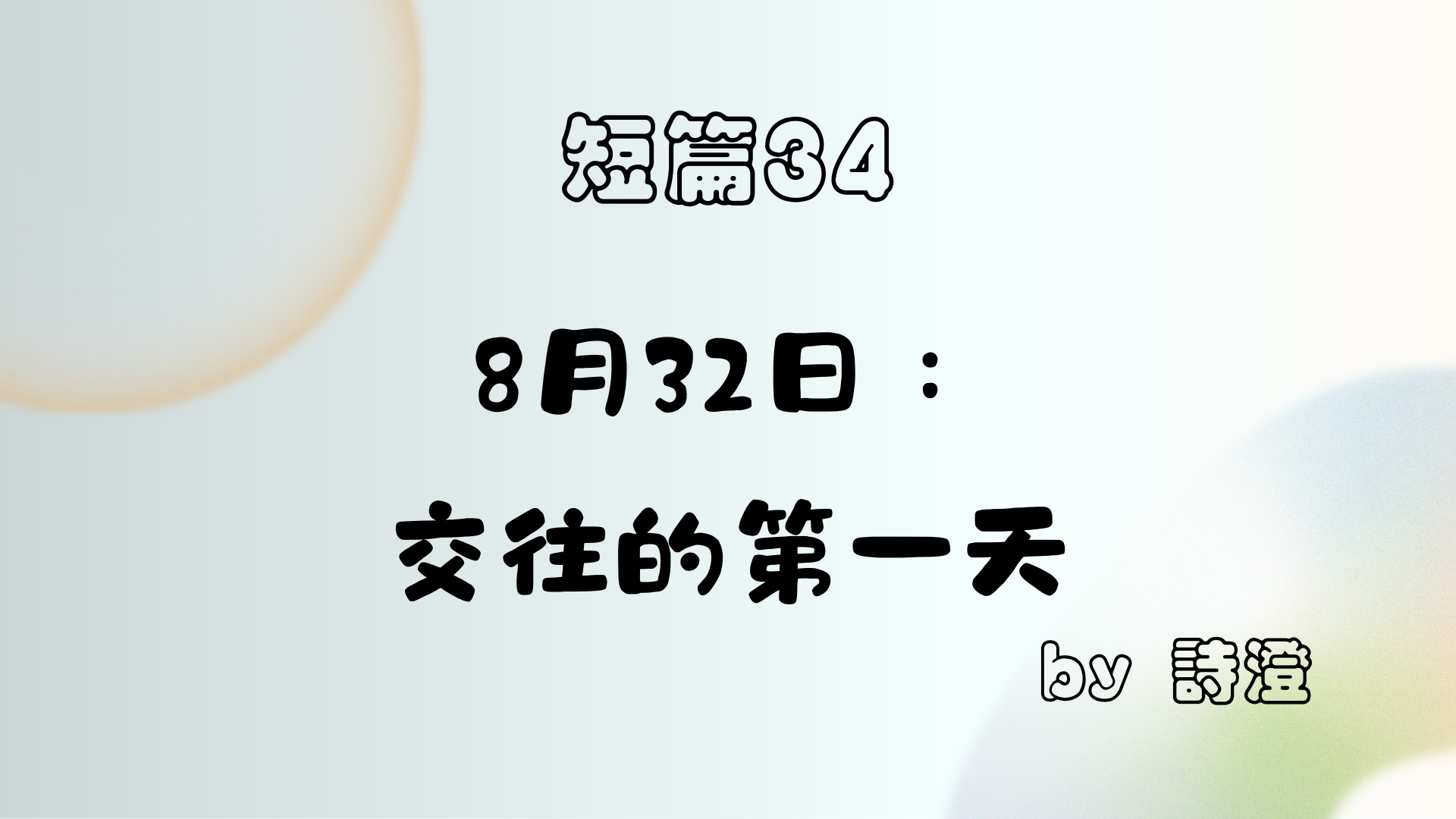炎夏初至,她來到了這個陌生的地方,這裡離市區不近,交通挺不便,她沒有跟朋友一起,只是一個人來到這裡,她是來度假的。
她背著一個小小的背包,包內有少量替換衣物,除此之外她身上就只有錢了,那只夠幾天的錢。
這裡有個很大的海灘,海灘旁一個小小的士多有一個年輕的男生,難得看到這個來自城市的少女,急不及待的走上前,熱烈地介紹那裡的名勝,並表示可以帶她遊玩數天,更介紹自己家開設的旅館。
少見人蹤的他對於一個同齡異性是很好奇的,他沒有太多的機會認識一個跟自己生活背景不同的人,更何況是女性?
沒有行李的負擔,她很快就叫他帶自己去不同的地方遊玩。
那個地方其實不大,卻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座殘舊的廟,他說在數十年前這裡還是香火挺旺的,但是近年來了個新的宗教,這廟就被冷落了。
她拿出電池還有一半的電子相機,拍了一張廟的門口照,照片中還把廟前的獅子石像也拍了下來。
獅子石像被雨打過多年之後已經不再勇猛了,缺了一只耳朵的牠,反而有一種滑稽可笑的感覺。
更有種久歷滄桑的淡淡哀傷,他被冷風吹了吹,清醒了過來後無意發現她的眼角有點淚光,
他慢慢退了半步,在衣袋拿出面紙,沒有立時的遞給她,只是默默站在她背後,數分鐘後她也醒了,回頭一看那個在太陽底下的他,她面上抹上一絲的弧度。
她順手的接了面紙,抹了抹面上的水點,小心的把它放好,再次叫他帶自己去不同的地方。
他帶她去了自己以前就讀的小學,那個校園很簡陋,有個小小的操場,課室也只有數間,樓高只有三層。
她在玩那個早已褪色的跳飛機,他在旁的乾地上坐了下來,喝了口水,看見她的笑容,他也忘記了室外的溫度其實很高。
正午的天氣很好,白日無雲,萬里晴空,他們去了他小時常吃的一所小吃店,吃了價位便宜的便當,他說那顆滷得通透的雞蛋是必吃的,她沒有女人應有的猶豫,很爽快的點了一客,一客兩顆,不知是玩笑還是想多謝他,她夾了一口的滷蛋餵給他的嘴邊。
他輕然一笑,張口一咬,然後不放口,看到她面紅了,他才放開那對充滿自己愛念的竹筷。
她沒有換筷,而是夾了另一顆滷蛋細細品嚐,發出那勾人心神的叫聲,好吃!
短途的快樂,那分開的時刻會是多麼的痛苦。
人與人奇妙的關係,在於有些人可以在三數秒之間可以跟你混熟,變成好朋友,這就是人的奇妙之處,相處本是一件微妙的事,不是言語能解釋的,不談。
吃了便當後,他倆在小吃店乘涼了半小時,待得天氣涼一點才起行。
下午他們去租了單車,遊了半條村的時間,那時天黑了,他帶她還了單車,送她回自己家的旅館。
那時候外出工作的父親回來了,他的父親很熱情豪邁,對她的態度很放鬆,把自己珍藏很久的東西都拿了出來,若不是他母親的阻止,她應該會醉倒吧,他只能陪笑,對於父親他是尊敬的,一個大男人出外工作為了一個家,他一直都很想自己能成為這樣有承擔的人。
夜空掛了一幅美妙的星畫,皓月也出現爭一線的輝煌,他母親照顧喝醉了的父親,而他則帶她回了自己的房間,告訴她晚點帶她外出一回,她洗了個暖水澡,換了一套比較輕鬆的衣服後下樓了。
見他帶了一塑膠袋子,似乎載了不少東西,她沒有問只是默默跟著他,他帶她去了村子中央的大湖旁,那兒有個小小的碼頭,也有少量的村民會在這裡休息,他把袋子打開,是小型煙花。
她眼睛滾得豆大,拍掌連連,他連忙拿出火機,為她點了一枝,火花之中影出了她的紅臉頰,他笑容更甚,沒有說話只是和她一起把玩煙花。
那夜凌晨,只有他和她,兩人彼此知道心意,卻只是把一切留在這時間。
她會記得這個日子。
他也會記得這時間。
沒有深一步的交流,兩人回到旅館,眼睛甫一合上,天也光了。
她梳洗過後,看了看掛在牆上的鐘,八時正。
他上樓的聲音被她聽到了,她狡猾的一笑後躲在一角,就在他敲門沒人應門後,他提著膽進入房中,看到空無一人時,虎軀一震,回頭之際,她就撲了出來,怎知兩人撞在一起失了平衡,大家就躺在床上了。
女上男下,女的撐了雙手令自己不倒下,但兩人面額相近,呼吸可聞之時,她竟然閉上雙眼,唇齒閉合,向下侵襲。
他緊張的快要死去,忙著閉眼,很快就感受了那草莓的微溫,有淡淡的薄荷味道,這是他的第一個感覺。
三秒過去,她退出了這份溫馨,在他耳邊說了句:「就當是昨天的回禮吧。」
他呆滯了數秒後她已經下樓去了,在旅館的飯堂中吃著早飯。
吃過早飯後休息了一小時,他提議不如去釣魚,她沒有拒絕,但心情顯然有些傷感,當然他還未發覺。
他父親不用上班,很主動駕車載著他們去大湖,母親在其後也來了,帶了一個燒烤爐,似乎是有意在湖邊午餐。
他父親雄亮的聲線,加上專業的技術,很快就好有不少魚獲了。
母親也在趕緊的弄些飯團,她學了一下釣魚後就來了幫他母親的忙,兩人好像挺談得來,有講有笑的,他看在眼底好像夢一般,他父親也不期然的一笑,比之前又更努力更大聲叫喊。
「烤好了!」
湖中鮮加上一點早上剩下的煎蛋卷,配上一口飯團,她顯得很滿足,主動的泡了茶為大家添了一杯。
大家樣子都很滿足,彼此談了天馬行空,時間就過了不少,突然的一聲悶雷,把她驚嚇了,他很自然的抱著他,父母兩人當機立斷收拾一切,著他照顧好她後,天就無情的下起豪雨來了。
事態突然沒有雨傘,他只能把上衣脫了為她遮掩一下,最終也避不了著涼。
她病了,發了個不合時的燒。
請了村中唯二的醫生來,開了服藥後她就睡了。
那時他無聊得發悶之際看到了她的相機,他想了一下看一下她近日拍的照片吧。
一直看著,大多是花草,有時是自己的呆臉,當然也有他的父母,他的窩心一笑後看到了一個男人的照片。
他很年輕,不比自己差,樣貌頗俊,旁邊有她勾著他的手臂。
他嘆了一口悶氣,好像整個人被抽乾了似的。
只是看到這裡就放下相機,然後沒說什麼,繼續的默默照顧她,換毛巾,餵熱粥,該做的他都做妥了。
第二天醒來,她好了,但他不在了。
她問了聲他的父母,說他一早就出門了,沒有回來,她沒有多少的懷疑,吃了口早餐就沒胃口了,因他不在,她只有拿自己的相機來看看。
她快快的看完了,就在最後的照片中,即他看到的照片時,她毅然的按了刪除鍵,畫面中的歡樂消失了,但他不知道。
她收好相機,去樓下看看他回來了沒有,當然是還沒回來,她只好再次回到房中,把背包中的日記拿了出來,振筆揮毫了兩句就寫不下去了,她向他母親要了杯熱水,送了服藥,倦意就來了,小睡了片刻,她發現他坐在自己的床邊,但目無表情的。
她坐了起來,雙手緊抱著他,但她發現他很冷,跟昨天的他完全不同。
她流起熱淚來,她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只是他沒有任何回應,只是慢慢的說了句。
「我送你去車站吧。」
她最後的防線也崩潰了。
她永遠不知道,照片中的他是他的弟弟,死了兩年的弟弟。
原來他的弟弟在城市認識了一個女朋友,也因她遇到了車禍,就在兩年前他第一次去了城市,陰差陽錯的,她遇不到他。
她抹乾了眼淚,他冰冷的軀體動了,但著不自然的活力,走了下樓,她沒有行李只是把衣服都收拾好後也下樓了。
他一手拿了一個大的木盒,是村子傳統的工藝,是用來送給重要的的人,他一直走在她前面,沒有說話。
她很納悶,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但她也開不了口。
就在車站前,他把手中的木盒交給她,對她笑了最後一次。
「其實... ... 」
她把說到口邊的話吞了口去,沒有說下去,上了那可能不會回頭的旅遊車。
她坐在最後一排的位置,清楚看到他的寂寞的背影,他沒有回頭,她很失望。
就在車開的一刻,她打開了木盒,有一封信躺在盒中,她來不及讀過就哭了起來,車行漸遠,她終於有勇氣打開它。「你好。 原 來這幾天我都沒有問你的名字,就連弟弟也沒有提起你的名字,你就像一個新的人來到我世界,我很高興,你對弟弟的愛是真的,這幾天的相處,我知道你是好女 子,這是我的親身經歷,騙不了人。對不起,我私自的看了你的相機,若果不是我也不會變得如此冷漠,我知道你還緊記弟弟的愛,我知道他是很好的男人,不會令 女人傷心的,這是父親的血統,不會錯的。這樣的話那就讓當那個狠心人,為這段小小的插曲劃一個句號吧,多謝你的愛,原諒我這個壞人,這個令你傷心的壞人。 P.S. 盒中有弟弟留下的草帽就留給你吧。 珍重」
馬路上只有留下兩行車痕,也許是她的淚痕的倒影,也許是他雙腿的遺證。
兩年後的他來了城市,是父母親交代了一門相親,城市的空氣很俗,令他很不舒服,在好心人的提點下,他找到了相親的地方。
他看了看招牌竟然只是一間咖啡廳。
他被安排在一個角落位置,等了十五分鐘左右,她來了,戴了一頂淡黃的草帽,一身輕裝。
他被震撼了一下,然後會心一笑,再沒有冷淡,帶著一份勇氣。
「你好,請問可以怎樣稱呼你?」
她開口了。
「叫我壞人吧。」
他使壞的把手指放在下巴之下,做了個「V」字,很老套的喜劇橋段。
然後兩人彼此互相取笑,就像重新認識了一遍。
時間已經不重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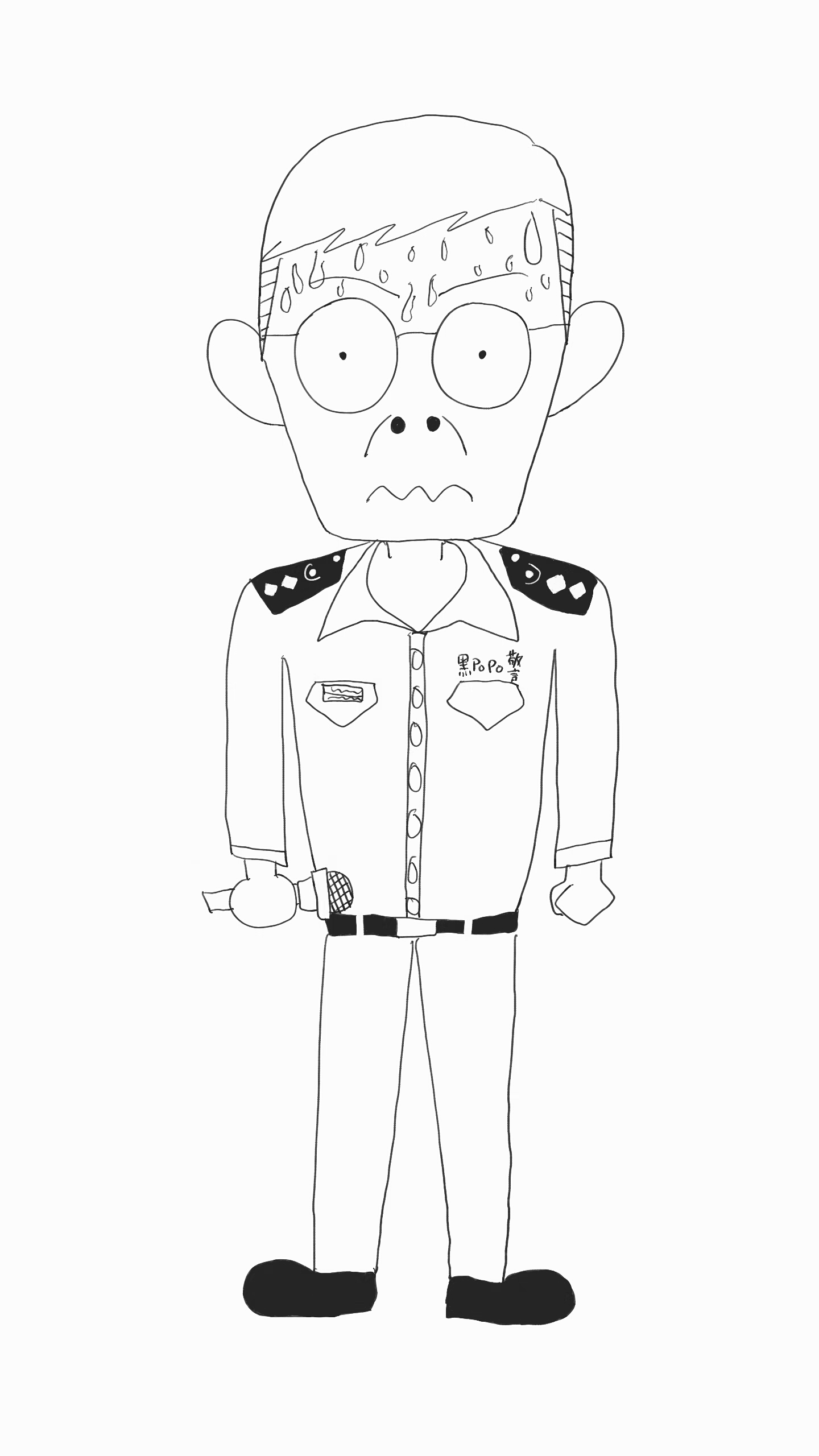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