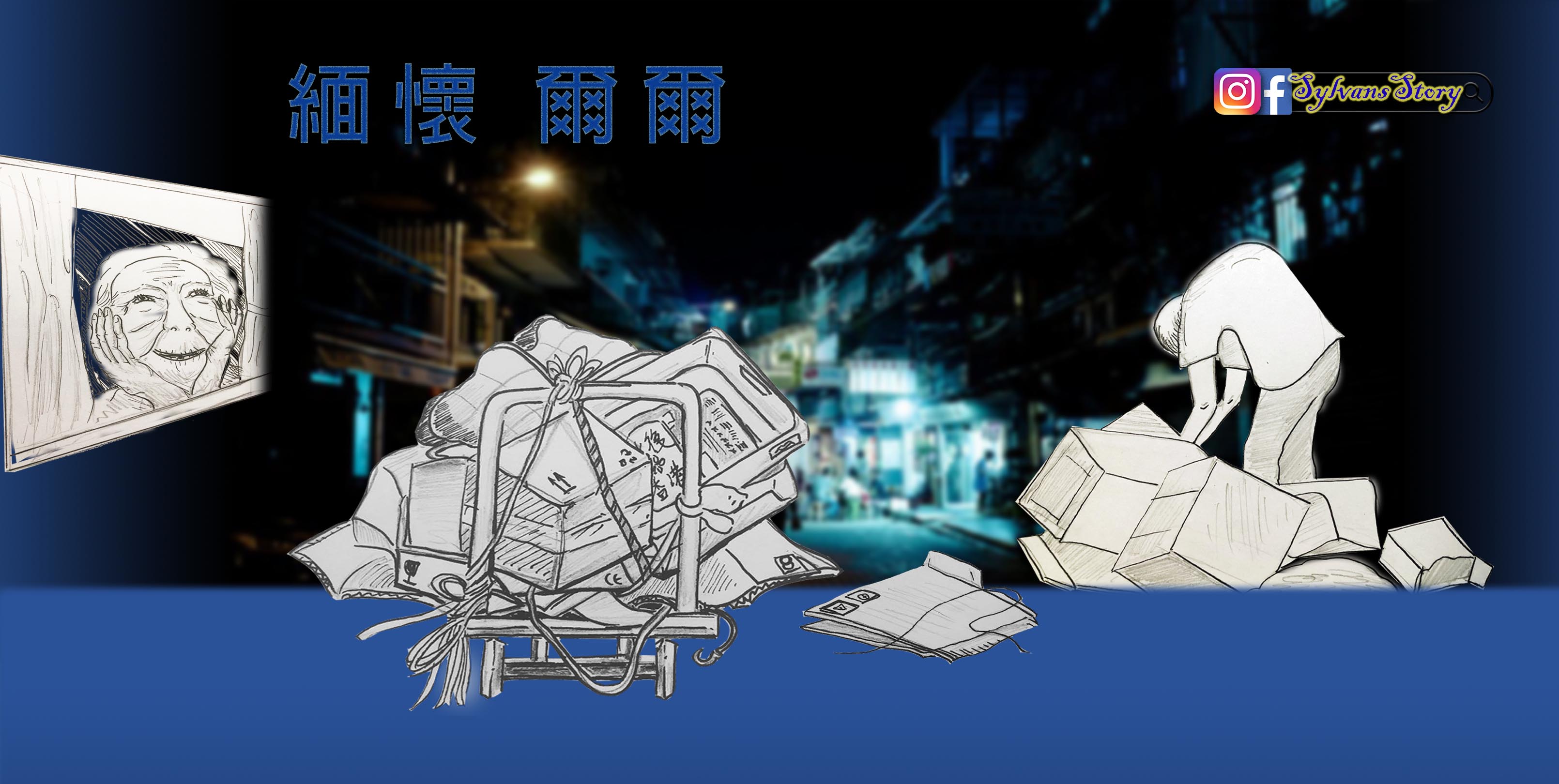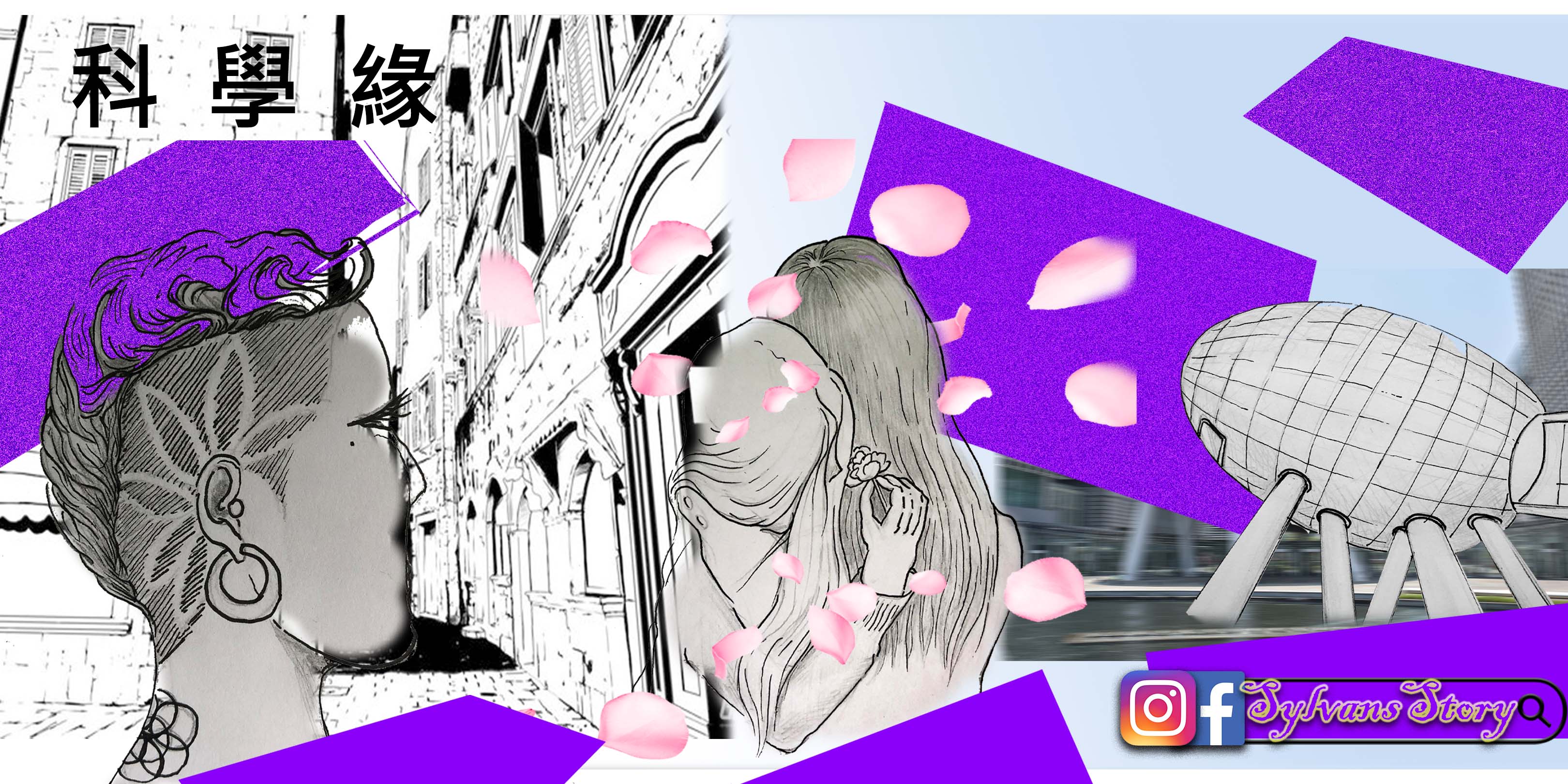辛勞了一整個上晝的李大一正在悶熱的倉庫角落享用他的稀粥和饅頭,這算是他一生努力幹粗活換過的最好待遇了。
「長鼻子、藍眼睛,他們說話你要聽;
或傭人、或精英,所有規矩他們訂;
要緊守、要記清,做錯難淆到天明;
不反抗、不作聲,望見白髮盼流星;
是罪過、是反醒,前人作孽今人清…
在烈日當空的集中營廣場上,孩子們吟詠童謠的歌聲傳到了李大一的耳際。令他心忖回想,成年後的他,除了這個短得可憐的中午飯時間和每晚規定好的六小時睡眠時間外,就只剩下兒時的強制性教育最叫他歡容放鬆了。
「長鼻子、藍眼睛…前人作孽今人清…
廣場上繼續傳來陣陣歌謠聲,李大一情不自禁地跟著念起來,
不竟這也是他兒時常常詠唱的一首。猶記得只要他們班的同學能夠捱過中午的日曬,異口同聲地詠唱一百遍,便可得到一些甜食或糖果。儘管很多時候他們早就被日曬得頭暈目眩,儘管五十多人一個班的他們完成任務後所得的總是不夠分享,但他們仍然選擇賣力地吟唱,直至到嘴唇龜裂的他們大聲地朗讀完最後一遍。
「阿一,你有發覺接受強制性教育的孩子好像一年比一年少嗎?在洗牌之前,我族總數可是超過十億呢!」比較愚鈍的王立三疑惑地問大一,表情帶點不甘。
「三,這不是必然的事嗎?師長們都說過去了!
「怎麼說得過呢?」
「我是明白的,但是阿一,難道你甘心自己一出生便被定為罪人麼?」
大一咬了一口饅頭,若有所思。他心裡明白他不可能是一個天生的罪人,他對任何人都很好。但他知道他在這裡只能是個罪人,就像當年納稅分子眼中的猶太人一樣,只能苟且偷生。這些都是他們的同族老師-文強偷偷在課堂上告訴他們的,在規定的課程上,他們只能夠學會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字(如方向、基礎數學、度量衡、普遍物品名稱和自己的名字)及普通的溝通技巧(一些接受指令和對答的禮儀和應對)。
「李大一,難道你不記得文老師要我們銘記的那句話了嗎?」
「三,不要再說了!我怕下一個放假的人是你!」李大一突然想起了那個老師的下場,叫停了立三。
文老師消失了。
聽後來的替代老師說,他是因為擅自篡改課程,被革職了。亦有其他老師說他因教授了我們不該知道的事,被剪掉舌頭了。再後來,隱約聽見師長間傳出他因捏造及篡改國定法規課程被「放假」了,大家都變得人心惶惶。即使有同學問及他的事跡都只有支吾以對,只要一有同學提及納稅黨或猶太人,老師們便會驚惶失措,嚴厲地斥責他們不應該討論這種異想天開的無聊故事。
再過一段時期,便再沒有人提起過這個老師的消息了,就像他從來沒有出現過一樣。
縱然是如此這般,但老師的那一句話,一直在李一心坎中迴盪,並成為了推動他努力存活的座右銘。
「只要下一代學懂團結和勇氣,我族才有機會逃過全滅的厄運!」
這句話一直在大一心坎中迴盪,他一直偷偷收集有關納稅黨與猶太人的事兒,但是平輩得知的都不過是這些詞彙是「禁語」會引來壞事,也勸諫他不要再追問其他人了,以免遭遇不幸。
這天,李大一如常鍥而不捨地向人追問有關「禁語」,有人便建議他找倉庫的唯一老頭,或許會知道比較多,至少活得比我們久。終於李大一遇上了他-白頭翁-張貴平,眼看大慨五十餘歲,在集中營算是少有的老輩。大一戰戰兢兢地問了一個他最想知道答案的問題。
「張貴平檢察官,你知道猶太人為什麼有罪嗎?」
白老頭突兀地皺了一下眉頭,似是被突如其來的問題嚇到了,繼而反問他:
「小子,你是怎知道我名字的呢?」
李大一指指他的衣襟名牌,一臉期待著他的答覆。
「那麼到我問你了!你知道你們每日每夜搬運到倉庫的石頭和鐵塊有什麼用嗎?」
「我猜想是用作準備第四次洗牌的儲備,不是嗎?」
「臭小子,你真聰明!看來,你可以放假了!」
「放假?不!我要將老師的話傳承下去『只要下一代學懂團結和勇氣,我族才有機會逃過全滅的厄運!』難道你不想我族存活嗎?」
「單純的聰明或許在第三次洗牌後已不再管用。當貧富、強弱、貴賤,都被完全地統一管理,在沒有支派分黨,只有獨裁制度支配的體系下,人們需要的是安分守己。要努力自保,若能確保自身能存活下去,又何懼滅族呢!」說罷, 張貴平檢察官便命人將小子帶走。
「只要下一代學懂團結和勇氣,我族才有機會逃過全滅的厄運!」
他在這個沒有公義的世界,懷抱了希望,並在那張殘破的英文剪報上寫下了這句話。
諷刺的是剪報上的大標題—《第三世戰後的最後一批無差別異族屠殺將如期完成,歷時三十三年》。
https://www.facebook.com/sylvansstory
https://www.instagram.com/sylvansstory/
https://www.penana.com/user/71075/sylvans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