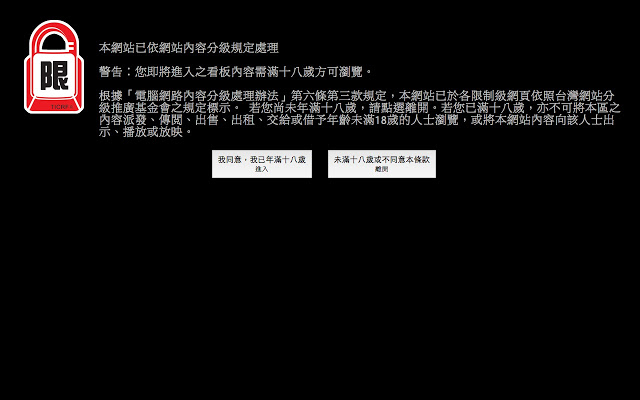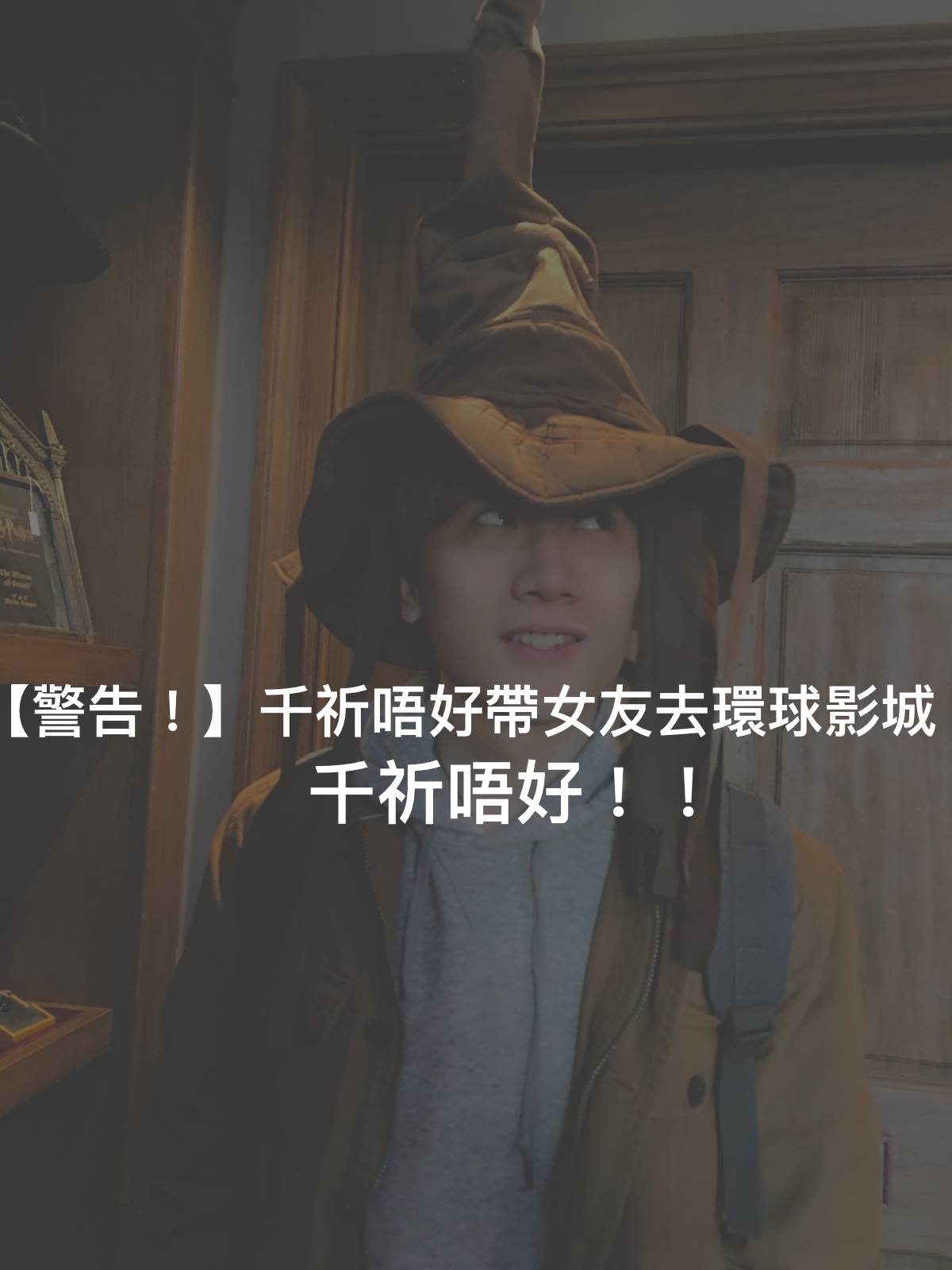仔細地查看每一個角落,有如慢鏡一樣,看著泛黃的相框﹑殘舊但整潔的飯桌﹑蓋著塵的一大堆光碟﹑通花的白色窗簾﹑早已超載的書櫃。
「做咩你好似第一次上嚟咁?」你一邊脫鞋一邊漫不經心地問。
「係咩?」我心虛地敷衍道。
難道不是最後一次嗎?我想記住在這裡發生過的每一件小事。內心總穩穩瀰漫一種不安,好像隨時就要分開那樣,有時我想:不如由我來結束會比較好吧?同時又不禁心存僥倖,想著或者拖下去就會一輩子吧。我可以這樣自私下去嗎?
在一個懶洋洋的下午,電車搖晃著,坐在你的旁邊,任滲著熱氣的風吹亂頭髮。
漸漸我覺得自己的說話很多餘。我想說些什麼去反駁自己腦中這種自嘲的討厭想法,同時每次開口之後都後悔;如果開口與不開口都一樣難受,感覺都一樣不對勁,或者問題不是開不開口。
「人生好短,短到你唔夠時間後悔就已經完咗,人生真係好短好短。」我用平淡的語氣掩飾自己內心的歇斯底里。
你沒有回應,抑或其實有呢?我記不起了。我不希望有一日你後悔自己的時間都被我浪費掉,我不想發現或者是不想你發現,原來你沒有我會過得更好。
旁人在嘻笑,我們坐在一旁的圓凳上,依傍著頗此睡著了。聽著吵鬧的嘻笑聲醒來,接過別人給的一張即影即有相片,迷糊地看到相中迷糊的我們。
「十年之後我哋著同一件衫,做同一個動作再影一張好唔好呀?」我帶著期盼和不安問。
你的回應我想不起來了。大概是「睇吓點啦」﹑「哦」﹑「嗯」或者只是聳一聳肩。習慣冷待一個人和習慣被一個人冷待都一樣有害有毒,我們都有責任不讓自己變得冷酷或者卑微。
在西鐵列車上,我有一句沒一句地跟台灣的他笑說自己分了手終於才瘦下來了。
「為什麼?沒吃飯嗎?」一個很合理的回應。
「因為之前他都讓我吃太多吧,說要把我養胖。」我沒多想就回應道。
「那是他關心妳吧」附上一個竊笑的sticker。
突然腦海又湧現許多許多過去的情景。被冷待久了,我忘記了自己確實有被愛過。是曾經的幸福還是最後的冷漠令我更心痛呢?或者是前者吧。
我以為從各個時刻的陳述中,別人會明白我對這分開的期待和不捨。其實不然,深刻的感情牽扯到到太深刻的﹑沒有形的﹑不能言的東西。
在分開的一刻,我失去了毫無保留的自己,再也沒法用同樣深重得可怕的感情傾注在一個人身上,彷彿從新領悟到人是群居的個體,沒有誰不得不跟誰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