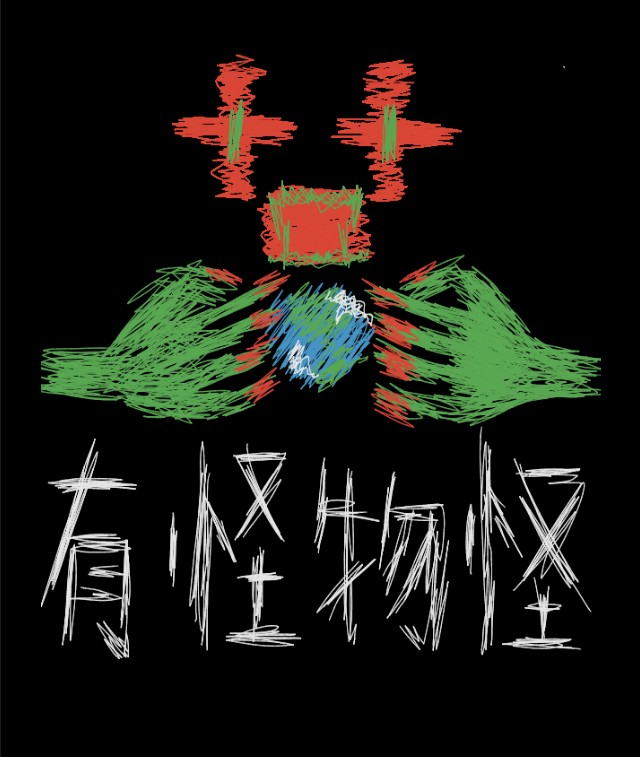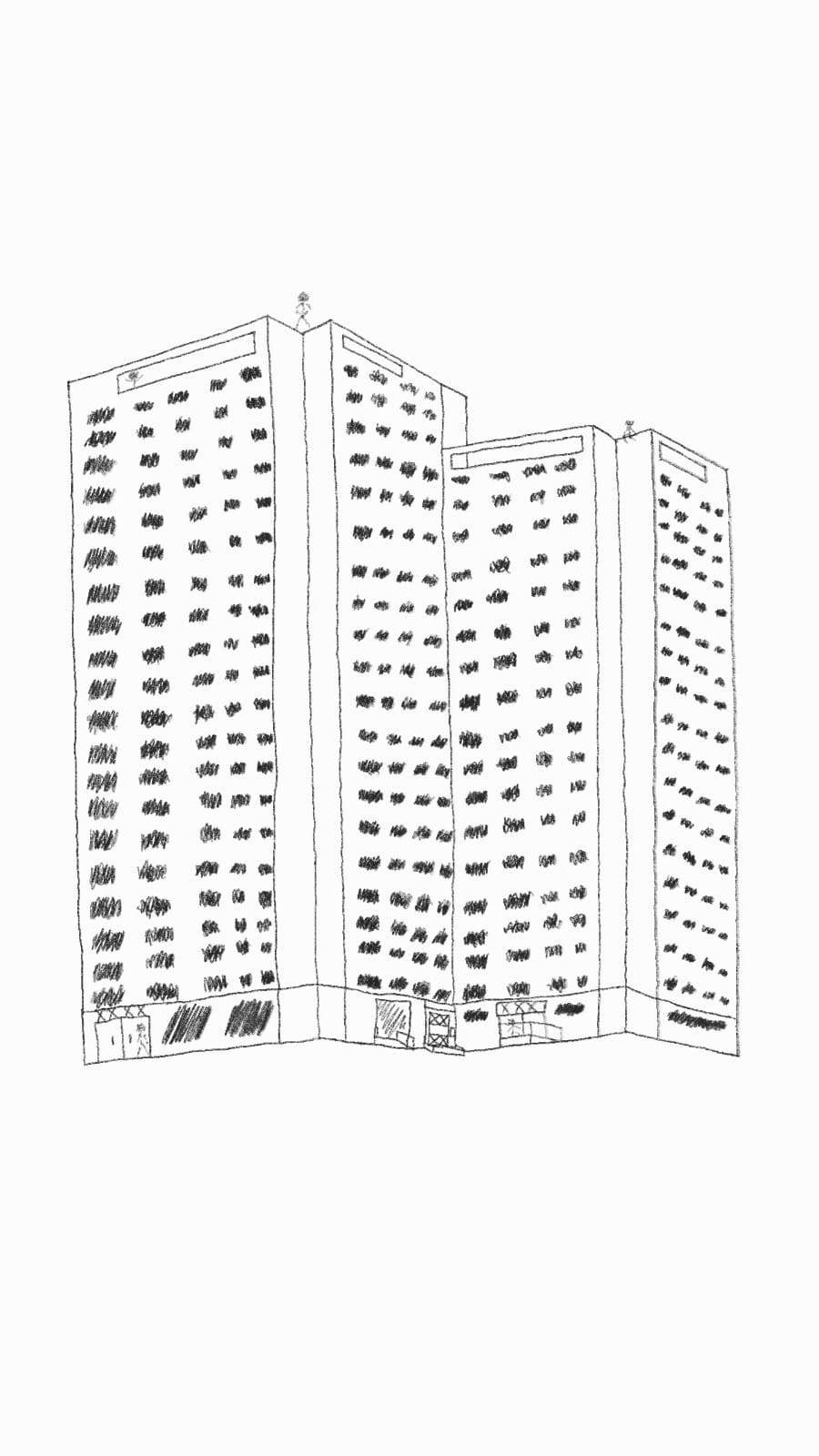風光已不再,眼見就成埃
回頭便是厭,來世或相見
「殺人要填命」、「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些說話我終於完完全全明白當中的含意,因為除了這兩樣選擇之外,我現已沒有其他路可以給我再選擇。
今天,我將要受刑。
吃過人生最後一餐之後,我的人生只剩下兩項任務讓我進行。第一,是祈禱、撥出最後一通電話,還有與獄中牧師交談。第二,就是重新鎖上手銬、腳鏈,準備步入行刑室去填補死者的生命。此時,我將會消失在這世界上。
那年暑假,父母外出工幹,家裡只剩下我自己一人,所有起居飲食均須自己搞定。他們只在枱頭放下二千元還有一張簡單的字條。
「兒子,我跟你爸兩個月後才能回家,家裡所有東西你自己搞定了啦!有什麼事就打電話給我們吧!」
其實這種生活方式我習以為常,已經持續了很久很久。然而,我開始覺得父母只是不想跟我一起生活才找藉口,說什麼外出工幹來避開我。故此,當時我萌生了一個念頭,好讓他們對我多加注意,不再忽略我。而當時「黑社會」跟「童黨」興起,我看見他們都會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吃喝玩樂,夜晚又會在公園流連,愉悅地「圍威喂」。從而,這令我的反叛心愈來愈強烈,更想融入他們的圈子裡,那就不用整天待在家中那四面牆,可以跟他們在一起談天說地,暢所欲言。因為,家裡根本沒就沒有任何渠道來讓我跟別人傾訴。父母在我小時候已經限制我的朋友圈子,不容許我跟沒有家底、學識還有他們所謂的「智慧」的人當朋友,這令到我在學校變成一個獨家村,沒有朋友、沒有肯跟我談天,每個同學都怕了我。我已經受夠了這種「冇人冇物」、被父母限制、被隔離的生活。我很想交真心朋友,我很想融入別人的圈子來讓其他人重視我。
幾經一波三折,我順利加入隔壁邨的童黨。我還依稀記得那群童黨的稱號是「大飛」,意味著我們這群人是鼎鼎大名的「飛仔飛女」,要所有人都記得我們一個二個。當時,我還覺得首領「飛鷹哥」英俊瀟灑,性格既豪邁,又爽朗。而且,他還有一位國色天香的女朋友,一班聽話的班底,簡直是「人生大贏家」。如今,我只覺得他只是一隻過街老鼠,還有是個不折不扣的正混蛋。是他害到我被判死刑、是他害到我在某段時間身無分文、是他害到我......總之多災多難就是的。這首領輕則借錢不還,重則招兵買馬,「吹雞」攞架生「隊冧」仇家。當時我仍然覺得一群人在街頭,跟仇家對峙兩三個小時,一堆人圍在一起「食花生」是件極之威風凜凜的事。
殊不知,這件所謂「威水事」是會被警察拘捕,還被告上法庭。那時候只是覺得這些事都不關其他人事,只要麻煩不到街外人就能為所欲為,不會驚動到警方。
然而,世事哪會那麼簡單?打架傷人可是刑事呢!
「我們現已死心,決定跟這兒子脫離關係,以後有什麼關於這個人的事都不用找我們。從這一秒鐘開始,請他不要跟別人說自己姓王。他令所有姓王的人感到蒙羞!」
試想想,如果你的家人對你說這番話,你會怎樣?你會感到高興?還是好像我一樣,感到無比的絕望、人生沒有任何盼望,只是覺得很對不起自己的父母?他們供書教學、養大自己用了他們畢生的心血,只為了一件事—當個好人。父母看到自己的子女得到這樣結局,所承受千萬般撕裂的痛,遠遠比不上自己要受到死刑的痛。因為,這是自己拿來的。我並不害怕行刑所面對的情節,例如要面對劊子手、還有氣絕的那一刻。我最害怕的是,家人因此而離開自己。死後一刻,沒有人拜祭我、沒有人紀念我、沒有人想理會我。認識我的人只知道的是,我曾經是個惡名昭彰的某童黨手下,僅只如此。
在最後的這段時間,我身邊已經沒有任何至親,朋友,只是孤身隻影,獨自一人不停地在想「如果我還有第二次選擇」這問題。我要上行刑室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但我深信凡事未到最後一刻都有轉機,就是法官可能突然宣佈重審案件、刑期押後等等這些非常戲劇性、且難以成真的「阻滯」,令到我有機會被改判、甚至「出冊」。
先言歸正傳吧,如果我有第二次選擇的話,我很希望父母在我年小的時候給我多點家庭的溫暖,多陪伴我,好讓我不會那麼容易地行差踏錯。而且,我很想摑我以前的自己耳巴,給當時的自己清楚知道,加入童黨並沒有好處,只是死路一條,根本沒有所謂朋輩之間的溫暖,絲毫關心都沒有。他們只會「大難臨頭各自飛」,犯下錯誤只會推你一把,送你去死、「篤你灰」而已。然而,現在才醒覺為時已晚,並不會再有任何機會給你改過自身。錯了,就是錯了。要怪就怪當初的自己走了一條十分錯誤的道路。
然後,我寫了一封信來送給上了天堂的自己,交給獄警。希望把這封信,還有自己一起火葬。內容都是警惕來世的自己,做個好人。
「你還好嗎?我打聽到別人說壞人不能上天堂喔!你那麼壞,為什麼上天給你來到天堂的呢?哈哈!不知道現在的你會在天堂的哪兒呢?嘛......不管那麼多了,我知道你在行刑前想改過自身,然而已經沒有機會了。不過啊,現在的你已經可以試試改過自身了!無論現在的你身處何方,你生前想改過、想嘗試的東西,終於可以無拘無束地做啦!對不對?記住啊,來世投胎一定要做個好人,不要走回頭路,不然你就好像上世一樣這麼苦命了!就算父母抽極少時間陪伴自己也好,也不能夠,是不!能!夠!當個小混混!答應我好嗎?來世你一定要似回人型,絕不能走回頭路!我不知道你來世會是做人,還有做隻小貓或小狗,我但願你不要再加入童黨,這只會前途盡毀!好了,來世再見!你要加油啊,別再亂來了!」
寫這封信的目的只是希望來世的自己會變成好人,浪子回頭。我也希望來世的自己會努力做人,別再好像小孩子漫無目的地渡過每一天,來世一定要好好孝順家裡兩老吧。嘛,現在的我就是全世界壞男人代表,好像我的話只是死路一條,永無寧日。
獨自沉思過後,牧師走進我這間狹隘的牢房,為我祈禱、立定遺囑。我被囚禁將近十二載,並不符合「已監禁超過廿四年,且行為良好可以出獄」這條件,不然我有可能被改判。事隔十年多,我已變得稍有人性的我,只希望把一直以來的積蓄來幫助山區家庭,還有非洲兒童,幫得幾多就幾多。我今生已做盡大大小小的壞事,臨終前還不回饋社會的話,那我成何體統呢?加上,我總覺得我就算道多少次的歉,我的父母、還有死者家屬都不會原諒我這差勁的人,還有死後來拜祭我。
誰會掛念我?誰會說個笑話紀念我?我無親無故,孤寂一人......還要做盡這麼多壞事,必定沒有人會來拜祭我的。所以,我深信這個「誰」是並無此人,不要在發這些春秋大夢,還希望別人會來探望我?我在說什麼笑話啊?我憑什麼要別人來拜祭我?傻的嗎?只因為,弄成現在這結果是我咎由自取,完全不值得任何人可憐。
我對牧師說:「如果現在還有第二次選擇的話,我很想好好活著,回到最初。乖乖留在家中,等待父母揪著一串串的鑰匙,打開家裡溫暖的大門,給予我大大的擁抱。希望他們會問我功課進度、問我學校的大小二事,有什麼趣事或是衰事、又問問我成績如何。總而之問我什麼問題我都一一樂意回答,我只是很希望......很希望......可以多見他們一面,只是一面就好,我就此生無憾。我畢生最大最大的遺憾就是,我並沒有在我這寶貴的一生中去好好報答他們。你猜他們很想整天外出工幹嗎?他們很想每天勞碌地工作,很想長期離開這安全舒適的家嗎?他們那麼辛苦是為了什麼?是什麼?就是努力賺錢養活我們這一家而已,真的僅只如此,這道理就是這麼簡單明瞭。我非常後悔沒有撥打電話給他們,好好問候他們。我非常後悔踏出人生最錯的那一步,就是加入童黨。我已經沒有聽父母的聲音十幾年了,然而我還記得他們溫柔的聲音,還有慈祥的樣子。」
牧師聽到後,不發一言。他默默地望著我,直到警號響起,示意我將要離開這個牢房,重新鎖上手銬、腳鏈來接受最後一個任務,並是今天的重頭戲—被處決。
時間只剩下最後一小時,是人生最難熬的一個小時。這意味著我的天命將來臨,快要氣絕,與世隔絕。我欲哭無淚,只因為這是以前的自己惹出來的禍,怪不了任何人。要怪的,只能夠怪自己。這時,獄警遞了一張意向書,詢問我希望會以槍決、毒氣室、電刑、或是絞刑來處決。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電刑,因為這是四種刑罰中要用最長時間才會氣絕身亡,還有是最痛苦的。我只希望死者家屬會為我的受刑而感到安慰,走出傷痛。如今我已年三十,事隔已經十多年,然而那個混亂的情景我依然歷歷在目,難以忘記。故此,我完全沒法想像在家屬心裡是有多難受、悲憤、甚至可能曾經有揚言要親手當劊子手,以達成「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心願。
這刻,我合上雙眼。試圖去感受一下當下他們的兒子遇刺身亡,心裡有多悲痛、哀怨這種超級難受的感覺。我終於明白,永遠失去至親是多麼的痛苦。而當時未判刑的我還嘻皮笑臉、不知悔改、毫無悔意之心,還覺得這個行為是很酷、很帥氣。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腦袋,當時我的心理是有多麼變態、恐怖、還有冷血,殺死人還恬不為意,滿不在乎。我真的是喪心病狂,腦袋都不知道在想什麼,還覺得法官對我很不公平,自己是完全沒有錯的。
俗語有云:「未到死都唔知驚」,去到被判死刑的那一剎那才意識到自己犯下了最嚴重的罪行。可能......聽到「死」這個極端的字才懂得感到愴惶、才知道「驚」這個字怎麼寫。若果我被判坐幾年監的話,我的心態可能不會軟化得這樣厲害了,可能只是覺得:「幾年而已,好快就過!」,捱過幾年之後就可以繼續風流快活,優遊自在地活自己想要的生活。
「風光已不再,眼見就成埃。」以前只是當個老大的手下已經覺得自己威風凜凜,非常厲害似的。然而,現在已風光不再,死刑這判決已塵埃落定,並沒有轉彎的餘地,幾十分鐘後就要上行刑室了。
「回頭便是厭,來世或相見。」我的父母已經對我死心塌地,已經跟我脫離關係,亦不奢望我會回到頭來,當個「乖乖仔」報答他們,長大做個好男人。而來世,他們或會對我改觀,從而大家再相見。所以,我的心真的希望上天會在我來世的時候,讓我當個堂堂男子漢,正正經經做個好人,不要再行差踏錯,走回頭路。我已沒有其他東西想要了,我只想快點投胎轉世,洗底,重新做人。
彈指之間,警號已經響起。獄警、法官、死者家屬、還有其他人員陸陸續續進來牢房,將我整個人鎖緊起來,防止我越獄。接著,他們就押我到行刑室受刑。
雖然行刑室距離牢房只有短短三百米,但是我覺得這條路走極都走不完,彷彿在長佂一樣,既艱辛、又痛苦。拖了十幾年才處決已經非常便宜我了。途中跟我擦身而過的法醫捧著笨重的「白布」就好像望到待會被枱出來的自己的一塊玻璃鏡,完成行刑後程序後就讓法醫解剖鑒定。
此時,我已冷靜地坐上極高電流的椅子,這意味著這椅子一開動後,電流就會通過我的身體,若干分鐘後就會氣絕身亡。
斷氣前一刻,我還在思考同一條問題:
「如果我還有第二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