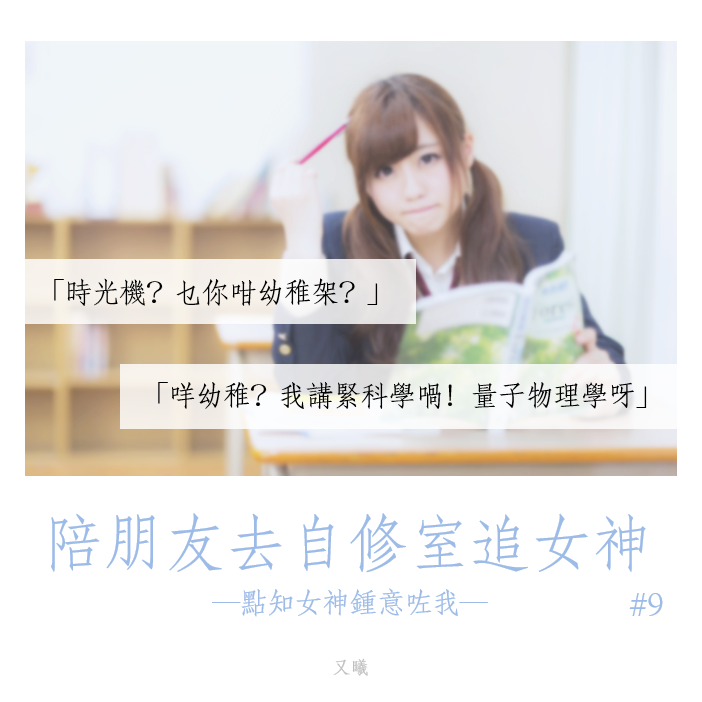我雖然家住在日本,但父母都是中國人。也許,應該說他們……包括我『本來』都是中國人,但為了逃避某個政權的壓迫,我們放棄了這個身份,在十六年前的一日之間變成了日本人,不過在我懂事之後,我就明白我們其實沒有變成日本人,只是變成了『不是中國人』罷了。
移民到日本的時候,我就只有四歲,可能由於離開的年紀太小了,加上來到日本後都再無說過半句中文,因此我現在只懂得作為『養娘』的母語——日文,而生娘的話早就已經忘得一乾二淨了,最多都只會說一些在港產片學到的廣東話詞彙。
而在日本出生的兩個妹妹跟我不一樣,她們身上已經完全沒有半點中國的味道,連名字都已經是地道的日文名,不像我這樣依然無可奈何地保留著一個中國名字。
也許「只是個名字」的話可能有部份人也覺得沒什麼關係,不過在社會上,以及我學校的生涯上,這個中國名字實在有著很大的問題存在,即使幸運地沒有受到歧視都好,人們也會將我定位作熟練功夫和拳法的高手。
所以我認為兩名妹妹才是真正的日本人,而我卻不一樣,我是個中國移民,這個身份是一生也改變不到的。
不過我還要是過生活的,當然我不懂什麼拳法又或是風水(雖然曾經有人告訴我作為一個中國移民,這是不錯的出路,不過我就是不願意,因為我討厭被人標籤),但由於自悲的反作用力,驅使我決定要做一個最『日本人』的職業,就是漫畫家。
我自問是一個很有恆心的人。幾年來我一直堅持練習畫功,從火柴人開始努力,到現在能已經畫出精美的插畫了,這就是努力的證明。
除此之外我的恆心不只在行動上,就連生活上也一樣,因為每天大清早起床,我都會堅持做一件事,首先是刷牙,接著就會洗臉,然後我就會更衣出門,踏上上學的路途。
當然,這不是我所說的「一件事」,起床刷牙洗臉基本上每個注重衛生的人也會做的,我所說的是每天出門後,我都會在同樣的時間,在卑斯麥(一間離我家兩個街口路程的麵包店)買個麵包作早餐,順便用視線去拜訪一下這家店那位留著八字鬍子、滿身肌肉的麵包店師傅兼老闆——西尾先生……的千金。
嘻嘻,你覺得我會每天故意去望一個肌肉中年男人嗎?當然有些人可能會,就像我某位鄰居X師奶,經常都會光顧卑斯麥,然後用充滿慾望的視線騷擾作為單親父親的西尾……
噢,不如我們先入一下正題吧,重點理所當然不應該放在西尾身上,而是他的千金——瑠璃。
瑠璃這個名字應該不是太多人知道,以我所知大部份人都會稱呼她作『西尾Sally』。
不過對我來說,比起那日英混雜的稱呼,我更喜歡叫她瑠璃這個名字,雖然到目前為止我是一次也沒有叫過出口就是啦。
我不知她的年紀大約是多少,聽聞完成了義務教育之後已經在這裡在這裡打長工,為的是減輕父親的負擔,跟我這個還在用家人的錢支付學費入讀漫畫學校的不肖子剛好相反,不過這樣說好像對我自己有點不公平,因為事實是當我學有所成之後,自然就會將家人所付出的十倍歸還。
不過以我推測,她的年紀好像是比我小,又或是同年的,至於證據的話……就她的樣貌吧,假如你看到她的樣子之後跟我說她已經踏入三十歲的話,我會建議你看看眼科醫生,又或是心理醫生。雖說矮細嬌小是與年經無關的,不過白皙無瑕而且滿有彈性的皮膚是不會騙人的,是只有年輕才能夠擁有的特質,加上身上所散發著如同花蜜般甜蜜的天然體香,你要我相信她的年紀會比我大,實在絕對不可能。
但是!假如事實她已經四五十歲也好,我亦是樂意接受的,誰會在乎一個各方面近乎完美的女人的年齡?
區區年齡是不能阻礙愛的!
話說回來,所以事情是這樣的,由於每天只來看她一眼的話我個人也不太好意思,要好好享受跟她共處的時光,情理上就必須買點東西,於是這就養成了我每天都會特意走多兩條街買麵包作早餐的原因。
我看看眼前琳琅滿目多種的麵包,再度陷入迷惘之中,究竟買什麼好,這是個讓人苦惱的問題。卑斯麥的麵包種類繁多,而且定期會有些古怪的新產品,所以我今次就選個……蜜瓜包好了,雖然今個星期已經連續吃了四天,但……這又如何呢?反正我現在的心情想吃蜜瓜包,這個原因已經很足夠了。
於是我將蜜瓜包夾到盤上,並走到店最深處的櫃台,準備享受我應得的時光。
三十秒後,我沒趣地離開卑斯麥,因為剛剛為我結帳的,是滿身筋肉的西尾,因為瑠璃今天休假。
我咬著那沒有甜味的蜜瓜包,行屍走肉地去到巴士站,等待那架沒個性的巴士,將我帶到那絕無朝氣的學校,度過毫無意義的一天,能夠在早上就看到一日的終點,實在是沒趣到極點。
「堯,早安喔!」聽到一把陌生的聲音,我回頭望過去,是一個紮著馬尾的陌生女子,這傢伙一看就知朝氣十足得過火,像隻體力無極限的猴子一樣。
「早安。」我也禮貌地笑著回答,同時一邊咬著蜜瓜包,一邊正式地打量她。
她穿著不知哪間高中的校服,上身是白恤衫與淺黃色羊毛外套,下身則是紅色校裙,整套裝束也是暖色系,與她熱情如火的性格十分相襯。五官看來也挺順眼,笑容亦是很甜美的,但唯獨雙眼異常地無神,產生了嚴重的違和感,看起來甚至讓人感到有點不安。
因為她外表雖然只是個十多歲的高中生,但雙眼所泄露的氣色卻像個道行很深的高僧。
「我每次跟你打招呼,你都總能毫不猶疑地回應我,實在讓我一次又一次懷疑你是否記得我們之前所發生過的事。」
除了讓人不安的氛圍之外,她還滿口讓人無法理解的話,但即使如此她還是個外貌可人的女高中生,所以我就大方地回應一下她的鬼話,姑且看看她有什麼目的:
「是嗎?我只是……」我話未說完,她就以那滿是朝氣的聲線輕鬆插話,代我將話說下去:「我只是認為作為一個有禮貌的人,應該何時都友善待人。」
我驚訝的問:「你怎麼知道的?」
她卻輕描淡寫地回答出一個不妙的答案:「好了,我也不說些無謂的開場白了,我是一名時光旅行者,今次已經是我第……差不多四百次回到這個時間點了。」
「等等,你有什麼問題嗎?」這已經超出我可接受的範圍了。
正當我轉身打算離開時,她並沒有作出任何行動挽留我,只是淡然地開口說:「你的名字是曹百堯,今年二十歲,在小時候移民到日本,原因是家人受到壓迫,喜歡的食物是瘦叉燒,最愛的電影是《男たちの挽歌》,夢想是當個漫畫家,家有父母與兩名妹妹,現在對於自己的前途感到十分迷惘的,昨晚吃的晚飯是很難吃的咖啡味咖哩,這一刻最喜愛的女人是卑斯麥老闆的妻子,雖然我還知道更多,不過再繼續說下去恐怕能說到今晚也不會說完的……」
說到這裡我已經回頭望著她的雙眼,在她的眼中仿佛看到一個疲乏的靈魂。
「因為你會懷疑我是否只是個單純的變態跟蹤狂,所以按照慣例,你每次都會再問我幾個問題去確認一下,對吧?」她依然淡然地問道。
事實的確是這樣,雖然她大堆的話已把我幾乎把我說服了,但同時,我也的確依然抱有她所說的懷疑,不過她這話聽起來不是有點矛盾嗎:「既然你知道的話,何不直接說出答案?這樣有助我相信你的話」
沒錯,假如她是時光倒流過無數次的話,大概已知道我會問什麼,所以按理應可以在我提出問題之前直接說出答案。
「不是你所想的那樣的,因為每次回流過後你都不見得會問出同樣的問題,所以你問我答是最有效率的,你要知道我們時間有限好嗎?」
其實基本上來到這一刻我已經有一點點相信她,不過她之前的話當中有一句我是無論如何都很在意的:「我只想問一個問題……你之前說……卑斯麥那個女子……她……她真的是老闆的妻子嗎?」
她爽快地回答一句:「抱歉。」
同時上前拖著我的手補充:「這是我騙你的,瑠璃當然是西尾的女兒。」然後一邊帶我離開巴士站一邊輕聲地說:「不過我剛剛所說的話有一點故意說謊了,就是……你最愛的女人……」
之後的話由於太小聲,我完全聽不到,不過即使再問追都好,她都沒有回答過我,只是背向我一味拉著我走,相信再問下去都只是自討沒趣,但一直看她的背影讓我有點尷尬,所以唯有將話題拉到其他地方:「你叫什麼名字?」
她似是隨意地回答一個字:「鈴。」聽起來實在難以分清楚虛實。
接著我們來到一個班馬線的位置,交通燈的指示是紅色,讓我們能從急促的腳步停下來一下,也讓我能跟她並站著,有機會再次看清楚她的容貌。
假如要將她的五官逐一去評價的話,大概也不會得到什麼好的分數,因為要求不高的我都認為她的鼻有點過份的尖長、嘴有點太大、眼角有點下垂、髮質亦有點乾旱、皮膚亦不夠白皙,但組合起來卻感覺卻不太差,也就是挺順眼的。
然後她也許知道我心裡還有新的疑問,所以早一步跟我說:「在去到目的地之前能拜托你安靜一點嗎?」
「但……」我正想回應的時候,卻被她無情地打斷:「他們正在監視著我們。」
聽罷我無意之間也提高了警戒,看看四周有沒有什麼可疑的人同時問:「誰?有誰這樣做?」
「命運規劃委員會。」她毫無感情地吐出這個不知所云的名稱。
同時我總算見到一個戴著黑超,身穿整潔西裝,坐在輸椅上的老人正交差著手,在馬路的對面望著我……但聽到她所說的話,我卻突然覺得那位老伯並不可疑,因為在我身邊跟我拖著手的這位少女所說的話絕對是更可疑。
我開始再度質疑她是否一個有重度妄想症的少女,所以質問:「什麼委員會?這是什麼鬼東西。」
「你要我一時之間怎樣跟你解釋好?你知道當中牽涉多少的因果和因緣嗎?總之你要知道我們的時間是有限的,十幾個小時之後事情就會發生,我盡可能也不希望給予『他們』太多我行事的線索,所以你就乖乖地跟著我去到目的地,到時我什麼問題都會回答你。」
對於我的質問,她的態度是絕對不讓我有任何反駁的,同時交通燈已經轉為綠色,我們又再度出發往著未知的目的地前進。
其實我大可以甩開她的手然後轉頭就走,但礙於怕事和懦弱的性格,我不敢這樣做,同時亦很好奇她將會有什麼舉動,所以只好默默跟在她背後,不久我們就去到一間就近的定食屋。
進到去裡面,人不太多,裝修亦很平凡而且簡樸,一桌、一椅、牆壁、地板都充滿著歲月的痕跡,一找好位置坐好,她就馬上點餐,所點的菜也許不一點是我此刻想要的,但都是我所喜歡的,假如她不是一個時空旅行者,就絕對是一個十分了解我的人。
點餐過後,她喝口水就靜止下來,大概是對現剛才的承諾吧,所以我就向她發問:
「你不斷回到同樣的時間,究竟有什麼目的?」
她表情沒什麼變化,但語調有點失落地回答:「我要救一個人……」
「救一個人要用得著時光倒流四百多次嗎?我看你的樣子也不笨,也許會失敗幾次,但只要能記住整天所發生的事,要救一個人也不會是這麼難的事吧?」
「問題就是這樣……你可能會覺得很簡單,不過實際執行起來的話,其實絕不是想像中輕鬆,因為無次也存在著很多變數。」
「變數?這不可能存在了吧?還是說,你是指由你個人所產生的變數嗎?」
「當然,我個人會產生變數,不過既然我個人會產生變數,其他人也自然能夠產生變數的,始終我們也是具有思考能力的人……」
「即是說還有其他穿越時空的人嗎?」
「不,我所指的是每一個人,連你也不例外,雖然不論哪一次回流你都會走同樣的路到卑斯麥,但你所選擇的麵包卻並非每一次都相同,這樣說你應該明白了吧?」
「我看你的樣子大概還是不理解,果然還是一如以往的笨。」「我就說得簡單點,人的行為可以大概分為兩種,就是習慣,還有選擇。習慣是難以改變的,如同你每早都會刷牙洗臉,每早都會去卑斯麥一樣,不論回流多少次這也是不會變的。不過選擇就不一樣了,每次進行選擇,你都會思考,當你思考就會產生變數,於是你今次選擇了蜜瓜包,上次選擇了炸咖哩包,再上次選擇了海螺麵包……這樣說你就能夠理解吧?」
這種話聽起來真的夠衝激性,至少這是我至今都沒聽說過的理論:「這樣說的話,即是現實不像《12猴子》那樣,進入無限的輪回嗎?」
「當然!就是這樣!你終算明白了。所以按道理,每個人思考後的選擇造成微妙的改變,並漸漸轉化成巨大的影響力……」
「這樣說的話,你回流一次不就已經會產生出多得不可估計的平行世界嗎?」
「你這個推斷是正確的,我也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但我可以告訴你,以我所知平行世界並非我們想像中的複雜……而且很可能比想像中少很多……」
「但你不是說人們的思考會轉化出巨大的影響力嗎?」
聽罷她頓一頓才回答:
「不,實事並非是這樣的,因為這個世界存在著『命運規劃委員會』。」
再度聽到這個名稱,讓我想起過往曾經讀過的一些著作,它說瘋子不是單純的脫離邏輯,剛好相反,他們的想法是比任何人都更有邏輯,只是常人不能理解他們的邏輯罷了。而她非常乎合這一點,因為那個什麼什麼委員會實在過於天荒夜談。
我們可以將其理解成之前她所說的大堆似是而非的說話的起源,也就是她個人邏輯的根基。
當然她是疑點重重的,不過同時也有很多說服人的地方。在這個模稜兩可的情況下,我不知出於什麼因由,在直覺上還是選擇相信她的。
她繼續解釋:「顧名思義,就是規劃命運的一個群體,他們可能是人,也可能不是,不過這並非我們需要關心的地方,我們只需要知道他們在玩弄著我們每個人的命運就可以了。」
「但以我所知,他們並無權力干涉到每個人的思考,即是他們不能控制人的思想,然而他們卻可以控制人以外的東西,就是機率。我可以這樣跟你解釋一下,在歷史上我們都知道總是有些幸運得怎殺也死不了的人,例如希特拉、卡斯特羅或是某個遠東的大魔頭……也有些命運太過不幸的人,例如莫扎特、梵高或是特斯拉……如無意外,這些都是『命運規劃委員會』所搞的鬼。」
「聽這樣說的話,他們大概就是神吧?」
聽罷她看起來怒了,並高聲地說:「不!絕對不是!」
這引起了餐廳每個人的注意,無能為力的我就只能不斷勸她冷靜點,接著她可能也在意到自己的失態,所以低調下來,壓下聲線地說:「他們只是一群擁有過份巨大權力的瘋子!也許他們以為自己所作的一切也是基於『阿克夏紀錄』,不過誰知道這是否真的?也許跟他們聯繫的不是阿克夏紀錄,而是一個在美國德洲酒精上癮的酒鬼呢?」
「你一大堆話裡,實在包含著太大的訊息量了,假如我聽得懂的話大概已可算是某方面的天才吧……」說罷,我試圖組織她所說過的說,並作出一個簡單的總結:「總之,你每次回流也遇到來自『命運規劃委員會』的阻力,所以四百多次都不能成功了吧?」
聽到這個總結,她的表情看來是『你這個呆子總算明白了』,接著就說:「他們會用盡意想不到的方法,去殺死他們認為必須要死的人。所以我已經試了四百多次都好,還是救不到你……」
說完那個『你』字,我知道她肯定想將那個字吞回肚子裡,這是一種無意的失誤,至於為何是一種失誤?大概因為那個『你』所指的人就是『我』吧。
我自然反應地反問:「我……?」這聽起來真的夠衝擊,你知道被人告知死期的感受是如何嗎?
首先我的頭腦有點停止運作的感覺,然後我甚至感覺到自己失去了焦點,一直想張開口也做不到,想說話也說不出,亦控制不到身體任何部份,然後開始有種抽離的感覺。接著不知在這種狀態下不知維持了多久之後,有一種強烈的情緒一下擊中我的內心,就像佛寺的大鐘在耳邊被擊響一樣,我不知那是一種什麼情緒,只是它驅使我發出一種從來沒有發出過,充滿消沉、絕望以及死亡氣色的笑聲。
我瞪大雙眼望著鈴,並以毫無半點感情的聲線問:「你是說……我今晚會死嗎?而且是沒有奇跡,無論如何都會死嗎……?」
她看到我的樣子後,表情顯出自我們見面後最大的一次波動,看起來是悲傷,也不是驚訝,而是一種慈悲。
她慈悲地捉緊我的雙手,然後帶著覺悟地安慰我說:「不。今次不一樣。」這是絕對我聽過最勇敢,最讓人感動的說話。雖然我不知道她為我做過什麼,但我知道她不是開玩笑,而是貨真價實地認真,我幾乎可以肯定她甚至會願意犧牲自己去救我,她對我的感情,是一份充滿覺悟的愛,雖然相見不足半小時,但我知道她是愛我的,而且是無可否認地愛我。最後她補上一句:「今次……你要相信我,我無論如何都會救你的。」
這徹底地將我從絕望的深淵之中拉出來,望著眼前這個女人,我明白到自己對瑠璃的愛慕是多麼的膚淺,因為這個眼前的她才應該是男人一生所追求的。
此刻,她在我的眼中已不再一樣,也許這樣說有點不設實際,但她看起來的確比起剛才更加明艷照人,同樣的五官似是以另一種方式在我眼前出現一樣,黑得深不見底的瞳孔,還有強作歡笑的嘴角,都散發著似曾相識的感覺。
彷佛這一刻我才真正地認識到她一樣,也許我沒有很了解她,但她卻很了解我;也許我忘記了她,但她卻從來沒有忘記我。
我們或者真的曾共度過了無數個今天,無數個晚上,也經歷過無數次死別,然後又重逢,但我卻自私地忘記了一切,讓她一個人承受所有的痛苦,但她依然一次又一次為我而回來,為了拯救我而回來。
我真是個幸福得過份的人。
但同時間我亦是個不幸的人,因為雖然擁有一個這樣的她,但我能記住她的時間……卻只剩下十六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