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是個最高檔的全職,最全面的總經理,只是沒人給薪水而已。油米柴鹽一肩擔上的母親,在她成為母親前,也是一位在書房褢的小姐吧。
黃昏了,淡淡的陽光把窗簾的輪廓投射在地板上, 母親背對著我,打開窗簾,任由陽光直接照射她,她指著窗外說:「你看, 多麼美麗!」霞彩把每一庭山都蓋上一層淡粉的薄紗,溫柔美麗令人瞠目。她問:「你想要一個家嗎?」「媽,這就是家啊。」她搖搖頭,依然背著我,說:「你是時間結婚了,這個家,再也不堅固了。」
年邁的母親再也不像以前為我顛簸為我折騰。她老了,真的老了,老去的女人喜歡唸人,老是重覆說同一句話,記憶也漸漸失去。每次工作完,還沒到家時給她的一通電話:「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你是我的女兒..」「對的,媽我很快就到家了。」「我等你好久了..過..過了那麼久才來看我,我很想念你。」「媽,你又記錯了,我天天都和你在一起啊。」「是..是哦,那你快回來,我想你。」
每晚睡前,我會幫母親的手塗上潤滑油,我抓起母親的手時,才怔了怔。她手背上的皮,抓起來一大把,是一層極薄,滿是皺紋,像是脫掉棄置的乾皮。我把油倒在手心上,輕輕搓揉這雙曾經勞碌不堪、青筋暴現而今燈盡油枯的手。我因為工作的問題,有時候會不在家兩天,和母親見時容易別時難,離開她,是個複雜的工程,離開前二十四小時,就得先啓動心理輔導。我輕快地說:「媽,我明天就要走啦。」
在很長的歲月裛,可能有一天,屋裹頭的燈光特別燦亮,人聲特別喧嘩,進出雜沓數日,然後又可能歸於沉寂。我是年輕,要四處工作,時常不在家。留在屋裹沒走的人,體態漸孱弱,步履漸蹣跚,屋內愈來愈靜。剩下的那一個人,又往窗外指去,仿佛見到有一天,來了一輛車,是來接母親的。她有機會鎖好門窗,然後慢慢出去,又有可能坐著輪椅中,給推出去,也有可能是一張白布蓋著,給抬出去。
晚上與母親散步,走在綠油油的大草坪上,正好路過草地上的婚禮。白色的帳篷一簇一簇搭地綠色的草坪上,海風習習,明月當空,細葉在夜空裹飄散,像落花微微,幾百個賓客坐在月光裹,樂隊正吹著歡愉的小喇叭。我牽著媽媽的手坐在草坪上,遠望著那對滿臉笑容的男女,互相交換戎指,然後留下深深一吻。這時媽媽獨自顫巍巍站了起來,我眼角餘光瞥見他頹然的背影,然後我也站了起來,跟著她後面,回家。
一個人固然寂寞,兩個人孤燈下無言相對卻可以更寂寞。
「你應該像剛才那女人一樣,幸福。」我突然支吾,不知所云,眼淚像滴水無聲無色地落進茫茫大漠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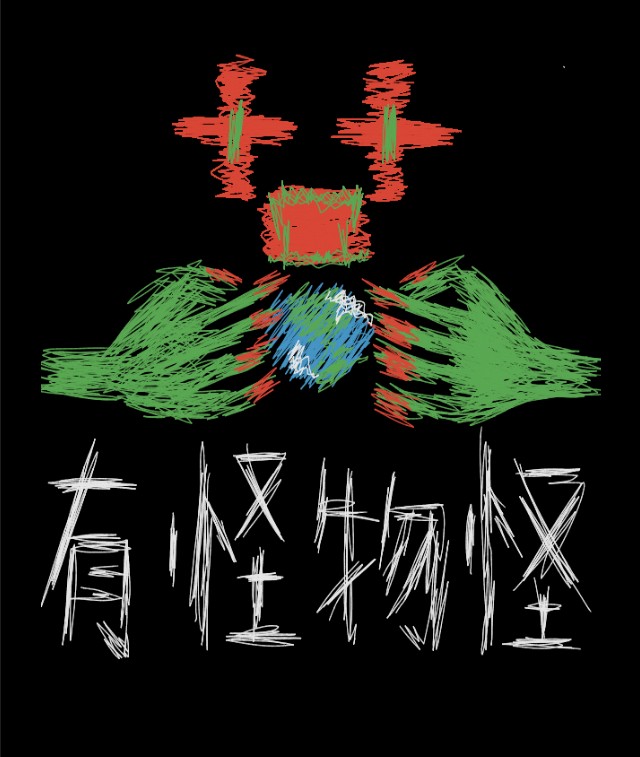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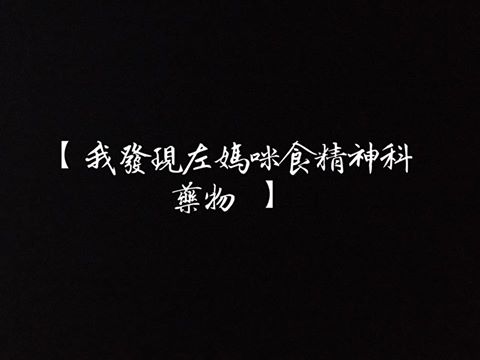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