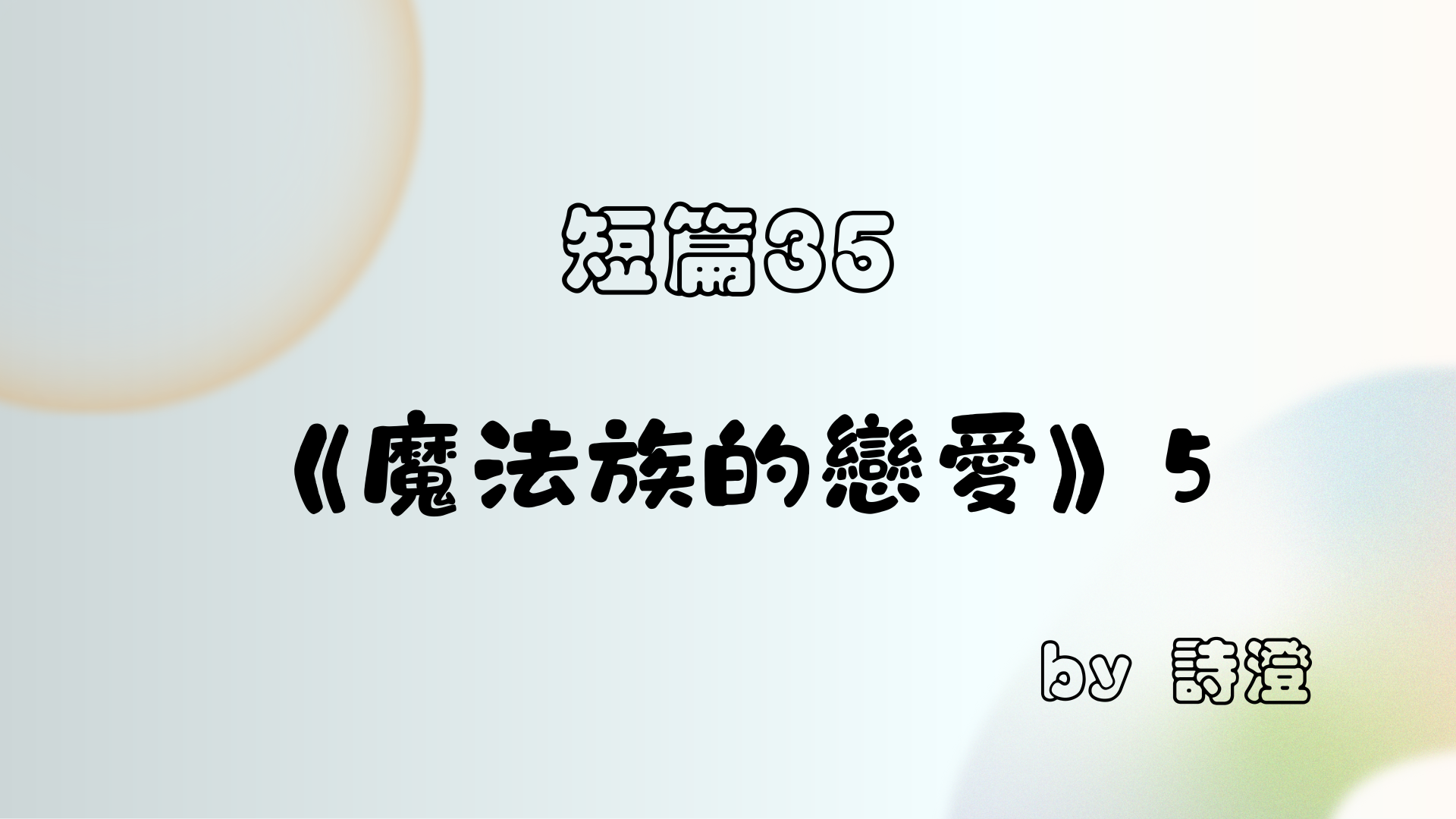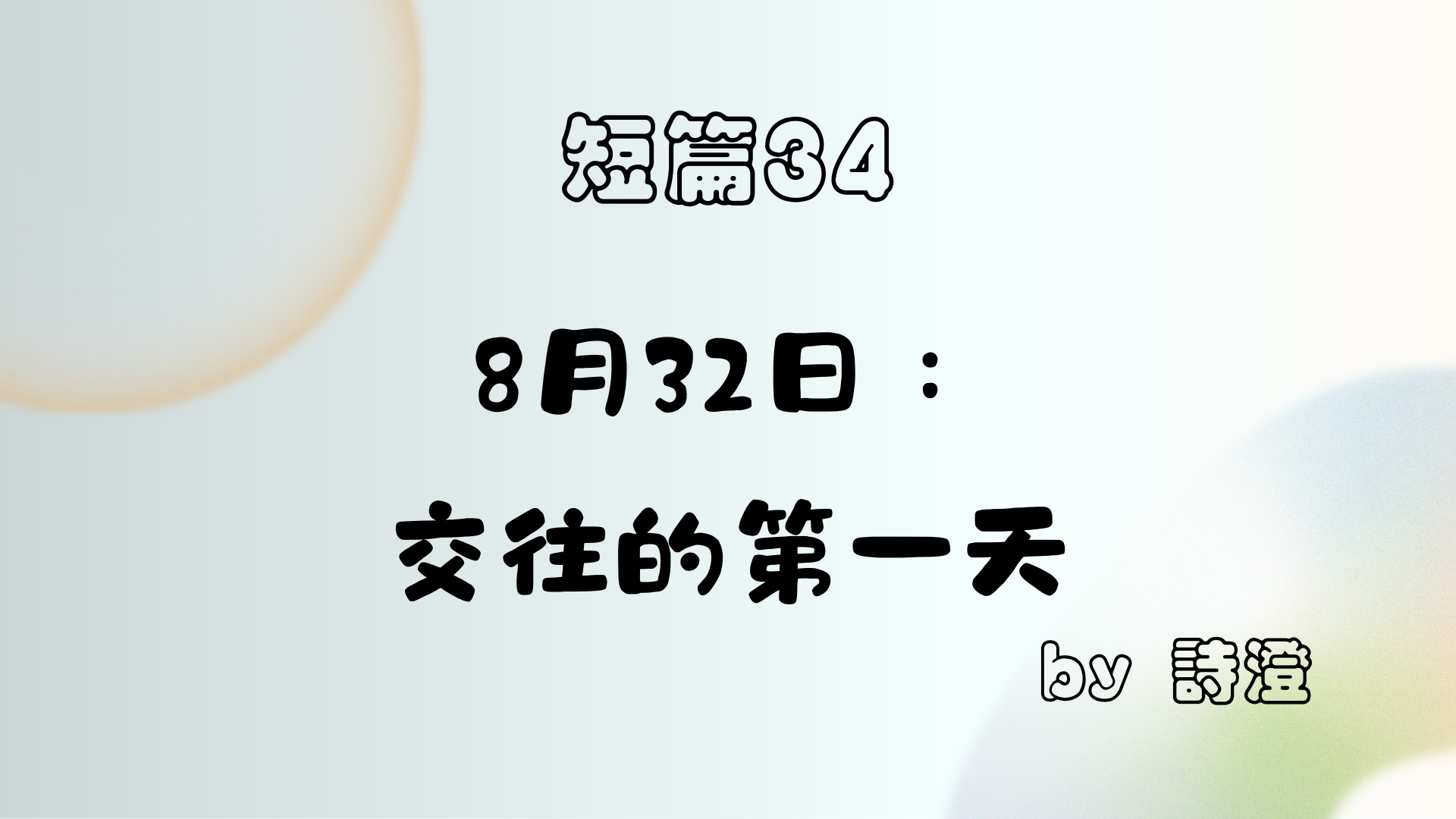從感情出現問題,到日漸疏遠,到「經已很無望」。分手的發展就只差一句說話去道明,但我靜靜的不說話,我天真地以為不開口不道破,世界也好命運亦好,就會被我瞞著,以為我真的沒有分手,而事實仿佛會因而出現轉機。直到你開口了,我再也沒法瞞住自己,我嚎哭,我在街頭放聲大喊,任由途人躲開,注視,接近,甚至被保安人員護著,我也不知道他要保護的是誰,最後被領到一個休息間去平伏。那是一個放棄的態度,對所有的事我都不想再干涉什麼。
筋竭力疲的我,好不容易回到了家,在進家門之前,我回覆了一個友善的短信「唔緊要啦,做返朋友啦」,按下發送之後,我轉上日常的面孔進家門。初時我還沉溺在守著這個秘密的迷信,我不敢告訴誰,只想靜靜的平淡的睡去,我不要驚動誰,也不要再承受什麼,我要扮演「我」,那個還有著男友的「我」,終於明白什麼是身外物,所有事物都與我無關。
在床上躺著,我不想哭,但淚私自滴下來,我連責怪它的心思都沒有,就任它自由,也任他自由。所有所有回憶都像猛獸一樣,我只得乖乖默不作聲,但求安然地跟著時間走,不著痕跡。我以為我的肚皮不知道心痛,我以為它會喊著說吃飯,但肚皮乖巧的陪我從黃昏待到早上再待到晚上,原來它也知道心情。終於我也不好意思讓身體陪我沉淪,畢竟它已經很忍讓。領著輕得沒感覺的身軀,踏出房門就遇到了媽媽,我擋住她的去路。
媽媽從來不是那種慈愛的母親,絕不會說愛,亦不會親,就會像最好的摰友一樣──大聲恥笑我的每個失誤,亦毫不修飾地指出我的胖肉,更會為我的可笑而笑得氣喘。
她躲不開之下,正懷疑,卻被我抱住。「我分咗手啦」我用最簡單的句子重重地說出這個努力守護的秘密。她抱著我。「下幾時發生架?」她關切地說。我用了很長的時間,把一切都說出來,她重複著很短的說話告訴我這沒什麼大不了,她為我做了最閨密的事──說他的不是,我做了最奇怪的應對──其實他沒有什麼不對。為自己深愛的人說話並不浪漫,因為那是出於內心最簡單真摰的說話,沒有一絲虛假,亦不能掩飾,就像是打呵欠一樣自然,一點也沒有浪漫。
然後我開始到處跟別人說這個最新消息,連看醫生時也向醫生透露我剛分手了,每個朋友圈﹑每個whatsapp group我也說一次,連新鮮的前男友的姐姐我也向她說一次。然而每一次,我也是對我自己說的。當初我想欺瞞命運,如今我只想令這個消息公開得像常識一樣,讓自己清楚明白逝去的是什麼,別再在早上睜開眼的那一刻心酸,別再在晚上睡覺前望著電話發呆,別再在書店前面淚流滿臉,別再以為一切只是夢。
《仁至義盡》
停止 她不想要的花 乾脆別送
停止 應將杯中苦澀 流放在 去水管中
停止 别在別人樓下 企一萬分鐘
長夜已斷送 換不到個短訊
Wyman說「如果你失戀揸車,係會聽G-Dragon 嘅話,咁我無嘢好講啦!」,失戀聽廣東歌,根本是車禍的前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