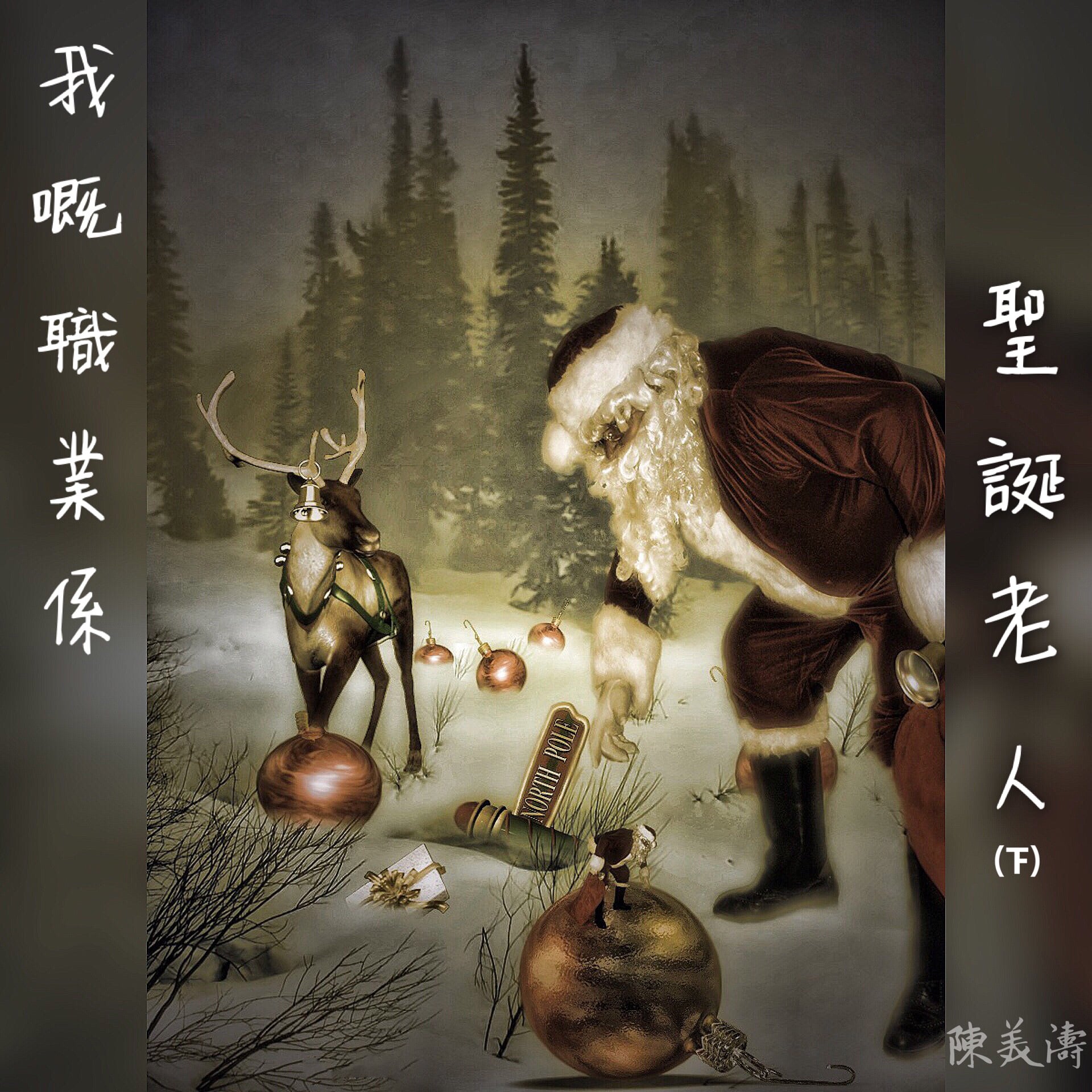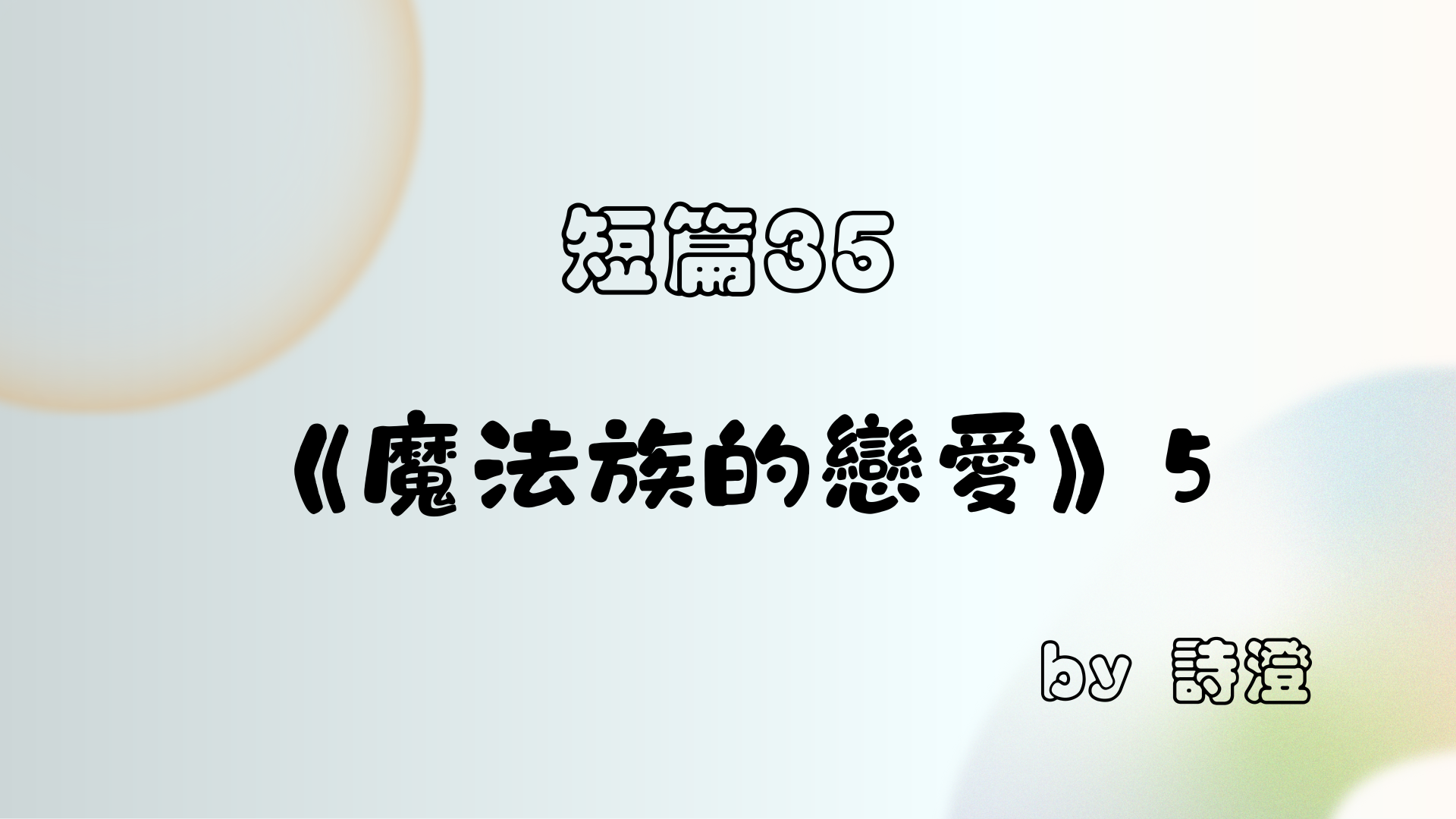《亡命巴士路》
那日,忘了是單數或是雙數日子。
總而言之,是辭去上一份工作的那天。
放下辭職信以後仔細收拾好桌面上的一切東西。
用得著的文具、用不著的擺設都一一放進從影印房裡取來的紙箱內。
收納整齊有序,不浪費任何一個角落空間。
這邊插入一支油性筆,那裡放著一本記事簿……
蓋上不太穩妥的紙箱蓋,用看來比紙皮可靠的透明封箱膠紙上下左右給箱子嚴實地包裹起來,然後抱著它出席歡送派對。
散席時已是超過於日常慣用的交通工具的運作時間。
我看看錶,但似乎看不清時針分針所指的羅馬數字符號。
站立在馬路前看著深夜無人的街道。
統一地全都蒙上了一層紫藍色色彩,就好像被從天而降一杯清洗過水彩筆的污水所染一樣。
左手抱著紙皮箱,揚起右手想要召一輛計程車時,突然清醒地想到從今以後不知道哪天才有一份正式工作,應該節省一點。
右手便又放下,輔助著左手,捧著紙箱往大街的巴士站走去。
腦袋裡略帶搖晃的感覺,但雙腳仍步伐實在的在柏油路上走著,邁向被店舖廣告燈箱和附近樓宇所映照得莫名通紅的大街。
記得從前夜深回家,我總愛乘坐計程車。
方便嘛!
也因為我真的不懂各路巴士的路線行程。
那時候,相愛兩年的阿娟會跟我說:「只要是向那個方向的巴士都會在屋苑的車站前停下。」
說時,手指會不自覺向著家中某方向指去。
我往那邊看,當時是一個興建中的屋苑地盤,背後墨綠色的山脈仍清楚看見。
今年再看,那裡已被一座又一座粉橙色的大廈所遮掩。
我沒有不開心,因為碧綠色的落地玻璃窗和小露台多少帶來另一種讓人開懷的氣氛。
我捧著紙箱,耐心等待寫著「那個方向」的巴士來到。
不多久,往「那個方向」的巴士來了。
我捧著紙箱,大步跨上去,不太順地拿出錢包掏出硬幣投入錢箱,在行駛中左搖右擺的車廂裡隨著巴士搖晃擺動踏上樓梯走到上層。
聽說巴士上層比較舒適。
這是阿娟說的。
而當坐在靠近樓梯旁的那個空位,才發覺即使上層位置依然會嗅到倒流的汽車廢氣味。
洋溢著機油味的空氣中有阿娟的聲音飄盪過來。
「忍耐一下,很快便到。」
我回頭看。
隱約看到阿娟露出於巴士後排座椅上的頭顱。
如娃娃般化著細緻又美麗的妝容,五官在四周全是方格子車窗和梯形椅背扶手柄的映襯下顯得份外立體。
我扭過頭,坐正,看著面前深夜的街景。
霓虹燈照牌和街燈將夜路照成粉紅色的迷離。
「要是乘坐計程車早已回到家了。」另一把聲音說。
估計那是阿娟的新伴侶所說。
因為緊接下來,阿娟說。
「不好嗎?這樣便能多一點時間跟你在一起。」
我聽著。
想起從前也都聽過類似的說話。
可能是在某個陽光燦爛的日子裡在山徑間抱怨說天氣很熱時她說過:「你看,我們的前路是怎樣的一片光明。」
又或在步行街上人多擠逼時她故意貼近然後說:「這路設計得真好,我們可以大道理地黏在一塊。」
這類惹人歡心的說話,阿娟藏了多少在嘴巴裡?
我低頭,隨巴士行駛而搖頭晃腦。
從附近風景所得知,距離我家還有一段路途。
我百無聊賴地,手指刮著紙箱盒面上的膠紙邊緣。
同時背後仍不時響起阿娟的甜言蜜語。
「有時候經過這地方的時候我會想如果老了住在這種樓下是大公園的住宅便好了,早上或是黃昏一起散步。」
「有些人養狗會給寵物名字加上姓氏,我們日後如果要養也這樣做嗎?」
「明天想吃甚麼?為了你難度多高也可以,但最好不要太難,否則會煮得難吃。」
我打從肺部最尖端的部份深深吐出一口帶有微微酒味的悶氣,手指不耐煩地刮著紙箱上的膠紙。
巴士仍未到我應要下車的站,但我卻選擇在中高速行駛中離開座位站立起來。
後座的阿娟明顯看到了。
她略提高聲量說:「阿良?小心啊!不要站在樓梯旁,這樣很危險的。」
我看向她。
那雙在黑色眼線筆描畫下更顯童稚的眼睛,無辜天真地看著我。
阿娟走過來。
明明已是比我矮的了,卻仍裝模作樣地彎腰再抬頭看我。
「喝酒了嗎?」
時代感十足的桃紅色光感唇膏下的嘴巴果然隨時能說出幾句關懷備至的話語。
她摸摸我的紙箱:「怎麼不坐計程車?」
我以紙箱將她推開:「別說了,我想吐。」
當然,我沒有吐。
只是感覺嘔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