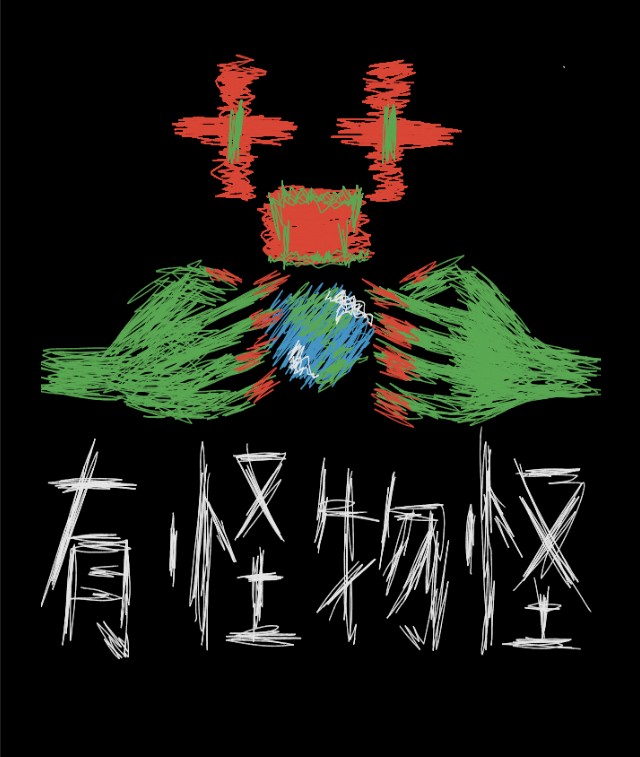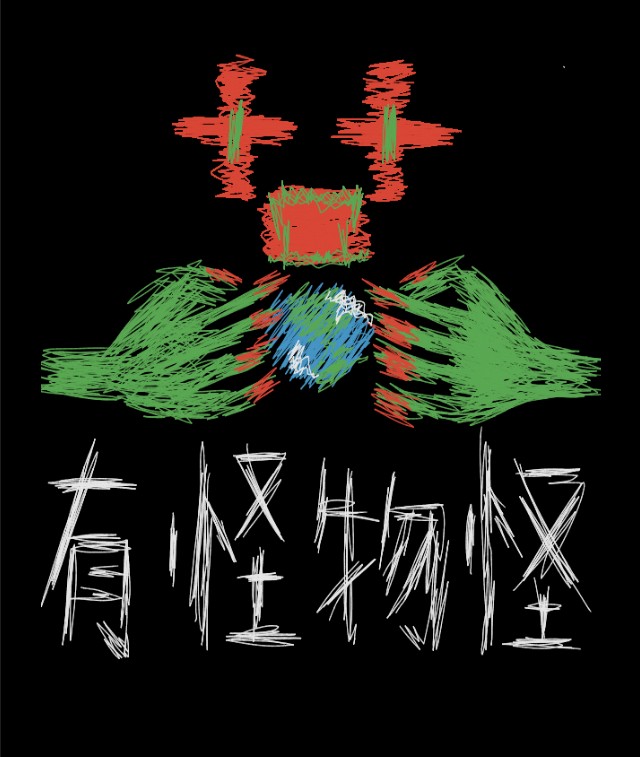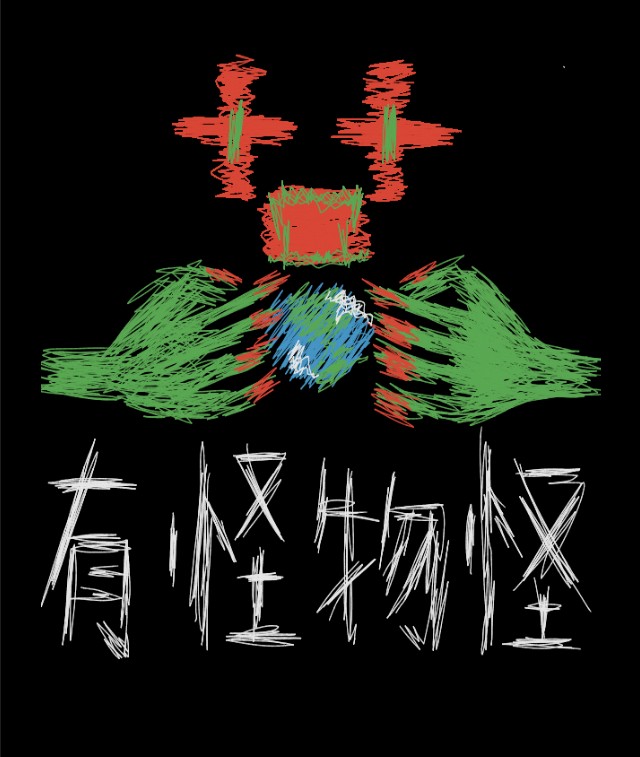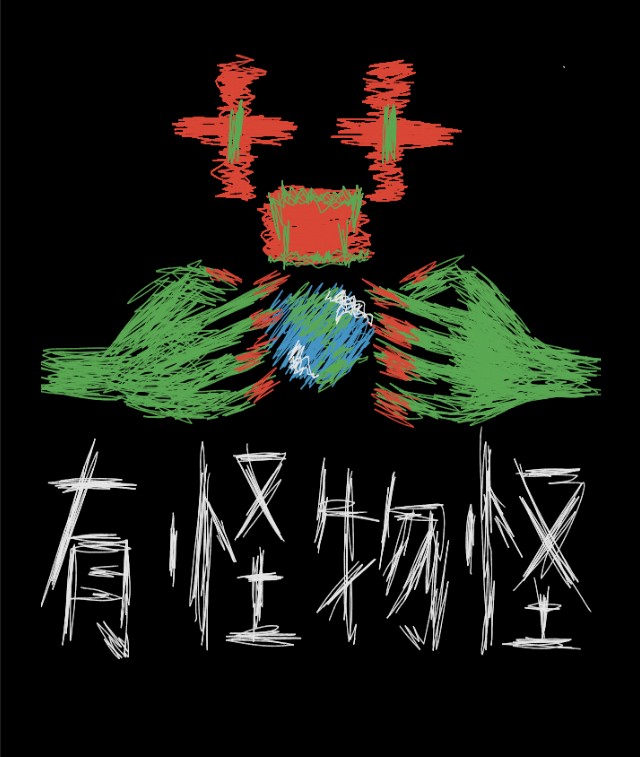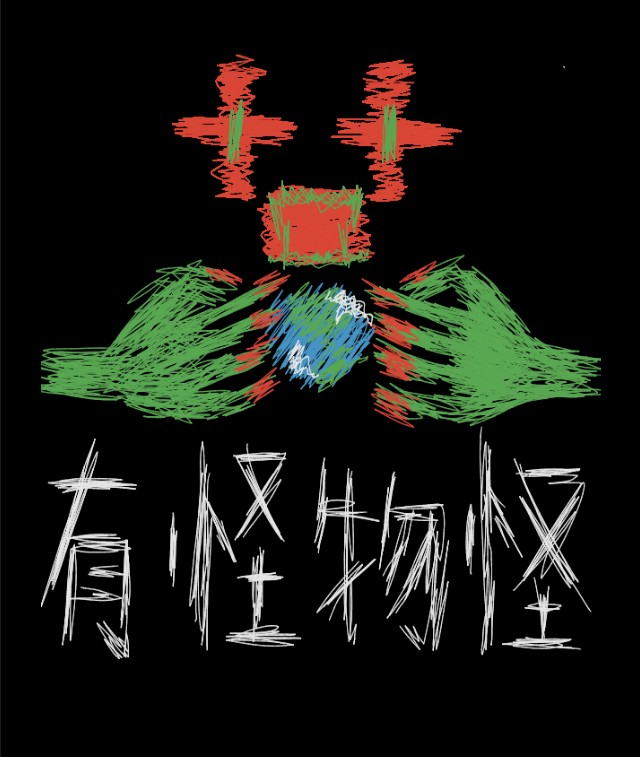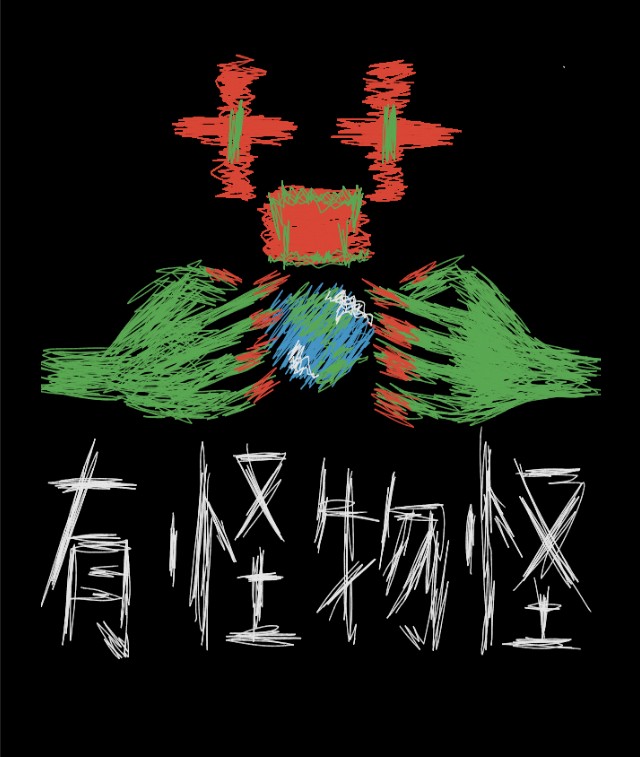開源道的蝴蝶是黑白色的。
牠們翅膀上長了像眼睛一樣的花紋,專家認為應該是為了求生,欺騙天敵所用。
蝴蝶停靠在工廈灰白色的混凝土牆上。我看不凊牠們翅膀上的脈絡—蝴蝶的翅膀是有顏色的,不同於蜻蜓—透明的翅膀,脈絡清晰可見。
説來奇怪,近來雨季期間我幾乎未見過蜻蜓出沒。
而且,那眼睛似的花紋未免太逼真了,久看著有種莫名奇妙的不安感覺,在微弱光線下更會反射出異樣光芒,像瞳孔中的深淵一樣。
有看過蒙羅麗莎的微笑嗎?據說它的眼會永遠和觀看的人互相凝望,專家指這是繪畫技巧所造成的視力錯覺。
開源道身處的觀塘屬於工業舊區,道路交通設計等配套放諸現在早已不勝負荷。街道頭尾兩端都是迴旋處,如果閣下有玩過模擬城市的經驗,大概會知道迴旋處並不適合設置在車流擁擠的地方—因為效率太低了。
人車擠迫,衛生欠佳的工業舊區,我不曾看過有蝴蝶出現,大概只是偶然吧?我不太懂得昆蟲的習性。
我常常在觀塘殘舊工廈的橫街中穿插。走橫街內巷可以避開塞滿走道的行人,雖然冷氣滴水很嚴重,溝渠排水坑也很臭,地下也不時有老鼠曱甴的屍體。按理而言,蝴蝶應不會出現在這樣的地方對吧?
最初我也是這樣覺得的。
一開始蝴蝶在開源道的廢氣中搖擺不定穿梭,滿步蹣跚前進,數量也不多。
日子久了,我發現了蝴蝶的數量增加了,甚至開始在室內出現,牠們多停靠在暗角的高處,乍看下甚至會令人以為只是屍體—其實牠們會動的,只是慢得幾乎察覺不到。
我察覺到的原因是,公司走廊的暗角有一隻蝴蝶,牠停駐了一個月有多了。
我出入走廊時觀察,發現了牠們應該是厭惡光線,喜歡躲在暗處,還會小心翼翼地稍微移動身體。
同事們最初都覺得好奇,牠是如何飛進室內冷氣空間?後來大概是見慣不怪了,不僅僅是公司,全港很多的室內地方都有。政府對此的解釋是近來適逢蝴蝶的遷徙季節,市區會經常看到蝴蝶出沒。於是大家的好奇心就滿足了。
奇怪在政府的新聞稿件竟然從未提及蝴蝶的品種;我也嘗試上網查看一下蝴蝶的品種,答案是一無所獲。
我試著和同事討論一下,該不會只有我感到違和吧?
結果他們彷彿像本能反應般乾笑一下,然後將話題轉成對客戶和老闆的抱怨—這些日復日茶餘飯後的標準話題更有趣味,大家都很熱衷。
初入行時前輩告訴我,上班時應該多想些亂七八糟的瑣碎事,這樣日子會過得比較快。
他們告訴我人生無聊得很,多想些亂七八糟的瑣碎事有助平衡心理,説畢時自己還不明所以地乾笑幾聲。大概成年人的玩笑都是無聲勝有聲的,掌聲笑聲都是表子,裏子只可心領神會。
某月初,我需要在公司加班,最後離開的我負責關掉冷氣電燈。
夜晚漆黑一片的辦公室相當寧靜,隱約可以聽見電腦待機的風扇聲。我作出最後的檢查,打算鎖門然後盡快離開。
缺乏冷風對流的悶熱空氣迅速蔓延開來令人不適,汗水由額頭流到頸上,我開始感到煩躁。
今日好像比往常更熱,但我才剛關上冷氣,怎可能會那麼熱?儘管有些許疑惑,但檢查完成了,上廁所然後趕快離開吧,我是這樣想著的。
公司廁所是隱藏式的,啞面銀色的大門和牆壁融為一體,材料的紋理在燈光反射下像某種特殊符號,遠看更像一塊銀色金屬碑。
我很少在公司加夜班,此刻我感到些不寒而慄,也許是辦公室太熱令我胡思亂想了,快洗臉然後離開吧。
洗手盆前的我脫下了眼鏡,閉上雙眼用雙手將臉沾濕,往常不過—有點不對勁,違和感彌漫全身,此刻我依然是雙眼緊閉的。但我感覺到背後有人,更準確地形容,是有生物的視線望著我。
廁所內的裝潢是用上玻璃和金屬,光線不足,冷酷的無機質感,詭異已不足以形容此刻的氣氛。
我在鏡中的反射看到身後有一隻蝴蝶,牠一如既往停靠在牆上的陰暗角落。翼上的紋路反射出瞳孔似的深諳,像黑暗中的獵人凝視獵物—我甚至不確定應該用‘’牠‘’還是‘’他‘’。
我感覺到彷彿像人一樣的視線。
理智上我不斷強調是錯覺,也許是我太累了。可是未免太奇怪了,蝴蝶會那麼靈異嗎?平日廁所有那麼寒冷嗎?身體瞬間憶起了這種令人極為不安的寒冷感覺。
實際上這些不是氣溫帶來寒冷感,冬天或冷氣的寒冷感並不是這樣的,你可以輕易分辨出來,這種寒冷感像由全身血液中散發,教人渾身躁動不安。
領取先人遺體的經驗之談,停靠屍體的殮房就是這樣。
可是離開公司路上必須要經過走廊。
本能驅使我應該盡快離開,我馬上轉身,將視線放在蝴蝶上不敢移開,然後快步奔出門外。
平日停靠走廊的蝴蝶消失了,但此時此刻不是思考的時候,本能和恐懼感告訴我必須盡快鎖門然後離開。我也沒有想太多,急步經過走廊鎖門然後走到升降機大堂了。
大堂的面積大約是半間標準課室,同樣有一塊落地玻璃。夜晚的燈光可以輕易照射進來的。燈光是自動感應的—正常而言,但今晚的大堂比往常更光,我感到有點刺眼,光暗的強烈對比令人看不清楚玻璃外的街景。
玻璃外側停靠了幾隻蝴蝶,牠們伸展雙翼,令我覺得毛骨悚然—像是玻璃箱內被觀察的動物。
「仆街,依家係咪玩野呀!」我開始用粗口咒罵替自己壯膽,嘗試掩飾自己不受控制地顫抖的雙手。甚至已經不肯定自己有沒有按下升降機的按鈕,直到升降機到達樓層的聲音響起。
但我總覺得比往常來得更久。
公司所在的樓層不高,來往地下只需要十多秒,升降機的設計是啞面銀色配以三面鏡子。
配合著咒罵聲,我右手不斷按下關門的按鈕。
接下來漫長的十多秒,我秒速地思考著那如同恐怖片主角的經歷,下一秒懷疑自己休息不足出現了幻覺,再下一秒懷疑自己得了精神病;還是説這一切都是夢境嗎?不,身在夢境中是不能夠記起事情發生起點前的記憶,今早的早餐是金拱門,所以這是現實。
「地下,Ground Floor」大概將我拉回了現實。下一秒的我倒開始懷疑起了‘’現實‘’。
升降機外的地下大堂漆黑一片,更不用說平日大廈管理處的看更不見了—大廈是廿四小時運作的,入職以來我不曾見過關燈。
儘管察覺到情況真的詭異得難以形容,但我可不想再逗留糾纏了,應該盡快離開。萬幸的是大門並沒有像俗套的恐怖片情節一般鎖上,令我暫時鬆了一口氣。
「屌你老母...」我甚至已經不知道此刻‘’你‘’的主體是什麼。
眼前的開源道沒有任何車,寧靜得令人覺得可怕—按理總會有汽車的聲音吧?你印象中見過沒有任何車的開源道嗎?
沒有,甚麼都沒有。車,人,一個都沒有。
手機顯示的時間是十點正。
暗黃色的街燈指引著唯一的方向,盡頭隱約可見地鐵站和迴旋處。平常我會在橫街中穿插的,比起開源道會更快到地鐵站,今晚恐懼感凌駕了一切,理智上可不想走在沒有任何燈光的後巷。
我的意識卻是相反的,不知怎麼雙腿竟緩緩走向了平時走的後巷。
我很好奇,腦袋裏有一股聲音慫恿我走進去。我是把恐懼感拋諸腦後了嗎?大概不是,只是暗得無法看清前面的小巷像黑洞一樣把我牽引著,有一股難以形容的吸引力。我很好奇,好奇小巷裏的是甚麼,是答案嗎?還是更多的疑問?那股聲音告訴我,必須要走進去。
後巷的入口很窄,和平日不同的是,左右牆上都佈滿了蝴蝶。數以百計?不—數以千計的蝴蝶佈滿在牆上,微弱的月光在大廈間的空隙照射在混凝土牆上,面前有數千雙以上的眼睛注視著我。
「當你凝視深淵時,深淵同樣凝視著你。」
我心理開始崩潰了。
平常看恐怖片,玩鬼屋,我們知道是虛構杜撰的,常理科學可以解釋的,因此不會害怕—或者是距離真正意義上的害怕很遠。此刻我卻解釋不了眼前的一切,人對一切未知的都充滿恐懼。
恐懼感支配著我全身,可是雙腿一直不聽使喚,像被操縱似的繼續走向後巷的深處,向著深淵進發。黑洞將一切有形無形的吸引著,即使光也不例外。
僅存的理智發現了有一隻蝴蝶停靠了在我手臂上,不知從何來的本能反應告訴我應將牠拍打趕走,可是腦袋裏的聲音極力反對,原本的耳語開始變得猙獰,我能感受到那如同泥沼一般的惡意在聲音背後。
看來是我對昆蟲厭惡的本能反應戰勝了一切,儘管我一度覺得自己失去了對身體的掌控能力。
正常的昆蟲拍打下應是會飛走的,但蝴蝶在右手拍打下竟迅速化成了一堆銀色粉末,粉末極其幼細,在微弱的氣流下迅速飄散。伴隨著更多的疑問,雙腿也突然變得聽使喚了,本能反應地馬上拔足跑回開源道。
我跑了有多久?中途經過些什麼?我有拍卡入閘嗎?回過神來早已身處在車廂內。
夜深關係,車廂內的人不多。
我勉強地大口呼吸著,近乎窒息似的,橫膈膜傳來陣陣的刺痛,久未鍛煉的身體在腎上腺素爆發後有點疲憊,思考的能力因為缺氧暫時停止了。
現場環境看來很正常的—我暗自慶幸了起來,相比先前的種種現象。除了人們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之外,最低限度我可以肯定是來自於‘’他‘’和‘’她‘’。
「衛生署宣佈,將會降低疫苗接種年齡下限至十二歲...邱騰華表示下週將會和各大院校代表商討學生接種疫苗安排...漁護處表示近日有大批蝴蝶遷徙,都是來自西藏新疆的獨有品種,形容情況並不罕有,呼籲市民...」大概因為夜深關係,可以比平時更清晰聽見車廂的新聞。
剩餘的車程我在腦中假設各種的理由解釋,唯一解釋就是我精神失常了,以致於我反復確認自己不是精神病—指甲劃過手臂有痛楚的感覺,但精神病人能夠察覺自己是精神病嗎...倒不如google如何辨別自己有精神病...所以我懷疑自己真的有精神病嗎?痴撚線?會有人覺得自己不正常嗎?...腦內反覆自問自答。
然後了?
使用人多的交通工具回家,一如所有的恐怖片一樣,落單往往是最危險。
父母親都很正常,家中也沒有任何蝴蝶,暫時安全?我將方才的種種經歷告訴父母親,情節離奇得可以拍成電影了。
「啊仔你係咪返工太攰?」
「黑到咁依家上柱香定下心先啦。」
「近排你好黑咩?睇你印堂都無咩事啊。」
「所以成日叫你唔好咁夜返。」
父母親的輪流問候,是平時我熟悉的家,看來應該可以放心了,經歷了今晚種種我也需要梳洗一下然後馬上休息。
今晚是漫長的一夜。
心力交瘁是此刻的最佳形容,不知不覺間眼簾敵不過睡意,視線回到了一片黑暗之中。
鬧鐘響起的時候是十點,說起來我有調教過鬧鐘嗎?
一切都很正常,客廳的單車消失了—父親大概是外出踩單車了,母親大概是和朋友有約外出了。
未戴眼鏡的我視力模糊,但在熟悉的環境下活動還是綽綽有餘的,我決定先梳洗一下。
廁所安裝的燈光偏白,洗手盆的鏡上帶些白色的水漬。洗手盆前的我閉上雙眼用雙手將臉沾濕,往常不過,除了一件事情以外。
‘’它‘’的視線。
牆上的‘’它‘’。
和鏡中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