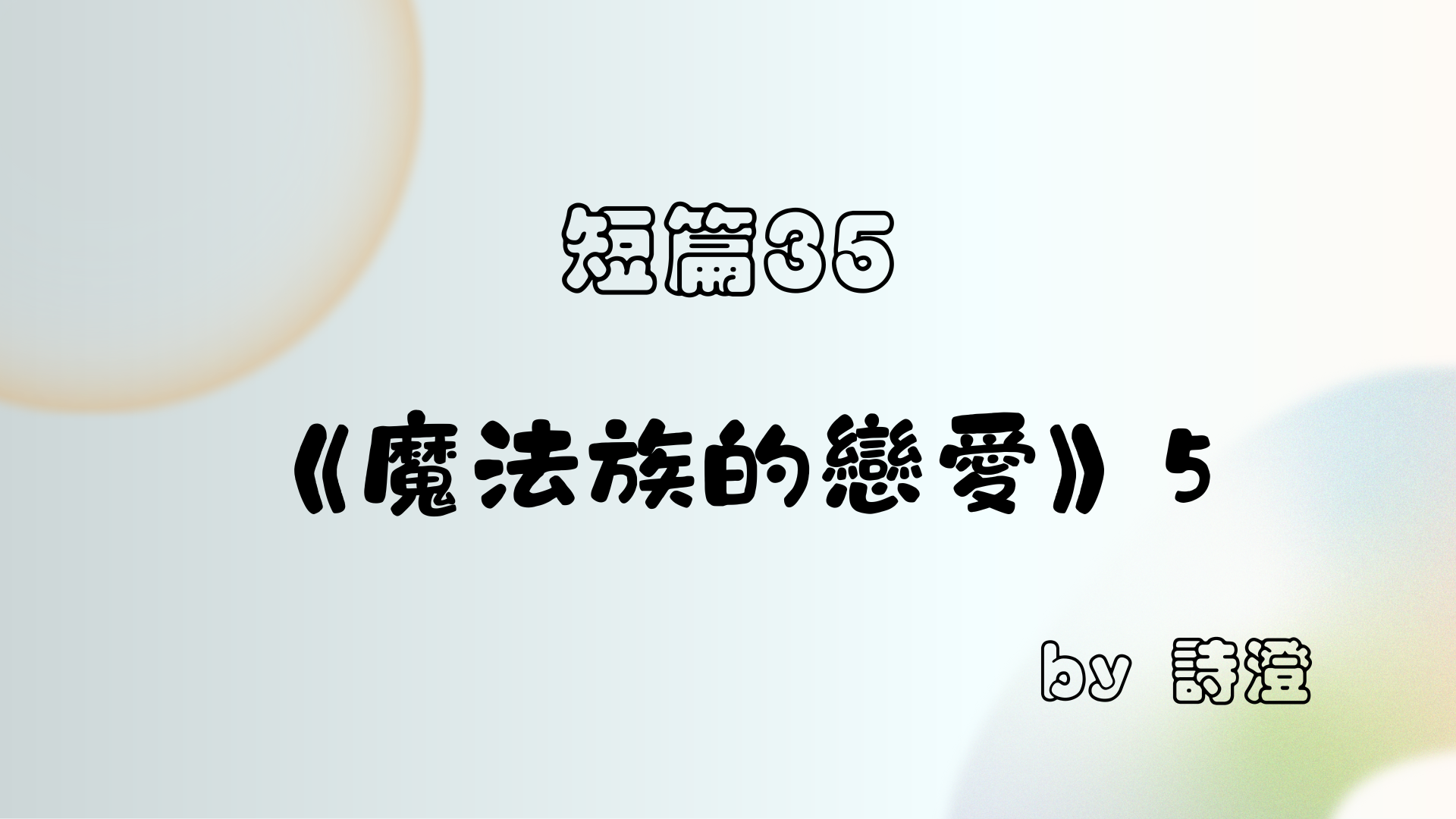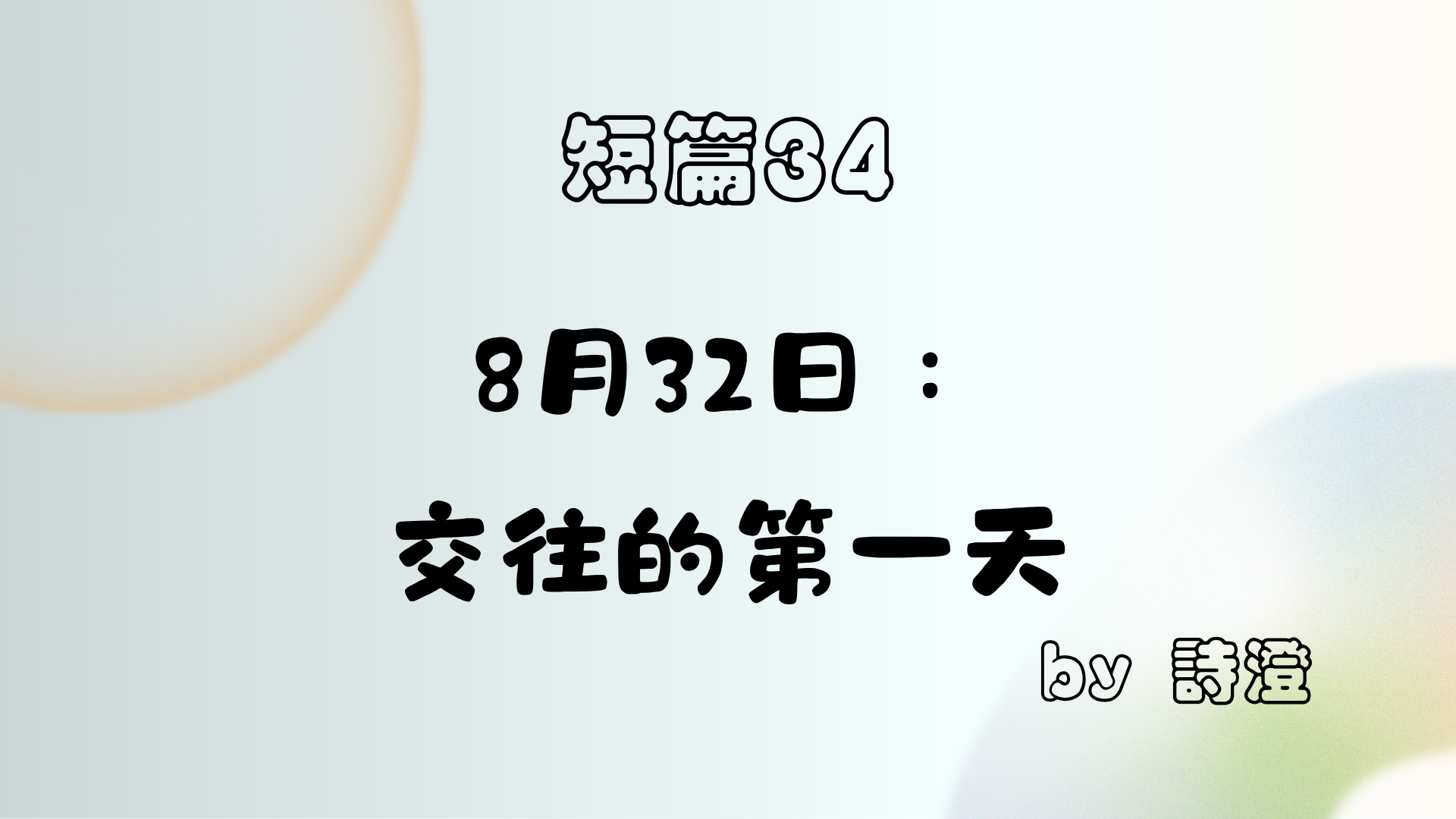太陽高掛,天空沒半絲雲,熱騰騰的暑氣似要把大地熔掉。
這時候,躺在涼榻上午寐自是人生一樂。
又或是喝著冰鎮酸梅湯,和三五知己說說笑笑,倒也悠然。
在竹林下圍棋,在柳岸邊垂釣,消閒玩意真是多不勝數。
只是這些都不屬於夏侯暖。
她愛幹活,她喜歡流汗,她希望憑著雙手獲得成果。
在這麼一個艷陽天,她束起頭髮,穿著粗衣,擔起水桶,赤足在泥畦上與佣農們一起下田澆水。
如有外人看見,還道這雲莊的少莊主,不是呆子,便是瘋子。
「少莊主----」僕人從遠處跑來,喘著氣:「夫人回來了,著你快去見她。」
夏侯暖回到府邸,沐浴更衣,然後來到大廳。
「娘親,路上辛苦了。」夏侯暖為娘親捧上香茶。「可有好消息?」
「暖兒可聽說過鳳家?」
「鳳家乃榮國第一首富,孩兒自然聽說過。」
「那鳳家的當家又是誰?」
「鳳文婕鳳大家為經商奇才,年僅二十已把家業經營得有聲有色,甚至被皇上封為御商,在榮國內可說翻雲覆雨。」夏侯暖說:「但我們夏侯家和鳳家一向沒什麼來往,娘親提起鳳大家,有什麼原因嗎?」
夏侯夫人話鋒一轉:「暖兒,自你爹爹去後,雲莊只靠娘親一介婦孺苦苦支撐,現在所剩的不過是偌大的門面,實則外強中乾。」
「娘親辛勞,孩兒自是深知,只恨孩兒愚魯,未能為娘親分憂。」
「眼下債主快將臨門,再無應對良方,只怕祖業不保。」夏侯夫人說:「幸好娘親這次到京師,偶遇鳳大家,她答應送我黃金十萬,以應燃眉之急。」
夏侯暖一聽,心裡便隱隱覺得不妥:「商人重利,怎會無故相助?她開了什麼條件?」
「她……」夏侯夫人有點吞吐:「……她要成為雲莊的女主人。」
「她要佔據雲莊,那豈不是同樣祖業不保?」夏侯暖不解:「那我們何需向她求助?」
「她要的不是雲莊,她要的是……」
「她要什麼?」
「她要的是你。」
夏侯暖一愣:「孩兒不明白。」
「鳳大家願送上妝奩十萬,要嫁你為妻。」夏侯夫人咬咬牙:「娘親已答應了她。」
夏侯暖失笑:「娘親說笑了。」
「婚姻大事,豈同兒戲?」
「娘親----」夏侯暖皺眉:「孩兒怎可娶妻?」
「娘親也知道委屈了你,但這是拯救雲莊的唯一方法。」夏侯夫人說:「難道你忍見雲莊百年基業毀於一旦?他日娘親死落黃泉,你叫我有何顏面對你爹爹和列祖列宗?」
夏侯暖迫於無奈,只好咬牙答應。
今天是雲莊少莊主夏侯暖迎娶大富商鳳文婕的大喜日子。
鳳家極豪氣,不單大排流水宴,還派錢派糧,大街小巷盡皆歡騰起來。
一對新人在喜堂上一拜天地、二拜父母,互相交拜,禮成。
新郎新娘給牽進新房。
夏侯暖看著正端坐在喜床上的新娘,腦海裡不覺泛起了半月前的一幕。
----三更時份,夏侯暖踏月而來,在鳳府後園與鳳文婕會面。
「鳳大家----」
鳳文婕回頭,只見她容顏端麗,一雙眼睛深邃靈動。
「夏侯暖深夜造訪,實在是情非得已,還請鳳大家多多包涵!」
「我倆快要成為夫妻了。」鳳文婕微微一笑:「夏侯公子何需客氣?」
「夏侯暖正為此事前來。」夏侯暖說:「在下很感激鳳大家義助雲莊,但我倆不能成親----鳳大家借給雲莊的銀兩,夏侯暖定必想辦法儘快歸還。」
「夏侯公子何出此言?」
「夏侯暖其實是……」夏侯暖猛一咬牙:「……是女子。」
----夏侯暖想像過鳳文婕知道真相後,會驚惶失措,會勃然大怒,會尖叫哭鬧,卻怎樣也想不到,她居然臉露微笑,柔聲說:「那又如何?」
「這……」夏侯暖輕皺眉頭。「鳳大家可曾聽清楚----夏侯暖和鳳大家同是女兒身,怎能成親?」
「文婕認為無妨。」鳳文婕依然雲淡風輕:「這是我倆閨閣之事,外人無從得知。」
夏侯暖一愣:「你明知夏侯暖是女子,不能成為良人,仍堅持嫁我為妻,究竟為何?」
「這當然有原因。」
「還請鳳大家坦白告知。」
「文婕已懷有身孕。」
夏侯暖給震住。
「我兒不能成為野種,受人唾棄。」鳳文婕淡淡地說:「夏侯家作為名門望族,我嫁你為妻,孩子一出生,便是名門之後,將來前途一片光明。」
「怪不得……」夏侯暖喃喃的說:「怪不得……」
「夏侯公子可願意助文婕達成心願?」鳳文婕說:「當然,文婕為報答大恩,自當竭盡所能,助夏侯公子中興雲莊。」
夏侯暖心裡一番計算----鳳文婕願意襄助雲莊,已是求之不得;她嫁自己為妻,還會為自己生子,那自己是女兒身的秘密便不愁被他人識破了,這真是兩全其美的好事。自己又怎能拒絕?
「夏侯暖謹遵鳳大家吩咐。」
「文婕深感夏侯公子盛情。」
回想到這裡,夏侯暖也知道不應耽誤下去,於是拿起喜秤,挑開新娘的紅頭巾。
兩人四目相投。
「鳳大家----」
「我倆既已成親。」鳳文婕輕聲說:「夫君應換過稱呼才是。」
鳳文婕含笑說:「夫君,是時候喝合歡杯了。」
「這……」夏侯暖吶吶地說:「這酒不喝也罷。」
「我倆雖是假鳳虛凰。」鳳文婕說:「妾身還是希望能夠依循俗例,還望夫君成全。」
夏侯暖也不便拒絕,只好把玉杯斟滿,遞給鳳文婕:「娘子,請酒。」
兩人交纏著玉臂乾杯。
----這酒極醇極香,夏侯暖喝進口裡,卻感到絲絲苦澀。
「夫君,我們早點安歇吧!」
夏侯暖看著這大紅喜床:「娘子,你上床休息吧!」
「那夫君呢?」
「我睡在軟榻上。」
「以後年年月月,夫君打算一輩子睡在軟榻上?」
「這……」
「我倆同是女兒,同床共枕想也無傷大雅。」鳳文婕一派從容:「夫君毋須顧慮。」
「……好吧!」
鳳文婕當著夏侯暖面前,大大方方地解開喜服上的扣子。
夏侯暖連忙轉過身去。
鳳文婕脫掉身上喜服,只剩下貼身衣物,然後鑽進被窩裡。
夏侯暖拖拖拉拉地躺到床上,卻也不敢掀開被子。
鳳文婕輕輕挪近夏侯暖,把被子拉到她身上。
兩人的肌膚驀地相接,夏侯暖如遭火灼,登時縮開。
鳳文婕輕笑一聲,背過身,才一會,便發出清清淺淺的鼻息。
折騰了一整天,夏侯暖也早已累極,不久也墜入睡鄉。
一夜好眠。
第二天早上,夏侯暖睜開惺松睡眼,赫然發現兩副嬌軀正交纏在一起,說不出的親蜜無間。
夏侯暖身子發僵,一動也不敢亂動。
感覺到懷裡人兒正緩緩轉醒,夏侯暖馬上閉眼裝睡。
夏侯暖感到一隻小指頭正輕撫自己的眉目。
夏侯暖只覺癢不可耐,稍稍別轉臉。
但小指頭追蹤過來,順著夏侯暖臉頰滑過,在她下巴嬌嫩處徘徊。
夏侯暖裝不下去了,只好打個呵欠,順勢翻身坐起來:「……娘子,早安。」
「夫君,早安。」鳳文婕柔聲說。
「現在天時尚早,娘子還是多歇一會吧!」
「夫君既已醒來,為妻子者又怎能不起床侍奉?」
「娘子毋需多禮。」夏侯暖說:「我自少便習慣了每朝早起,到後山練武。」
鳳文婕失笑:「我倆新婚燕爾,夫君卻早起練功,妾身難免會遭人笑話。」
夏侯暖一怔:「那……我不去了。」
「謝謝夫君體諒妾身。」 鳳文婕說:「其實我們起來也好,也要向安人請安了。」
夏侯暖點點頭。
鳳文婕起床穿衣,梳洗一番,再坐到鏡台前梳理髮髻。
夏侯暖也趕快把自己打理妥當。
夏侯暖看見鳳文婕從妝奩取出金釵,不往頭上插,反往自己指頭劃去。
夏侯暖猛吃一驚,出手如電,一手握著她的玉腕,一手奪走金釵。「你幹什麼?」
鳳文婕嘴角掛著饒有深意的微笑:「聰明如夫君,難道還不明白?」
夏侯暖稍一動念,便明其所以----等會有下人過來驗喜,不見落紅,人多嘴雜,一旦洩漏出去,叫她們如何應對?
夏侯暖也不說話,逕自用金釵把指頭劃破,再用力一掐,鮮血便泊泊流出。
她把鮮血塗在雪白的锦帕上。
鳳文婕執起夏侯暖的素手,把那受傷的指頭放到嘴裡輕啜。
十指連心,一陣酥麻的感覺直往心頭傳去,夏侯暖大驚失色,卻呆呆的不懂反應。
鳳文婕用綉帕把指頭擦乾淨,再順勢緊扣她的五指不放。
夏侯暖稍微掙了一下,掙不開,也只好由她了。
夏侯暖和鳳文婕並肩而行,十指緊扣,儼如一對甜蜜的小夫妻,眾人看在眼裡,無不心生羨慕。
她們來到大廳,看見夏侯夫人早已端坐座位上。
「娘親早安。」「安人早安。」
「乖。」
「安人請茶。」鳳文婕正要按規矩跪下,夏侯夫人忙把她托住:「媳婦不必多禮。」
----得人恩果千年記,面對著雲莊的大恩人,夏侯夫人可不好意思端起做婆婆的架子來。
反倒是鳳文婕堅持跪下向夏侯夫人敬茶。
夏侯暖念著鳳文婕懷有孩子,怕她受累,連忙扶起她,把她送回椅上安坐。
鳳文婕回頭向她甜甜一笑。
夏侯暖心裡一跳,回到自己的座位,低頭喝茶。
夏侯夫人皺眉:「你是新嫁婦人,怎可獨自出門?但生意也不能耽誤,不如讓暖兒伴你同去吧!」
「媳婦自是求之不得,不知夫君可願與妾身同行?」鳳文婕看著夏侯暖。
「這個當然。」夏侯暖想也不想便回答。
「謝謝夫君。」鳳文婕說:「那我們收拾一下,明天便出發吧!」
第二天吃過早飯,她們便出發了。
馬車廂內佈置精巧華麗,寬敞舒適。
夏侯暖看書,鳳文婕看賬本,車廂內寂然無聲。
不一會,鳳文婕想是有點累,把頭枕在夏侯暖的肩膊上,打起盹來。
夏侯暖稍稍調整著坐姿,讓她睡得舒服一點。
看著鳳文婕極美的睡顏,夏侯暖不覺心生憐惜----鳳文婕自幼父母相亡,偌大家業靠她一人維持,箇中辛酸,自不待言。現在她身懷六甲,卻不得與心愛之人相守,想必內心悲苦之極----自己便儘可能關顧她多一些吧!
夏侯暖伴著鳳文婕,踏遍榮國各省各地。
每到一處,鳳文婕也會把夏侯暖介紹給各店主管認識,告知他們夏侯暖的主意就是她的主意,要他們絕對聽從夏侯暖的指令。
鳳文婕細心指導夏侯暖如何稽查賬本,如何考核僱員,如何與有關官員週旋。
夏侯暖對鳳家的生意認識越多,便對鳳文婕便越加敬佩----一個女兒家,能在詭雲多變的商場佔一席位,當中所需的智慧魄力毅力,絕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
夏侯暖既想中興夏侯家,也希望能替鳳文婕分憂一、二,所以即使對營商之道沒多大興趣,也竭力用心學習。
鳳文婕在人前英明果斷,氣度雍容。但每當和夏侯暖單獨相處時,便會卸下堅實的外殼,搖身變為弱柳娉婷,對夏侯暖百般依賴。
夏侯暖心底柔絲總是不由自主地給輕輕牽動著……
那天,她們為避風雪,不得不在一個小鎮留宿。
儘管暖爐熊熊,一床錦被,鳳文婕還是手足冰冷,輾轉難眠。
鳳文婕的聲音彷似悲鳴:「……妾身好冷……」
夏侯暖心裡一軟,掀開被子,伸手把她抱在懷裡,用自身的體溫去逐散她的寒意。
鳳文婕環抱著夏侯暖的腰肢,輕蹭她的頸窩,在她耳邊呢喃:「……抱緊一點,求你了……」
夏侯暖只好把她再摟緊一些,兩人之間已無空隙。
似有還無的幽香在鼻際縈繞,懷內人兒猶如軟玉,夏侯暖的心窩似有頭小貓在搔癢。
鳳文婕卻變本加厲,嬌軀不斷往她懷裡鑽,似要把自己揉進她的血肉裡。
夏侯暖給迫出一身薄汗。
過了好久,鳳文婕的手腳轉暖,人也慢慢睡去。
看她睡熟了,夏侯暖試著拉開她的手,但她仍是緊抱不放。
夏侯暖輕嘆,只好由她。
自此之後,兩人每夜相擁而眠。
那天,夏侯暖早起,一眼瞥見床鋪上沾有小片嫣紅。
身為女子,夏侯暖當然猜到那是什麼。但按日子算,自己的月事應該未到,而身體也沒有絲毫不適,那葵水不會是自己的。不是自己,那便是……
夏侯暖心裡猛然一驚----不會是鳳文婕的胎兒出了什麼問題吧?
夏侯暖略懂歧黃之術,乘著鳳文婕睡熟,替她細細把脈。
結果令夏侯暖大吃一驚----
夏侯暖怕自己不小心斷錯,再三把脈,結果仍是一樣。
「夫君不用再診了。」鳳文婕突然睜開眼晴:「是的,妾身沒有身孕。」「沒有身孕,沒有情人,妾身當日所說的,全是謊言。」
「你……」夏侯暖給震住:「你為什要騙我?」
「不這麼說,夫君又怎會同意娶妾身?」
夏侯暖只覺腦裡亂成一片:「你明知我是女兒身,卻願送上豐厚妝奩,甚至不惜說謊騙我,你究竟打什麼主意?」
「妾身對夫君情根深種,所作所為,無非想與夫君終生相守。」
「情根深種?」夏侯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我素昧生平,你怎麼會……」
「是夫君把妾身忘記了。」
----那一年,她們只有十歲。
那時候的鳳文婕還沒有和家人相認,只是一個孤苦無依的小乞丐。
大寒之隆,漫天飛雪。
小文婕躲在破廟裡,又冷又餓,已是懨懨一息。
與家人失散了的夏侯暖,恰巧來到破廟避雪。
她看見那躺在角落的小女孩,十分同情。
夏侯暖沒有嫌棄小女孩又髒又臭,讓她偎靠在自己懷裡,把身上的錦裘脫下來,把兩人密密包裹著。
夏侯暖還把懷裡的糕點慢慢餵給她。
小文婕肚子飽,身子暖,迷迷糊糊便睡了過去。
天剛亮,僕人尋到破廟,不由分說,便帶走夏侯暖。
夏侯暖只來得及把隨身小玉佩塞在小文婕懷裡。
小文婕醒來,發現了玉佩,上面刻了一個「暖」字……
「就因為這樣,你便對我鍾情?甚至不在乎我是一個女子?」夏侯暖輕聲問。
「那夜的溫暖,妾身從來沒有一刻忘記過。」鳳文婕緩緩地說:「在以後的日子裡,無論遇到再多的困難,妾身也沒有放棄,因為,妾身心裡有夫君,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與夫君並肩同行。」
「可是----」
「妾身知道,夫君還沒有喜歡上妾身。」鳳文婕輕咬櫻唇:「不要緊,妾身可以等,即使要等上一輩子……」
看著鳳文婕眼裡深情,夏侯暖只覺胸口又酸又麻,忍不住脫口而出:「不用這麼久……」
她的話給堵在唇邊……
-全文完-
( 個人作品集 – www.方愚.com )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