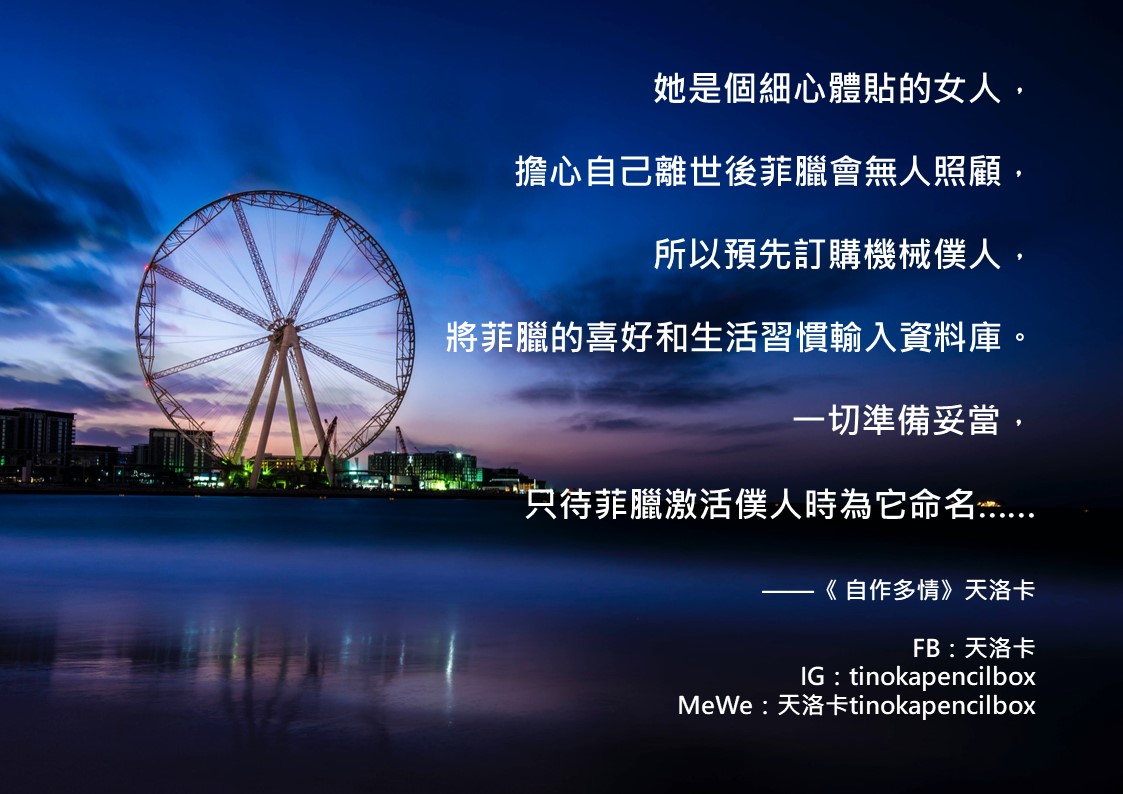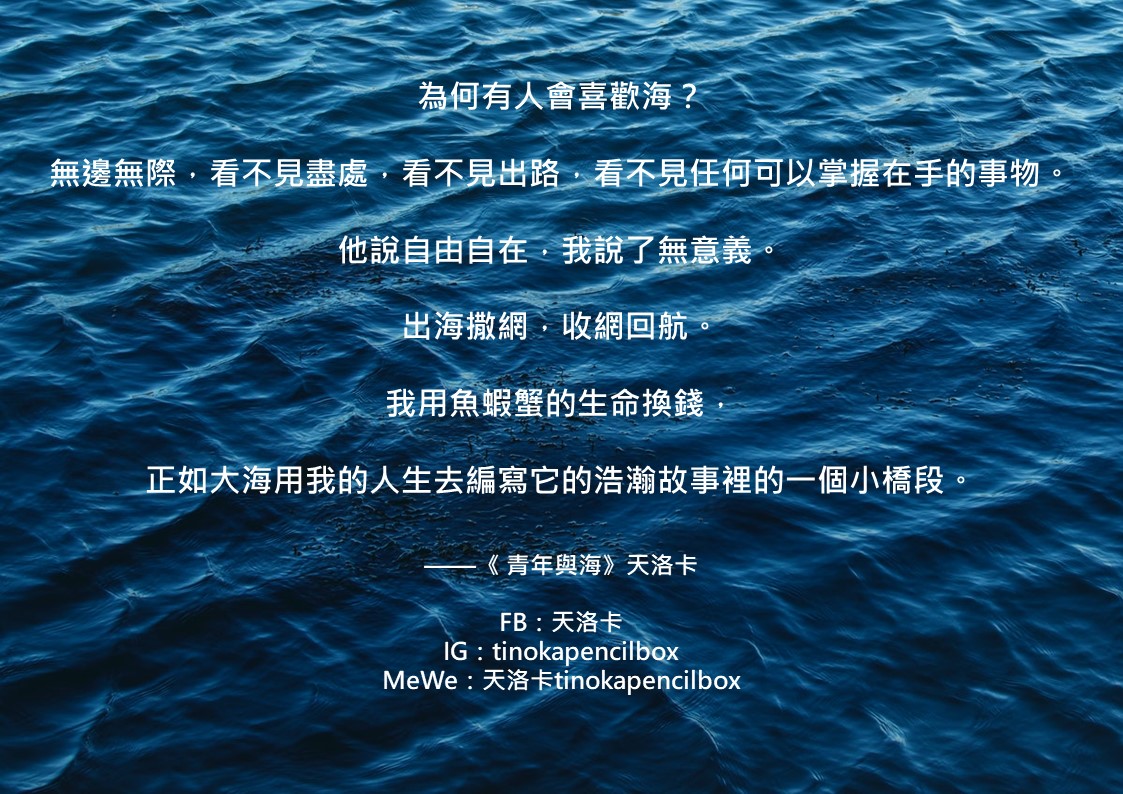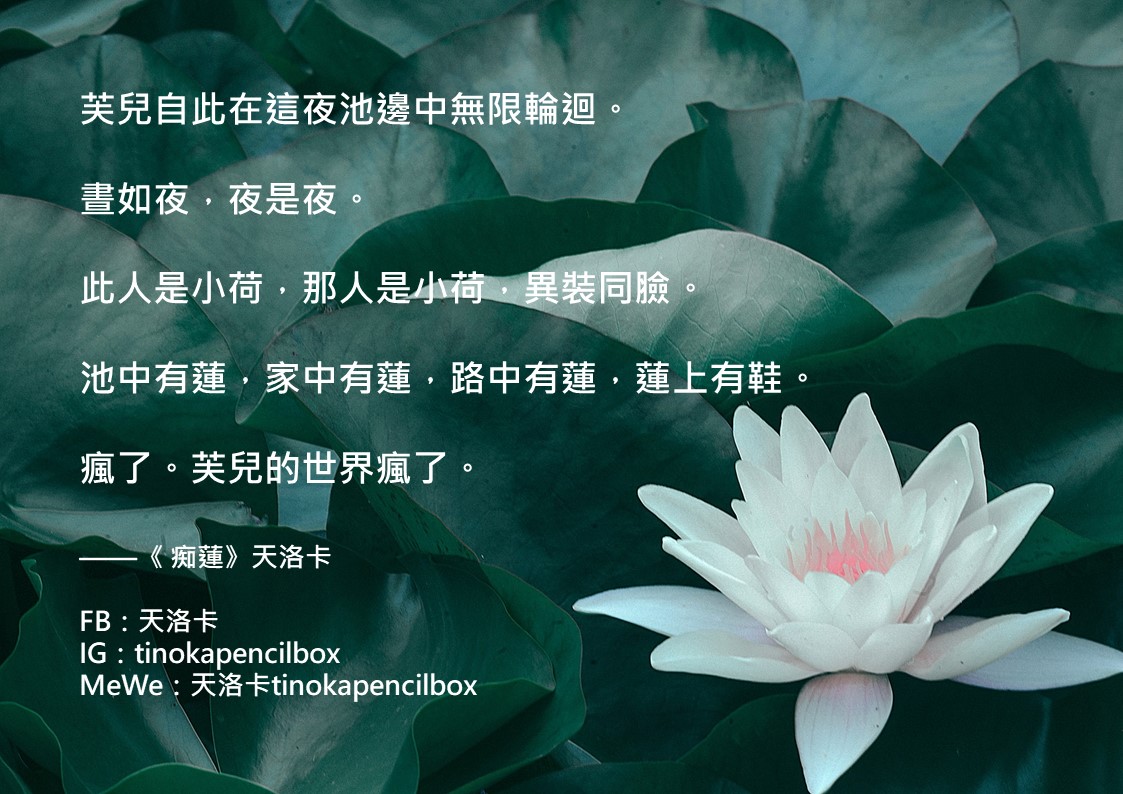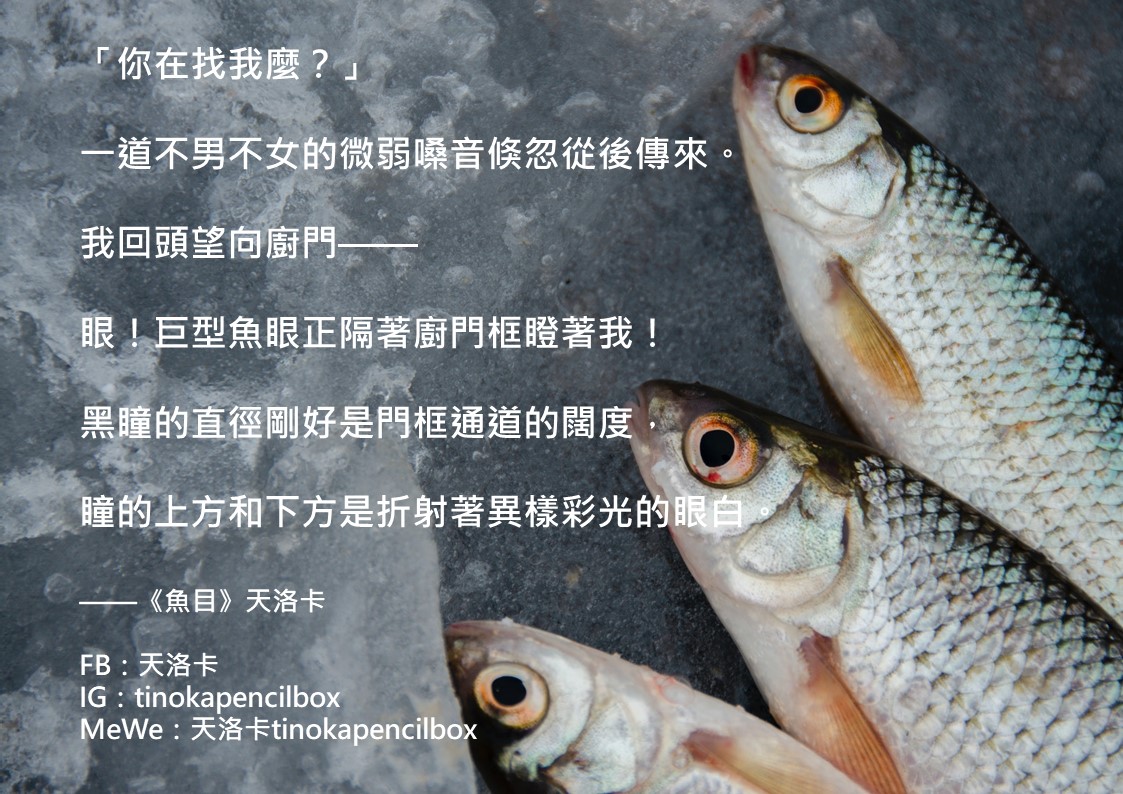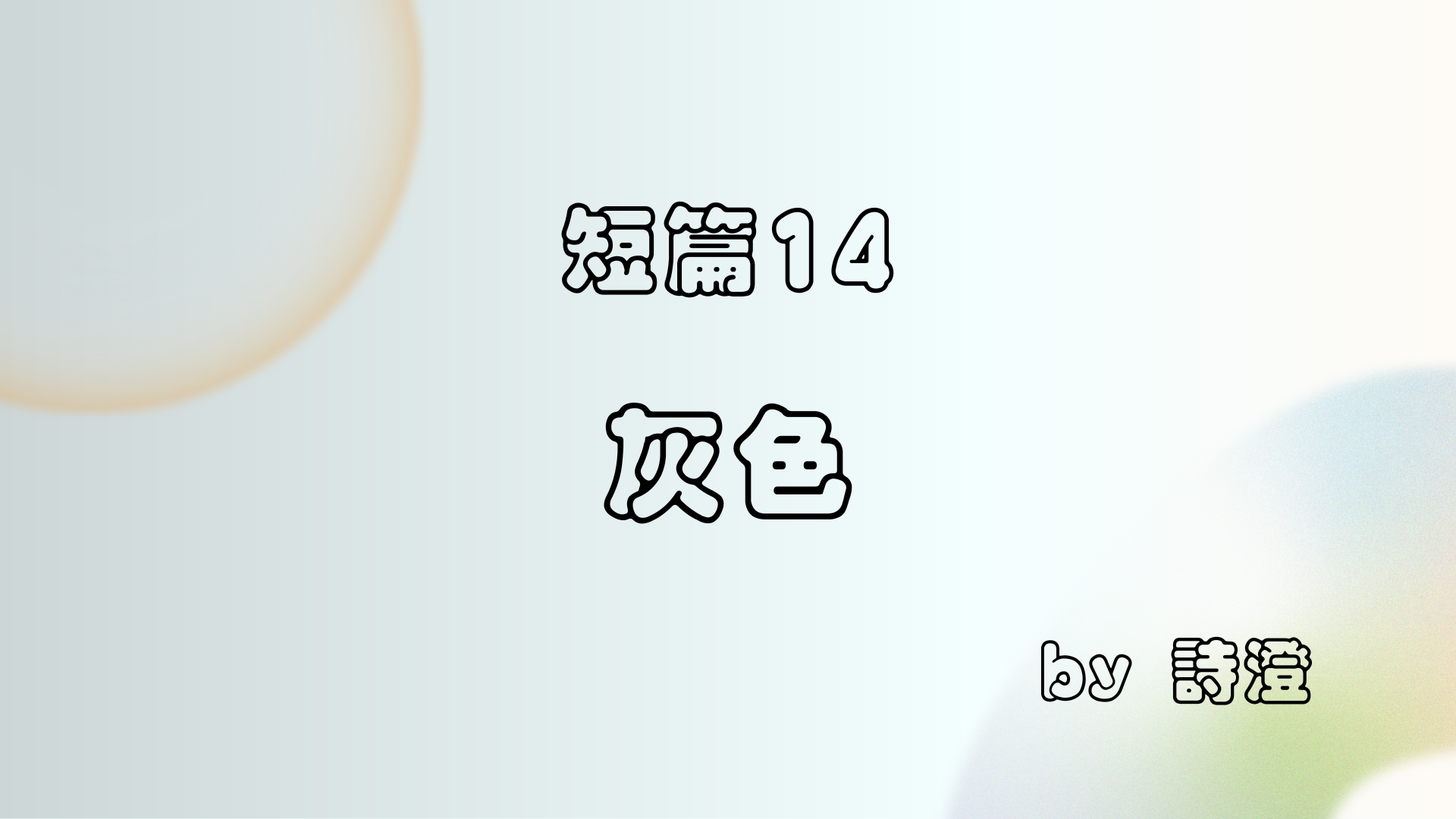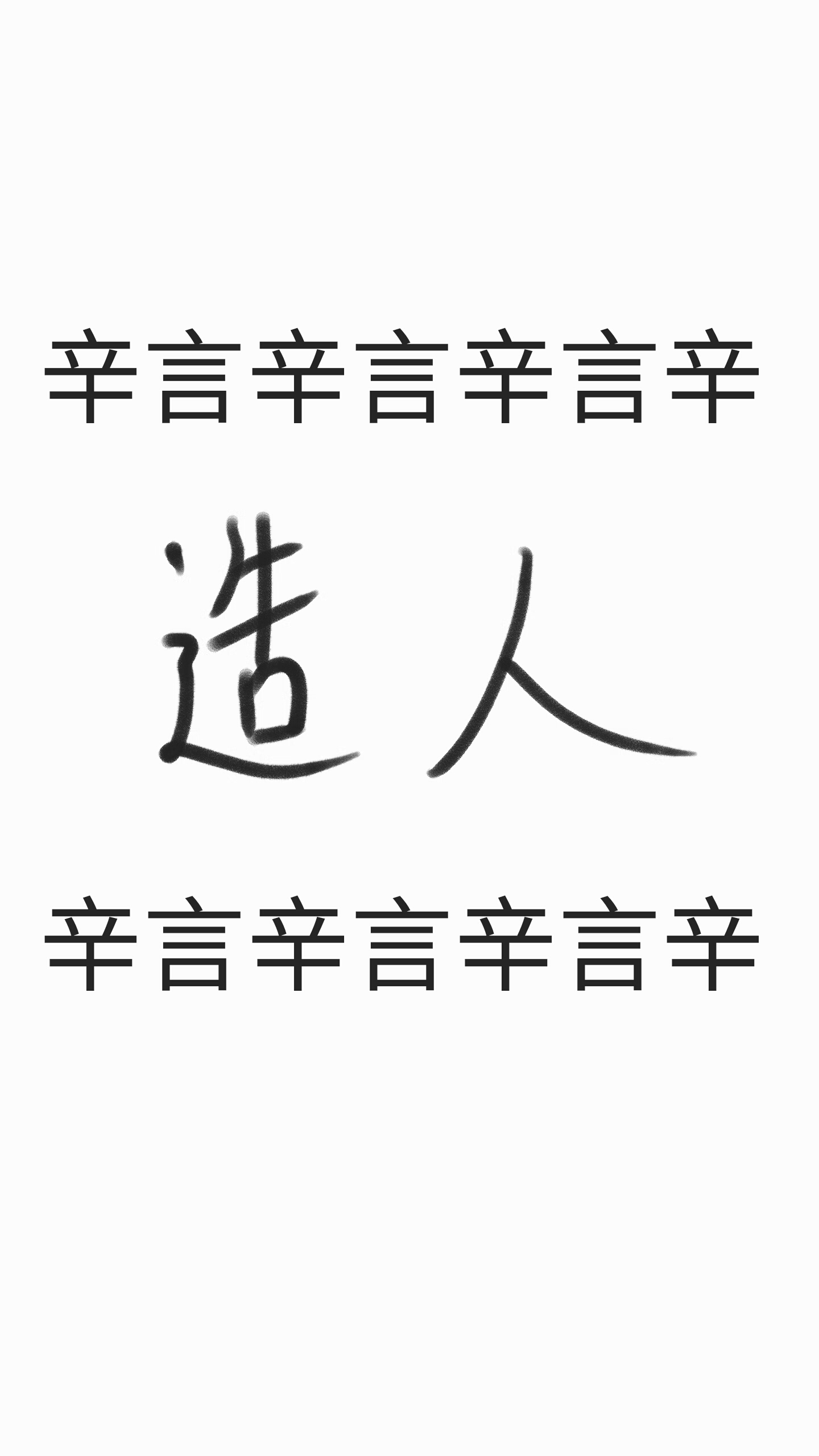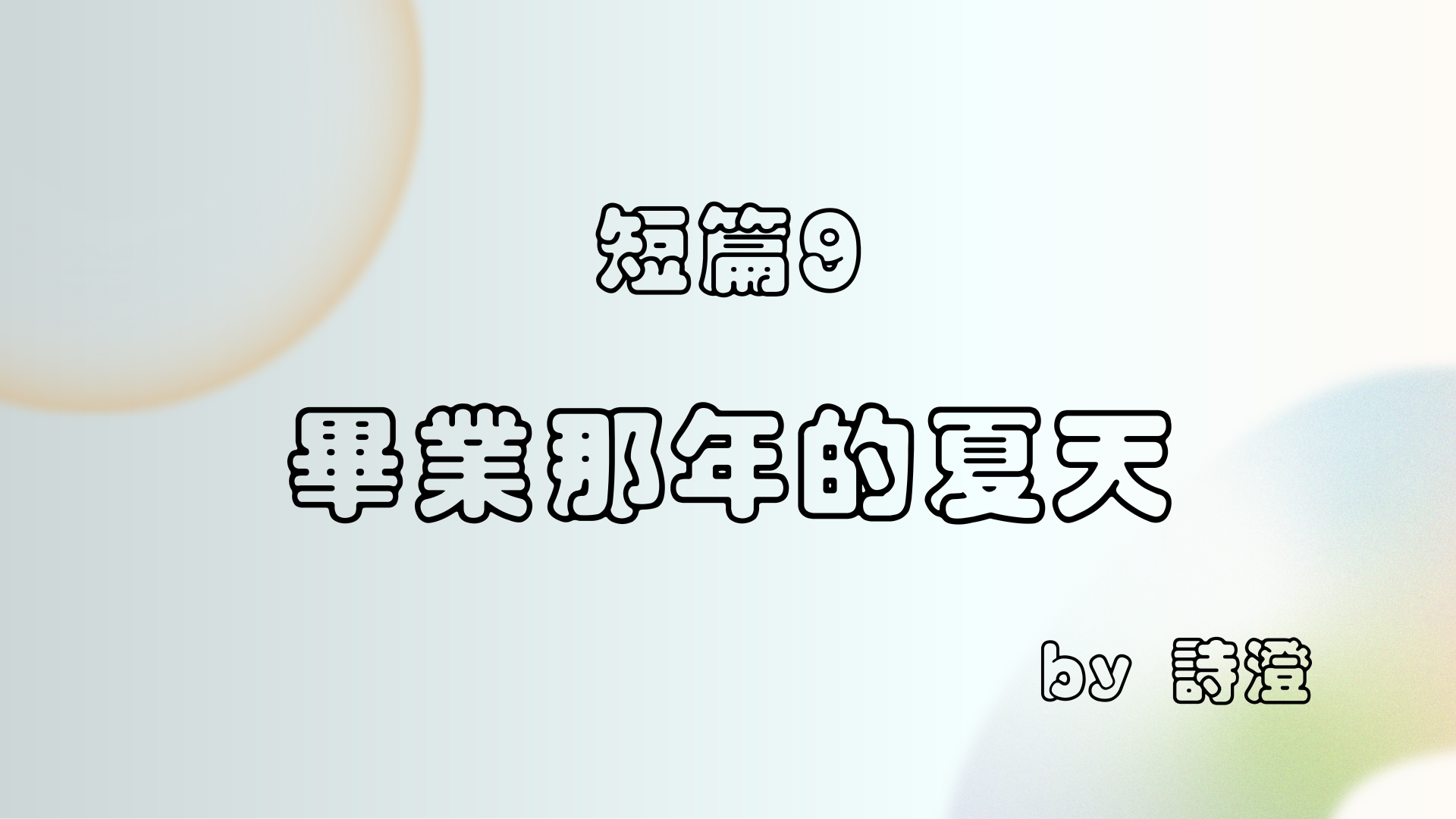「這一句話,我會記上一輩子。」
二十年前,我拋下這麼一句話,頭也不回,離開那個家。
某位於港島區的咖啡店內。淺啡木紋地磚和同調木紋膠板桌椅,配襯白色牆身和米黃色燈膽,輔以多個小盆栽和青色咕𠱸作點綴,簡潔得來帶有滿滿的溫馨。完全符合阿妹理想中「家」的形象。
我們齊齊長大於日本文化盛行的年代,對日系風格情有獨鍾實屬在所難免。惟鍾愛歸鍾愛,我不禁在心裡吐糟眼前的芝士蛋糕:虛假的芝士味道和香氣,甜得發膩的化學甜,有如焦土的乾癟質地。怎麼可以如此難吃?
「不喜歡?」阿妹冷道,沒望我一眼,逕自品嚐她的芝士蛋糕和朱古力咖啡。
「嗯。」我放下叉子,放棄價值五十元的蛋糕,暗嘆浪費。我寧可花同樣價錢,去茶餐廳吃鹹魚雞粒炒飯。
「這是區內最有名氣的芝士蛋糕。」阿妹對我的口味不以為然。
「以『難吃』見稱嗎?」我冷嘲,惹得鄰桌的情侣竊笑。
阿妹面色玄青,無視我,低頭享用她的下午茶。
我沒趣地拿出手提電話消磨時間,目光時而在通訊軟件上遊走,時而偷瞄對座的阿妹。
我倆之間,是一張深度六百毫米的枱,也是二十年的空白。見面之前,我記憶中的阿妹是個廿三歲大學畢業生,純真無邪,略懂打扮;碰面當刻,舊印象驟然消失,獨一無二的阿妹變成充斥中環的普通辦公室女郎。微卷深啡長髮,濃妝豔抹,粉綠色及膝連身裙,純白色短袖小外套,三吋高跟鞋。
曾幾何時,我深信自己會跟阿妹一樣,成為打扮斯文的辦公室女郎。
我的思緒飄到遙遠的平行世界去,直至阿妹放下叉子:「走吧。」
截下的士,我們直驅醫院去。車廂中,又是令人窒息的沉默。我從倒後鏡瞥望阿妹。她托著下巴,似是對著窗外景物發呆,亦似是從玻璃車廂的模糊倒影觀察我。
「待會兒,態度必須要溫和。」阿妹的口吻帶有「命令」的味道。
「盡量。」我是個直腸直肚的人。
「難道你沒能大發慈悲,讓媽咪『離開』得安詳?」她略略加強語氣。
「所以我沒有拒絕,而是答『盡量』!」我強抑怒火:「你不是不知道她的嘴巴就是不饒人!難道我要盲目啞忍所有過份要求?」
「那天以後,她性格大變,嘴巴再也硬不起來。」阿妹神色放軟。
我沒駁斥,任由沉默張牙舞爪。
進入私人病房前,阿妹從手袋拿出一個小紙袋,塞到我手裡:「給媽咪的小禮物,佯稱是你買的。」沒待我答允,她已推門內進,不讓我有拒絕的機會。
病床上的媽咪,戴著頸箍,缺了左腿,全身插滿連接儀器的喉管。床頭櫃有熱水壼和膠杯,櫃側有一灰色的膠椅,椅上有她最鍾愛的墨綠色的毛衣。出乎意料,毛衣多年以來仍忠實地守候在她身邊,活像她幻想出來的完美女兒。
「送你的。」根據阿妹的指示,我奉上紙袋。
媽咪的頭動不了,眼皮使力地開開合合,眼珠子艱難地轉動著,幾經辛苦才成功對焦,看見我。眼淚暴瀉,雙唇微顫,千言萬語卻離不開齒間。
「喚媽咪吧。」阿妹怒目相向,恨我的狠。
縱先前對媽咪的病情略知一二,惟在此情此境,我竟反應不來,原地愣住。喜怒憂懼愛憎欲,好比混在一起的彩砂,沒能再分開。粒粒彩砂本來顏色鮮明,在此刻偏偏成了惹人眼花撩亂的雜訊,佔據每吋視線,令我看不清楚自己的心意。
「媽……咪……」我耗盡力氣,千辛萬苦才擠出兩粒字。不情不願,因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心甘情願,因為這是最後的聚頭,該盡力讓事情有個不差勁的結局,算是清還她的養育之恩。
阿妹招招手,要我湊近媽咪,讓她看清楚多年不見的女兒。
一絲抗拒掠過。我沒打算捕捉它,隨它消逝。我的手腳開始沒那麼生硬,乖乖依從阿妹的指令,走近床邊。阿妹要我給媽咪奉水,我照辦如儀。阿妹要我為媽咪披上毛衣,好,沒問題……不知底蘊的人看見「母慈女孝」的畫面,定會誤會我仨關係良好,感情深厚。
整個探訪過程,媽咪沒能吐出片言隻字:她的喉嚨受惡菌感染,非但沒能進食固體食物,甚至失去語言能力。
不得不承認,我賤格。表面和藹謙恭,底裡毒如蛇蠍。我幻想,如果二十年前的媽咪已失去語言能力,我會否仍生活在這個家,是個千依百順的好女兒?
兩小時後,媽咪倦極入睡。阿妹要我先離開病房,在門外等候她。
甫踏出房門,我與阿姨碰個正著。
死八婆!若非她當年在旁煽風點火,我和家人的關係未必會破裂收場。
「我就是知道你會來。」阿姨擺出料事如神的姿態,以冷峻目光掃視我全身:「很缺錢吧?」講完莫名其妙的一句後,她掏出一張支票予我。「你的報酬。」
我沒有立即接下,思疑她在打甚麼鬼主意。
湊巧,阿妹從病房出來,看見我和阿姨在門口僵持,立即上前解釋事情因由:「我沒有告訴她關於支票的事。」
「你的意思……她不是為錢而來?」阿姨拿著支票的手緩緩垂下。
「嗯。」受壓於阿姨的強勢,適才不慍不火的阿妹怯怯點頭。
「那麼……」阿姨猶豫了半晌,最終還是決定將猜忌放進問題裡。「你為何而來?」
「出於對老人家的憐憫和惻隱。」我胡謅,強裝正氣凜然。其實我未曾細想自己為何而來。
「很好。可以省掉。」阿姨有意無意地將支票在我面前晃來晃去。逗狗似的。
「如果沒有別的要事,我先離開。」我選擇了忍耐。
醫院外的大路上,人不多,三三兩兩的。探病的、求醫的、久病初癒的、迴光反照的。我屬於哪種?該是「半死不活的」:情況沒有差得要死,卻怎也活得不好。
缺錢?工作不順利?與丈夫婚姻不和諧?與子女有代溝?統統不是。
僅是純粹的不快樂,若有所失。
每當我感到幸福時,記憶就會成為粘粘的漿糊,將我黏在內心的缺口上。
「等……我……」阿妹的聲音從後傳來。
我佯裝聽不見,加快腳步,務求撇下腳踏三吋高跟鞋的她。
「家姐!」豈料阿妹不顧儀態,高呼大叫,吸引途人們的目光。
我的雙腳不自已停下來。
不消十秒,氣喘如牛的阿妹跑到我身邊來:「謀……殺……嗎?」
我鐵著臉,沒意欲跟她開玩笑。「那張支票,是誰的主意?」
「媽咪。」阿妹不敢正視我雙眼:「她覺得你會拒絕到來。」
「你們仍舊認為我是嫌棄家境窮困而離開嗎?」我本不欲重提舊話,奈何我忍不住要再次辯解。
「我們想不到其他原因。」阿妹的答案隱含委屈。
「我從不認為我們家境窮困。」我氣得開步走。
阿妹連忙拉住我的衣袖,轉換話題:「有興趣跟我和阿姨吃晚餐嗎?我們會與你討論遺產事宜。」
「沒有。」我乾脆利落地拒絕。
「僅僅一頓便飯而已。」阿妹屢敗屢試。
「不了。」我稍稍施力甩開她的手。「你倆把錢分掉吧。無需通知我。」
「我會轉告阿姨。」世故的阿妹知道我在顧忌誰。「但你可以和我一起晚餐嗎?只是我跟你!」
我意識到這是她最後一次的邀約,再也講不出拒絕的說話,迷迷糊糊地與她並肩而行,行到醫院附近的咖啡店。她為我點了抹茶蛋糕和朱古力砂冰,聽聞是鎮店之寶。
我嚐了一口。
甜得要命。
「你是否不再喜歡吃甜品?」阿妹從我的難受表情找到端倪。
我傻傻點頭,驀然記起自己曾經是個無甜不歡的傢伙,對咖啡店的精緻甜品更是愛不釋手。
「我對你的印象停留在二十年前。」阿妹眼裡盡是懷緬。「溫柔的、膽小的、笨笨的家姐。」
「我自問從不是溫柔的傢伙,純粹是害怕開罪別人而假裝溫柔;我不是膽小的,至少我比你更有離家出走的勇氣;我不是笨笨的,起碼我有能力比你更先離開。」我努力提起叉子,再嚐一口蛋糕。很難吃。
「難怪你要走。」阿妹噗嗤假笑,表情苦澀得複雜。「我們自以為了解你、明白你,不明白何以你最後竟捨棄我們……」她那握叉的手重覆戳向蛋糕,直至它成漿成糊。
「其實我也不了解你們。至少,我沒有想過你們會利誘我來探望媽咪。」我苦笑搖頭:「我理解他們何以會不明所以。」由始至終,我在意的人只有阿妹。「你呢?你比他們更了解我的處境!別以為我不知道你當時同樣想走!」
「你終於承認當時是知道我的想法!」被我戳到痛處,阿妹失儀地將叉子擲在碟上。金屬叉子碰瓷碟,有如我的話碰她的心,發出響亮而清脆的碰擊聲。
「為何你不帶我走?我日盼夜盼,盼望你會聯絡我,帶我走。在意識到你不會帶我走時,我又開始催眠自己,說你遇到意外,說你被壞朋友騙了,說你尚未安頓下來……我不知道該要怎麼辦!
我有很多很多問號!
我不明白你的想法!我不清楚自己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我不明白為何我要為你編作解釋!我不明白為何我信任的人會拋棄我!我不肯定自己能否負擔起整個家!明明是我倆的共同責任,為何我要獨自承受?」
「因為你是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草。」思緒千迴百轉,最終我決定長話短說,淡然將描述她揮金如土的萬字怨言吞回肚子去。
霎時間,阿妹答不上話,直視我雙眸,似是觀察我的表情,希望能夠從中找出一絲歉疚,亦似是在乞求我大開金口,施捨半句道歉話。
可惜,我沒打算繼續在她的生命裡留下甚麼。
「算了吧。」為打圓場,阿妹選擇口不對心:「反正我們以後不會見面,不需要執著彼此。」若果她真的能夠放下執著,適才就沒能細數她的痛苦點滴。
「是的。」我釋懷一笑,放下叉,不再勉強自己清掉碟上的蛋糕。
用餐過後,我和阿妹公式化地道別,從此分道揚鑣。
我看看手錶,晚上十時許。路人不多,疏疏落落的。黃光路燈斜照著路人們,照出多個長腿叔叔。故事中的長腿叔叔是個擁有美滿人生的紳士,現實中的我們卻是破碎殘缺的獨立個體。東一塊,西一塊,難以湊成一個家。
需要感到遺憾嗎?無需要。
曾有感到遺憾嗎?曾有。
會繼續感到遺憾嗎?不會。
我慢步走向鐵路站。
慢慢的,慢慢的,有如二十年歲月一樣慢。漫長的二十年裡,我一步一步走過來,無數次踏在內心的缺口上。自以為腳掌會感受到缺口的虛空與不平,自以為低頭就會看見缺口的廣闊與無邊,自以為缺口會永遠存在。殊不知缺口已在不知不覺間被時間撫平。
剛才我不是故意將不快記憶輕描淡寫,而是無論我怎麼努力去回想,所有細節都經已模糊不堪。最清晰的,只有我當年留下的那句話。
「這一句話,我會記上一輩子。」
簡單的十一個字,濃縮了多年的壓抑和不滿,是負面情緒的頂點。
說話離開了唇角,繃緊的情緒失去支撐物,慢慢紓緩下來。由最無關痛癢的,至最為要緊的,一點一滴隨年月悄悄消逝。我忘記了誰講出讓我記上一輩子的說話,忘記了對話的內容,忘記了對話的前因……取而代之的,是能夠被握在手心的現在和能夠被觀望的將來。
我倏忽停下腳步,換個方向,走到便利店,買了罐冰凍啤酒。
為何仍清楚記得那份恨意?
我知道答案。
答案像啤酒。
啤酒不是必需品,但我習慣在心情欠佳時喝啤酒。
那份恨意不是必須存在,但我習慣了它的存在,習慣用它去概括描述我離家出走前的人生。久而久之,那份恨意就成了那段日子的代名詞。那段日子只有恨意,沒有願望,沒有七情,沒有喜好,遑論快樂。
我將啤酒一飲而盡。空空如也的啤酒罐精準地落入垃圾桶裡。
若果我可以同樣將記恨習慣拋入垃圾桶,該多好!
不要緊。給我二十一天,戒掉壞習慣。
我保證,往後滴酒不沾,吋恨不記。
*****(完)
FB:https://www.facebook.com/天洛卡-1844883209067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