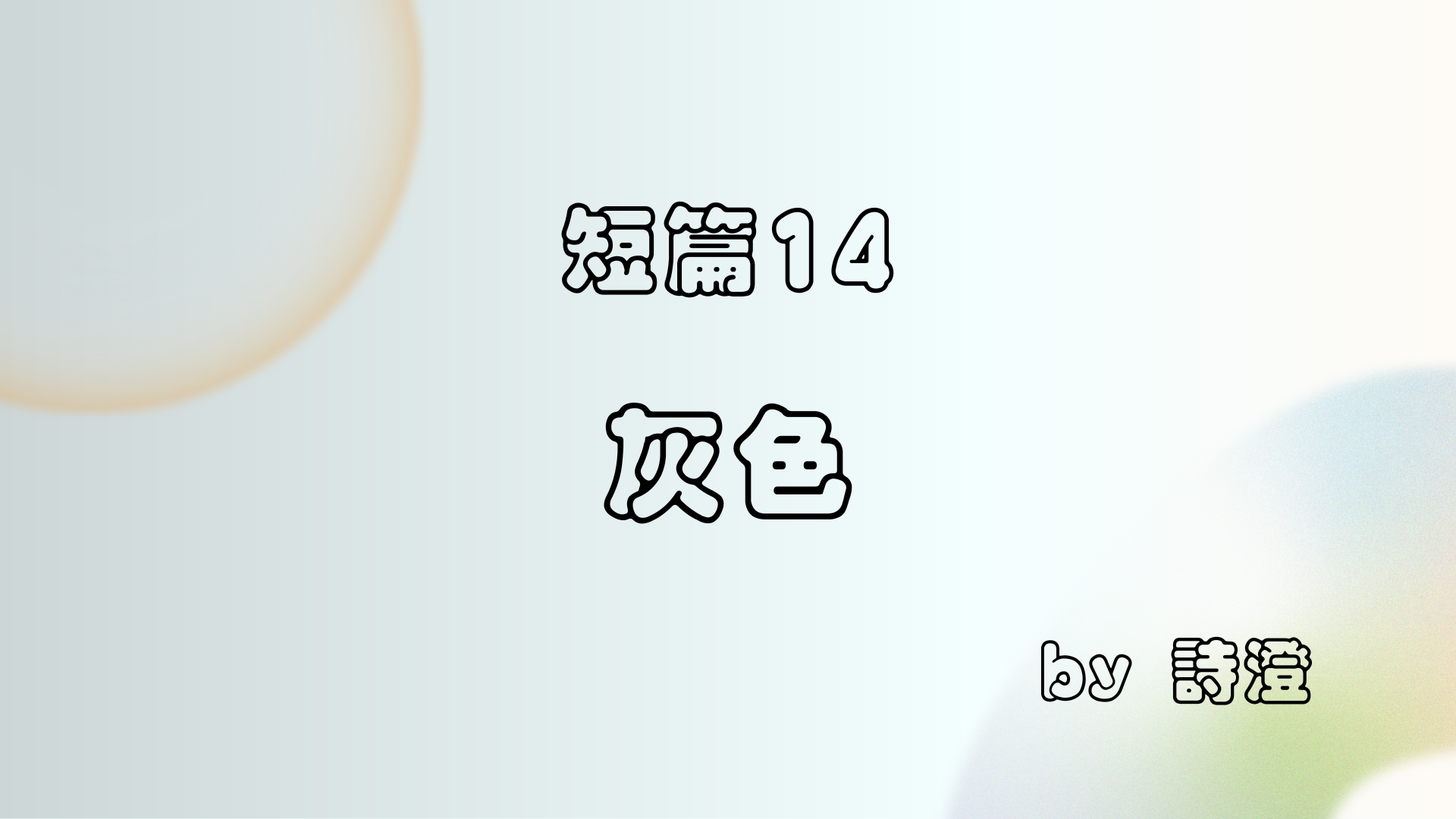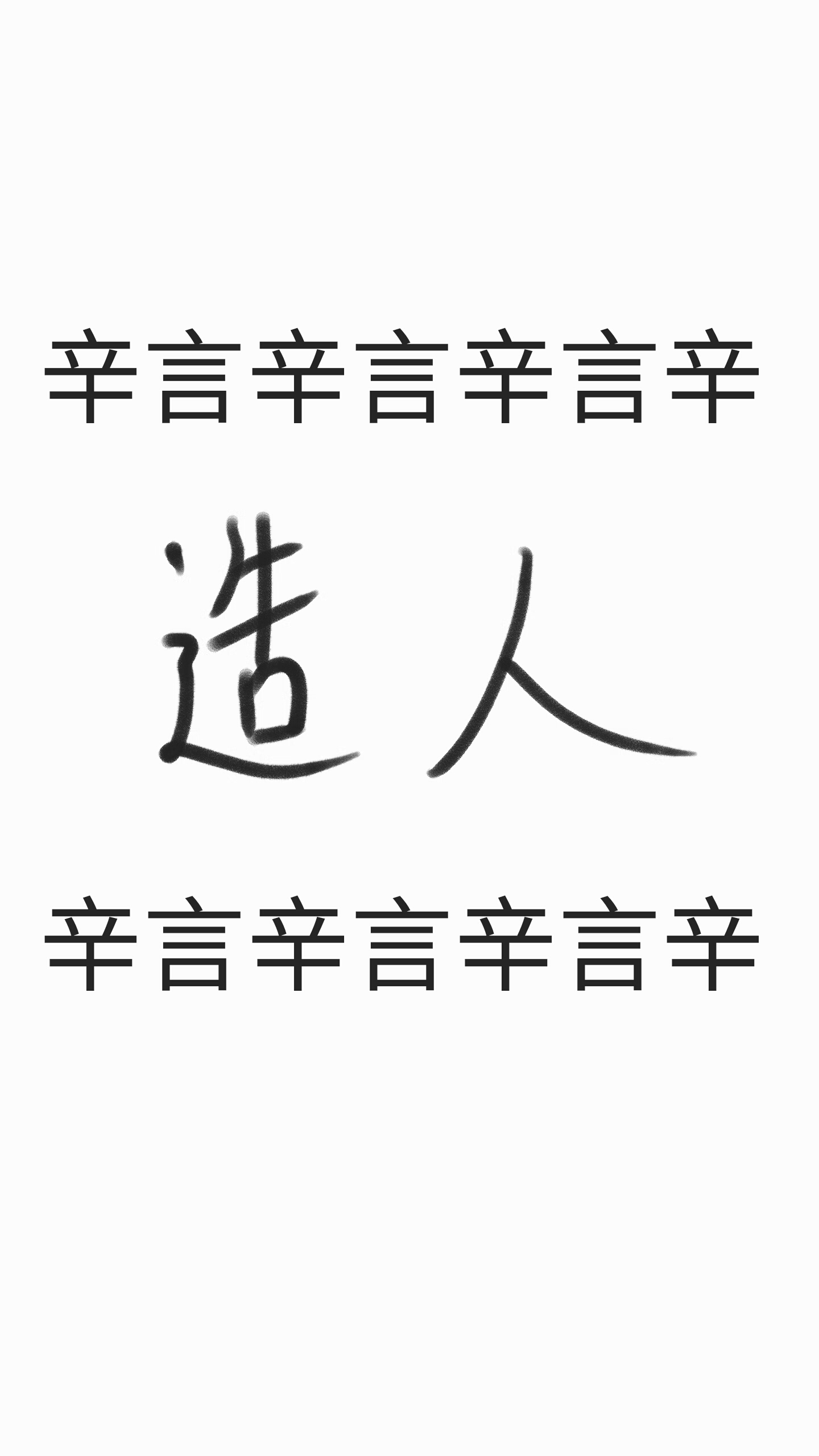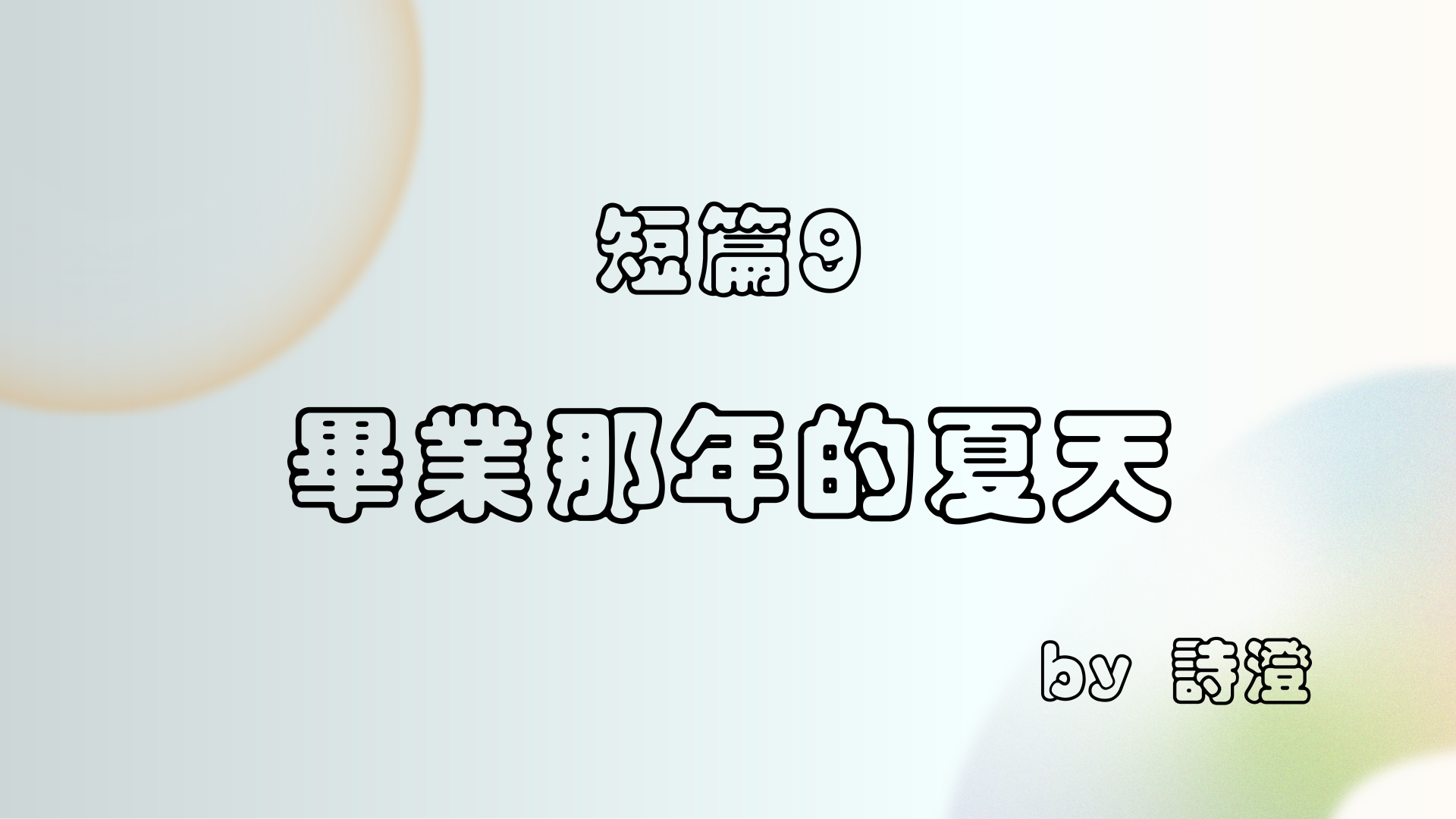剛好趕上的公交駛得晃蕩,她勾着把手,耳畔響起那首老歌:「你在南方的艷陽裡大雪紛飛,我在北方的寒夜裡四季如春。」,正午陽光從車窗灑進,打在她寂寥的臉上,一閃一閃。
你愛過嗎?或者,是誰教你搞懂愛。他曾握着她手,一筆一劃,喃喃的道出,這是愛,今後再也沒人對她像他般好過。
回家第一件事是攤在沙發上喘口氣,母親弄得廚房滿是蒸氣,不出意料的推開門喝我,讓我趕緊褪去外衣。
「我不吃了。」
咔嚓的關上門,把包一扔,又重新攤在床上,用棉被緊緊地裹住自己,酸痛感突襲腰間,大概是路途上站得太久。把手是大人才觸得到的距離,我愛在車上站得筆直,仿如取代了昔日誰的位置,就表示自己已經足夠獨立。
啪啪,「你爹的電話。」,母親顯然是怕燒焦了菜,聲音焦急得很,然而門內的人並無半聲回響,只是用臉埋在枕頭中,全身一躍一躍,如在抽泣。
半刻鐘後,疲憊的人兒已醉倒在夢鄉。我作夢了,夢裡真好。只是再無人再用美人魚的故事哄我入睡,在親暱地吻過我的臉頰後,循例的道聲晚安。
似乎唯有睡夢中才能與時間接壤。能記起他曾用寛大的手掌把我的握在手心,記起他的腳步總是快得我追不上、記起他替我系上馬尾時的慌張、記起我倆比賽啃骨頭誰快的遊戲,也記起他擁我入懷時懷裡的温存。我記得你第一次當父親的歡喜,那時候聽人們說,女兒是父親前世的情人,讓我一度以為能永遠騎在那雄厚的肩膀上走向未來。直到現在,聞到你愛用的那款古龍水香味,我還是會回頭。
醒來的時候,枕邊濕透,我擦拭乾澀的眼眶,睡夢惺忪的走出房間,坐在沙發上的母親見了我,卻是沉默,醞釀了幾刻後道: 「你父親坐明早的火車回來。」我荒唐的假裝輕鬆,只是點了點頭,心裡卻是一陣波瀾,像是被洩漏了祕密般渾身繃緊。
朝暮過去,翌日一早,母親讓我去車站接父親,我倉皇,卻又急不及待,因她早已褪去一身稚氣,如今亭亭玉立,憂心他無法在人海裡認出她來,而這天的來臨,叫她等待已久。
見面的時候,我終於明暸朱自清的落寞,看他從遠方走來,拎着大包小包,腳步踉蹌,而頭頂灰白夾雜,臉上佈滿了雀斑,明顯已年輕不再。
我頓時有點失魂,直到他雀躍地喊我名字,與那時。在校門前的聲音重疊,熟悉感湧上心頭,但擁抱的卻是陌生的身驅。他粗糙的指骨生了繭,與我十指相扣,我想起自己曾經在他身後亦步亦趨,要踩他的影子,如今卻是他在我身旁走得蹣跚,這光景如此陌生。
但他身上的古龍水香始終提醒着我,這次回頭,見到的確是我心中所想。
我最熟悉的陌生人,你是否亦有在遠方播過那首《南山南》,寫這首歌的馬頔講過,你聽到這首歌的時候,你掉的眼淚,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故事。你是否記得你離開家鄉到外地的那天大雨滂沱,我坐在地上哭喊着,不肯讓你走,而我的思念,是否曾能飄至遠北,與你連繫在一起。
你為養妻活兒出走半生,如今有我拉着你踏入家門,跟你說聲,歡迎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