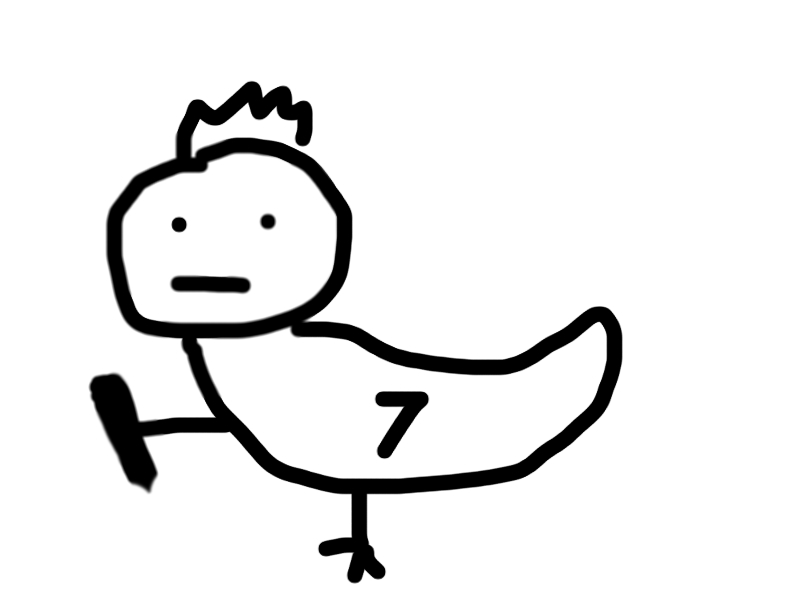「唔好意思先生,你八達通唔夠錢。」
「嗯?我張八達通自動增值架喎!」
片刻,我恍然大悟,今早我已經自動增值了一次,已超出了本日的增值上限。
我面帶尷尬地望了收銀姨姨一眼,她那種強迫裝出的笑容教我有點不自在。
「哈哈⋯⋯唔好意思。」
我望著空空如也的荷包,嘗試在身上其他地方尋找應急的零錢。可是我身後的人龍漸漸傳來不耐煩的鼓噪,所以⋯⋯還是算吧。
「哎呀,我去撳個錢先!轉頭返黎俾錢!」
= = = = =
「我仆你個街⋯⋯」
自動櫃員機裡的畫面將我的面目照出一面青光。
結餘:$20。
距離出糧日子尚有三日,然而在這個令人面色發青的餘額下,想要捱過這三天一定比登上珠峰難。
我可以怎麼辦呢?
明天的午餐錢呢?晚餐怎樣處理?車錢呢?還有孩子的零用呢⋯⋯一切本來很易解決的問題,突然間比寫大學論文還要難。
嗶嗶⋯⋯嗶嗶⋯⋯電話聲就好像催命一樣以急速的節奏響著。
「喂?」
「阿匡哥仔,你響邊呀?」電話旁邊是我的上司,發哥。
「發哥,六點鐘啦喎。」
「咩呀?唔撚洗做呀?我都未收工你就走左?我仲幫你執緊手尾呀!」
「我個女病左,我老婆未收工,要返去幫我外母湊呀嘛。」事實上,我內心在數算著我的乖乖女在本月應該「病」了第十次⋯⋯吧?
「我唔鳩理呀!你今個月條數點呀?開夠單未呀?打左cold call未呀?搵到新客仔未呀?」發哥:「你個柒頭,成條team業績比你拉低晒。你聽日同我打夠三百個call,開到單先好走呀!」
卡嚓—!
嗶嗶嗶⋯⋯嗶嗶⋯⋯!電話才剛收線,又再響起。
「又點撚樣呀!喂!?」
「細佬。」
「家⋯⋯家姐?」
「你今個月交左租比老豆阿媽未?」
「對唔住。」
電話一旁來了一聲長長的感嘆。
「你今個月係咪唔係好惦呀?」
「嗯⋯⋯係呀。」
「我幫你交住先。」
「多謝家姐。」
「細佬,你咁大個人,家姐實在唔想鵝你。你知唔知你已經好幸福啦?老豆留左間公屋比你同老婆住,裝修又幫你出埋。而家只係象徵式咁比返幾千蚊租老豆唧?咁都做唔到?」家姐:「由細到大都要屋企人睇住你。你而家有老婆、有仔女,唔可以再係咁啦。買少D無謂野,為自己、為你老婆仔女打算一下啦。」
「知道。」
= = = =
「喂,七叔。可唔可以R枝煙黎食下?」
我抱著擾人的煩惱,不經不覺來到觀塘公眾碼頭旁。
「嗱!咁0岩我食左半枝。」七叔將半支煙遞給我。七叔是住在碼頭裡的露宿者,由於我經常於放工後到碼頭散心,所以不知不覺地與七叔熟稔起來。
「多謝。」我將這半支煙夾在指間,凝視著煙圈。
「酒呀!要唔要呀後生仔!」七叔。
「凍唔凍先?」
「我撚有雪櫃呀柒頭!」七叔飄出一堆粗口,將一枝啤酒放在我旁邊,但他倒是友善的。
我笑一笑,內心很感謝他的慷慨。可能七叔慣於身無一物的生活,所以也不介意與我分享他所擁有的。
其實我不會抽煙,甚至非常討厭煙味。但偏偏我卻喜歡香煙慢慢地燃燒著的畫,還有自由自在飄在半空裡的煙圈。
此時此刻,在喧鬧的都市、在揮之不去的煩惱中,好像找到了一絲的寧靜。
「七叔呀。」我呆望煙圈:「點解做男人咁辛苦既?」
「辛苦就做女人囉!」 七叔打著赤腳來到我旁邊。
「一個星期返足六日工。仲未計ot。已經冇咩自己時間。一個月搵到三萬。係呀,係唔算差呀。又唔洗供樓。但係為左屋企,為左老豆老母,為左仔女⋯⋯唔覺唔覺洗晒。七叔呀,你明唔明一出糧就糧尾既心情?」
「仆街仔你而家係咪潤緊我?」七叔:「不過我明呀!就好似⋯無間地獄咁!」
我無奈地說:「唉⋯⋯點解做男人咁辛苦。」
噠!我將煙尾彈出海面,在空中留下紅色的孤光。
「份工做得唔開心。壓力好大。換轉係細個既我,一定神早走人。但係就算準備晒cv、有人in我都好。臨門一腳我都唔夠膽見。我怕搵唔返而家呢個待遇。」
我喝了一口酒,道:「走又走唔到。壓力要焗食。屋企人好似唔係幾明白我,嫌我比錢屋企少。同屋企人D拗撬多左。」我:「去到三字頭呢個年紀,我開始忘記咩叫開心。唉⋯⋯我好耐冇掂過相機!我好想做自己開心既事之餘,又可以照顧屋企!」
我嘆一口氣,說﹕「其實有份工黎緊會IN我。直頭係另一個行業黎。人工又好唔穩定,又知請唔請。但係呢份係我鍾意既工,可以日日做我鍾意既事!我唔想每日一都行屍走肉呀!⋯⋯七叔呀,其實男人為左屋企,係咪咩都要放棄架?」
「我都冇屋企人你問我托柒呀?」七叔頓一頓,又說:「後生仔,你膀頭攰唔攰呀?你揹住咁多野,點飛呀?」
我不太明白地望著七叔。
「好似呢度咁。幾多老友記響呢度霸地方搭屋仔訓。嗱!旁眼人睇好似好亂!」七叔搭著我肩膀,指著碼頭上形形式式的「木屋」,又說:「事實上,呢度就自己一套規律!」
我看不見亂七八糟的碼頭有多規律,也許這是無家者才會看見的秩序吧?雖然如此,一面污穢的七叔卻笑得滿有自信⋯⋯唉,他又人生教練上身了。
「我地個個都知呢個地方始終係公家野。所以我地就算有幾唔拾得都好,都會間中掉下野。始終太過份,政府就會趕走我地嘛。但係對我來講又唔係難事。」說著說著,七叔從褲袋裡拿出一張發黃的照片他又說﹕「呢度一張櫈一塊木都可以唔要,甚至我人生入面咩都可以掉。但惟獨呢張相就一定唔掉得。」
說著,我聽到了一點酸楚。七叔慢慢地向我展示出這張發黃的照片。年輕的七叔意氣風發,身穿西裝,端裝地坐著。他旁邊是一位有著中國傳統婦女氣質的女性,是七嬸。站著二人四周的,正是七叔的子女,一共有八位。看他們的衣著可知,照片該是拍攝在一五、六十年代,而且他們該是非常富貴的一家。
這一張相正是七叔最珍而重之的全家福。
「男人呀,冇左屋企,就咩都冇架啦!」七叔一笑,彷彿笑出了六十多年的辛酸﹕「所以,後生仔呀!你揹住咁多野,點飛呀?你覺得邊樣野阻住你飛既,你未掉左佢囉!」
七叔拍一拍我都肩膀,就跑到其他朋友身邊繼續閒聊。
我望這個大老粗,好像明白了些甚麼。
此時,我懷中的電話響起。
「喂?」
「老公。 你響邊呀?咁夜都未返。」
「散下心姐。阿女呢?訓左未?」
「訓左啦!你成日唔返屋企,佢就黎唔記得你啦!」
「老婆呀⋯⋯我想⋯⋯」
「想轉工呀?」
「你點知架?!」
「你寄出去既求職信唔夠郵費彈返轉頭呀!唉!」
「對唔住呀⋯⋯ 人工可能會少好多。」
「少未少囉。最多我同你食少D。家用少D。」
「真係?!」
「唉!快D返黎啦!」
卡嚓——!
我深吸一口氣,依希,我的嘴角帶著笑。我喝光啤酒後,便起身將要回家去。
「喂!後生仔!」七叔見我要走,便揮手叫道﹕「你老婆係咪好靚架?幾時帶黎比我識呀?」
「你食屎啦!」我揮著手
「哈哈⋯⋯有咩幸福得過有屋企呀!係咁先啦!」
「下次見啦!BYE!」
(完)




-01.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