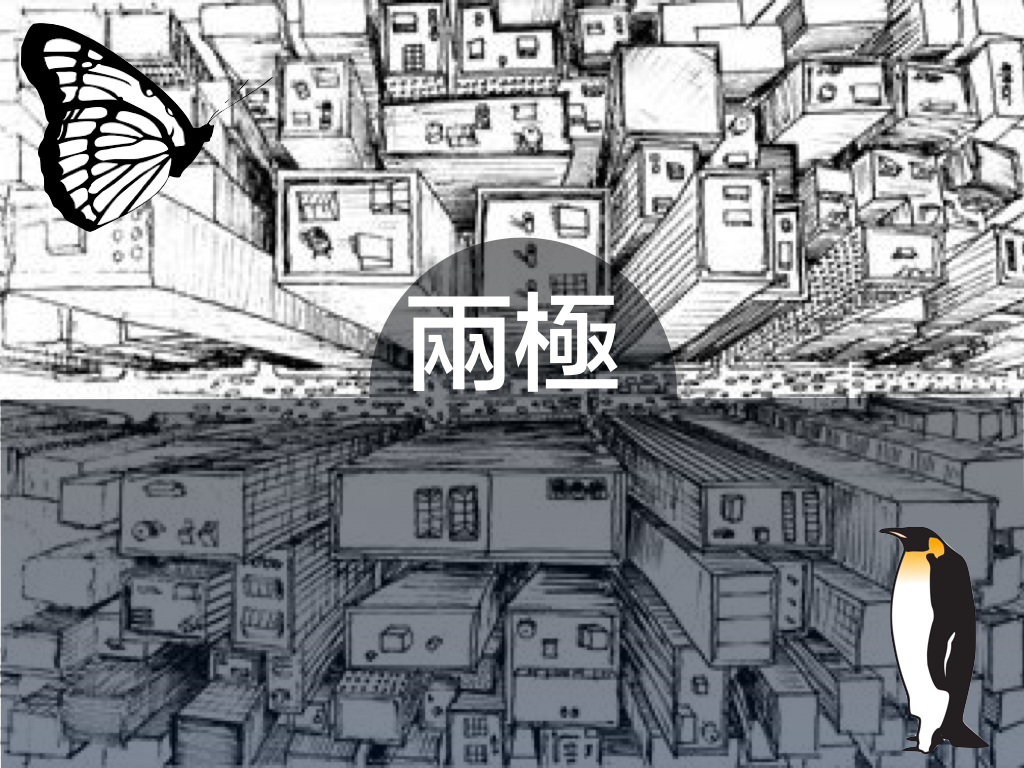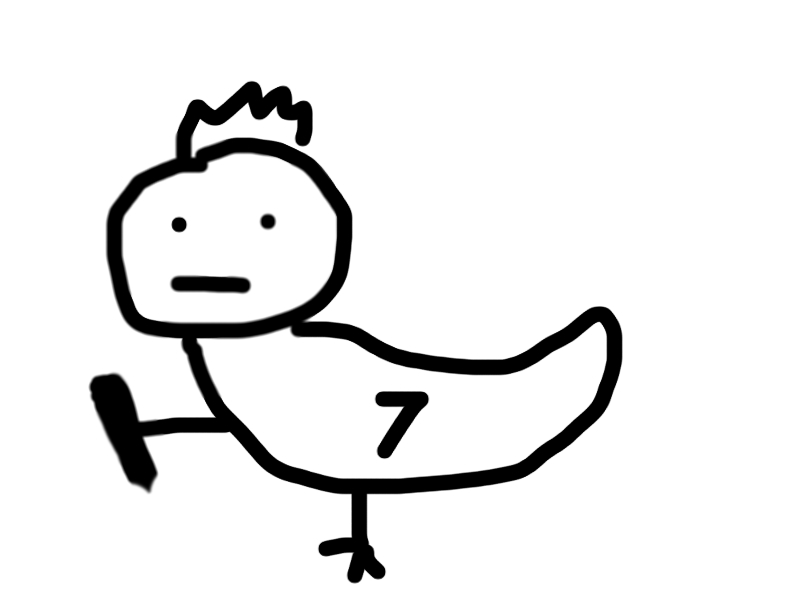話說,那不再滾的洗衣機也退役了好一段時間,事隔一個月又十二天,終於,新的進駐了,說實在,這陣子每每清洗衣服也得借用上層同屋主的洗衣機,著實好不麻煩。然而,在借用的同時,我發現了她們在廚房的一道牆上架起了一條筆直的長鐵作掛衫之用,這倒真是個好法子,畢竟濕塔塔的衣物掛在不透風的小房子內,總是會讓房間產生出陣陣霉味,雖說發霉獨男住在充斥霉味的房間內是完美搭配,但我仍心存一絲希望,倘若能把房間的霉味除去,或許,我的人生也可擺脫這發霉的每一天,我,是這樣相信的。
於是,我聯絡上屋主,詢問他能否在廚房內同樣地架上掛衫的橫鐵,他爽快地批准了,只是所有費用得由我自己承擔,而且退租時,要把鐵拆下還原。不知怎地,我堅信著這是一個契機,誇張點說,就是一個轉捩點,一個讓我在潮濕春季中,重拾生氣的轉捩點。
很快,我便找來裝修師傅到屋內作專業的量度,也許,你會認為只是在牆上鑽兩個小孔再買來一個鐵架鑲上便可,如斯簡單何用大費周章找師傅來弄?但於我而言,這可不是鑲上一條鐵的小事,這倒是關乎我往後人生的重要一環,我渴望完美,期待更好的改變,所以,我要找專業的。如果,你認為這終究是小題大做,那就當我這獨男懶散怕麻煩,只懂窩蛋免牛飯好了。
體格高大的師傅量度過尺寸後,便從背包中取出一本厚重的產品目錄來,瞥見目錄用上寶藍色的硬皮封套,封面中央還印上一頭燙銀的天鵝,翻到掛衫鐵架的部分,眼前是形形式式的鐵架,三層雙層單層雕花金銀銅鍍金,琳琅的選擇讓我認定找師傅這舉動是明智的,專業,就是有選擇。最後,我選擇了價錢較相宜,款式最簡潔的銀色單層鐵架。
約定的三天後,師傅帶備所有工具再次到訪,經過將近五分鐘毫無內容的寒暄問候,他終於開始動工了,而我則待在房間內,幻想著鐵架鑲在牆上的霸氣,過了這天,我將可脫去積藏體內已久的霉。
大半小時過去,他輕輕的敲上我房門,心中暗喜:改變的時候來了。可是,當我開門看到他的懊惱樣子後便心知不妙,步進廚房,只看到那銀色鐵架單邊的掛在牆上搖晃著,千萬個問號從我腦中沒有經過任何過濾直接浮現在臉上,接著,師傅便開始他那滔滔不絕的解說,說實在,我一句也沒聽懂,只是知道最後的解決方法是要在原有的鐵架中加上特別的鑲嵌配件,而這需要額外費用。裝修這回事,撫心自問識條鐵?師傅一句要加這加那,作為門外漢的我除了痛快地掏出錢包,還可怎樣。最終定案,鐵架將於一星期後升起。
七天,在漫長延綿的期待中度過,師傅再次威風凜凜的到來,從他雙眸中,我看得出一份傲氣和自信,又一次不著邊際的五分鐘寒暄後,他徑自走到廚房動工,我則步進房間雀躍地執拾著準備要清洗的一籃子髒衣物,十五分鐘過去,師傅在門外傳來一句一切辦妥,我便立馬走到廚房想要欣賞那偉大的裝置,怎料,那不是偉大,而是龐大!這鐵架鑲嵌好後,從牆壁延伸出的深度,竟就佔了廚房的三分一,若要具體的把境況形容,就是說我坐到餐桌上用膳時,我的背部便會被掛在鐵架上洗淨的衣服溫柔的撫摸著,而當當我站在流理台前洗碗烹煮時,頭上便會被這堆濕塔的衣物輕拂髮堆。
瞪目結舌的看著這吞噬了我三分一個廚房的龐然巨物,我從驚嚇中慢慢定過神來,一腔的憤怒再也壓抑不了,我脫去禮貌的臉譜,連珠炮發地向身旁的師傅理論,然而,他卻亳不客氣地把所有的責任歸咎於我,最後,我深知再多的唇舌也不過只能讓內心的不滿發洩,真正解決問題的永遠都在褲袋的錦囊內。於是,我著他為收拾這爛攤子報價,那是一個遠超我預算的數目,頃刻間,我頓覺踏在腳下那冰冷的已不是地板,而是針板。
又三天過去,經過上一輪的爭執後,師傅再沒有多餘的寒暄,直截了當在廚房動工,而這次我亦不再待在房間,而是在旁金晴火眼的看著他,看著他利落地在牆上鑽兩個小孔再把鐵架鑲上,過程不消十分鐘,我開始安慰著自己:「真夠專業,才不消十分鐘。」
完工後師傅便匆匆的離開,而我則站在廚房內,凝望著這終在粉白牆壁上架起的鐵架看得出神,精準的尺寸比例、完美的設計線條,真儼如一件毫無瑕疵的藝術裝置。我連忙把髒衣投進新洗衣機內,這次,我沒有再欣賞著滾筒的轉動而領略人生,反之,我靜靜地仰望著那安穩而筆挺地附在牆上的鐵架,開始計劃人生。
思索加速了時間的流逝,轉眼間一機的衣服已洗畢,從滾筒中取出一件件的衣物,直接掠到衣架,然後準備把它們井然有序的掛到鐵架上,但當我竭力地蹬起腳尖,伸直手臂,衣架與鐵架還是有一尺多的距離,這是我一生中遇到過最遙遠的距離,千算萬計,就是遺留了高度的考量。
最終,這高高的鐵架,應說是,這「高貴」的鐵架,就這樣,以藝術品的姿態呈現在廚房內,恃著一股可遠觀不可褻玩的霸氣,存在於我生活中遙不可及的一隅,而我,則繼續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