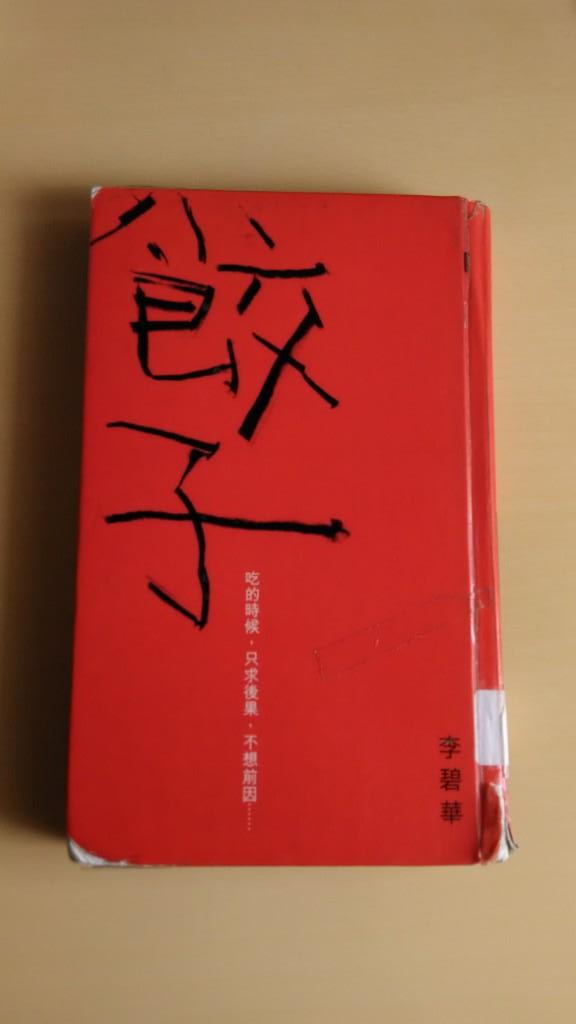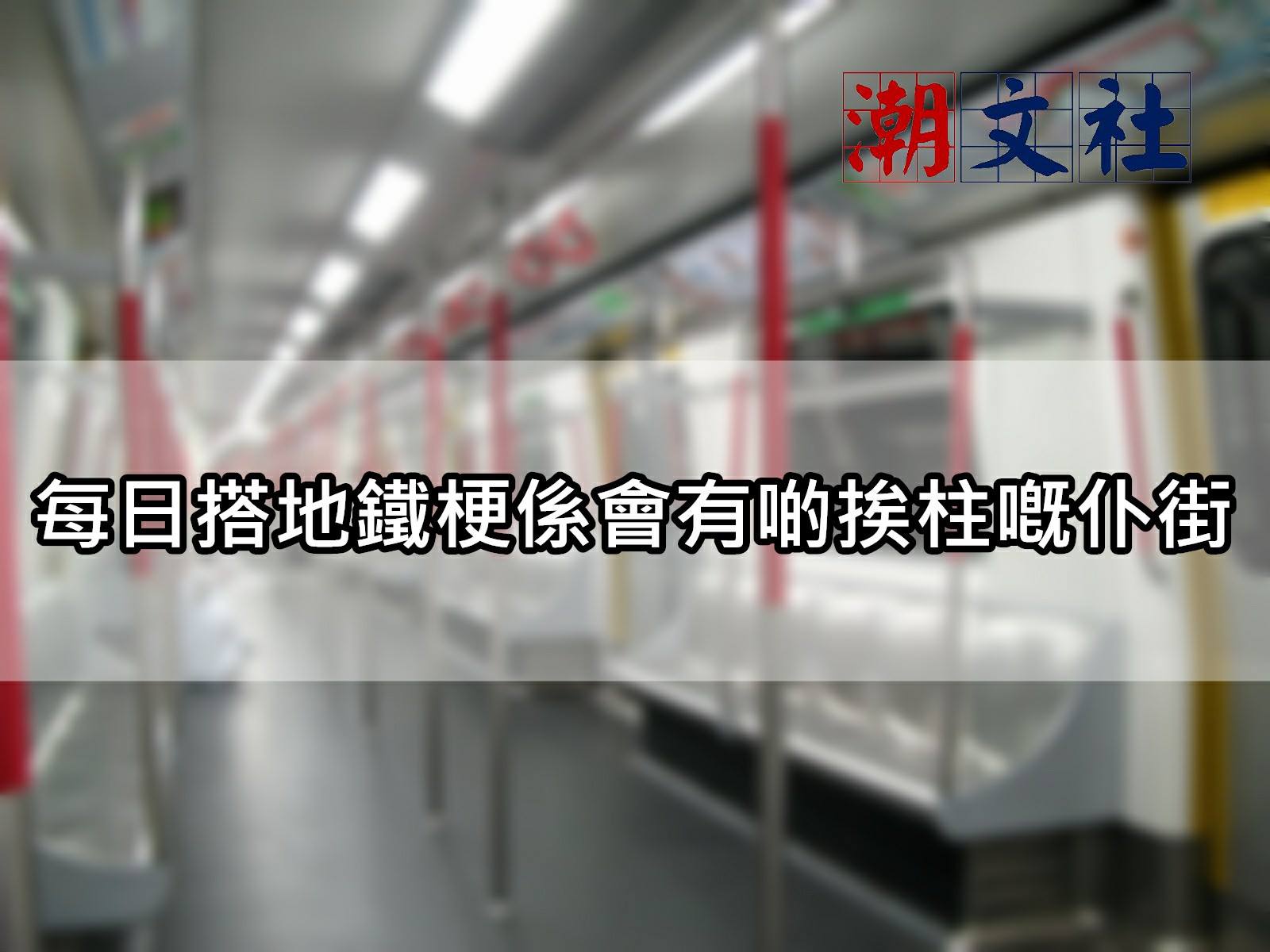大叔制伏許小姐後不久,仲佑也因麻藥發作而倒下了。於是,大叔成了屋內唯一的主宰。「害人不淺的毒婦,看來你得為你的過錯負上惡果了。」大叔邊蓋回右眼的眼罩邊說道。
大叔轉過身去、正從褲袋掏出電話時,許先生悄悄的從洗手間飄了出來 。大叔雖已蓋上了陰陽眼,但多年的除靈經驗還是讓大叔感到了身後許先生的存在。大叔自恃法力高強、兼之對許先生有雪恨之恩,是以大叔不虞有詐,仍自顧自的撥著電話。大叔卻沒料到,身後的許先生吸收了被許小姐殺死的嬰孩們不甘早逝的怨氣,道行徒升數倍,即使大叔全力以赴亦未必能討得了好去;而如斯鉅大的怨氣聚合體,亦絕不會因許小姐鎯鐺入獄而了事。「啊!」大叔慘叫一聲,身後怨靈已佔據了他的身體。
許先生得手後,馬上對許小姐施以手段。許先生粗暴地撕碎了昏厥在地的許小姐身上淡紫色的絲質連衣裙,露出了貼身的紫色蕾絲胸罩和丁字褲。許小姐雖已三十有四、又是一子之母了,但在入目的嬌軀之上卻絲毫不覺歲月與生育的痕跡。許小姐那豐滿而柔軟的一雙美乳在胸罩的呵護下,顯得格外的堅挺動人;光滑無暇而婀娜的纖腰,微曲著擺成誘人的姿勢;而她下身那小小的丁字褲之下,是一處陰毛修得整潔漂亮的小洞天…
看著眼前香豔的尤物,已是識途老馬的許先生仍不禁暗暗垂涎。許先生把許小姐抱進了寢室,用不曉得從哪弄來的繩子把許小姐的雙手緊緊縛起;一雙光滑而修長的美腿則被曲起來分開縛著。然後,許先生從櫃子裡找出一瓶油質的透明液體,仔細地塗遍了許小姐身上每寸肌膚。當許先生雙手遊到許小姐的敏感帶,像是乳尖、大腿內側還有陰核的時候,許先生更是塗了厚厚的一層。許先生復仇心切,甚至把些許液體灌進了許小姐的後庭。
不一會,許小姐的呼吸變得急促、雙頰也泛起了陣陣的紅潮。原來那瓶油質液體,竟是下三濫的催情藥…這瓶催情藥既能外敷、亦可內服,再貞烈的節婦一旦誤墮其障,亦只會淪為慾求不滿的淫娃;何況許小姐被淫藥浣腸,比塗之肌上更能被身體吸收。「哼,見效了吧…我可沒能讓你在獄中安逸的度過餘生。」許先生那怨憤的音聲縈繞於屋子裡。「只是身陷囹圄也太便宜你了!我要你變成人盡可夫的蕩婦,去到哪裡都得乞求別人的雲雨!」
倏地,許先生感到身軀傳來強烈的排斥感。雖然許先生偷襲得手,但大叔畢竟法力高深、兼之自身魂魄之楔合度終究非野魂可比,因此在勢均力敵的角力之下,大叔自是佔了上風。囤聚法力半晌後,大叔逐點取回了肉身的主導。「啪!啪!」的兩聲,大叔折斷了右手的拇食二指。原來剛才大叔的一雙飯筷,乃係許先生生前之物,是故跟大叔建立了連繫。如今兩指既折、連繫已斷,許先生自是被大叔驅離了肉身。
許先生頓失肉身,道行一時散逸。大叔趁機掏出一把稻米,撒向許先生的怨靈。「大膽妖孽,竟敢恩將仇報!」大叔恨恨的切齒道。「看我把你打得灰飛煙滅!」大叔咬破左手食指、在地上畫符借法,封住了怨靈的行動。大叔趁機回到客廳、從包袱中抽出桃木劍,再跑進寢室一劍劈散了許先生的鬼魂。
那邊廂,許小姐伴著春潮悠悠醒轉,檀口吐出了氣若遊絲的嬌喘。大叔朝許小姐瞥了一眼,但覺許小姐渾身紅霞、一片美陰更已是淙水潺潺,把紫色的蕾絲丁字褲染上了深深的水跡。同時,大叔也察覺了許水姐眼中的矛盾,時而挑逗、時而渴求,卻又時而驚懼。「莫非…?」大叔若有所思,走到床沿把手指捅進了許小姐的美陰。「啊…!」隨著大叔手指的侵入,早已飢渴難耐的許小姐吐出了長長的一聲嬌吟。
「果然如此!她是太久沒跟男人行那周公之禮,結果陰陽失衡而陰氣極盛,影響了身體、更扭曲了心境。難怪她既是心狠手辣的獸母,又是驚恐嬰靈的弱女了。」大叔心中暗嘆。「可她畢竟是心存惡念方始鑄成大錯,終須償還惡行。只是她體內的陰氣…看來,唯有能把男性的元陽精氣注進她體內才能解決了。不然則她不只心智失常,更堪有性命之虞…」
道術之中,本有房中一派,其史更是源遠流長。自軒轅黃帝時代以降,此術一直流傳不斷,更被載於醫書藥經之中。若追溯其源,在最早期的醫書《黃帝內經》中已可見其蹤、而《素女經》更是以此為軸的著作。房中雖不同於丹鼎、茅山,但在五千年文化融和的過程中,各支各派的界線已日漸模糊,正如學術上的釋、道、儒一般。在歷史彼岸曾是壁壘分明的流派,於現代已揉合成一種共冶一爐的道術,是以大叔於此亦有所涉獵。
大叔收斂心神,準備對眼前的尤物施那雲雨之事。要知道兩性之事本乃烙於基因中原始之慾求,稍一不慎即沉淪其中。而許小姐又是如斯的性感火辣,其兇險之處更不可與的尋常庸脂俗粉同日而語。於大叔來說,這比昔日一切經歷更為驚心動魄。另外,此舉本是冒犯之行、加上大叔並不知道適才被附體時塗藥之事,是以大叔並不解開許小姐手足之上的綁縛,免了一番唇舌與掙扎。
「得罪了。」大叔輕聲說道。大叔扶起並從背後環抱著許小姐、一雙厚唇貼上了許小姐火熱的耳垂。「唔…」隨著大叔濃厚的鼻息噴上了許小姐的粉頸,尤物鼻中哼出了一聲愉悅的低鳴。大叔無暇詫於眼前嬌軀敏感的反應,淺淺地吸吮著、輕嚙著許小姐的耳垂,靈巧的舌尖更時而輕薄著尤物的耳背與耳窩,教身前的性感女郎嬌喘連連。
大叔一雙破蒲扇般的大手也沒閒著。解開了尤物身上僅餘的寸縷之後,大叔的祿山之爪不斷輕捏著許小姐那碩大而柔軟的胸脯;卑劣的手指更不時拂弄著淡啡色的乳峰,時而劃圈、時而揉玩、時而拉扯,一雙乳尖在如此褻玩之下漸漸勃起,慢慢變得挺拔無比。
許小姐自昏厥以後,對身邊之事矇然不知。睜開美目時,許小姐但覺渾身赤裸、手腳頓失自由之餘還以淫蕩的姿勢示於人前。本來女性在陌生人面前赤身露體,應是羞恥之事;但在催情藥的效力之下,許小姐只想來一場轟轟烈烈的性愛。待得大叔如她所願施以侵犯,許小姐早把一切的節操都拋諸腦後了,更忘了自己在不久前才想殺了眼前的大漢。其實以許小姐久旱的嬌軀,只須稍作挑逗就已情慾勃發了。何況,現在還被催情藥塗了滿身。
面對大叔房中術的奇技淫巧,尤物被挑逗得春情勃發,只想大叔用他的寶貝填滿自己下身的空虛。這時大叔把許小姐轉了過來,一口含住了人妻的乳首,並用舌尖快速挑弄著。大叔有如嬰兒般大力吸吮,竟還真的吸出了淡淡的乳汁。「啊啊!」從胸前傳來的強烈快感刺激著許小姐的大腦,使她不禁叫起床來。
隨著耳畔傳來忘我的淫聲浪語,大叔知道自己已佔了上風、眼前的美人已完全進入了發情的狀態。接下來只要控制情慾,就能把許小姐征服於胯下。大叔加緊手段,吻遍了美人身上每一寸白皙的肌膚。同時,大叔左手向下遊移,掀開了許小姐下身那早已濕透了的丁字褲,輕叩著尤物勃起了的陰核。
「嗯…嗯…啊!」在大叔經驗老到的愛撫之下,許小姐忘我的淫啼浪叫著。隨著大叔手指的進出,美人的嬌喘起落不斷,而她的鼻息已是呼多吸少了。大叔漸漸吻到一雙美腿,他把許小姐每一顆葡萄般圓潤的腳趾都吮了個夠,再慢慢從小腿邊吻邊舔到了大腿。當舌尖劃過許小姐的大腿內側時,尤物以高八度的聲線「呀!」的一聲叫了出來,表達著她的敏感。大叔見狀把舌尖停駐在此,不停打圈挑弄著。直到許小姐被舔得痙攣似的抽搐著,大叔才把舌頭遊移到美人的下陰。
舌尖甫觸及美人的陰核,許小姐立刻觸電似的抖了一下,畢竟舌頭的柔軟非手指可比。大叔的靈舌時而輕拂、時而劇抖,仔細地舔遍了大小陰唇和陰核;同時大叔的手指仍在苦幹,不斷於陰道口抽插著。忽然,美人雙眼反白、全身顫抖著泛起紅霞、陰道一搐一搐地夾著大叔的手指、口中呼出連串嬌啼…然後尤物的愛液如噴泉般暴發,把大叔的一張臉都沾濕了。原來許小姐太過亢奮,竟然潮吹了!
大叔輕吻著美人的粉頸、雙手褻玩著一對蓓蕾,好讓眼前的美人享受潮吹的餘韻。半晌,許小姐嬌軀上的紅霞漸退,理智也稍稍恢復了點。「給我…」美人乞求著。「還不夠…我還想要…」大叔眼見時機成熟,掏出了胯下的巨根。許小姐一看之下竟楞住了,大叔的陽物極粗極長,直如的嬰孩前臂一般。大叔並不急於攻城掠地,而是把胯下陽具遞到許小姐的嘴邊。許小姐如獲至寶,馬上張開檀口含了下去。
許小姐雖然雙手被縛,但仍賣力地扭動著腰肢,前吞後吐著大叔那雄偉的陽物。龜頭傳來久違的男性氣味,教久曠的尤物嗅得心神蕩漾。美人在狼吞虎嚥中不失細膩,三寸丁香舔遍了玉莖的每一處,連龜冠下的那條小溝都沒能放過。在許小姐鉅細無遺的伺候之下,大叔的陽物前端滲出了亢奮的前列腺液。許小姐見狀,立即有如久旱逢露般把那晶瑩吮了乾淨、還仔細地清潔著大叔的馬眼跟玉袋…
另邊廂的大叔可也沒閒著,正為兩人的前戲譜上謝幕的樂章。大叔的手指撩撥著許小姐已是一片狼籍的下陰,把陰道裡過多的愛液輕挖出來。男女性器興奮時分泌的液體本來是用以減輕性愛時摩擦產生的痛楚,但過多的分泌物卻又會導致摩擦不足、減低了雲雨的快感。情慾不足則精氣不純,採陰補陽之效自會大打折扣。因此大叔先把多餘的愛液給挖走,以便待會兩人齊達情慾的巔峰。而在這過程中,許小姐也獲得不少的歡悅。
大叔眼見時機成熟,於是扶正了兩人的姿勢、陽物輕輕抵住了美人的玉門關。許小姐合上了一雙妙目,準備承受眼前這男人的侵入。但等了半晌,大叔卻只以陽物摩擦著許小姐的陰戶,總不肯一插到底。早已春情勃發的美人禁不住如斯挑逗,開口求饒道:「尚師傅…別…別再弄了!求…求求你,給我一個快活吧…」許小姐最後的告白宣告了大叔的勝利。大叔再也按耐不住,提起陽物、緩緩侵入了尤物那濕潤緊緻的美陰。
「啊…!好…好粗!尚師傅你…你好硬!」許小姐但覺下身被根又粗又硬的火燙棒子給填滿了,傳來瘋狂的快感。但事實上,大叔只是塞進了龜頭而已。隨著大叔緩緩的推進,尤物的淫聲浪語也越發忘我狂烈。「呀…!到…到底了!」大叔的龜頭越發深入,終於抵住了許小姐的子宮頸,怒漲的玉莖卻還只進了大半。「快…快幹我!狠狠的…幹死我!」美人歇斯底里地喊著。大叔緩緩地抽送起來,回應著許小姐熱烈的渴求。但沒插了多少下,美人又是一陣抽搐、一抹紅霞,再一次攀上了情慾之巔。
「昇…昇天了!啊…!好爽…呀!」美人失了理智,淪為情慾的奴隸,忘我地叫喊道。其實許小姐每高潮一次、體內的陰氣就洩了一陣,因此大叔也樂助其成。大叔加快了抽插的速度,把許小姐留在了巫山之巔。狂抽勁插百餘下之後,大叔把美人翻過身來、以狗趴式繼續狠狠地幹著眼前的尤物。許小姐但覺前所未有的愉悅,扭動著曼妙的腰肢迎合著大叔的侵犯。
大叔扶起了許小姐,以「龍舟掛鼓」的姿勢性交著。許小姐雙手遭縛、無可攙扶之物,全身的重量都聚到了下陰之處、嬌軀更是敏感,許小姐甚至還能感受到大叔陽物的形狀。大叔的龜頭一下一下的撞擊著美人的花蕊、龜冠不停地輕刮著陰道的內壁,弄得許小姐高潮不斷。美人低頭望去,只見腳下的地毯被自己的愛液弄出了一大片水跡,頓時紅暈撲臉;但羞恥之心卻又馬上被強烈的快感蓋過了,只剩下無窮無盡的情慾與墮落…
「啊…!太…太深了!好…啊!幹…幹死我了!」大叔加重了力度,性器的交合處濺出了陣陣的水花。隨著一次又一次的高潮,美人的子宮頸已變得鬆弛。大叔奮力一插,終於突破了子宮頸,攻進了前人未及的新天地。許小姐嬌軀劇抖,子宮一縮一縮地吸吮著大叔的龜頭。大叔抵受不住如斯刺激,自知精關難守,於是把許小姐進到床上,以傳教士式拚命地再抽插了數百下,每一下都突破了子宮口。然後大叔「啊!」的大吼一聲,把陽物插到了尤物的子宮裡,精關一洩如注,把火熱的精子都注入了美人的最深處。「啊…!好爽…啊!好燙…啊啊啊啊啊!」在大叔火燙的精液灌注之下,許小姐到達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境界,強烈的快感直衝腦部,使美人昏死過去。
大叔伏在許小姐的嬌軀之上喘著氣,同時感到美人體內的陰氣已被消弭。良久,大叔從疲倦中回復過來,抽出了半軟的陽物。大叔整理好衣冠、替許小姐穿回了衣物,並召來了警察。許小姐由於體內的陰陽之氣劇變,失卻了被打昏之後的記憶;而大叔則由於此事有失體統,是以一直秘而不宣。許先生的魂魄雖已被打散,但為了守秘,大叔事後騙仲佑已超渡了許先生。而許小姐由於墮進了淫藥的魔障、淪為慾望的奴隸,在獄中終日自慰洩慾;但卻也因此而使得體內的陰氣得以宣洩,不致再次鬱結成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