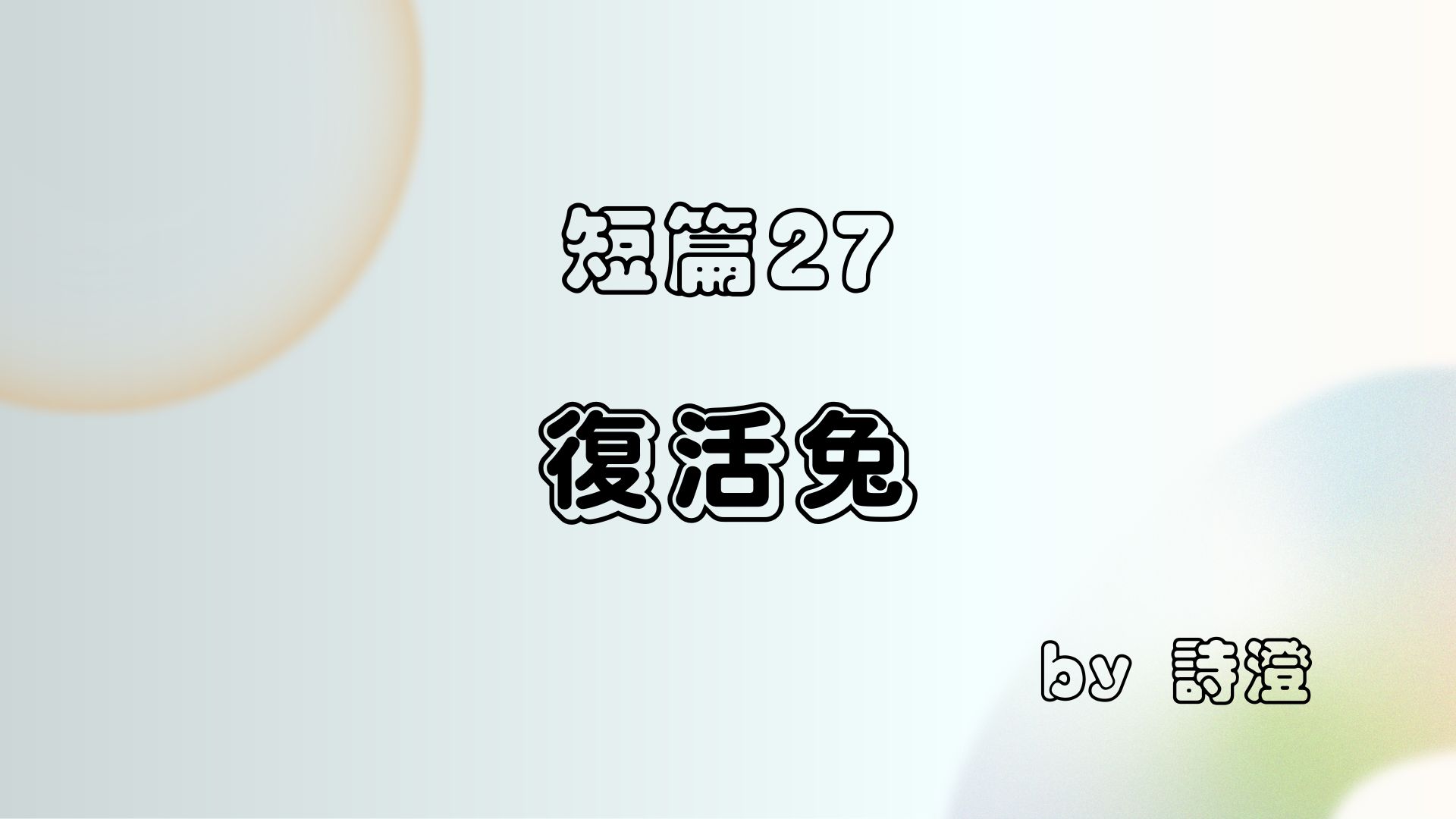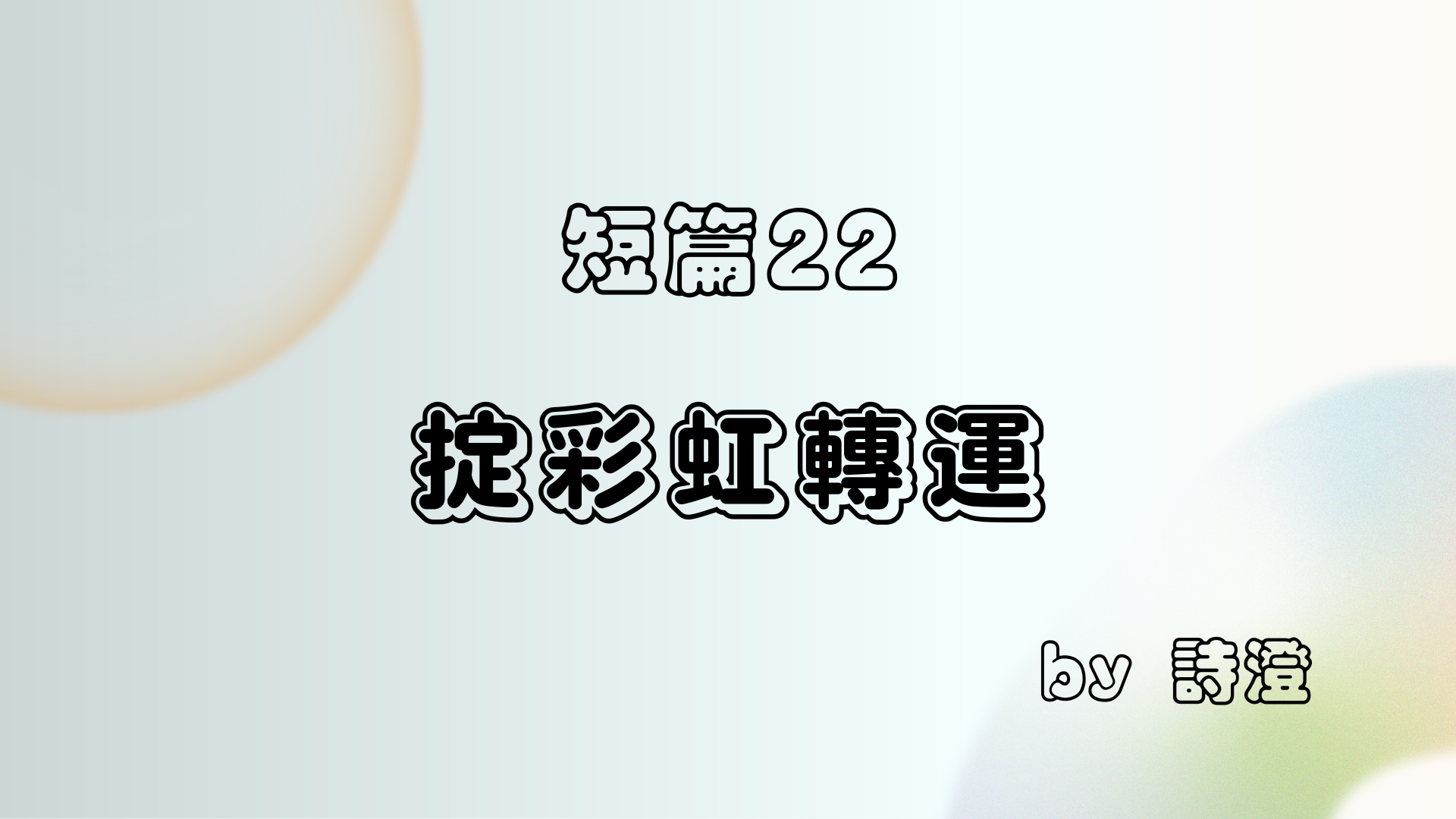我駛著42號巴士,前往未知的終點站。
上一手車長沒有給我訂定車資,
也沒有給我安排路線,
他只說了一句:「路線自己決定,但要為你的選擇負責,總之要駕著它抵往目的地。」
「目的地?」
他沒有答便消失了。
望著周圍的車輛都有車頭燈光照它們的道路,
我暗自妒忌埋怨,
為何這巴士的車頭燈起初便壞了…
但我沒打算維修,
應該說這已是無法彌補的缺陷。
我費盡心機把這天生便殘破不堪的車身用黑色粉飾一番,
然後踏踩油門,展開我的旅程。
巴士經過海岸公園,
可是我駛得太快,
眨眼風景便溜走了,想倒車也倒不了,行得稍慢也被砵。
紅燈停,綠燈走。
那些人可以走快點嗎?恨不得衝燈直剷。
我看到42號車站牌,
這是提示我要停下來嗎?
車門開了,
我不在意誰登上了這車,
只希望他們給我投入幾枚硬幣或拍下八達通。
「師傅,幾錢?」這年頭還有人喊「師傅」的嗎?
而且我很明顯是女性吧…
算了,也慣了給誤認。
「你喜歡。」
滿似不在乎乘客給我多少,
但看到有些給了五毫,有些給一毫,大部分甚至不付錢,
我有點懷疑當初為何要著力粉飾這輛廢巴…
算了,也慣了白費心機,也慣了徒勞無功,其實心裡很在意。
雖然那個消失了的車長說沒有既定的路線,
沿途卻有一個個42號巴士站,
我不想行差踏錯,不想負責任,便按著那些提示駕駛,乘客也載得滿滿了。
42號似乎要穿過香港仔隧道,
那條經常堵車的隧道,
車龍龍尾已到收費廣場,
我想繞道走,
可惜剛駛過了「自動收費」那條關卡,
我想越線,
無奈道路交通條例列明大型車輛必須靠左駛,
而且切雙白線也會違例…
那唯有等。
一小時,兩小時,
車子前駛了一碼;
半天,一天,
一星期,兩星期…
乘客們耐不住,
一些破口大罵,
一些嚷要我在隧道裡給他們開門下車。
我沒有理會,
直至後面的車龍不斷傳出滋擾的響號聲,
我也迫不得已的要大聲響號呼應,
突然不能自己的流下淚來,
這回我才發覺原來按響號的真正意義純粹是用來發泄。
車龍開始消退,
在不透一點陽光的管道逗留了不知多少日子,
終於能夠重見天日,
我又不由自主的響號起來。
巴士在隧道出口的第一個42號車站停下,
開門,車箱頃刻空空如也。
「砵--」
之後接連過了幾十個車站都沒有人上落。
我與這輛笨重的巴士在兩條白線內的灰色地帶相依度過了不知多少日子。
有時車尾會發出「呯嘭呯嘭」的嘈雜聲,
我意識到有些危險,可我沒有理它。
入夜後不如其他車輛,
我沒有兩顆車頭燈的關照,
只能依附其他發光的車輛和一絲絲微弱非常的街燈,
還有肆意的響號躲避沿途的障礙物。
我看到遠處有道強光射過來,
於是下意識的在那位置停下。
門開了,
走進一個提著手電筒的女孩,
我臉頰的淚珠在電筒下曝光了。
以後每逄日落,
她都為我照亮道路,
如果可以,我決不想讓她下車。
「我在這裡落便可以了。」
我沒有剎車,
我怕門開了夜晚便不再有人為我照明,
我堅決不停下車子,不打開車門。
「請讓我下車吧。」我不停響號。
她用槌子撃破大平門,跳出去了。
因為我沒有剎車,
從倒後鏡裡隱約看見有條光柱在地上滾了數圈。
車尾的「呯嘭」聲愈發起勁,
似乎向我發出義怒,
遣責我自私的行為。
我再次跌入漆黑中,
怎麼也摸索不到任何42號車站了,
只懂望著倒後鏡駕駛,
這樣還有什麼意思,
與其繼續這條盲目無謂的旅程,
倒不如終止它。
我在路中心剎停了。
「砵--」
隨後的車子白喊了,
巴士車尾被撞凹。
「砵--」 警察來了…
「砵--」
吹了波仔,
我沒有飲酒。
他們看到我停不了的眼淚和響號,
懷疑我有精神問題,需要接受心理輔導。
勉強是不可行的,
我把錢箱裡的幾個錢交給剛才撞到巴士的司機作賠償,
然後駛走了巴士。
我想下車,可是安全帶扣住了我的身體,
不讓我離開,死也不讓我離開,
不是我想的。
「砵--」
我不想接觸任何東西,
只管望著那倒後鏡,
以後有人想上車我都一一拒絕接載。
「呯嘭呯嘭」,我沒有理會。
走多兩里,車尾著火了,這次我不能再無視…
我輕易解下安全帶,
下車灌水滅火。
原來車外很光猛,
只是我當初用了黑色覆蓋車身和長期封閉車門,
以致不能透光。
我打開車門,讓陽光透入,
才發現車箱內堆滿塵埃、垃圾,
而我一直都沒有為意。
我打掃乾淨,
並修理好車尾的零件,
到附近的加德士入油。
我把倒後鏡拆下了,
重新踏上油門,
我要望的是前方,
而不是把我的視線一直停留在倒後鏡裡。
42號車站又出現了,這次我打開了車門,乘客再次上上落落。
「師傅,幾錢?」「你喜歡。」
我望向前方,踏上油門,
儘管仍不曉得42號的目的地是哪裡,
只要跟著那些提示,應該可以走到終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