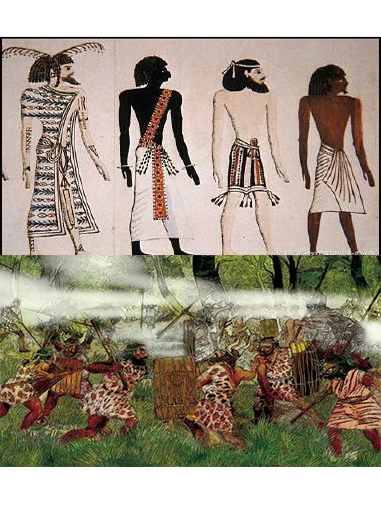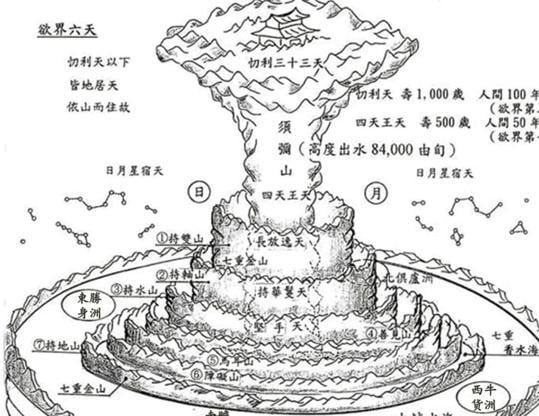現在我得收拾心情,不容自己思緒再混亂,我要安靜下來,這些只是幻覺,是的,我應該先去餐廳找點東西吃, 吃飽了人便清醒。3樓船尾有個宴會廳,在那裡休息一下才到控制室關掉機械吧,這樣處理比較好。為了讓平板電腦省點電,我轉用手機記錄當前情況,就是在船長室裡取來那台手機。
我沿走廊前行,除了眼前的情況,沒有甚麼比我心情更糟了,這裡的隔音可否造得差一點?過份寧靜的空間使我更感孤獨,求生意志隨之變弱。圓筒形的玻璃昇降機運作正常,我寧願選擇沿旁邊的樓梯往下行,實在需要省點電力,郵輪上的物資還剩多少?一想到剩餘物資,我雙腳便發起軟蹄來。
終於來到宴會廳,廳外玻璃門沒有上鎖,門外迎接我的是一輛違例泊車的餐車。何以連你也要擋我路?怎麼?我似乎看見宴會廳裡坐著一個人!是我餓壞眼睛嗎?我沒有選擇餘地,是鬼是先知也好,上前問問便知道。我鼓起脹不夠的勇氣,移開餐車、推開門,一步一步靠近宴會裡那個人,是一位白人老婦。希望她是人,也請不要消失,何以我又不敢太接近她?卻見她低頭啜泣。
「Hello」,我的問安無法牽動她一絲回應。那麼:「Bonjour?」是法文的Hello,我還懂日文版的:「こんにちは」,可惜她對聲音全無反應。我走到她面前,坐在她餐桌的對座上,她同樣無視我的存在,啜泣何必太認真?我嘗試用右手輕按她手背?試探她是實物,抑或幻影?我摸到她,是實物,但她對我的觸摸毫無知覺。
慢著,她抬起頭,皺著眉,望向我後方,然後四周張望。我見她一頭霧水,我更加不知所醋,為免誤會我縮起我的右手。之後她用德文說了些話,又跟我左邊的空間高聲對話,我卻只聽到她一把聲音。忽然,她猛然收回手背,她從恐懼中站起來,退了幾步,再用德語說完最後一句話後便轉身逃去。我站起來想追上去,她卻在我眼前消失了。怎麼?我剛才還摸到她,她是實物,她又看見誰?使她聞風而逃,逃至消失?
突然,有一股力向我手中的平板電腦從後向前推了一下,電腦掉在地上,然後消失了!不是違失,又是消失!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平板電腦連同老婦竟然在我眼前一併消失,站在我後面的是透明人嗎?還是有人在隔空取物?所有人和物,包括平板電腦,都在我面前、毫無遮掩下消失得無影無蹤,實在比船長的消失更決絕!不妙!至今未有Network,之前在控制室用平板電腦記錄的文字都要胎死腹中,再無讀者能閱讀我的第一集 (第二集的文字是用手機輸入的),第一集的記錄連同平板電腦和老婦一併消失了!
我要到廚房找些食物,吃完東西人便會清醒。 我轉入廚房,對怪事習以為常,廚房內沒有廚師但電磁爐是開啟的,很正常,因為郵輪上不准生明火 (不是無廚師而開啟電磁爐的原因);廚房外沒有賓客但US Prime牛扒是熱烘烘的,很正常,因為郵輪上的食物多得足以我吃幾年 (也不是無故存在一塊熱烘烘牛扒的理由),姑不論有太多幻影或虛像呈現眼前,只要當前美食和飲料是實體便可以,先來一杯Margarita吧!
宴會廳那個空蕩蕩的舞台,正在上演寂靜,樓高3層、偌大的玻璃窗如常播放漆黑,在華麗與空虛之間享用頂級牛扒是一種寫意嗎?是我畢生追求的嗎?宴會廳裡沒有宴客,玻璃窗外也沒有景觀,如何培養心情細味安格斯那份絲滑綿密的口感?肉汁再豐富都不過在問我此刻心情有多酸溜溜?似有段鋼琴聲掠過耳邊,怎麼忽然想趕時間?這塊頂級安格斯的吸引力,就此被這段多麼真實的琴聲牽走了。
I.T.人是務實的,所以我差不多要回到控制室。起行之際,餐桌上浮現一部相簿,是我之前看漏了眼的嗎?我總想用手摸摸它的真實,是一本翻得開的相簿,內裡的照片……正是剛才見到那位白人老婦。相簿裡有很多照片,是一些旅遊照,還有些……相信是她跟丈夫和兒子合照的,相片旁有拍攝資料,攝於亞美尼亞,旁邊有一段經文:「For we live by faith, not by sight. 」署名是Jakob。Jakob?他丈夫的名字?中國人是眼見為憑,德國基督徒是憑信而行,馬丁路德就是那種能灑脫地挑戰權威的人。
再翻去下一頁,老婦似乎是一名家庭主婦,他的丈夫是系統工程師,兒子穿上拜仁球衣,怎麼又是拜仁?多蒙特也不錯。好吧,該回控制室了,那裡還有些事要處理,手機只剩48%電力,希望在控制室裡找到其他手機,船長的手機螢光幕太小,邊行邊打字很費神。
吃飽飯的人,步伐也帶點勁,回到控制室又再次遇上這個轉動不停的雷達,同樣掃不出任何島嶼實物。怎麼?我看見一台平板電腦很面善的放在操控舵的支架上。這……這不是剛在宴會廳裡消失的平板電腦嗎?怎麼會出現在這裡?我啟動了它,有兩件事讓我愣住,一個是好消息,另一是壞消息。好消息是平板電腦的電量有100%,壞消息是平板電腦的電量為何會有100%?是誰給它叉滿電?還這麼神叉的快叉滿?抑或這是另一台電腦?我即時登入電腦求證,發現之前的記錄全部在桌面上,所以我肯定這是那台在宴會廳裡消失的平板電腦。
世事、人和物都變幻莫測,眼見為憑在這郵輪上不管用,唯有這句經文實在:「For we live by faith, not by sight. 」我確切失去信心,但憑信心分析,各樣怪事之間存在某種關聯和共通性,這裡為何風平浪靜?所有人去了哪裡?船長室的鋼筆為何插在椅背上?船長本人為何在浴室裡發出聲音,及後又消失了?是的,船長當時說了一句英語「Who did it?」誰做了甚麼?船長這句話帶有怒氣,怒氣中夾雜一點怯。有甚麼事可以令經驗豐富的船長生氣、害怕?莫非氣有人把他浴室裡的燈關掉?浴室的燈是在我進入船長室前已關上,一段時間後船長才問:「Who did it?」難道他怕黑?連沐浴不關門也不怕,豈會怕黑?
太多不可思議的事件,怎麼才可以把它們串連起來?是的,往船長室時經過7樓走廊,看見牆角上塞進半邊手袖,我應該到那裡尋找線索,但事先我得在這裡留下字條,一旦老婦或其他人再次來到控制室,至少可以讓他們知道船上還有其他倖存者。繼而我停了郵輪的引擎,關掉一些費電的機械,以保留船上的電源。雖然這些儀器我一點也不懂,總之寫ON的Switch向OFF好了。花了不少功夫,郵輪停駛了,燈與空調也關了,船上若有其他人,一定會來控制室,字條須留在當眼處,並寫著:「I'll be back in an hour.」讀起來也有點帥,在控制室要辦的事都辦妥,之後要探探那個塞在牆角上的手袖是怎麼一回事。
(約5分鐘後) 摸黑的感覺真不好,因為我足踝扭傷了,我不應該在這時侯踏錯梯級。現在我坐在7 樓走廊上休息一下,唉,真是禍不單行,不應該關燈,更加不應該關掉空氣調節,此刻有點喘氣。我已經想放棄,很吃力,為甚麼人間有苦難?海難是人為的嗎?無辜嬰兒夭折是因為孕婦過份抽煙嗎?為甚麼要我一個人留在這裡?要我死何不直接點?神啊,可否給我多一點時間?我已經戒煙多年,請不要把我留在這裡,我必須前行,耶穌不會為我一口煙把我留在這裡。For I live by faith, not by sight. 我不怕黑!
(約10分鐘後) 到了,已經看見這個塞進牆角的手袖。我從黑暗中舉起手機電筒掃瞄手袖,雖看不太清楚,但總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對了,手袖與牆之間沒有縫隙,是貼貼服服的將手袖塞進牆角裡。手袖看起來是立體有質感的,我的意思是手袖裡看似有隻手肘,我應該割破衣袖,打開求證嗎?我得先找來刀子和踏腳物,宴會廳的廚房裡有刀子,椅子也不難找到,好,先去廚房吧。
(約15分鐘後) 來到宴會廳,再次看見這幅3 層樓高的大玻璃,沒想到關上燈的宴會廳彷彿變成一艘鬼船,有個50年代紅衣女鬼在舞台上唱歌,說笑的,不望舞台便沒鬼。對比漆黑的宴會廳,大玻璃外也不是全無影像,窗外有影像?我在窗外海面上的確見有物體,且是很高很高的,這樣一幢大黑影形態有如香港IFC矗立在不再發光的維港上。太黑,看不清楚,何處能走出外面?
我跑到船尾甲板上,看見這幢大黑影最少有數百米高,闊也超過100米,但不是山,因為很筆直,太平洋上怎麼有這樣的鬼東西?這大黑影究竟是甚麼?來了一陣風,很強的風,暫時打不到字…… (之前習慣邊行邊記錄)
(約1分鐘後) 剛才有一陣風,維持了近一分鐘,很猛烈的風,跟現在這種尤如密室裡的氣流,感覺完全不同,我是否應該開啟郵輪射燈,但若光線對不準這幢大黑影,背光下更難看清楚?然而汪洋大海上因何矗立這樣一幢大黑影?它既沒有山的曲線,也沒有建築物的直線,從黑影中隱約看到它的形態,就跟我已知物件中沒有一樣配對得上,但我總認為,有必要靠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