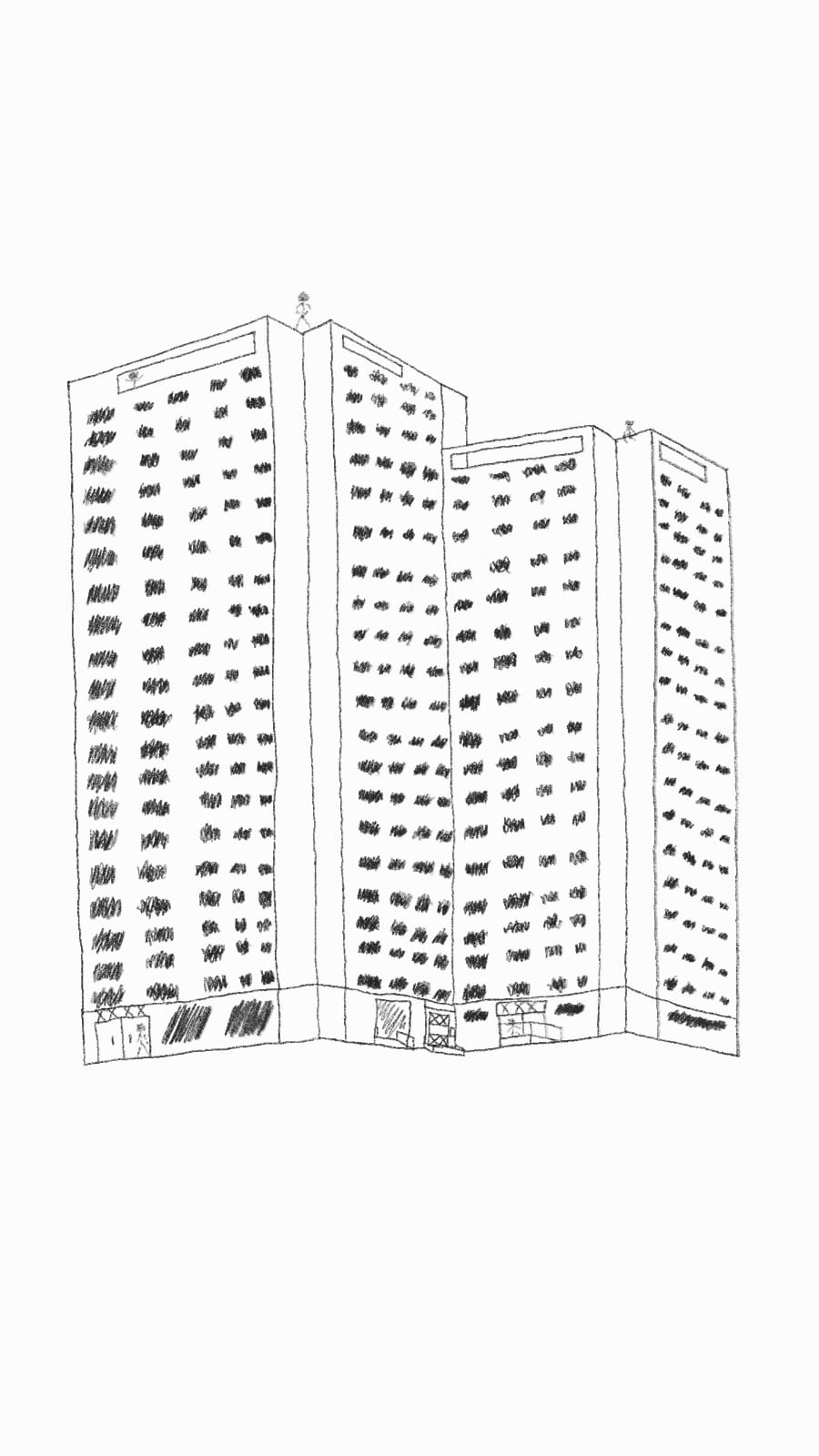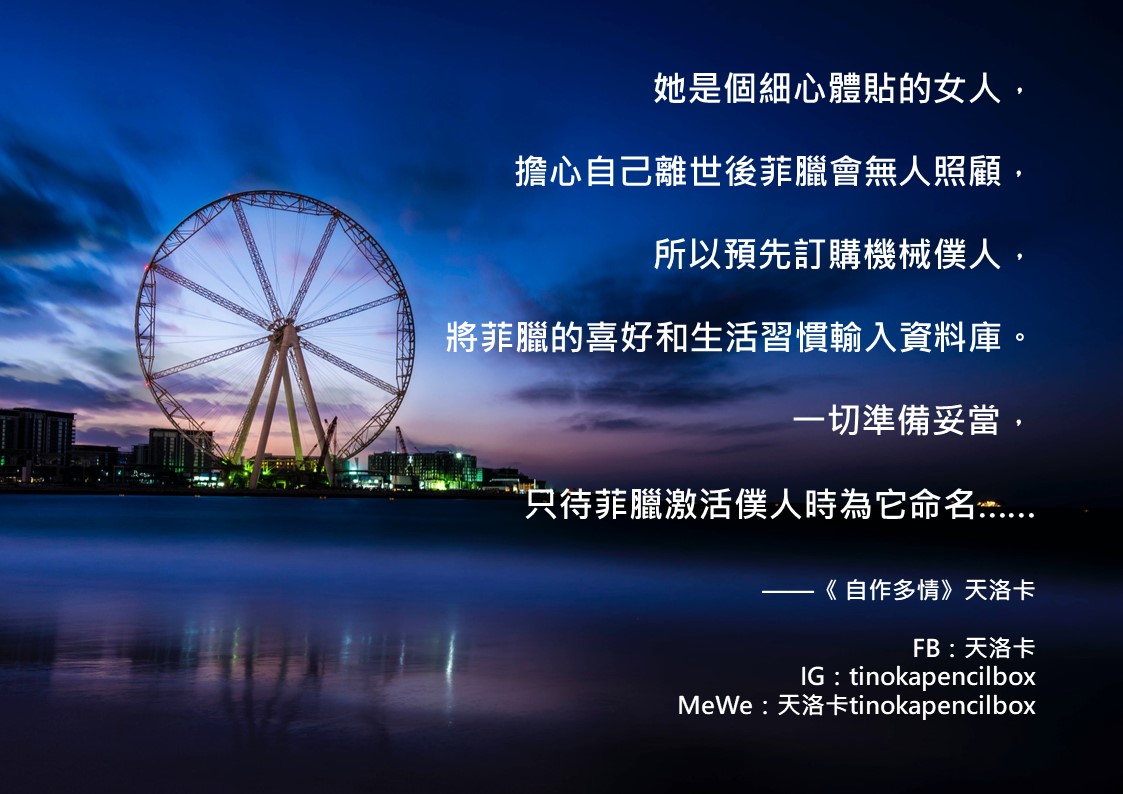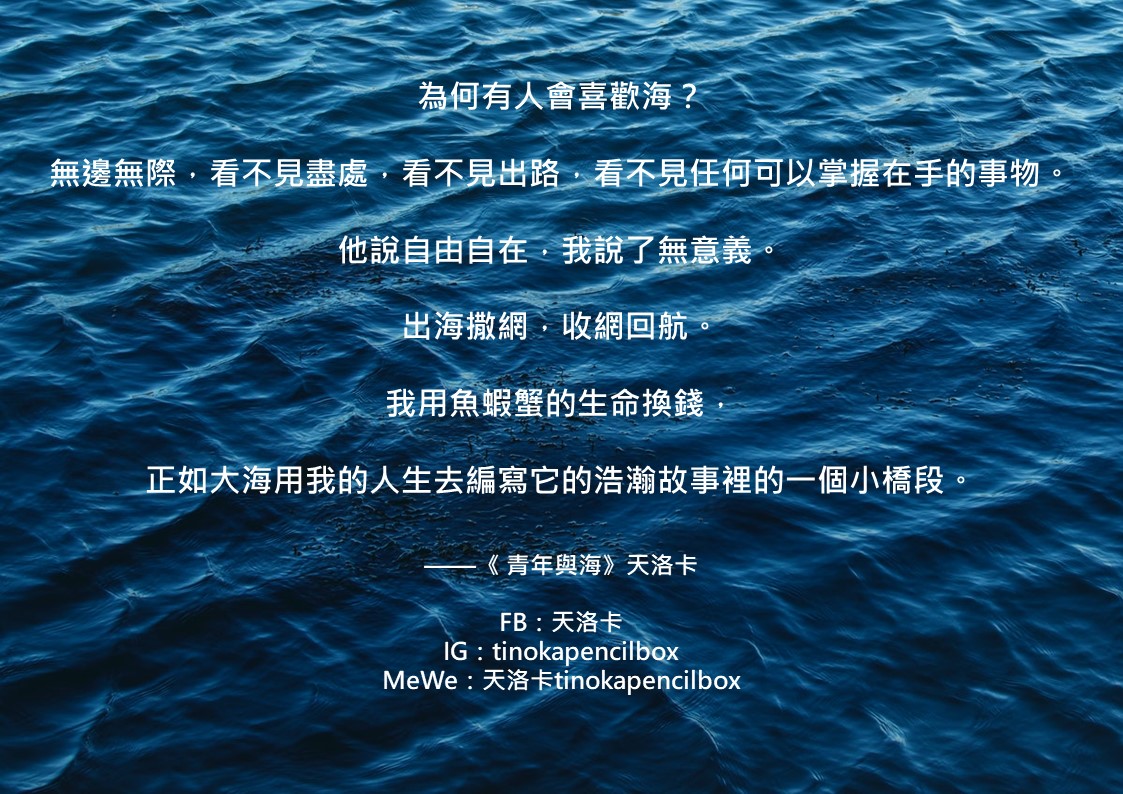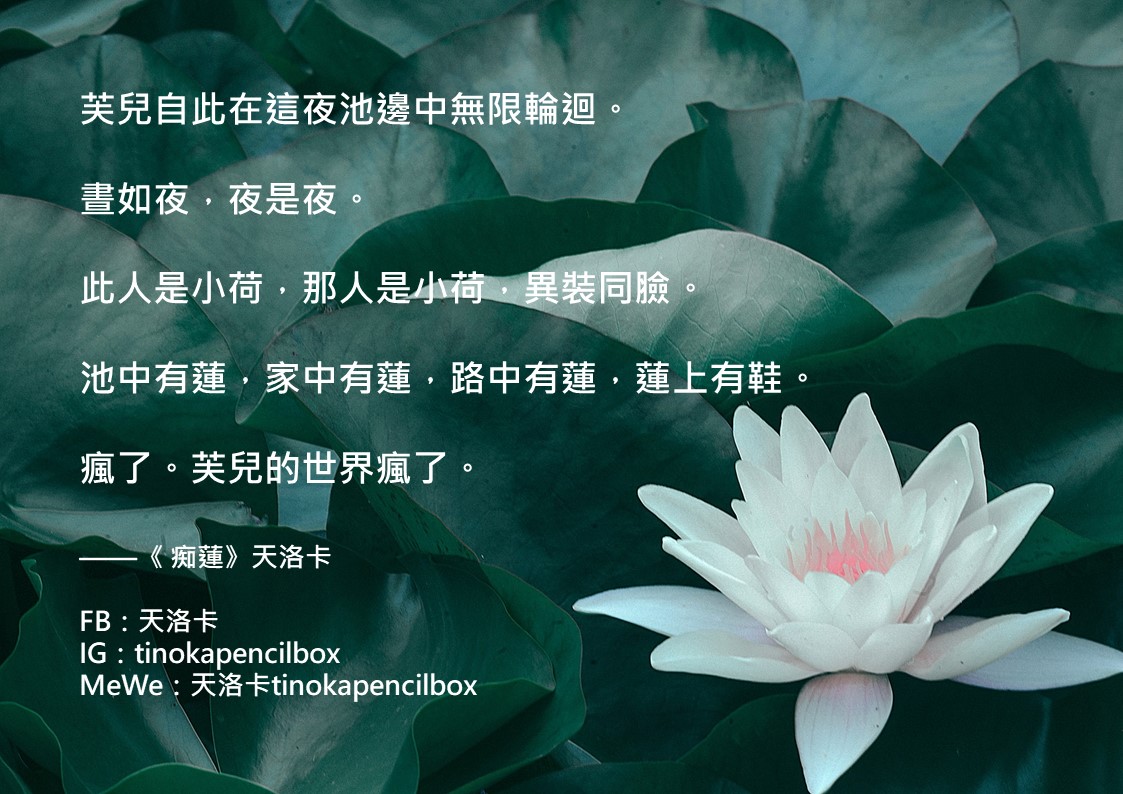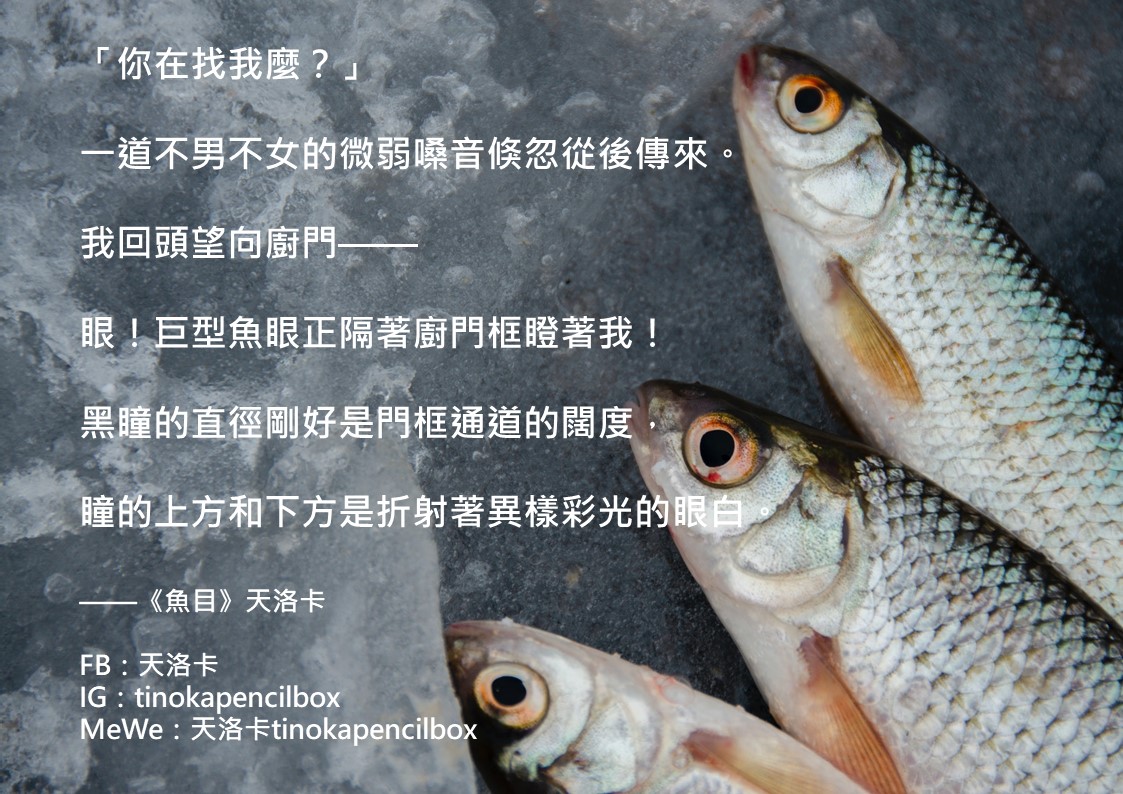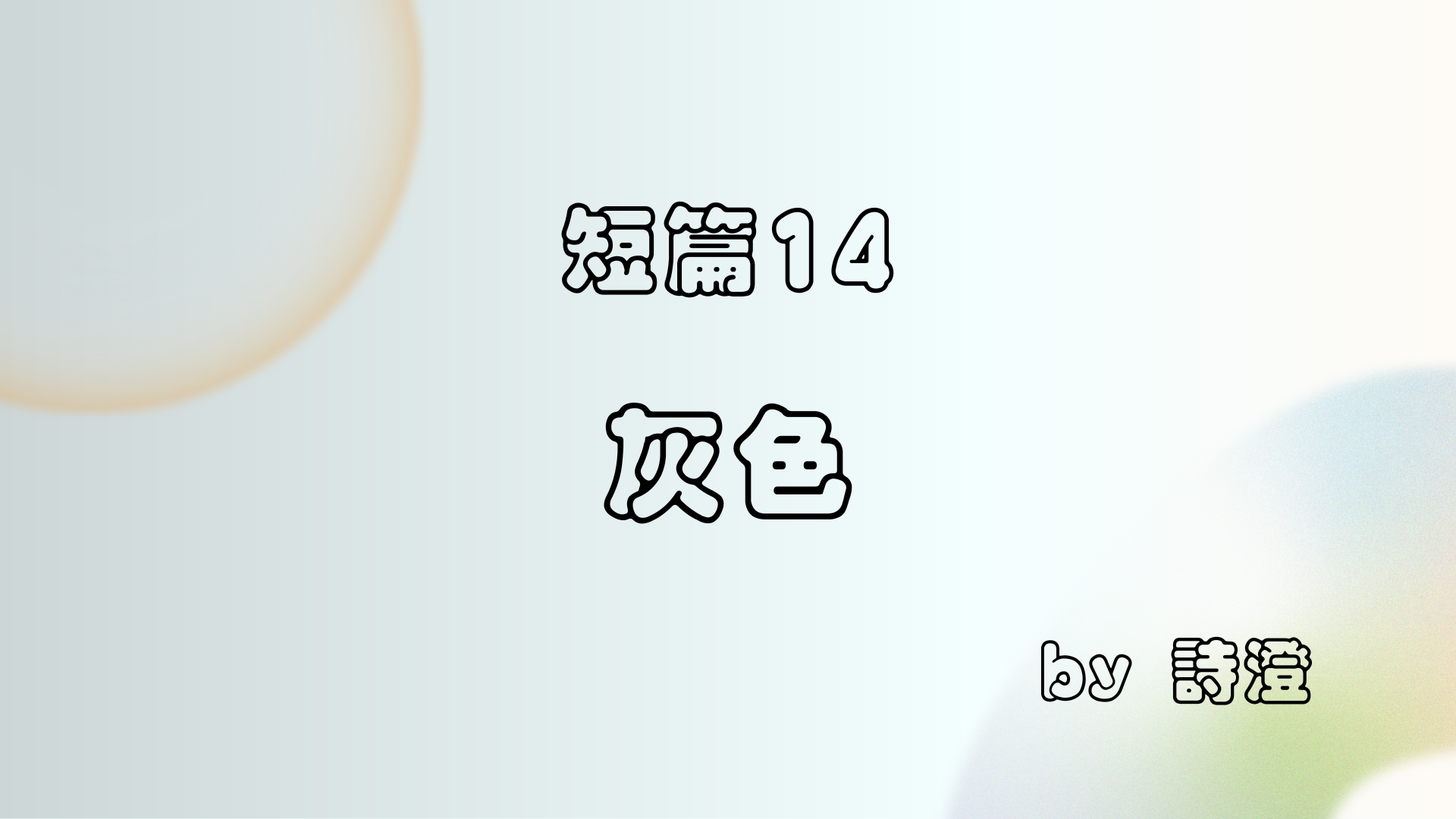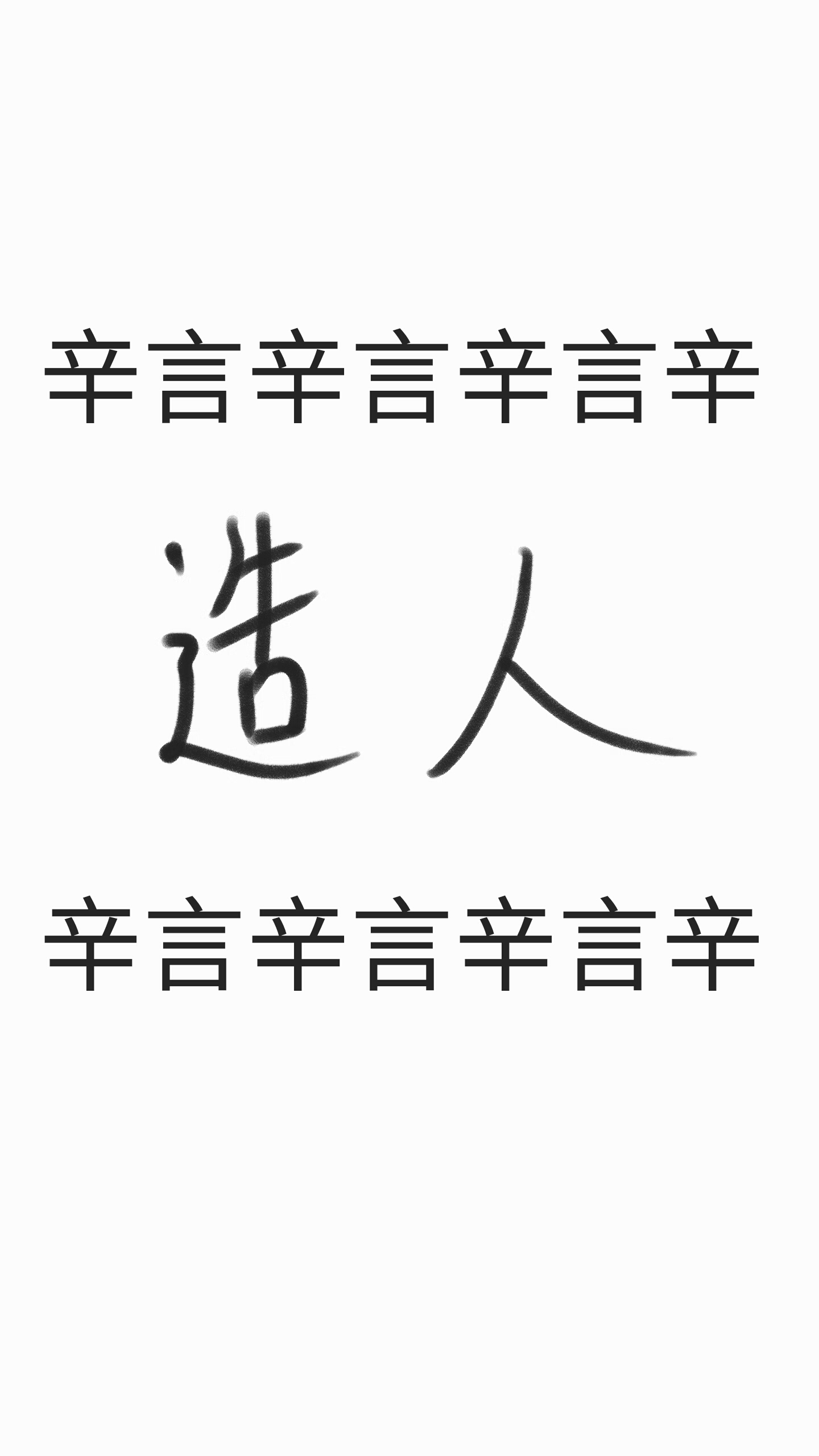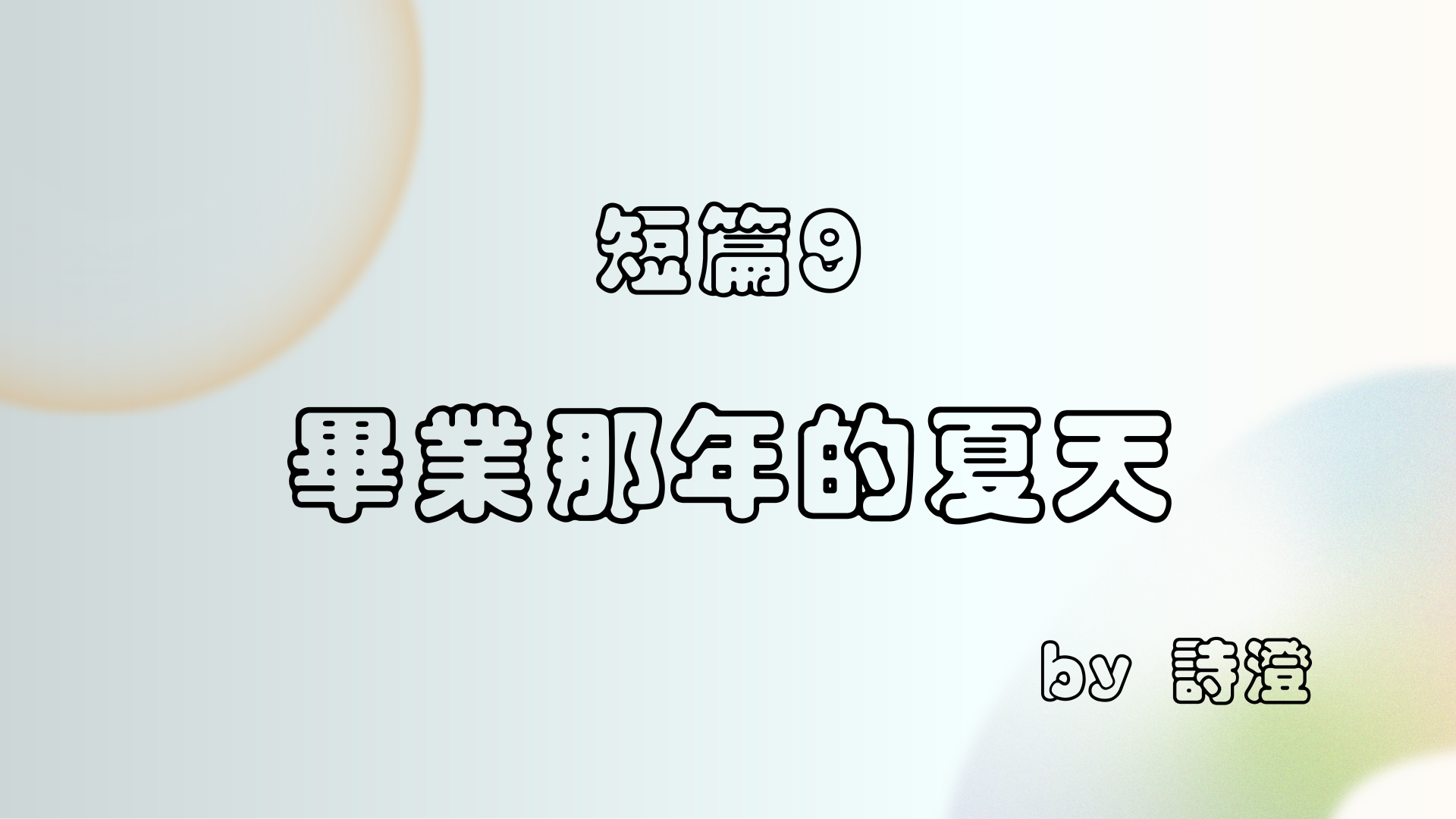小屋裡、睡床邊,她架上老花眼鏡,小心翼翼用開信刀拆開今早收到的奇怪信件。
純白的信封上沒有註明地址,亦沒有郵票、郵戳和收信人姓名。明顯不是透過郵政服務寄來的,而是有人將信件直接放入她的信箱。
是誰?有誰會寫信給她這個孤僻木訥的八旬老婦?該不會是兒子——他已好幾年沒有前來探望,電話聯絡亦少之又少……
「啊!」看見信中物,她不由得發出一聲驚嘆。
壓花書籤。
紫藍色的小花在純白色托紙上尤顯孤獨冷清。
「毋忘我……」她雙唇微顫,熱淚盈眶,回憶片段有如走馬燈在她腦海中快速運轉。
初遇於了無邊際的毋忘我花海……情信信箋一角上畫有一朵線條簡單的毋忘我……他突如其來捧上的毋忘我花束……她在婚宴時戴著的紫藍色毋忘我花形耳環……他在窗前花槽播下毋忘我種子……他因頑皮兒子摘掉花槽裡的毋忘我而氣得流鼻血……他拒絕遷往大屋是因為捨不得花槽裡的心血結晶……年邁的他偶爾忘記淋花施肥……患病的他忘了花、忘了她……她為失智的他戴上紫藍色冷帽,笑說他是一朵毋忘我……每年清明重陽或其他大時大節時,她都會帶上一束毋忘我前往拜祭他……
難道是老伴的來信?
是!一定是老伴自天堂寄來的!
明明有很多合情合理的說法去解釋信件來歷,她偏偏選擇相信無從證明的鬼神之說。
或許,真假從不重要,合乎心意的表象才是真正有意義的。
這來歷不明的壓花書籤正好滿足她對老伴的思念之情。
她流淚,她微笑。她憂傷,她幸福。她空虛,她富足……
剎那間,她重新經歷體驗數十載的喜怒憂懼愛憎欲千萬遍,不斷發現、擁有、消磨、失去。
一切歸空,如夢如幻如泡影。
努力活著,只為失去?
放眼望去,小屋冷冷清清。兒子遠去,老伴不在。花槽裡的毋忘我早日被鄰近頑童連根拔起,散落滿地,肢離破碎。垂吊耳珠上的花形耳環已然褪色,只餘帶有花亂刮痕的啞色金屬配件。情信信箋受潮發霉,角落的毋忘我污跡斑駁……
無論如何用心留住一切,終歸逃不過失去的命運,對嗎?
很累。
放下眼鏡,揉揉眼。
想睡。
放下開信刀時,刀尖劃過手腕,留下血痕。
有意或無意?她自己也說不清楚。
該要馬上包紥傷口。
但看著血流不止的手腕,心裡竟沒有絲毫焦急。
沒所謂。反正終歸逃不過失去的命運。
她懶理手腕血流如注,安坐搖搖椅上,對著壓花書籤發愣。
時間流逝,體溫流失,記憶流竄。
她的意識逐漸模糊——想不起他的墳頭是甚麼形狀,記不清楚他的冷帽是否以純低針編織而成,忘記了肥料是從哪裡買來的……
他的臉和身體分崩離析,成碎,成灰,成粉,最後甚麼也不剩。沒有形體,因其而生的神情動態亦不復存在,遑論聲音、氣味、情感……
被遺忘才是徹底的死亡。
她曾痛恨上天帶走他的生命。
現在呢?
她主動放棄記住他。
上天或她更可惡可恨?
世上有靈魂嗎?他會怪責她嗎?
「死者已死,沒能怪責。」他的聲音來自壓花書籤:「一切只是生者的心念。」
迴光返照。
她撲前將枱面的書籤摟在懷裡,哭哭笑笑。
書籤是書籤,不是他。毋忘我是毋忘我,不是他。回憶裡的他是回憶裡的他,不是他。
是她將一切與他扣上關連。
如果她不復存在,整個世界跟他亦再沒關連……
手腕倏忽劇痛。
醫院。
病房裡擠滿前來探病的人,熱鬧非常。唯獨是她床邊兩條通道空蕩蕩的。
不曾期望兒子不會前來,但她心裡難免一陣失落。
當時是否不該報警求救呢?
這念頭生起還沒兩秒,一個小巧身影踏著小跳步來到床邊。
「莊遜太太,午安!」女孩不過十歲,雙頰通紅,眼眸明亮有神。身穿白色連身裙,裙上印滿碎花圖案,是紫藍色的毋忘我。
「午……安……」她和顔悅色禮貌應道,暗裡搜索枯腸,卻硬是想不起這娃兒是誰。
「喜歡我送你的壓花書籤嗎?」女孩喜孜孜的,不知自己差點兒害死眼前老婦。
「喜歡。」她強抑心底裡的一陣震驚,輕撫女孩頭頂:「為何你送我書籤呢?」
「數天前,我和祖母路經你家,看見你跪在草地上,捧著散落的毋忘我痛哭。所以我回家後馬上動手製作壓花書籤。送書籤時湊巧發現你不在家,只好把書籤放入信箱,讓你先睹為快!」女孩從裙袋掏出另外兩張毋忘我書籤送給她。「看!書籤上的毋忘我永不枯萎!多漂亮!」
這時,女孩的祖母才拖著蹣跚步伐趕至。
原來是鄰居費爾斯太太。
十年前,老伴去世後,費爾斯太太每天抽空前來相伴,與她談天說地、為她焗製香氣四溢的果批、陪伴她到市場買肥料……直至孫女出生,費爾斯太太忙著照顧初生小娃,才不得不淡出她的生活圈子。漸漸地,她亦忘記費爾斯太太,變得孤僻木訥……
「小小心意。」憂心不已的費爾斯太太捧上一個毋忘我小盆栽。
「謝謝你們……」她受寵若驚,緩緩伸手接過小盆栽。
右手手掌上是鮮活的毋忘我,左手手心裡是永不枯萎的毋忘我。
活的死的都在她手裡,只待她怎麼處理。
她打算怎麼處理?
未決定。
那就先收拾心情、養好身體吧。
活著,才可以想及將來、擁抱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