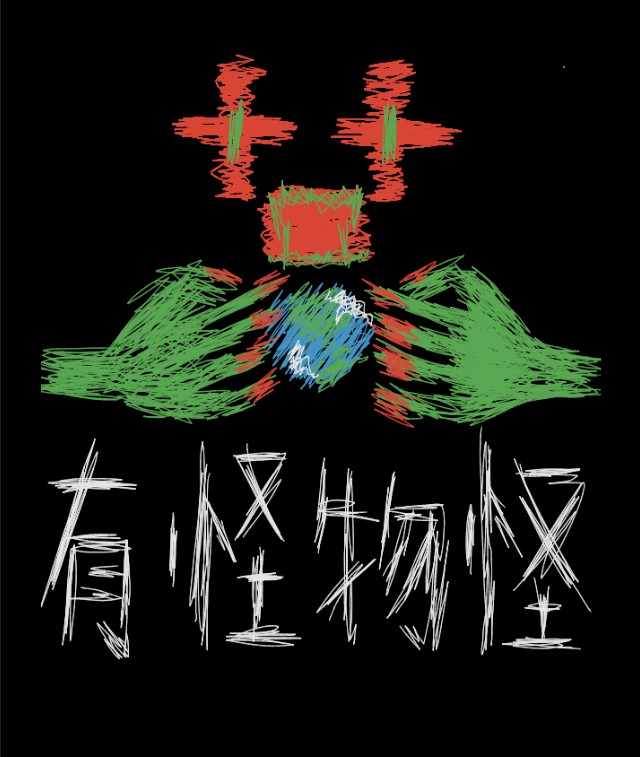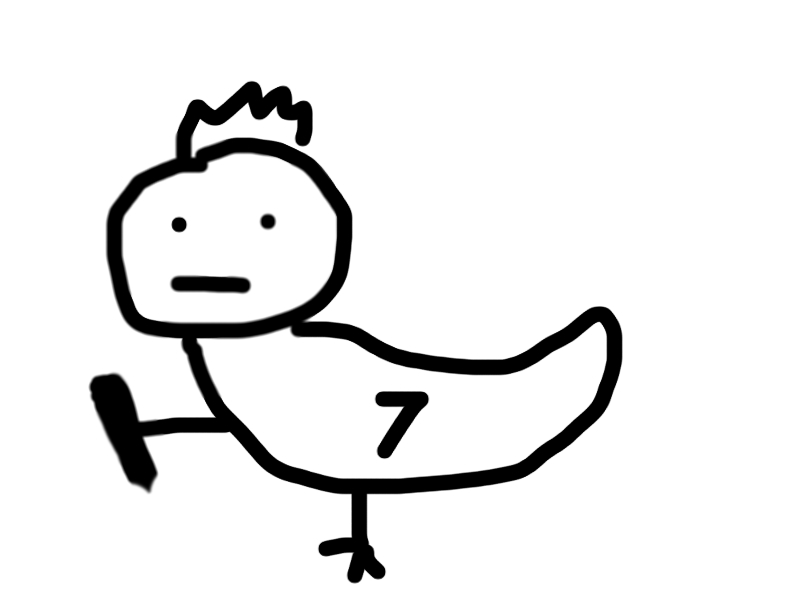「有看到左方的那部軍車嗎?」長官用無線電跟我通話。「看到,長官。」「等會兒他們的指揮官一下車就開火,明白了嗎?機會只有一次!」「是的,長官。」我把眼睛埋到狙擊鏡前,屏息以待,一發子彈,一個機會。
我就躺在距離軍車不遠處的山坡上,指揮官一下車,將紅點放到他頭上,憋住呼吸:彈指之間,一聲之下,他就倒下了。整個過程由下車到倒下不消5秒,畢竟也征戰沙場5多年了。
「做得很好喔!」「還真是有點料呢,貝利兄……」每次任務完成回到營裏都是這模樣:一整班大男人在搭肩抱腰、左擁右抱,讓我感到有點噁心,而且還滿身泥濘大汗。其他戰友們都在熱烈慶祝時,只有我坐在房間裏,本身自己的性格被戰友形容為有點孤僻、冷酷,但我卻不這樣覺得……起碼戴爾不是這樣想。我和他在戰爭前就是同窗了,更重要的是我們對攝影都是情有獨鍾,尤其是我自己。
誰說軍人一定是剛烈的,你何不知軍人也有鐵漢柔情的一面?據戴爾的說法,我清理鏡頭的時候有如母親抱住小嬰兒一樣,又說我不當保姆真的有點浪費,最後他也是比我懲治。的而且確,我對相機、鏡頭這種東西照顧有如親兒女般:每天都清理,不論有沒有用過。
在還沒參軍前在一間影樓中工作,為別人拍明信片,每一張都務求最好、最完美,可能這種心態對一名狙擊手有幫助吧。我總是覺得用鏡頭殺人是一種異常殘忍的方式,有點像用自己兒子來殺人一樣。
口袋中有一張女孩的照片,是我的女兒艾瑪,又黃又舊,但這是我拍過的最好的一張。相比之下,「完美」死在我鏡頭下的人成千上萬,有時還覺得,攝影師當狙擊手令人有種違背職業道德的感覺。
「要出發了」戴爾在催促著我「走吧」,今天的任務要到叢林中進行,「拍照」對象是某敵方軍官和其一行人。如常地,在適合的地方藏身、上彈、等待,習以為常的工序,快要比拍照更熟手了。
但總覺得,有點不太對……
(to be continued )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