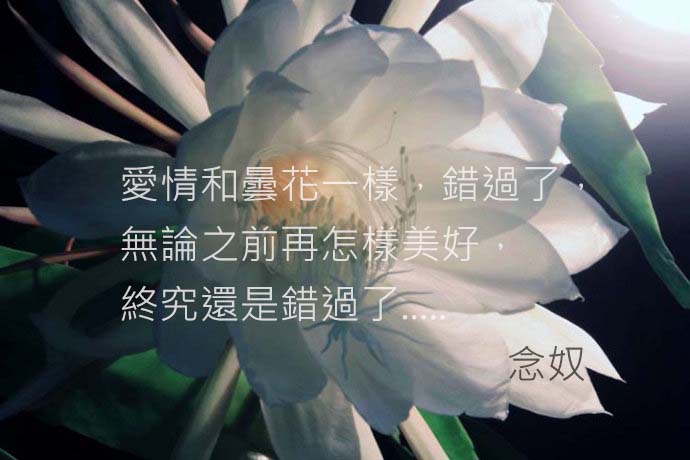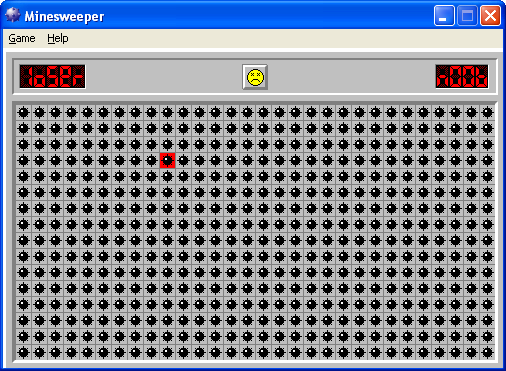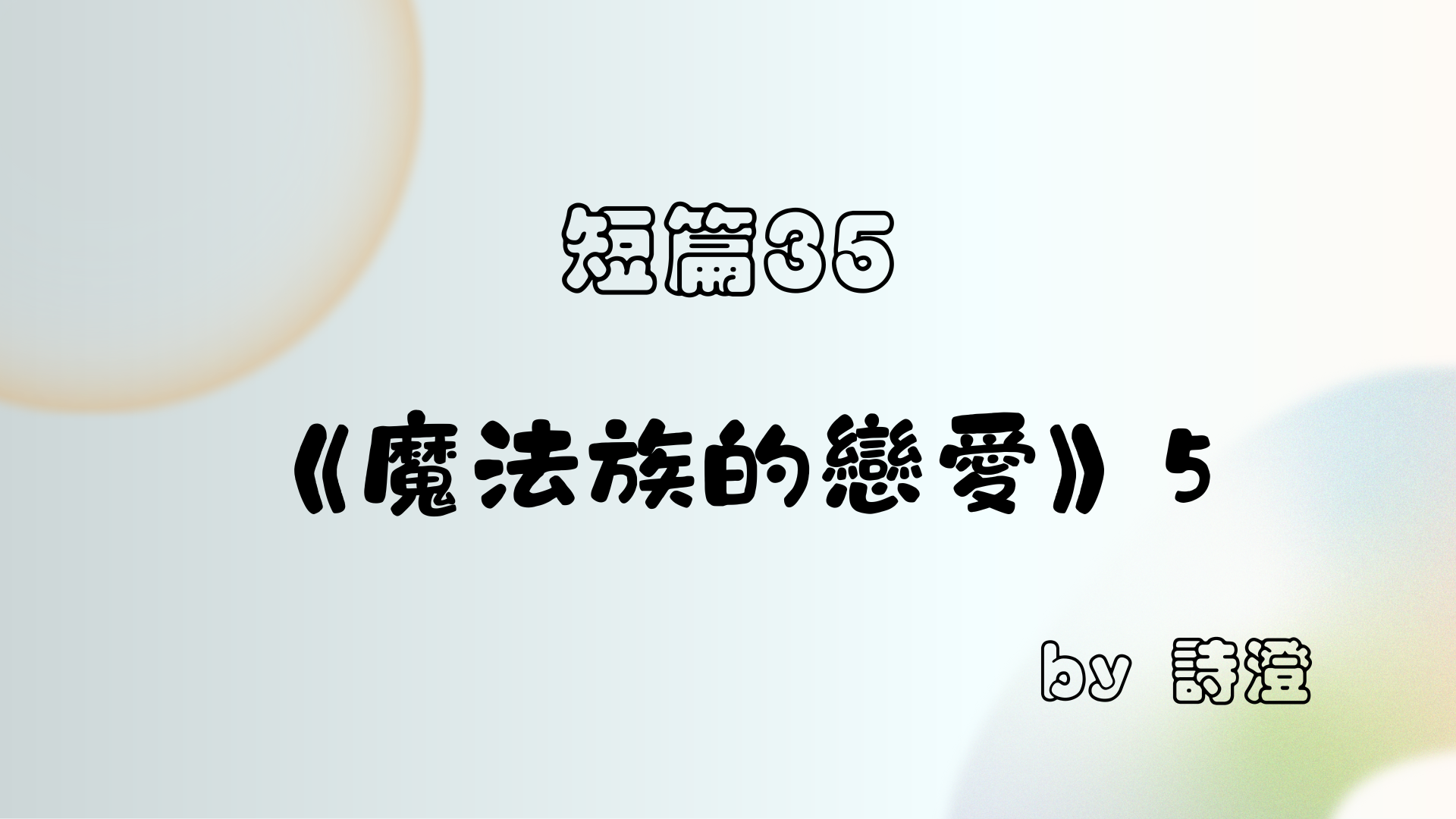「你他媽的在耍我對不!」傑利大力往桌上一拍,口供紙飄起了一毫米,原子筆滾落到地上,砸死了一隻路過的螞蟻。
「不要激動,大吵大鬧一點也不符合天才幹探的作風。」大衛笑著說。他低頭看錶,還有五分鐘便過合法扣留時間,應該趕得及回家看八時半的『歡喜冤家』。
一打警員在單向鏡的另一面看戲,天才幹探傑利終於碰壁啦!
傑利重重的呼了一口氣,他左手撐腰,拿起桌上的文件再看一次:
大衛.標,33歲,未婚,獨居,在『普通大學』畢業,在『普通公司』任職文員,整個人都很普通,大頭照亦是本人沒錯。
「我說啊,你真的沒認錯人嗎?」傑利向站在牆角的女孩問道。
「是他沒錯,肯定是他…應該是…?」女孩側頭,又托著下巴。
「你現在承認記錯人的話,我還可以饒了你。」傑利說。
大衛朝他望著的牆角看去,「請問你在跟誰說話?」
傑利轉向他,臉上寫著『不耐煩』三個字,「在跟被你殺掉的可憐少女的鬼魂溝通啊。」
大衛身體微微往後仰,對他投以一個關懷智障的眼神。他向牆角揮手,盡可能擠出一個笑容。
「我的天!他可以看到我!」
「別鬧了。」傑利搖頭,眼睛回到女孩身上,「珍妮,我再覆述一遍你的遇害經過,晚上你從朋友家離開,回家路上遇襲,頭部遭重撃昏迷,然後被兇手拖入冷巷,致命傷是割開喉嚨的一刀,心臟被掏出——」
「不要再說了,好可怕啊。」珍妮掩著耳朵打斷道。
「可怕極了,你們一定要抓到兇手。」大衛說。
傑利向他反了個白眼,兇手就是你啊,他說:「珍妮,重點是案發時間。」
「我不記得呀,大概是八時或九時吧?」
「是八時還是九時?結我準確的時間。」
「我直到十一時都在公司加班,升降機大堂的閉路電視可以做證。」大衛說。
「閉嘴!我不是在問你!」傑利向他哮道。
「對不起。」大衛歉意的搔頭。
「珍妮,回答我。」
「不知道呀,我沒有看時間的習慣。平時都是寫好作業便回家,沒有固定時間。」
「朋友的名字是瑪莉,她家有開電視嗎?你離開時電視在播甚麼?」
「不知道,我不看電視。呀,當時在播歌,旋律是,哼~哼哼~啦啦啦~」
「是『歡喜冤家』的片尾曲,那麼案發時間是八時半至九時。」
「我也喜歡這套劇,很好笑。」大衛說罷被傑利兇巴巴的瞪了,他只好把嘴唇的拉鏈拉上。
「法醫說你有被性侵過,但陰道內沒有精液,不知是因為體外射精,還是兇手性無能。」傑利往大衛一撇,只看臉的確是個帥哥,性格隨和,收入穩定,卻沒有女朋友,可能真的有性功能障礙。「你說看到兇手離開時的背影,中等身材,短髮,穿西裝。在這個城市,一塊招牌掉下去能砸死一打這樣的人,你是如何斷定一定是他?」
珍妮撅嘴,雙手抱胸,「我也不知道。」
「你他媽的在耍我對不?」傑利手掩半臉,指頭搓揉額心,「你是我見過最難纏的傢伙。」他看到大衛在偷笑,「不要洋洋得意,我不是說在你。」
「對不起,明明是我死了,我卻幫不上忙。」珍妮說。她的身體輪廓變得模糊,她快要消失了。
「不要氣餒。在你面前的是全世界唯一貨真價實的靈媒,是萬中無一被神選中的人,我的通靈能力就是要幫你們這些枉死的亡魂沉冤得雪。說我是現代版摩西也不為過,從未有案件是我破不了的。」
大衛低頭看錶,「時間到了,警察先生。」這句話聽到傑利耳中是:『你輸了,稅金小偷。』
傑利嘆了口氣,收拾物品,去撿地上的原子筆。審訊室的門打開,警察說大衛可以走了。
「等一下。」傑利突然抓住大衛的左手,把他的衣袖拉開,手腕有一個明顯的紅印。
「捉到你的馬腳了。」傑利胸有成竹的一笑。
「你誤會了,這可不是死者還擊時弄到的傷啊。」大衛展示戴錶的右手,「那是因為長期戴錶做成的,偶爾換手戴錶轉換心情也不錯吧。」
圍觀的警員們笑成一團,天才幹探傑利急中生亂啦!
傑利保持他自信的笑容,指著大衛的右手,「真正有鬼的是這隻手,你敢把錶脫下來嗎?」
「合法扣留時間已過,我沒必要跟你合作。」正當大衛想把手放下,傑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抓住他的右手並把錶脫下來。他的手腕上有一顆難看的膿瘡。
傑利單手翻開文件夾,取出珍妮屍身的照片,她的背部長了數顆膿瘡,拼到大衛手上一看,幾乎一模一樣。
「根據法醫報告,這些膿瘡是被案發地點的螞蟻咬到所致的,而且是屬於澳大利亞大蟻,並不是本地的蟻種,估計是遭人棄養。好好先生要如何解釋這種傷呢?」
大衛沉默不說話,但閃縮的眼神已出賣了他。
傑利搭著他的肩膀,在他耳邊虛音道:「甚麼也不要說,把事情和盆托出一點也不符合變態殺人犯的作風。」
警員把大衛帶去作身體撿查了,不久就會有結果。傑利走出警署,今夜是明月高掛的晚上。
「這樣算是抓到他了嗎?」珍妮試探的說。
「是的。」傑利說,「沉冤得雪的心情如何?」
「身體輕飄飄的,有種放下心頭大石的感覺。」珍妮笑說,「我安心前往那邊的世界了。」
「祝你在天堂和地獄都找到幸福。」傑利揮手道。
珍妮留下陽光般的笑容消失於夜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