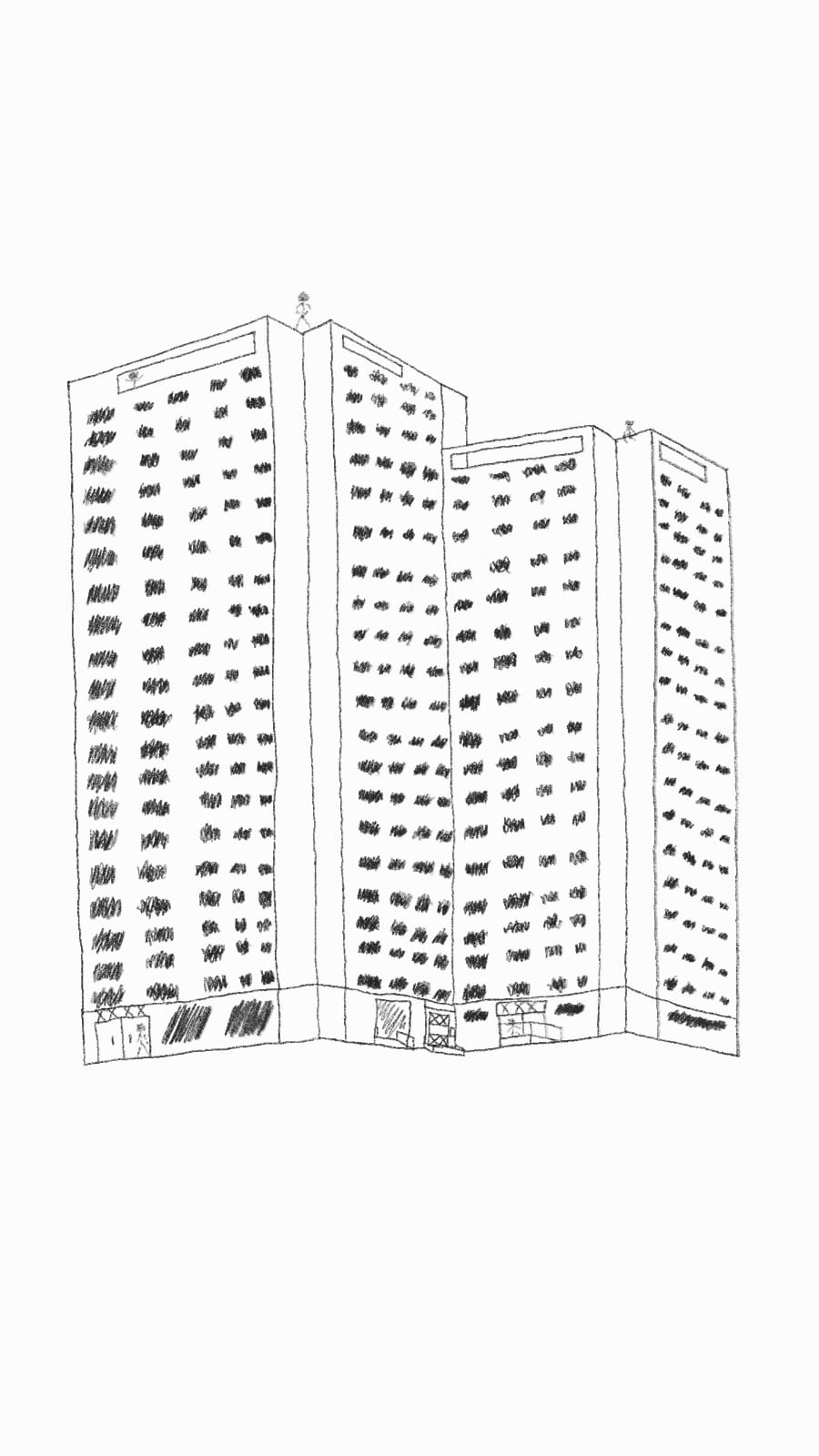他看着熟睡的妻,稍稍猶豫一下,把手指放到她額頭的位置,輕輕點了三下。只見妻的額上浮現出一個長方形,它的黑邊慢慢加深,位置也逐漸下陷,然後那長方形就像道門般向內打開。妻的額上出現了一個長方形的窟窿,她依舊睡着很沉,只剩沉穩的呼吸聲,整個人沒有任何動靜,就像入定的老僧一樣。那窟窿內是無邊的黑暗,沒有血肉沒有細胞沒有器官,就像有條隧道硬生生的把額頭和整個身體切割開來。
那黑暗裏傳出「踏踏」的腳步聲,每步都會伴着輕微的水聲,就像一個人在黑暗的水渠中涉水從很遠的地方走過來一樣。那腳步聲愈來愈近,而且聲音也愈發厚實,就像已經穿過水流踏上地面一樣,腳步聲也逐漸加快,到後來很容易就聽得出是在奔跑。
奶白色的小手扶着長方形邊沿,在黑暗中走出一個小人兒。那小人兒有着人的形狀,就像麵粉揉成的人形公仔,以簡單的線條構成無任何細節的身體手腳,面上沒有五官,身上奶白色的薄膜發着微光。
它雙手扶着長方形的邊沿坐下,雙腳前後搖擺,左手不停輕拍着妻的額頭。
「還是沒法避過﹖」他急切的問道。
「還是沒無避過。」小人兒搖搖頭,聲音從它的身體內傳出來,那是一把女人的聲音。
「甚麼地方出了錯﹖」
「我打不開那窗子。不論我用力捶打,甚至把整個袋子撞過去也沒有用,然後那事情就發生了。」
「不要灰心吧,這樣我們又剔除多個可能性了。總有一天我們能想到辦法阻止那件事的發生,」他咬着唇猶豫了一下,「我知道這樣會很痛苦,但或許我們中間遺漏了某些重要的細節,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夢再說一次嗎﹖」
小人兒沒有回答,一動不動的像是陷入一場漫長的睡眠,良久後才開始說話。那聲音緩慢而帶着距離,就像老奶奶坐在床邊跟孩子說着那遠古的故事一樣。
「每次我睜開雙眼,我就發現自己又再坐在那小巴上,身上扣着那無法解開的安全帶。那夜下着大雨,雨不停地打在車窗,雷聲大得就像天空快要被閃電炸得裂開一樣。身邊乘客的樣貌像加了特效的照片般扭曲,不論我怎樣大聲叫喊他們都聽不見。車子急促地前進着,無論水撥動得有多快,我都無法看清前面的路。小巴每次都走着同樣的路,司機會在一分鐘後會向左急轉,每次都分秒不差,然後就會遇到那件事。」
「所以現在打破窗子是行不通的,我們得再想想辦法,」他用手指敲打着頭腦,仿佛要在裏面撈出甚麼東西似的,「既然是夢,就一定會有逃脫的方法。」
「兩年來差不多甚麼方法都用過,我已經厭倦了這套不停播放的電影,不如就把那玻璃碎片在手上一割,只要我死了,這樣一切就會完結。不論是你的痛苦或是我的痛苦。」
「遇到困難輕易放棄,這可不是你的性格,」他強自擠出笑容,「相信我,我們一定可以想到辦法的。」
「我已經相信了太多次,你根本就不明白。你能想像貨櫃車把小巴整個撞成兩半的情況嗎﹖你能想像玻璃碎片插遍你身上的每個地方的痛苦嘛﹖你根本就不明白。」
「我或許不明白,但我卻知道你為甚麼會看不到其他人的樣貌。那是因為他們都已經死了,所以你才會是那小巴上唯一有意識的人。只要我們想辦法脫離這個夢,你才會有機會醒過來。」
他說得太激動,聲音太大惹來護士們的側目。這兩年來他每天都會來探望因車禍而變成植物人的妻子,跟那看不見的小人兒討論如何逃離那可怕的夢境。其實就連他也不知道究竟那小人兒真的是她妻子的靈魂或只是他所創造出來的幻覺。護士對他的態度也由起初的同情轉至厭惡再轉至憐憫,如果他沒有做出太過份的事,她們對他奇怪的行為都只會睜一眼閉一眼。
「你看看大家現在都把我當成是神經病。我也曾經有懷疑過你是否真的存在,但我選擇相信,我不怕失去我的工作,我不怕每星期讓心理醫生笑話我的小人兒故事,我只怕你會永遠離開我。」
「請你離開。」護士站到他身前,冷冷地說出這句話:「陳先生,我相信現在你的狀態並不太適合繼續探病。所以我以護士長的身份請你馬上離開。」
小人兒靜默良久,在他被趕離病房時沉靜的對他說:「這兩年來辛苦了,我愛你。」
他想不到這句會是小人兒說的最後一句說話。翌日他就接到電話,說他妻子出現了意外的狀況。他趕到醫院後,卻看到她妻子對她眨眨眼,眼裏盡是笑意。
她事後憶述當晚坐在車上,手裏拿着前一日收起的玻璃碎片,想着自己所帶來的痛苦,慢慢把玻璃碎片放到脈門。她靜靜看着窗外的黑暗,像是想到甚麼,咬咬牙就把玻璃碎片割下去。
她忍着玻璃刺進掌心的痛,用盡全力把身上的安全帶割開,然後趕在意外前跑到駕駛座,用力踏下剎車掣。她受不住衝力整個人撞到方向盤上,之後就看到一片白,醫院天花的白。
「那時候為甚麼你會改變主意﹖」
「『上吊前先在繩子剪一個小口子,那麼當你快要窒息的時候,你就會整個跌在地上。如果之後你仍沒有改變主意,那樣你才有自殺的資格。』這句話不知為甚麼就從這窗外的黑暗跳進我的腦子裏,」她頓了頓然後微微一笑,「然後我突然想起意外發生時自己並沒有繫上安全帶。」
「那條安全帶只是夢的想像,並不是當時的環境,所以⋯⋯」
「所以那是我唯一能改變的東西。」
「幸虧你沒有想不通,當天我聽到小人兒這樣說,真的擔心以後都再見不到你。」
「其實除了最後一個夢之外,我完全記不起這兩年來發生過的事。其實小人兒是甚麼﹖它又是甚麼模樣的﹖」
他沒有說話,只是笑着在她額頭輕輕點了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