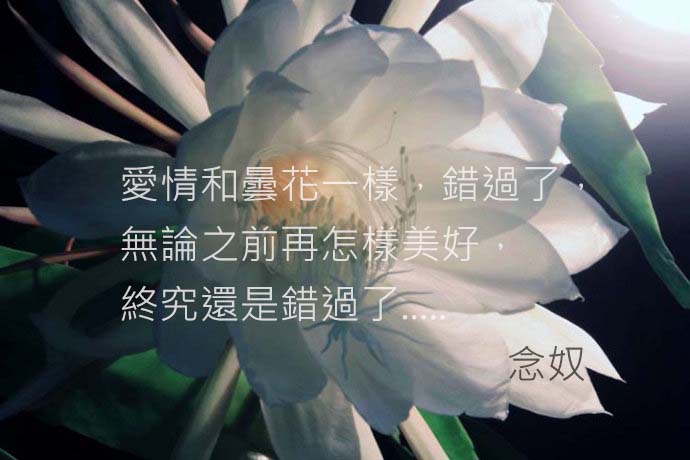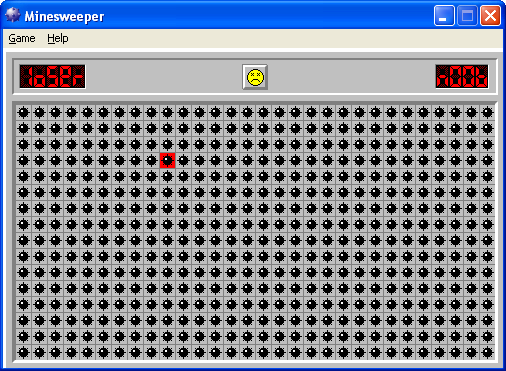《釋雨》
滴瀝。
碧玉般的湖水本應是安靜的,除非它被不安靜的雨水打擾。
滴瀝。
這場春雨下得不大,水珠亦細如銀針。細針刺出來的漣漪,也算平靜,只是平靜之中,卻有隱藏不了的忐忑。
滴瀝。
「小姐,下雨就別出去吧。」
說話的丫頭穿得很樸素,僅有一點粉紫較為鮮艷,其他都是沒有生機的顏色,臉上的稚氣尚未抹掉。
傘子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少,但這個丫頭半身已濕,因為那「小姐」似乎想在呆在雨點的紛擾中,不願步入酒家。
她完全沒注意到丫頭的半邊身體已溜出傘子。她痴痴望着湖面,望着雨絲,像有甚麼風流才子走在湖上,一手搖着扇,眼睛念起詩來比嘴巴念的更傳神、更情深。
女人心確是海底針,明明天下間所有人都只有一個腦子,女人的卻複雜百倍。她深邃的兩眸實在令人捉不透她的想法。
「小姐,我們還是進去好嗎?」
「進去有甚麼好?紅梅,你看看這雨,不是很美嘛?」
真正懂女人的男人實在不多,但女人之間亦不一定互相明白,尤其紅梅這種年輕的少女。一串串的珠兒又有甚麼美?下雨就是麻煩,身子會濕,不管下得大還是小,雨點總教人有些鬱悶。
「小姐,快看,那邊有個和尚。」
出家人果然與別不同,沿着湖畔一路走來,都沒有打傘,可是他的衣衫並無沾水。聽說內功雄渾深厚的人,皆有無形罡勁護身,看來此和尚是個高手。
「大師,你不怕下雨嗎?」
當然尋常女流是看不出來的。
「喔,施主過慮了,雨水不過是上蒼所賜,能潤萬物,驅熱生涼,怎有可怕之處?」
「雨水之所以可怕,是因為它的一種神奇的力量。」
「貧僧願聞其詳。」
女子的眉頭鎖起來,眼神變得更憂鬱,就似有無數難以啟齒的字句,馬上要一口道盡,但偏偏未想到如何才會說得清楚,說得妥當。
「貧僧大智未開,施主要是怕貧僧不明白,不說也罷了。」
「不,大師智慧過人,一定明白的。它輕如鴻毛,卻常常壓住人心,一下雨,心裡就不怎麼愉快,至少不會比放晴時的好。」
人云萬物有靈,花草樹木抑或天象都會影響着人。不過天下間最容易被影響的,大抵只有兩種人:文人和女人。文人善賦詩詞者,對風吹草動非常留意,秋風一起正是傷人的悲風,白雪飄落即是心底的淒冷,馬兒的徘徊總是萬分的不捨。女人不愛賦詩,卻比文人敏感千倍。文人將一切化作筆墨,宣泄在白紙之上,女人則流露在眉目、表情、動靜、甚至刻在心坎。文人的怨詩,讀過也罷,然而女人發自內在的各種失落悵惘,抹不了,揮不掉。
和尚驀然笑道:「雨珠兒又非千斤石,怎有此能耐?物我本為一,能壓着施主心頭的,似乎是施主自己。」
滴瀝。
「也許⋯大師說得對。」
「施主若困於往事,爲前塵所囚,還是盡早釋懷吧,執念乃是孽障,形神俱損,那又何苦呢?」
貪、嗔、痴都不是好東西,不過世人難以撇下。能夠封鎖着人的事物根本不曾存在,繫鈴的只是自己,可以解鈴的也該是自己。他已無用再說下去了,乾脆合十辭別。
「阿彌陀佛。貧僧這就回玉雲寺了,望施主珍重。」
滴瀝。
「大師⋯你願不願聽奴家心裡的孽障?」
「貧僧樂意恭聽。」
那種莫測的憂愁又湧上了女子的心頭,她的聲音彷彿都在顫抖。
「每一年奴家都盼着這場春雨,因為這些年來我都等着一個人。」
「然而這個人沒跟施主相見,這個人應該就是施主的情郎。」
「都給大師猜中了⋯⋯」
「我佛慈悲。如此多的痴男怨女,就是放不下執念。貧僧想施主的心裡其實很明白,那個人是不會回來的。」
「我知道⋯我知道⋯⋯」
滴瀝。
「貧僧還是要回玉雲寺了,有緣再遇。阿彌陀佛。」
「大師⋯奴家仍有迷惑。」
「甚麼迷惑?」
「奴家漂亮嗎?」
這句話來得太突然,和尚也不禁一呆,剎那不知所措。雖說如此,女子心中亦早有答案,出家人從來不會說別人醜陋,況且女人真是個美人。她不算年輕,從風霜刮過的五官看來,她應有三十來歳,絕對沒有行年二十的少女的朝氣活力,但比她們更吸引。這種感覺是少女沒有的,她多了一份冷,更有歷經滄桑的成熟。
和尚遲遲未答,就連看都不看,側首向着這女子。出家人四大皆空,六根清淨,莫非會羞於望着一個美女?
「大師,是不是我太難看,太蒼老了?」
「施主你誤會了,貧僧雙目已眇,眼睛早就看不見了。施主歲歳等着愛郎,難得這般情深情長,又怎會難看呢?貧僧肯定施主是個美人。」
「那他為甚麼不回來見我,他怎麼不願見我?」
「念佛之人不打誑語,貧僧實在不知其因。施主可否留下姓名,貧僧倘若有緣碰見了他,便好告訴他有這樣的一位女子等着他。」
「奴家叫紅梅。」
「他呢?」
「他⋯是個江湖人⋯⋯」
「江湖人?貧僧也認識不少。」
「他的雙劍從不離身,劍在人在⋯不過罷了,大師既看不見,又怎能認出他呢?或許他的劍早就丟了⋯⋯」
不再有滴瀝的聲音,萬里長空偷泣得累了。這無語的瞬間,亦不再有雨聲點綴,所以時間好像變得長了、難熬了。
「雨終於停了,貧僧真的該走了。施主,明年就不必等這場春雨了,能否相遇終究是緣份而已,莫能強求。阿彌陀佛。」
出家人皆比凡夫俗子活得逍遙,每步都輕盈,自然走得快。和尚的身影,淹沒於人群之中。
「小姐,你怎麼這麼調皮,竟然冒充紅梅?」
女子撫着她的頭,卻不打算解答小姑娘天真的問題。
「那和尚口中的寺廟叫玉雲寺,小姐的名字跟那座寺一樣呀!哈哈⋯⋯」
丫頭就笑了,女子都笑了。雨後的晴天,總讓人愉快些。
滴瀝。
原來春雨的聲音,就是淚水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