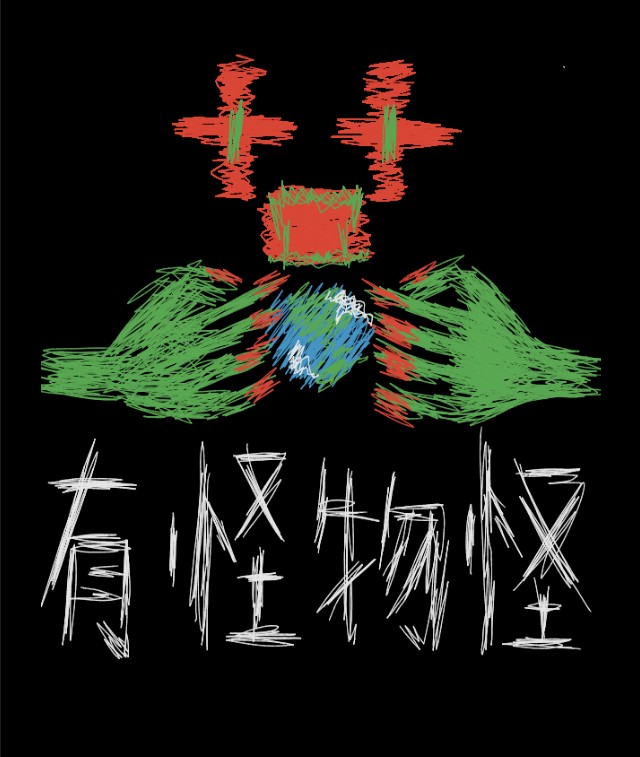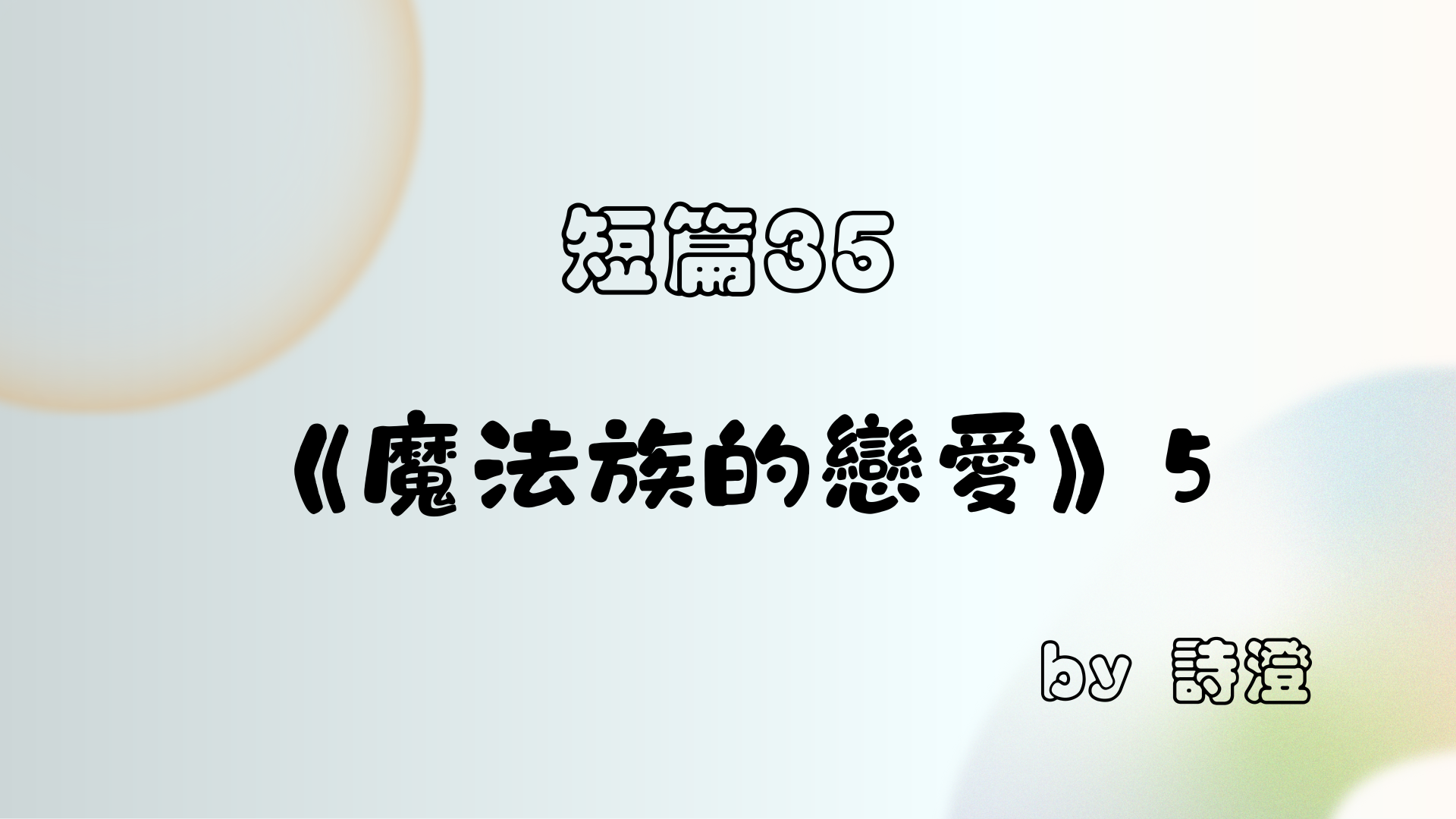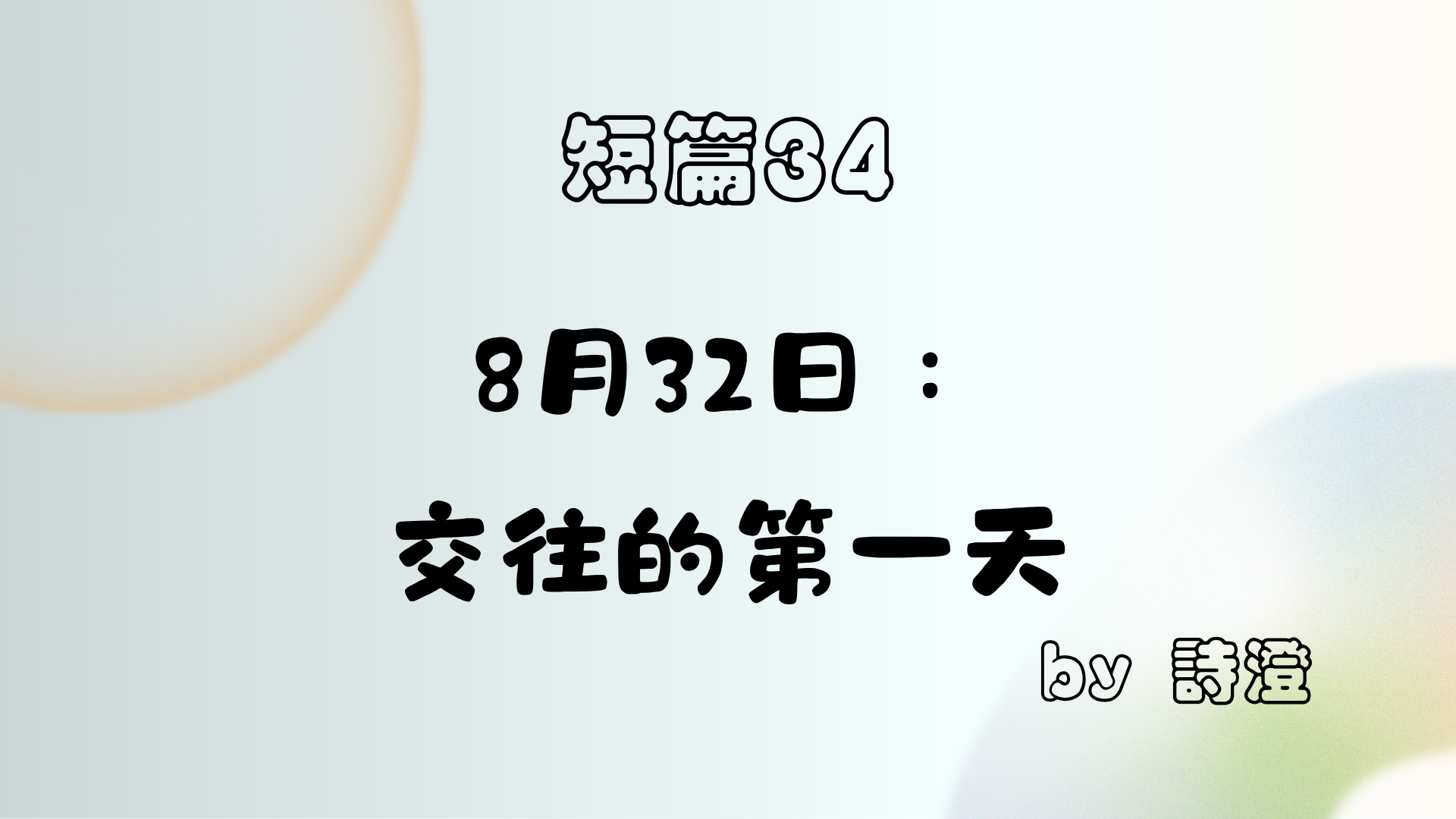江逸梅按著宋星寒的手,貼在臉頰上,閉上眼晴,淚卻流得更兇了。
「逸梅----」宋星寒的手在抖顫。
----彷彷彿彿間,眼前的愁容竟變成雲羽衣的淚眼,耳邊也響了雲羽衣的哀哭,宋星寒全身都輕顫起來。
「我明白,也沒敢多想。」江逸梅把宋星寒的手放下:「讓我們把
這一切都忘記吧!」
「對不起!」宋星寒根本不敢再直視逸梅,只好低下頭。
江逸梅輕輕說:「請你好好保重。」然後勉強站起來,一步一步走出去。
宋星寒呆呆地看著她的背影漸漸消失,心裡像灌滿了鉛。
過了不久,江逸梅解散了醉艷梅,更接了南洋的班約。人們都驚詫極,完全不明白她為什麼要拋下這裡如日方中的事業而遠走不毛之地。
旁人不為意,連雲羽衣也不察覺,宋星寒卻知道身體的一部份已隨著江逸梅翩然遠去……
然後,楊競筠出現了。
楊競筠是編劇界的奇葩。他年紀很輕,但文學根底及音樂造詣極深厚,對人對事,都有自己獨特的體會和見解。他所編的劇本,往往推陳出新,在傳統的基礎上注入新的元素,精練出一齣又一齣的杰作----雲羽衣對他尤其敬服。
這時候,雲羽衣開始淡出影圈。她一口氣把片約都推掉,說這些電影都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一部等如一百部,沒半點意思,她不想無止境地重覆自己,不想以賺錢作為唯一的生活目標,她要追求理想,在藝海中求進步----她的心願,是成為正印花旦。
其實,她現在的技藝比某些正印還要優勝,卻因為她擅演的,都是一些刁蠻潑辣的花衫角色,與傳統粵劇裡正印花旦賢淑柔順的形像格格不入----她的刁蠻小姐演繹得越傳神越生動,觀眾便越不能接受她的「改邪歸正」。
雲羽衣不單為自己的前途奮鬥,更矢志要改良粵劇,去蕪除菁,使粵劇成為殿堂級的藝術。難得楊競筠和她志同道合,他倆常常聚在一起研討,十分投緣。
雲羽衣的努力上進,宋星寒當然是百份百支持和鼓勵,她和楊競筠的雄心壯志更使宋星寒敬服,宋星寒清楚知道,粵劇的將來都在他們手上。
看著兩位年青人孜孜不倦,宋星寒便暗自慚愧----在她,粵劇是謀生的方法,甚至,談不上理想。雖然宋星寒也一直鍛鍊技藝兒,但只為了在藝壇立足;尋求的,都只是個人的進步以及觀眾的認同,什麼改良粵劇、教導觀眾,根本超出了她的認知範圍。
為了讓雲羽衣達成心願,最直接的方法,便是組織自己的戲班。於是,「雲映月」劇團成立了。
楊競筠的劇本,他們都戲謔為「女人戲」,因為那些劇本的主題,大多環繞中國古典的女性,如何在封建社會裡,對愛情的執著,對善與美的追求。在他筆下,女主角全是美麗善良聰明堅貞。字裡行間,都是濃得化不開的憐惜和珍愛;而男主角,卻是怯懦愚孝的文弱書生,唯一可取的,應算是對女主角不離不棄的痴情。
雲羽衣決意革除舊式戲班的陋習,嚴格規定各人必須參與綵排,按足劇本演出,杜絕所有臨場即興表演。服飾道具燈光音響,完全不惜工本,致力盡善盡美。
第一次開鑼,成績不算很好,平均只有七成觀眾入座,但報章雜誌給予雲映月極高的評價,說這是新派粵劇,還說是粵劇史上的大躍進、里程碑。
雲映月每屆演出,只做一個劇目,演期也只有一個月。由於楊競筠編劇需時,宋星寒他們也需要時間排戲,所以每次也要相隔差不多大半年才開鑼,在當時來說,算是極小產量的戲班。
漸漸,觀眾開始認同他們的努力,也接受了雲羽衣的「擔正」,票房越來越好,由第三屆開始,已是場場絕早爆滿。雲羽衣和楊競筠得到鼓勵,更是把全副心神都放到雲映月去。
時代在變,觀眾的口味也一直在變,粵劇電影,也無可避免地由最高峰慢慢走下坡。但觀眾對宋星寒仍是偏愛,在影圈吹著淡風的當兒,她的電影總還可以讓觀眾掏錢買票進場。
在雲映月休班的時候,宋星寒便努力拍電影還債。還的,都是片債和人情債,想來只要再還上兩、三年,她也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這一天,楊競筠的太太葉雅清約宋星寒喝下午茶。
葉雅清從手袋裡取出一疊信件,放在檯面。
宋星寒瞥見信封上寫著「楊競筠賢兄親啟」幾個娟秀的字,馬上便認出是雲羽衣的手筆。
「星姐,你看看這些便明白了。」
「這些是私人信件吧?」宋星寒皺眉:「我們怎麼可以私自拆閱?」
「星姐,你是君子,我是小人,一個小女人而已,現在人家都明目張膽下功夫了,我還要講究那見鬼的風度和教養麼?」她冷森森地說。
「你不肯看,可要我唸給你聽?這一封是『金風玉露一相逢,已勝卻人間無數』,那一封是『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還有這封,『山無陵,天地合,才敢與君絕』……」
宋星寒搶著說:「你別誤會,這不過是以詩詞入曲,研究劇裡曲詞罷了。」
「對,他倆一直借研究粵劇為名,旁若無人地廝混。」
「競筠和羽衣之間絕無曖昧,他倆不過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就像伯牙和子期一樣惺惺相惜而已。」
「何止志同道合?簡直就是情投意合了!」葉雅清抿抿嘴:「現在整個演藝界都傳得鬧哄哄了,就你一個糊塗?你是純,還是蠢?是裝聾扮啞,還是忍辱負重?」
宋星寒一怔:「你不要聽別人說是說非,你是競筠身畔人,總要相信他支持他。」
「就是因為我是身畔人,才什麼也瞞不過我----他心裡另有人,我怎會不知道?」
「這些日子以來,他一直在外頭跑,就是回來了,也只躲在書房裡,整天心神彷彿,兩天跟我說不上三句話。」
「我自問也算是個好妻子,家裡內外的事從不叫他費心,他愛靜,需要空間,我都由他,但他在我跟前想著別人,我是再也忍受不了! 」
「你以為我是沒事找事?你可知道我咬著牙關忍耐了多少個晚上?你可明白兩個人同床異夢是一件多悲哀的事情?我實在是撐不下去了,才厚著臉皮來找你。」
-待續-
( 個人作品集 – www.方愚.com )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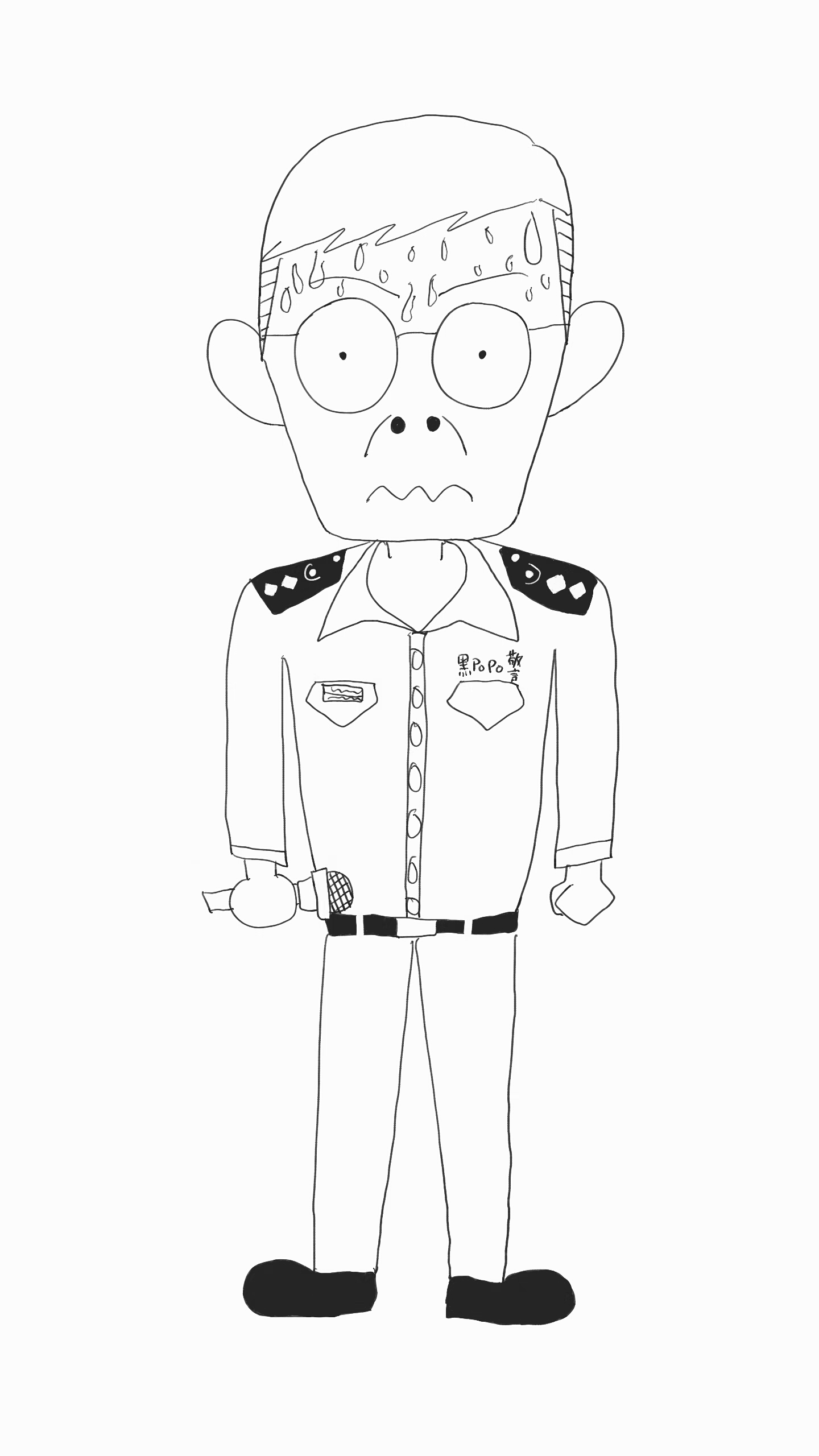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