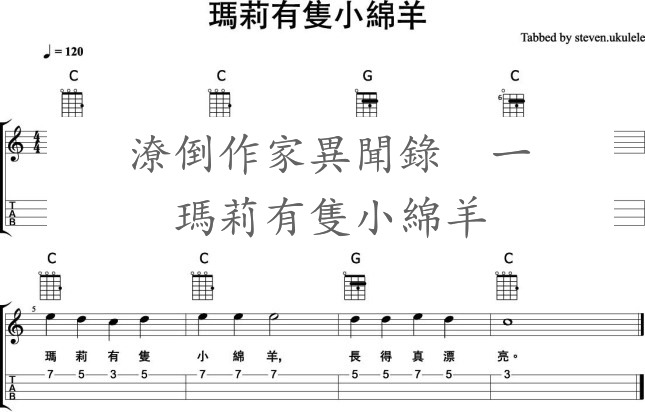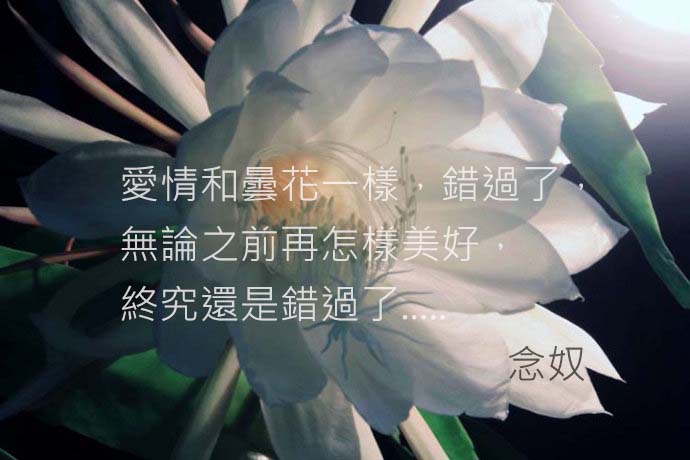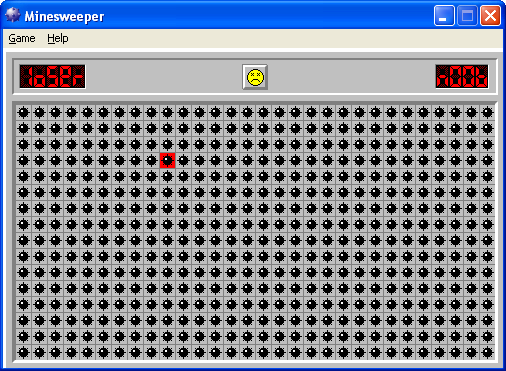在那天晚上,你曾說過,你害怕孤獨。
而我不會再次讓你孤單一人。
自從這場災難爆發開始已經過了一百零八天,總感覺不太真實。某一天,街上開始出現大量駭人的怪物,它們長着人形, 可身體卻是腐爛的,血淋淋的器官全數外露,還發出令人無法忍受的惡臭。了無生氣的眼球,恍似搖搖欲墜的,只剩下眼白和食欲的渴求,它們張着血盆大口,無情地撕咬著人類。是怪物,是沒有思想感情的怪物。
那一天早上,我被奇怪的噪音弄醒,不過我如常地打開電視,收看早上的新聞報道。可奇怪的是,電視上只顯示着緊急情況四個大字,文字鮮紅得令人感到不安。記者報道説,現在美國全國各地正遭受喪屍襲擊,懷疑與新型病毒——「W病毒」變種有關。消息指喪屍擁有強大的再生能力,一部份甚至擁有智能,而感染途徑是經由血液傳播,發病時間約為十五到三十分鐘,症狀包括頭痛、嘔心、神志不清等。軍方已經全面接手並展開救援行動,呼籲市民保持冷靜,並留在安全地方等待救護。
電視像錄音機般重複地播放着相同的內容,我還以為這是什麼大型整人節目。但待我從睡眼惺忪的狀態清醒過來後,我發現事情遠比我想像中的更為嚴重。打開窗戶,往街外望去,只能以混亂不堪來形容,汽車胡亂地鳴笛,人們爭先恐後地逃走,尖叫聲大得震耳欲聾。但最可怕的是,路上屍橫遍野,一大堆人形怪物正襲擊着途人。我不自覺地呆坐地上,久久未能平復心情。
我前往洗手間,用冷水迫使自己清醒過來,並立刻通知還在安睡的父親。父親與母親在我小時候就已經離婚了,他看起來吊兒郎當的,非常不可靠,平時最愛的就是捉弄我和講冷笑話。若我說他以前的職業是一位冒險家,你能相信嗎?但現在我與他相依為命,住在一間小小的公寓裏,也不知道為何當初會選擇跟他一起生活。唉,我開始有點明白母親的感受了。話說回來,遭遇這種情況,也還能安睡的,這世上也只有一人了。
在這之後,我清點了家中的食物儲備,看上去還能堅持一陣子。父親得知街外的情況後,竟然與平時的反應差距不大,還是一臉懶散,正好與我的焦急形成強烈的對比,總感覺我才是在杞人憂天。
但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情況卻是越來越糟糕。食物正一點點地消耗殆盡,但官方的救援卻遲遲未有消息。我們只好鋌而走險,嘗試各種籌措物資的方法。但把附近的物資搜刮乾淨後,也只夠我們多生存一個月左右,我們不得不想法子撤離這座大廈了。
我們把必需品收拾好,計劃明天一大早逃出大廈,駕車離開,尋找新的據點。
清晨五點,我們躡手躡腳地離開家門,盡量不發出丁點兒的聲音。根據以往的經驗,「它們」對聲音極度敏感,相反視力卻不太好,而且他們通常會在夜間活動,清晨可謂最佳的行動時間。父親站在我的面前打頭陣,仔細檢查每一層的情況,避免遭受前後夾擊,我們就這樣緩慢地前進。
地板上佈滿著屍體丶垃圾,血漿黏呼呼的感覺隔着鞋底傳達到神經,四處散發着腐爛的腥臭味,當中亦夾雜著濃得刺鼻的血腥味,我必須要聚精會神,才不至於吐出來。雖然已經見怪不怪了,但其噁心的程度依然。
就這樣,我們距離停車場只剩四層,當我以為我們可以就這樣順利地抵達時,情況卻突然急轉直下。
一隻喪屍躲在門的死角,當父親一打開門,喪屍應聲彈出,父親在千鈞一髮下,一腳把它踢開。可這一舉動,立馬吸引了附近的喪屍。我們只好硬着頭皮,加快腳步到下一層。但步入眼簾的是成千上萬即將湧入的喪屍,父親當機立斷,拚死把門堵住,我們才暫且逃過一劫。
但情況依然非常危急,老舊的防火門正一點點地裂開,樓上亦傳來了急速的腳步聲,父親用盡全身的肌肉支撐着門。
「兒子,這車鑰匙和指南針就交給你了。那枚指南針是我以前冒險時最珍貴的護身符,給我好好保管啊!我終有一日會回來拿的。」父親留下一個捉弄人般的微笑,以溫暖的目光向我道別,那是他開的最後一個玩笑話了。說罷,他便轉身撲向數不清的喪屍群裏。
我望著父親的背影,悲痛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我多想投身於幻想之中,逃避一切。可我迫使自己回到現實,使雙腿像機械般運作,不願去思考,不願再次回頭看,即使心臟像是要炸裂,筋腱像是要斷開,我依舊狂奔着。因為我知道,一旦停下來了,我便再也無法前進了。
一層丶兩層丶三層,我毫無知覺地踏着樓梯,撞開了閃着暗沉綠光的逃生門。接著我奔向車位,跳上軍綠色的吉普,然後催下油門,不顧一切地往前駛去,彷彿這是我的使命似的。
往前駛去,曾經的風景已物事人非。不知過了多久,我才在路邊的草叢處停下。
我手中依舊緊緊握住那堅硬無比的指南針,那是一個銀白色的丶有著獅子雕刻的精美指南針。我用手摸了摸,鼻子短促地呼吸著,全身癱軟無力地臥倒在方向盤上,我的心如缺了一角般,永遠都拼湊不起來了。
把指南針掀起,裏面夾住一張泛黃的照片,是一位男人與嬰兒的合照,外殼內側用小刀刻著一個日期,那是我的生日。照片裏的男人笑得非常燦爛,以溫暖的目光望向嬰兒。
一瞬間,與父親的回憶像走馬燈一樣在腦海裏播放,昔日的點點滴滴不斷地略過,可在終點等待著我的,卻是父親被嘶咬得血肉模糊的身影。如果,是我打頭陣的話;如果,我再小心一點的話;如果,我們沒有打開那扇門的話;如果⋯⋯
我用盡全力避免自己哽咽,牙根卻發出咯吱聲響。盡管想把聲音和悔恨通通吞回去,但它們卻一而再地突破我的齒縫。不知為何,我的眼角忽然發燙,視線一片模糊,淚水不自覺地不斷滑落,一滴一滴地落在父親的指南針上。待回過神來,我已在抱頭痛哭,喉嚨乾涸到連一絲聲音也發不出。留下的,只有自己的喘息和那顆空洞的內心。
自從這場災難爆發開始已經過了一百零八天,總感覺不太真實。即使,我不能阻止它開始。但至少,也讓我選擇結束的方式吧。
我把指南針放在胸前的口袋,準備走向那座高樓的頂端,好好地看完最後一次的風景。
跨過那破碎的玻璃門,我走進了這棟殘破不堪的大樓。但忽然間,前面的轉角處出現了一個黑影。隨着兩三下槍聲響起,我傾倒在後,背部狠狠地撞在冰冷的地板上。一點心理準備也沒有,倒也不錯就是了。
那黑影越走越近,像是觀察什麼似的,最終站在我的兩三步前。黑影朝着我的耳邊呼喊:「喂,你沒事吧?」
我沒有失去意識,但我總感覺有顆子彈擊中了身體。我摸了摸剛才疑似中槍的位置,從胸前的口袋拿出那枚指南針。我瞇起眼仔細一看,那顆子彈剛好卡在銀白色的外殼上,不偏不倚的。
「看來,我得聽從父親的決定呢。」我躺在地上,不自覺地傻笑了出來。
「你從剛才開始就在自言自語些什麼呢?」那黑影傾着頭,好奇地問。
我緩緩地爬起身,這才發現,那個黑影是個跟我年紀相若的女孩。她長著一頭柔順華麗的金髮,正好刻劃出她身體修長的線條。水藍色的大眼與蜜桃色的薄唇,相輔相成,拼湊出一幅美麗的圖畫。她臉上掛着的俏皮笑容,更為他增添一絲稚氣。唯一不相襯的,恐怕是她身上佈滿血跡的連帽外套,還有她手上那支漆黑的手槍。
「對於一個差點殺死我的人,我大概沒什麼可以跟她說的。」我冷淡地說道。
「那是意外,意外!不好意思嘛。」她吐了吐舌頭,絲毫沒有內疚地說。
「不說這個了,我叫安娜,你呢?」安娜熱情地問道。
「約翰。」我簡短地回答。
「原來如此!我看你的樣子也是孤身一人吧,不如我們結伴同行,聽說北邊好像建立了一個幸存者的基地。就這樣說好了,我們的目的地就是那裏!」安娜滔滔不絕地對我說,並對我投向期待的目光。
「我好像還未答應你,還有為什麼我要跟你一起去呢?」我嘆了口氣,不情願地回答。
「來嘛!來嘛!不接受女生請求的男生,可是不行的哦!」安娜把身體靠過來,誘惑地説着,眼中好像還藏著一絲捉弄的神色。
她強行把我拉起來,自顧自地推着我走。我本想擺脫她的手,但直到我聽見她在後方的嘀咕後。
「因為你跟我有點相似呢。」安娜用幾乎沒有人能聽見的聲線說。不知是否我的錯覺,我總感覺那句話裏,好像包含着一絲寂寞與悲傷,我在心裏不斷地猜想著那句話的意思。
可在下一瞬間,她又回復到剛才那樂觀的樣子,或許是我多心了。
就這樣,我們踏上了前往北方的旅途。駕駛著我的吉普,前往下一個地方。
在末日下生存可是十分困難的,我們試過一直找不到換乘的汽車,也試過差點兒被喪屍襲擊,甚至試過三天三夜都找不到食物。但憑着安娜正面的心態,這些難關都一一被跨過。
但她有的時候也非常令人煩厭,總是七嘴八舌地說着話,不斷地問著我很多奇怪的問題。
「嘿,約翰!你知道這世界上是有雞先還是有蛋先嗎?」
「不知道。」
「嘿,約翰!你覺得外星人存在嗎?」
「不知道。」
「嘿,約翰!如果我被喪屍咬了一口,你會怎樣做?」安娜又丟出一道奇怪的問題。
「啊!煩死了!你的話匣子再不停下來的話,我到時候就把你丟在一旁,自己一個人前往北方的基地了。」我實在忍受不了,不耐煩地對着安娜破口大罵。
「是嗎?」安娜在我身邊輕快地跳着步,向我露出一個意味深長的笑容。
雖然有時候,她的種種行為實在令我非常煩躁,但相處下來的時間卻是挺愉快的。我們倆人一起經歷了許多大大小小的事,在她那既樂天又搞怪的性格下,我好像也變得開朗許多。或許這些小事,就是末日當中的小確幸了吧。
「找到了!是我最喜歡的甜點!」安娜的雙眼像是要發光似的,像個小女孩般興奮地對我說。
「沒這麼誇張吧,就不過只是一塊普通的餅乾而已。」我翻了下白眼,沒好氣地對安娜說。
「不!你實在不懂得這甜品的美妙之處。鬆化可口的夾心餅乾,散發着淡淡的奶油香味,在上面抹上一層甜美濃郁的鮮奶油,再加上甜而不膩的草莓糖漿,三者簡直是天作之合!我已經可以想像到它在我的味蕾上翩翩起舞的樣子了!」安娜含情脈脈地望着那包餅乾,陶醉地向我講解。
説罷,她便打開包裝,享受著她那至高無上的餅乾。
「太美味了!」安娜展露出有史以來最燦爛的笑容,像個天真無邪的少女一樣,感動得手舞足蹈。
看見她那可愛的模樣,讓我對這塊餅乾也產生了些許興趣。我打開包裝,把一塊餅乾送進口裏。
「有夠甜的。」我望向安娜,嘴角泛起淡淡的微笑。
但相處久了,在她那樂觀開朗的表面下,意外地也埋藏著悲傷丶膽怯的一面。
「今天是我父母的死忌呢。」安娜在睡前,望着劈啪的營火,安靜地吐出了這句話。
「是⋯⋯是嗎?」我感到有些意外,不知所措地問道。
「你不用這麼拘謹啦!我已經接受事實了,只是有時候,也希望有人能聽一下我説話。」安娜苦笑著對我説。
我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注視着安娜,等待着她。
「別看我這個樣子,其實我很怕孤獨的哦!」安娜故作誇張地說。
「那天發生的事,我依然歷歷在目。父母在我的面前被喪屍咬斷頸部,死狀十分悽慘。」她用平靜的語氣敘述着,但那悲傷的眼神,卻是似曾相識。
「我很害怕,害怕自己從此以後就是孤單一人,害怕自己會就這樣死去。因此,我迫使自己比以前變得更加樂觀丶堅強,只有這樣做我才可以在這殘酷的世界裏生存。」她捲縮著身體,低聲說著,話語間彷彿散發着沮喪與失落感。
「抱歉,我話好像有點太多了。」安娜露出靦腆的笑容,不好意思地說。
「以後想說的時候,我很樂意坐在旁邊聆聽的。畢竟,我們是夥伴嘛。」我低下頭,愈說愈小聲,臉頰也漸漸變得紅通通的。
「夥伴,對吧!聽說夥伴會接受自己所有無理的要求,是真的嗎?」安娜又回復到平時的樣子,露出惡作劇般的笑容。
過了一會兒,她便心滿意足地入睡了,睡的時候還說着有夥伴真好之類的話。
看著安娜幸福洋溢的睡臉,我暗自下定決心,以後再也不會讓她孤單一人了。
「因為你跟我有點相似呢。」我望向深邃的夜空,自言自語地説道。
我常常在想,這樣吵吵鬧鬧的生活還能繼續多久呢?
但我再一次,捉不住掌心中擁有的事物了。
駕車到附近的地方尋找物資,已經成為我們的每天的例行公事。在一個平平無奇的一天,我們來到了一家被遺棄了的超市搜索。
即使現在太陽還未下山,但裏頭仍是黑漆漆一片的,我們要打開手電筒才能勉強前進。沿着大門向前走,看見的四周則是髒亂無比,貨架東歪西倒的,不少食物散落一地。屍骸丶玻璃碎丶雜物多不勝數,血腥味更加是重得異常。
安娜在我的前頭走着,打算碰碰運氣,看看還有沒有未損壞的食物。
我們走到兩排擺放罐頭的貨架中間,但令人有些不安的是,愈往前走,血腥味就愈發濃烈。貨架上血跡斑斑的,我蹲下來用手摸了摸,甚至有些濕潤。
「安娜,這裏有⋯⋯」我本想開口告訴她,但卻被中途打斷了。
「小心!」安娜焦急地飛奔過來,並全力向我呼喊。
我還未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安娜用盡全力將我推開,我的頭部狠狠地撞擊地面,痛得像快要裂開般。
「安娜,發生了什麼事?」我按住頭部,痛苦地對她說。
安娜一言不發,朝着旁邊連開數槍,最後依靠着貨架坐下。
「約翰,我們有麻煩了。」安娜用手指了指正在流血的腹部,苦笑地對我說。
「你沒事吧?難道⋯⋯」我斷斷續續地說,彷彿是不想接受這個現實。
「對於一個差點就死在喪屍手下的人,我大概沒什麼可以跟他說的。」安娜俏皮地笑了笑,模仿着我的語氣説。
「都什麼時候了,你還有心情開玩笑!難道就沒有什麼辦法嗎?對了,聽說只要把受傷的位置切除,就會沒事了。不,還是得先止血。」我急躁得語無倫次,在腦內思考着各種事情。
「沒辦法啦!難道要從中間截開嗎?我可不想只剩下上半身。」安娜反而笑得更加開心。
我絕望地跪在了地上,眼中好像又浮現出父親的身影,我又再一次的無能為力。
「聽說夥伴會接受自己所有無理的要求,是真的嗎?」安娜故作好奇地問道。
我沉默不語,甚至連望向安娜也不敢。
「那麼,可以請你親手殺了我嗎?」安娜展露出她的招牌笑容,把她手上的手槍向我遞來。
聽到她那簡潔的話語,我像是受到莫大的衝擊般,驚訝得無法動彈。但比起震驚,我更加後悔自己沒有好好地保護安娜,不能保護那為我帶來唯一救贖丶我最珍貴的人。我對自己的無能感到深深的羞恥丶慚愧丶憤怒,為什麼我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別人拯救,卻不能為他們付出些什麼,我就只是個沒有用的廢物。想到這,我實在按奈不住自己的內心,我把所有的情感發洩在這句話上。
「我怎麼可能下得了手啊!」我不顧一切地吶喊着,像是方圓十里都能聽到一樣。我用手不斷地錘打著地面,即使早已流血不止,我也不願停下。
不知不覺間,拼命忍住的淚水早已突破防線,牙齒不斷地打震,嘴唇也在微微地顫抖。雙眼已經濕透,眼淚就這樣脫眶而出,不管怎樣擦,視線仍然是一片模糊,眼淚也無法止住。我就這樣撕心裂肺地哭著,我的喉嚨像被炙燒一般,內心像被千刀萬剮一樣,靈魂早已支離破碎。
「不接受女生請求的男生,可是不行的哦。」安娜用溫柔的聲線說著,淚水在她美麗的臉龐上畫過一條弧線,眼淚像珍珠般一顆顆地掉落在地上。
安娜把手槍放在我的手上,那雙纖細丶温暖的手,如今卻像失去了溫度。
在那瞬間,兩人相處的情景又再重現在眼前,每一天的對話丶態度丶天氣丶甚至味道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裏,那是我最珍惜丶最寶貴的寶物。我多想回到那段時間,再次坐在她的身旁聆聽,再次與她打打鬧鬧,再次與她愉快地聊天,我多想回到那段時間。
原來從起點到終點是如此短暫。
安娜緊緊地握住我的手,露出我這輩子看過最美麗的笑容。然後把雙唇湊到我的耳邊,像是要訴説秘密一樣。
「我喜歡你,約翰。」
說罷,她便心滿意足地扣下扳機。
在那天晚上,你曾說過,你害怕孤獨。
而我不會再次讓你孤單一人。
「我也喜歡你,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