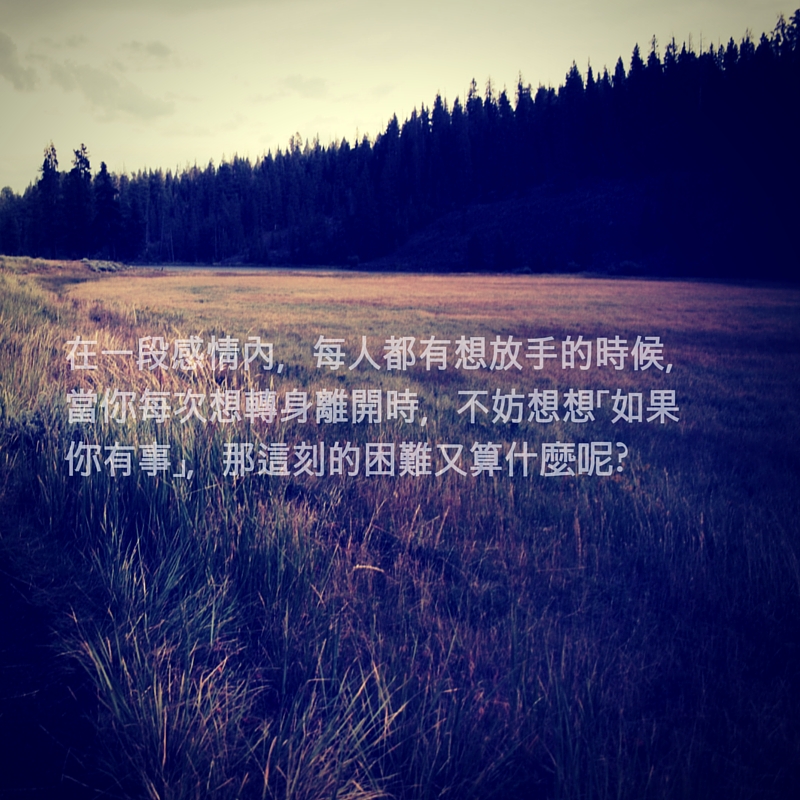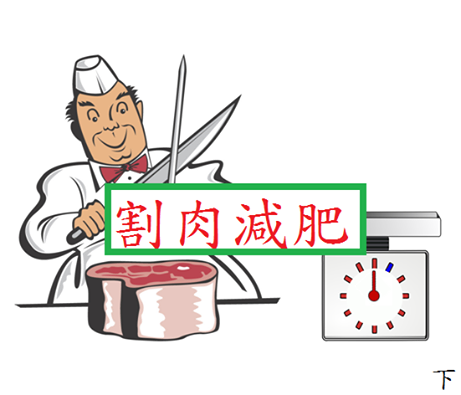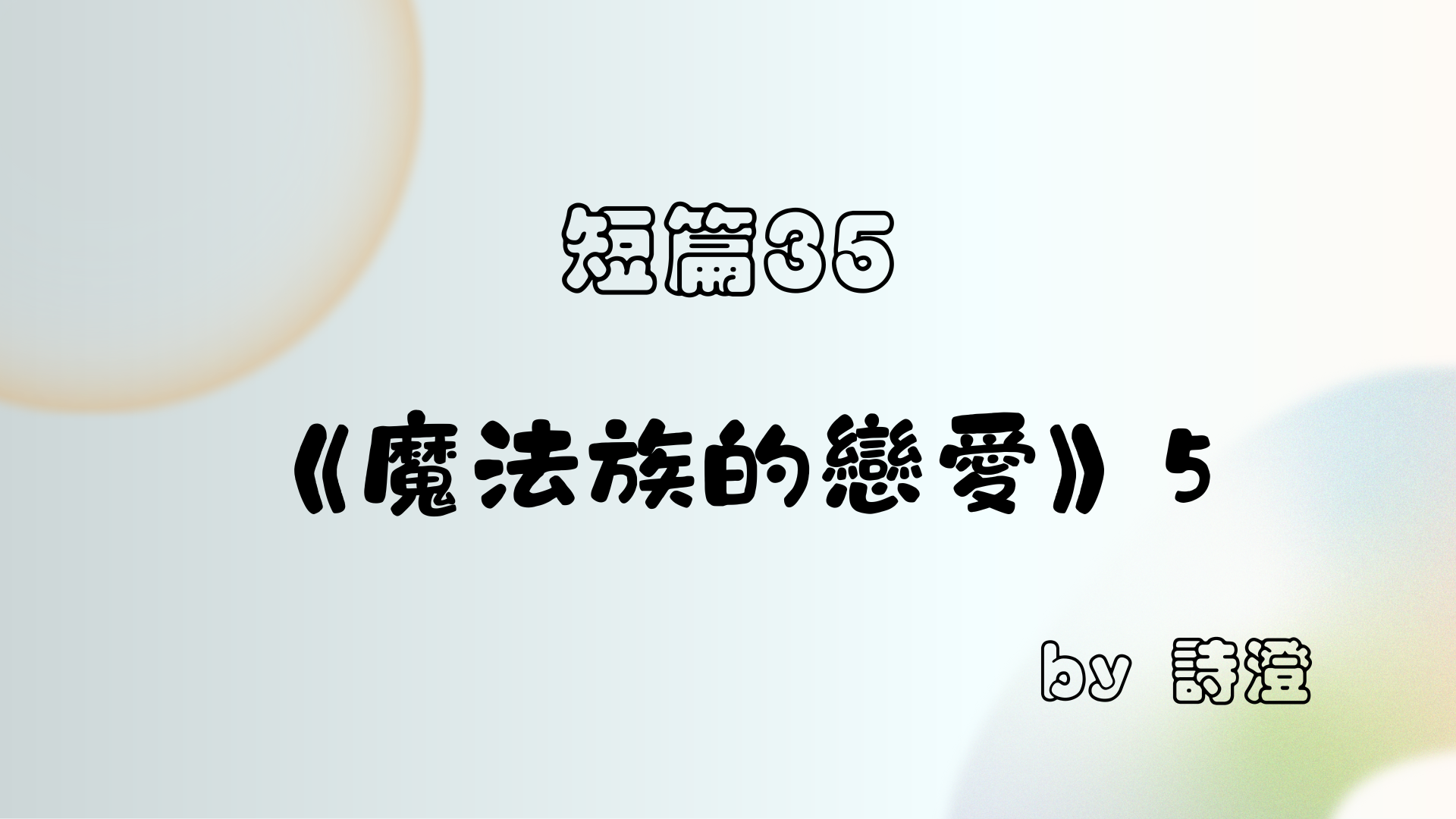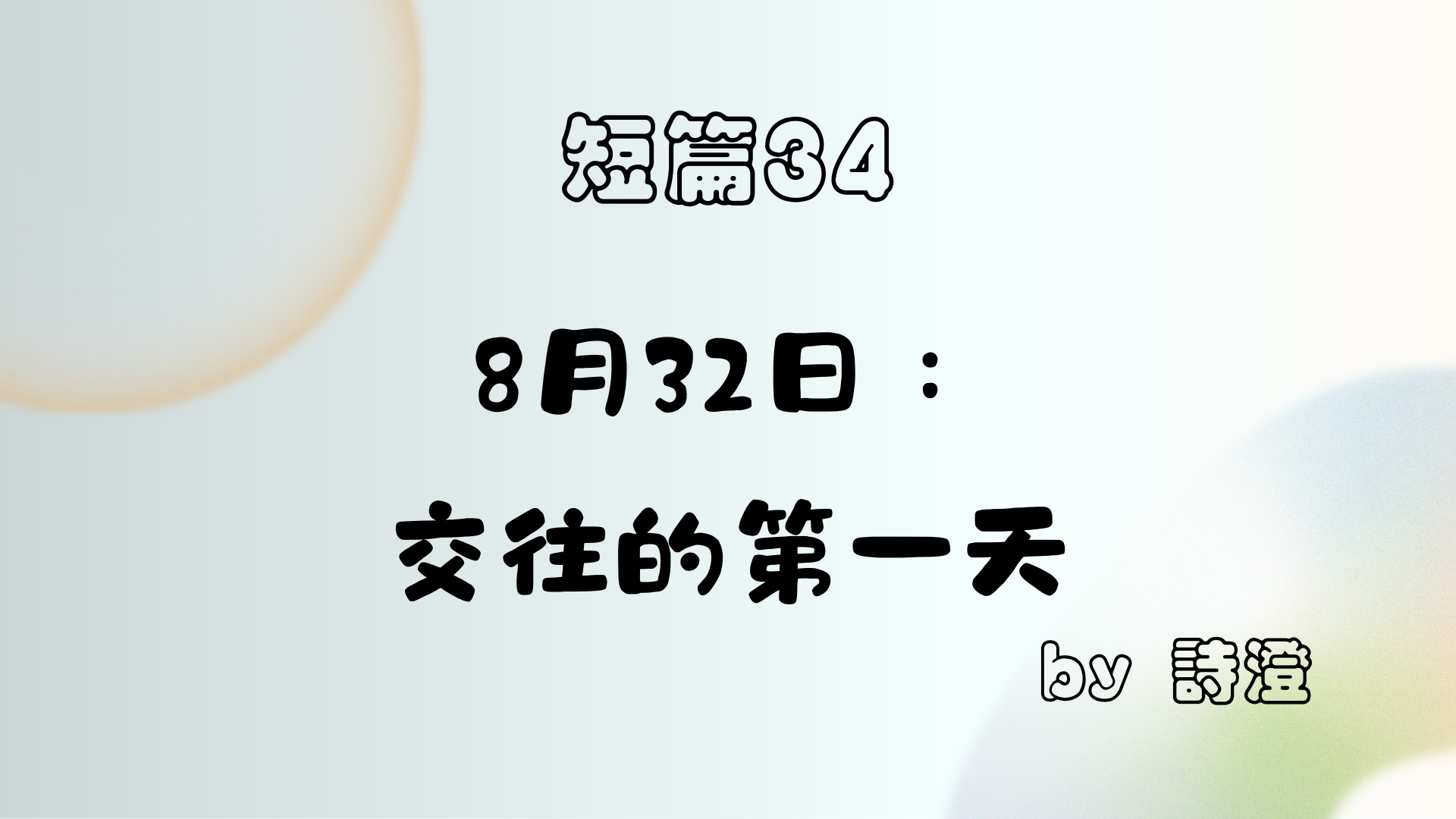我坐在沙田城門河畔的長椅上,欣賞清晨的河景。
仲夏七月,日間氣溫都在攝氏三十度以上,即使偶爾下雨或颳起巨風,炎熱的感覺還是不會消退。平凡人在這酷熱天氣下,無不大汗淋漓,可是我從來不會因為曝曬而流汗。特殊的體質,令我既方便、又不便。
坐在我旁邊的長椅的人,除了老伯伯,就是老婆婆。偶然也有些中年或青年在河邊跑步。無論是挺着肌肉還是肥肉的,無論是老、中、青、幼的,他們做運動時都總得汗流浹背。這就是健康。
我自出娘胎,鮮有感染風寒、腸胃炎等常見的病。
俗語有云:「小病是福。」我沒有「小病」,注定與「福」無緣。
「溫室公主」、「小冰女」、「病美人」等,同學替我起千般百樣的化名。可是有誰明白我接受他們取笑的笑容背後,是背負着多少生活的負擔和傷感。
我還有生存價值嗎?
我沉到黑暗的河裏。
-=-=-=-=-=-=-=-=-=-=-=-=-=-=-=-=-=-=
很多人以為我這種柔弱的女子,很容易吸引到男生的注意。的而且確有很多男生注意我,但沒有一位敢搭上我這個會隨時消失的人。
活着至今,我就是孤獨。連朋友也沒幾個的我,跟男生交往的事連提起也不想;直至他找我的那天。
我們邂逅於義工活動,那時候我才十五歲……
我就讀的中學規定每位高中生必須每年做八小時的義工服務。雖然我身患奇疾,但我除身體比較虛弱、容易疲倦外,日常生活裏與普通人沒多大差別,所以即使我申請「免役」,最終還是要貢獻社會。不過校方也非毫無人性,沒要求脆弱的我像其他同學般賣旗籌款,特別安排我到直屬小學,替小學生作義務家課輔導。但由於這是特別安排,我只能隻身赴會,沒有任何同學陪伴。
我是獨生女,同輩的親戚都比我年長,所以我沒有應付小學生的經驗。我踏入課室,看見學生們在追逐、嬉戲,即使是老師也不能喝止他們,我又怎能控制他們呢?
我們好不容易才令學生們坐好,但他們總是不能安靜。結果我只能管理他們的秩序,沒餘力指導他們的課業。在我手忙腳亂的時候,我期盼的救星突然出現。
「快點安靜地做家課,不然要你們好受!」一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喝道。學生們看見他都立刻安靜,專注於課業。可是穿着恤衫、牛仔褲和球鞋的他,外表溫文爾雅,一點也不恐怖,我真的不明白為何學生都如此聽他的命令。但他也很冷漠,他進入課室後,只有瞧我一眼,跟我點頭打招呼,然後便檢查學生們的家課,莫說自我介紹。只是他能減輕我的工作量,所以我也沒有特別討厭他。
我好不容易捱過兩小時的工作,精神和體力也幾乎耗盡。原來我所讀的小學學生是這麼頑皮,我從前完全沒有發覺,現在倒感受到老師的辛勞。學生們離開課室後,我不禁伏在桌上休息。
「這份工作不容易應付吧?」他倒了杯水給我,然後又說:「我叫阿康。」
「你好,我叫江悅,同學們都稱呼我做小悅。」
「江悅、江月,很有詩意……你是南中的學生吧?現在讀甚麼年級?」
「中四。」
「比我年輕五年呢。我現在讀大學二年級,以前也是南中的學生,我們應該見過面。」
我無言以對。畢竟說我從沒見過他似乎有失於禮,但又不想說謊。
「你有男朋友嗎?」
「沒有……」我羞怯地說。他問這個問題,究竟有甚麼用意呢?還是想表達甚麼呢?他真的是個很奇怪的人,我們才初次見面,難道就對我產生興趣嗎?雖說我並不討厭他,但我對他認識極少,總不能輕易跟他交往。可是他真的很有膽量和很厲害,至少他頃刻便能使我心跳加速、心如鹿撞……
「我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最基本的,不用太在意啊。我先走了,下週再見。」
他所說的「最基本的」是指甚麼呢?難道他已間接跟我示愛嗎?我很想知道。
-=-=-=-=-=-=-=-=-=-=-=-=-=-=-=-=-=-=
「小悅,你有心事嗎?」媽媽坐在縫衣機旁努力工作,也不忘注意我。
「沒有,只是今天被陽光曬得太久,有點精神不振。我先去休息一下。」
我對媽媽撒謊了。我整天也留在室內,何來陽光呢?可是她沒有辦法辨認真假,因為我從來沒有汗、沒有臭。但她看穿了我的心,我的確懷有心事。
我躺臥床上,舉起右手,凝視無名指上的情侶指環,耀眼的射燈光穿透指環的玻璃。起初刺痛我的眼睛,但我很快便能適應過來。不經不覺,我和阿康已經交往一年多了。這情侶指環是他正式跟我示愛的時候送給我的,算是我倆的訂情信物。可是它已經變得毫無意義,因為我們已分開了。
「小悅,起床吃飯!」爸爸敲着門說,把我喚醒過來。
我從少便接受醫生的建議,每餐的飯菜都維持少飯、少肉、少醬汁、多蔬菜。清淡的飯菜不單適合我的身體,還適合我的家庭。
以每月一萬多元收入維持普通一家三口的生活,應該是綽綽有餘。但我需要長期服藥和定期檢查身體,每月醫療費用要數千元,加上學費和生活費,我成為全家的最大負擔。
父母辛勤工作,使我得以生存,但我不但沒有報答他們,還白白遭蹋他們的愛意。我因為醉心於戀愛,會考成績強差人意。最後要父母親自向校方申請原校重讀的學位,校方也因為我患病才答應收留。
會考失敗後,我有好好反省過錯,但始終沒有改正過來。因為除父母外,阿康是唯一愛惜我的人;縱使現在已經不是。
我撥弄他撥弄過的我的頭髮,我親吻他親吻過的我的手背,每個動作也有他的影像。為甚麼我們的邂逅是這麼遲呢?為甚麼不讓我們相愛多一個月、一年、一生呢?
他花費數個月的時間來追求我,但我仍然不能弄清自己的心意。最後在他的「脅逼」下才勉強跟他交往。可是時至今日,我們分開後,我才發覺自與他相識以來,就一直、一直很愛他。他已經成為我的生命。
-=-=-=-=-=-=-=-=-=-=-=-=-=-=-=-=-=-=
今天我又到小學做義工。我有點兒想再見他。
我遲了十五分鐘才到達小學。當我去到課室的時候,他已經在指導學生做功課。我們依舊只向對方點頭,各自工作,沒有半點交流。不過我偶爾也有偷望他,也發覺他偶爾會偷望我;也許這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
義工時間完畢,學生都離開後,他說:「江悅,你精神不太好呢。」
「是嗎?怎麼說?」我緊張地說。
「現在好多了,臉都漲紅。」他微笑着說。
我又無言以對,臉變得愈來愈紅。
「那我放心了。你還會再來吧?下週再見。」
-=-=-=-=-=-=-=-=-=-=-=-=-=-=-=-=-=-=
在課室裏的他總是不苟言笑,認真地對待工作。而且他有為人師表的風範,最少他能確切明白地指導學生,又能穩定課堂的秩序,讓學生們留心上課,不像我們中學的某些老師般無能,連課堂的內容也搞不清楚便授課,又不能控制課堂秩序,又不能討學生歡喜。
「你將來會當教師嗎?」我問。這是我第一次當主動的一方。
「有可能會當中學老師,最好的打算是回南中當老師吧,比較多熟悉的人。或許我能當你的老師呢!」
「豈不是很奇怪?我們現在是同事,但霎時又變成我的老師。」
「搞不好會被人家說是師生戀呢!」他笑着說,我又害羞得無言以對。「再見。」他說。
還有最後一次相見……
-=-=-=-=-=-=-=-=-=-=-=-=-=-=-=-=-=-=
加拿大是個怎樣的國家呢?究竟加拿大是滿佈楓葉,還是個白雪天國呢?
他離開的時候,只留給我一個手機短訊:「我要去加拿大了。我不知道我會否回來,所以你不必等候我,儘管去愛其他人吧。」
他連同他的家人一起消失,他的朋友也不清楚他離開的原因,我用盡任何辦法也未能聯絡上他。
我傷心欲絕,但從沒考慮過放棄他。
他是個信守承諾的人,他曾經答應我此生此世都會竭盡全力地照顧我。無論我的病情是如何反覆無常,他都不會嫌棄我、捨棄我。
可是我早就感覺到,他對我的熱情正在逐漸減退。
他投身社會工作後,我們見面的時間愈來愈少。我明白他工作繁忙,我也不會每天每夜也嚷着要見面,但我只是要求每天用電話對話一次也好,即使只有數分鐘也好,或是一個短訊也好,我也想跟他有最低限度的接觸。
他一直也接受我這個要求,有時候他比我還更主動,但到最後率先生厭的始終是他。
追求我,但又拋棄我。
負心漢……
-=-=-=-=-=-=-=-=-=-=-=-=-=-=-=-=-=-=
今天是我最後一天到小學做義工。
對學生們而言,我只是眾多老師中的其中一位。而且我們只有數小時的接觸,談不上建立了甚麼感情。我們各自完成其責任,彼此不會再見,學生亦不會向我言謝半句。
結束了。學生蜂擁離開,片刻間課室便剩餘我一人。
我整理好桌子上的東西,又將學生的桌椅移回本身的位置,將抽屜和地上的垃圾都清理得乾淨,又把窗戶關好,以防雨水打進課室。我比平日做更多的工作,目的都是找藉口等待他。
他明明跟我說「再見」,但他始終沒有出現。
天已入黑,校工促請我離開校園,好讓他能下班。最後我只能帶着半點不捨離開小學。
人去樓空,小學校舍裡已空無一人,課室也沒有半絲燈光。我坐在校舍旁邊的公園的長椅,仔細閱覽母校的每一個角落。我嘗試回憶小學的生活片段,但我能記起的並不多。可能我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已經與他相遇過。只是當時的我並不在意身旁的人。
「你在等我嗎?」阿康突然出現,坐在我身旁。我被他嚇倒,不知如何應對,只有默默垂頭。他續說:「你是在這小學畢業,然後直升南中吧?」
我點頭。
「我曾經報考這小學,但沒有被招收,好不容易才考進南中。」
原來我沒有曾經錯過能與他共度的日子。
「不過我是否入讀這小學是不重要,最重要是能在這裡跟你遇上。」
他又使我覺得難為情,瞬間滿臉通紅。
「我很喜歡你。」他抓住我的手,兩人十指緊扣。我感覺到他的體溫從手心傳到我的身體,使我心跳加速,緊張不已,胸口更像被挖空一般,身體不禁顫抖。
他見我沒有反抗,卻沒有得勢不饒人。他沒有送我回家,只是送我到車站,陪我等候巴士。整個過程間,我們只是手牽手。沒有擁抱,沒有接吻,卻令我更信任他。以他作為初戀對象,即使過得平淡,更重要的是能讓我獲得安全感。
-=-=-=-=-=-=-=-=-=-=-=-=-=-=-=-=-=-=
可是他能撩動我的心,卻沒能完全佔據我。即使我們已經嘗過十指緊扣,但彼此沒有任何承諾,我始終難以放心。爾來數天,我們沒有聯絡,我對他的熱情也失去維持的倚靠,急劇下跌。到他再找我的時候,我始終沒有明言答應。這段關係持續數月。
他終於約會我,似乎要作「致命一擊」。可是他沒有準備甚麼禮物,也沒有安排甚麼隆重的節目,只是帶我到一個荒僻的沙灘。
晚上的沙灘幾乎空無一人,但萬里無雲的星空使我雀躍萬分。他教我看星,又告訴我一些他胡亂創作的星座故事。起初我只是取笑他無聊的創作,直至他說一個金牛座的傳說:「金牛座有一個很浪漫的傳說。相傳宙斯對腓尼基的美麗公主歐蘿巴一見傾心,於是化身成一隻溫馴的、有金色牛角的白牛。公主看到這隻牛異常美麗和溫馴,於是騎到牠背上去玩耍。宙斯乘此良機,衝到海中的克里特島,使公主無法退避,然後表明身份及愛意,最終獲得公主的芳心。」
我知道要來了。
他說:「現在的處境跟故事很相似吧?我就是等這個時候,讓你看到金牛座,讓我能借金牛座的傳說表達我對你的愛意,希望讓你更完全信任我。也許你會感到奇怪,為甚麼我當時初認識你的時候便對你萌生好感,看似很隨便。我當初也懷疑自己,但我發覺我們每次見面,我就愛你多一分,直至現在,我很清楚我是很認真的愛你。我衷心請求你,請你當我的女朋友吧!」
他的氣勢、他的身體把我完全壓倒。雖然像是脅迫,但這份笨拙的浪漫,使我心甘情願地答應他。
-=-=-=-=-=-=-=-=-=-=-=-=-=-=-=-=-=-=
在他心目中的我是怎樣的女生呢?他大概知道我身體並不強健,但總不察覺到我特異的體質。當我身體抱恙的時候,他總是以為我血氣不足,叫我多喝紅棗水、多吃櫻桃。我一直隱瞞自己的病情,並非我存心詐騙,而是怕他會嫌棄我。即使他接受我這個不會流汗的特點,也不可能接受隨時會死亡的我。可是這秘密還是被揭露出來。
猛烈的陽光把睡眠不足的我曬得頭昏腦漲,當我進入購物商場的時候,氣溫的急劇轉變令我瞬間失去知覺暈倒,當我甦醒的時候,我已經躺在醫院的病床。當然,除父母以外,阿康也在我身邊。我從阿康的眼神得知他已知悉我的怪病。
我滿心憂慮,擔心剛墮入愛河的我會失戀,又擔心父母會擔心我反覆的病情。尚未恢復元氣的我再次暈倒。
在黑暗中,我漸漸感覺到別人的體溫正轉入我的身體,我緩緩張開眼睛,瞥見有人坐在病床旁邊的膠椅。我閉目稍作休息,再望向那人,發覺她原來是累透了的媽媽。我還
能隱約嗅到她身體散出的布料味,肯定是徹夜不眠地工作後,立刻趕來醫院探望我。
我沒有喚醒媽媽,只是無聊地圍望四周,竟讓我發現阿康正在病床末的椅上坐着。他察覺到我甦醒過來,立刻喚醒媽媽。媽媽驚醒過來,流露出如釋重負的表情,然後交帶
幾句話便回家休息。她彷彿洞悉阿康的心意,甘願讓出與我相處的時間。可是阿康沒有立刻跟我說些甚麼,只是緊握我的手。
我感覺喉嚨乾涸,嘴唇乾裂,一時間說不出話,只有注視他,期望他能接收到我的訊息。他也明白我的意思,嘴角微微翹起,含蓄地微笑。雖然他沒有明言,但我知道他沒
有嫌棄我,反而由衷地展示他對我的愛,即使我身患奇疾,也不受絲毫動搖。也許有點言之過早,超越一般中學生的思想,但我已決定他向我求婚的話,我必定答應。
-=-=-=-=-=-=-=-=-=-=-=-=-=-=-=-=-=-=
為甚麼他會突然間拋棄我?為甚麼他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罕有地收到一封貼着香港郵票、打上香港郵局的郵戳的信件。我認識發件人的筆跡,肯定這信件是阿康寄來的。然後我小心翼翼地拆開這封他寄給我的唯一的信件,仔細閱讀信內的每句、每字……
仍多麼需要你 仍多麼需要你
如今天失去了 怎麼退怎麼進
如果可不要信 寧死都不要信
但看我手 再激動仍只得傷信 ──《傷信》
假若人真的能控制自己的眼淚,我會選擇一直哭下去……
-=-=-=-=-=-=-=-=-=-=-=-=-=-=-=-=-=-=
秋風使天氣涼意倍增,即使太陽高掛也不會使我感到炎熱和暈眩。他見天氣良好,立刻帶我去主題公園。
我第一次踏足主題公園,所有事物都顯得很新奇。我彷如小孩子般興奮,嚷着拍照和玩機動遊戲。也許是因為他比我年長五年,他的可靠和體貼入微更被凸顯出來,恰到好處的照顧我這「小妹子」。
我的活力可能感染到他,今天的他比平日活躍和有朝氣得多。平日的他比較沉默寡言和被動。當我們二人獨處的時候,他也會有淘氣、幼稚的一面,但當有其他人,不論是朋友還是陌路人,他的言行舉止也會變得較成熟和拘謹。但不論是幼稚的還是成熟的他,他始終是吸引着我的他。
我們早上便去到主題公園,遊玩到下午時份,我已經力竭筋疲,可是他仍是精力充沛,我的體能也因着他而發揮至極限,竟能如奇蹟般捱到傍晚時份也沒有倒下,最終還能堅持到觀賞晚上的煙火匯演。
煙火熠熠,隆隆作響。我倆十指緊扣,情意綿綿。
他說:「今天的你比平日有活力得多,這樣的你也很可愛。」
「今天的你也比平日活潑得多,我很喜歡這樣的你!」
兩人甜言蜜語,直至煙火匯演結束,我們才換個地方休息。
我們坐下後,他故作神秘地、誰也能猜得出他要給我驚喜地說:「你先把你的手提電話借給我,然後閉上眼,我說張眼你才可以張開眼啊!」
我閉目片刻,然後兩次問他可以張開眼了沒有,他也說不可以。直至第三次,他說:「你可以張開眼了。」可是他的聲音只是透過手機的擴聲器所發出。我聽見他的聲音後立刻張開眼,但他已經消失了。當我拿起電話想跟他說話,他已經掛線。我不停重撥他的手提電話和家裡的電話,但都沒有人接聽。
我還是滿腦疑惑的時候,發現身旁多了一塊純白色的絲質手帕。手帕的角落刺繡了我的名字,表面是一幅江河皎月圖。這份禮物真的很切合他的文人風格,也很配合我們初
遇的情景。
但這是開始,也是結束。
-=-=-=-=-=-=-=-=-=-=-=-=-=-=-=-=-=-=
河水十分混濁,我張開眼睛時,幾乎連自己的五指也看不見。我下沉不夠十秒,已經有膠袋飄到我身旁。奇臭難當的河水更漸漸滲進我的口裡,我按捺不住要吐出河水,可是我甫張開嘴巴,河水便湧進我的嘴巴、咽喉。我立刻用手掩住自己的口,但這時候,我體內的氧氣已所餘無幾,鼻孔已不由自主地呼吸,但吸進的只是一口又一口的臭河水,瞬間,我的雙眼只能望見黑暗。
長久的黑暗,是死亡嗎?人死後會到怎樣的世界呢?我會如宗教般往另一個世界去嗎?還是像現在一片黑暗,甚麼都沒有,連知覺都沒有呢?
我突然記起他跟我說的一句話:「當黑暗都沒有,才是甚麼都沒有。」
原來即使我沒有身體,但我還有意識,沒有眼睛,但還會感受到黑暗。
一切,我還是「有」。
-=-=-=-=-=-=-=-=-=-=-=-=-=-=-=-=-=-=
醫院不是寧靜的地方,絕對不適合心靈受創的人休養。所以我能活動自如後,我立刻要求出院。可是醫生和爸媽都擔心我的心理狀況,所以不允許我出院,更加叮囑護士要密切留意我的情況。
這些日子,即使每天有醫生、護士和爸媽的慰問,但我感覺自己大部份的時間也是獨自渡過。能與我分享時間的人已經不存在。
我們彷彿活在同一個世界,又彷彿活在各自的世界。
某天,媽媽突然給我一封信。撰寫這封信的人是阿康。
我乍驚乍喜,身體不其然地發抖。媽媽見我如此緊張,立刻握緊我的手,雙眼充滿信心地凝視我,打從心底地支持我拆開這封信,因為她知道我自殺的原因,必定與這封信的發信人有關。大概她也猜到,這封信的發信人是阿康。
然後我小心翼翼地拆開這封他寄給我的唯一的信件,仔細閱讀信內的每句、每字……
小悅:
你好嗎?我希望你過得很好,就像我們交往的時候,每天也綻放着燦爛的笑容,用最悅耳的聲線和最親切的態度跟你身邊的人相處。
對不起,我離你而去。我不清楚你能否想像出我突然消失的原因。你記得你曾經跟我說「小病是福是對的」嗎?當初我以為你說得對,因為經常有小病的我,的而且確沒有面對過大病。但我後來才知道「小病是福」也未然完全正確,因為我患上腦癌,而且是很難醫治。我和我的親朋戚友都不停諮詢不同醫生的意見,最後醫生建議我到加拿大找尋一位成功醫治跟我類似的個案的醫生。而我的病情已不容許再耽誤,所以我和家人倉卒決定遠赴加拿大。
雖說是倉卒決定,但我知道我的病情已經有頗長的時間,我曾經多次嘗試跟你坦白我的病情,可是我始終沒辦法說出來。我怕你會胡思亂想,以為是你帶來我的不幸。所以我決定手術完結後,才讓你知道即使多棘手的病,也總有辦法治好。我知道是我讓你投入這個世界,我不想將你獨留在這個世界;哪怕只有一分一秒,我也想帶你認識更多的人和事物。
但……對不起。
我寫這封信的時候,我請求我的父母在我手術失敗後才好寄給你。假若手術成功,我會親自找你解釋;但即使失敗,我也希望你知道我不是故意拋棄你;應說我從沒考慮過拋棄你。
這封信,是我目前為止所給你的唯一一封信,希望你能好好保存。然而,我最大的心願是你不會因為我的離去而變得意志消沉,而是能連同我的意志,更加積極地生活。
緊記,生命誠可貴。
祝
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康
-=-=-=-=-=-=-=-=-=-=-=-=-=-=-=-=-=-=
仲夏的傍晚,我在城門河邊緩纋地踏着腳踏車欣賞河塘月色,感受這世界的氣息。這時候的城門河已經不再臭氣薰天。我回想起當天自己嚥下幾口河水,不禁打個冷顫。可是這個回憶配合這個反應是最適合不過,因為可見我已經不再怨天尤人地面對過去,而是輕鬆地面對沉重的過去。
自從我看過阿康寄給我的那封信,我反而能解開心結,勇敢地面向外界的生活,不在是只活在自己的象牙塔裡的傻妹子。也許他在天有靈,會為新生的我而感到高興。
突然,一張熟悉的臉孔迎面而來,我錯愕之下失去平衡。正當我的頭快要栽到地上的時候,他及時過來扶起我。
「即使心境開朗了,但大意的個性還是改不掉,哈哈。」阿康說。
他一頂清爽的短髮跟以往暮氣沉沉的形象相比,實在是差天共地。但他確實是阿康,無論是臉孔、聲線、身型……我似是在發夢,卻活生生地觸碰他的身體。
「所謂『失敗乃成功之母』。想不到我手術失敗,身體卻不認輸。手術過後不久,腫瘤竟然漸漸消失,身上連半個癌細胞也沒有。也許我們真的感動了上蒼。你知道嗎?我真的很想念你,很想與你繼續活下去、愛下去。」他說。
這是奇蹟。
我依然不會流半點汗,但卻會流淚。
他從我胸口的衣袋拿出他送給我的手帕,為我拭抹着重逢的眼淚。
月兒似是孤單地高掛在半空中,但其實地球是永遠永遠伴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