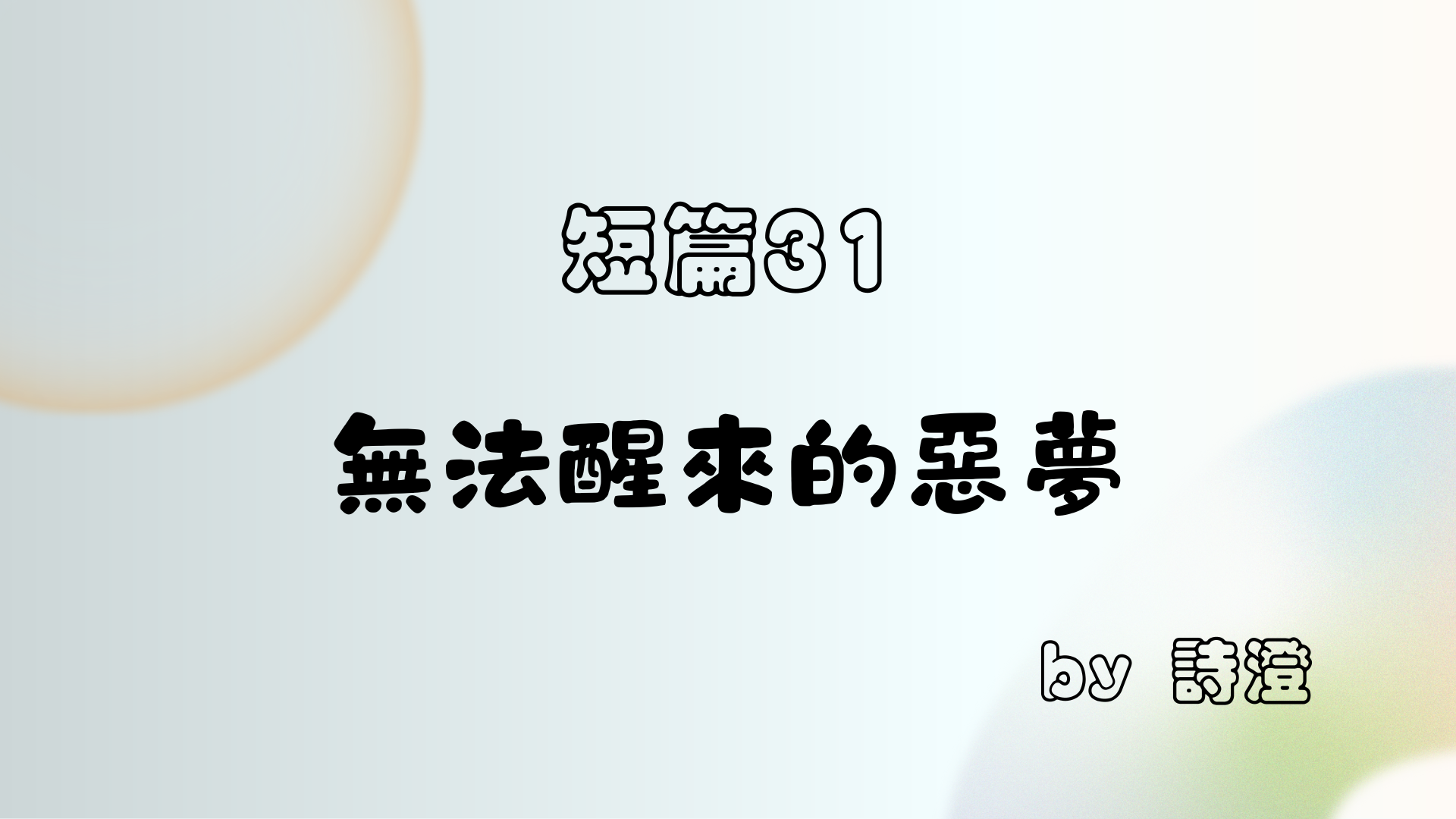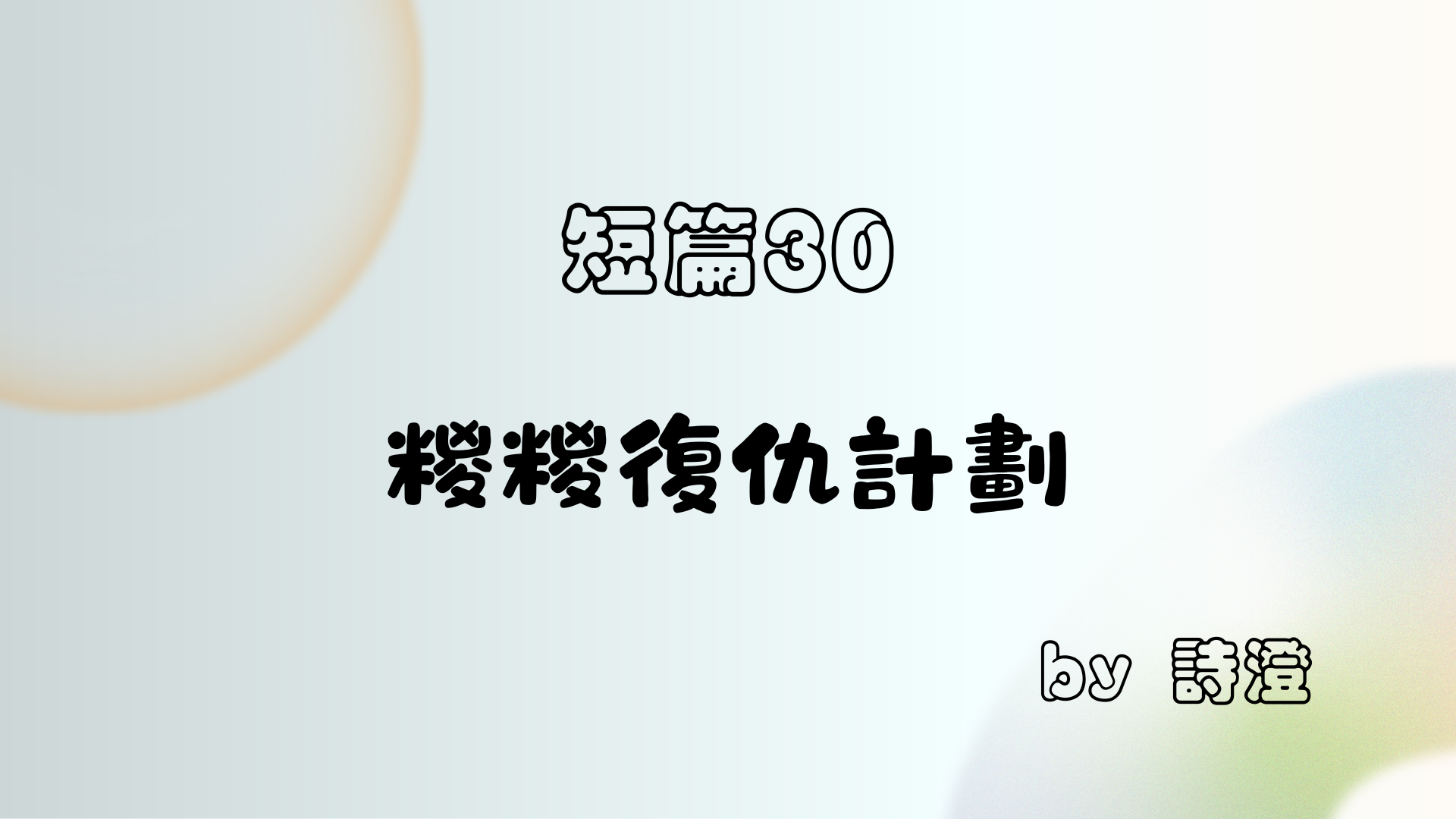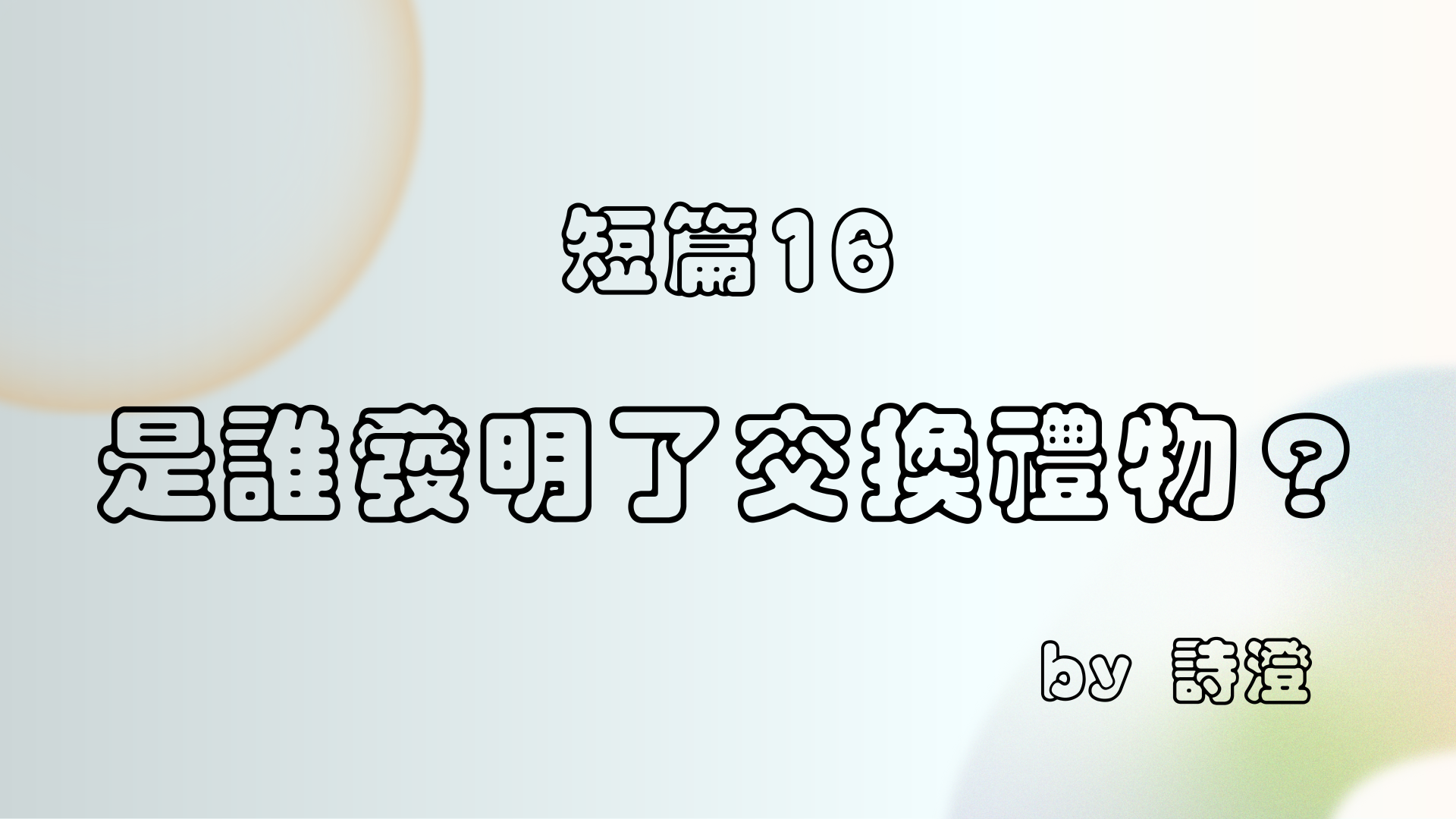自從被吳縱以兩分鐘極速射敗後,阿早、阿敏和阿星三人一直耿耿於懷,處心積累,不惜用盡各種方法都要令他失一次威,以報一箭之仇。然而,阿縱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學生,品學兼優,樂於助人,外表出眾,加上球技如神,老師同學都對他如珠如寶,班上恐怕只得阿早三人恨他,在沒有志同道合的伙伴的情況之下,要找出吳縱的缺點,只要依靠阿早三位人生路不熟的轉校生了。
起初,他們三人無時無刻雙眼都總會有一隻放在阿縱身上,無論上課、小息,還是午膳、放學,他們都遠遠地觀察他的一舉一動,但一星期過去,他們仍是沒有任何發現。時間一久,他們便沒有恆心,開始進入半放棄狀態,放在吳縱身上的注意力也越來越少,但這也是當然的,阿縱每次一到小息、吃飯和放學時間,都要過五關,斬六將,才能由三樓的班房落到操場,一般人用兩、三分鐘可完成的路程,他每每要比別人用多三倍,有時甚至是四倍的時間,只要老師下課晚了,那一個小息他休想可以去一趟洗手間;而他面對重重的人牆,卻永遠都報以微笑,從來沒有動怒,對著一個永遠也完美、循規蹈矩的人,他們想不放棄也不行了。
「『此人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尋。』吳縱這個王八,真的是無械可擊的嗎?」阿敏慨嘆。
「嘩!阿敏你竟然懂得唸詩,今天的太陽從西方升起了嗎?」阿星用男孩常用的溝通方法──挖苦來回答他。
「我們寒窗苦讀多少年,便吃了填鴨多少年,這種千古名句,不多不少也會被強迫烙印在我們的腦海中。」阿敏脫口而出。阿敏和阿星你一言我一語,完全無視阿早的存在,及至他們發現阿早原來一直坐在一旁,才停止互相挖苦。
「阿早,那個龜蛋真是難應付,看來我們真的無法在短期內發掘出他的缺點,不,應該說他根本沒有缺點能給我們發現,我怕我們只可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來向他報復,那些卑鄙的方法很難應用於他的身上。」阿星提議。
「人,沒有完美的,我絕對不覺得他會是例外。」阿早一邊回答一邊看著阿縱,「不過我徹底想過,要正式擊敗一個人,只有在他的專長裡取勝才有意義。不如還是再加倍練習我們的默契和球技吧!在十年的籃球生涯中,從未受過這樣大的打擊,我們稱霸了北村的球場,但卻在這裡敗得體無完膚,被當成是三歲小孩,真是羞恥!」
「啪!」一個粉擦擊中阿早的右臉,頓時白了一片,旋即引起全班的注目與哄堂大笑,特別是阿敏和阿星。
「上課專心點,不要談與課文無關的事,要談便放學後到隔壁的金咪茶餐廳,一面喝奶茶一面談。」「粉擦神人」教中化的錢老師語重心長地說。
「粉擦神人」是阿早唯一一個喜愛的老師,雖然永遠一臉認真,但其實在言詞間不斷有不同的幽默出現,能否領略得到而笑則要視乎你自己的能力有多高,他由始至終都維持同一張臉,比七十年代的「冷面笑匠」許冠文有過之而無不及。儘管每逢他的課同學們都是自由活動,或被他催眠,但班上始終有三位人兄是全神貫注地聆聽著,到笑位會一起大笑,他們便是阿早、阿縱和留短髮的女班長,三人成績差天共地,但都喜愛聽錢老師的課。
「你有沒有事啊?」當全班同學仍沉醉於取笑阿早,突然有一把女聲出現,有如天籟之音,對他說:「這張紙巾借你,下次上課要專心一點呀!」阿早呆了一呆,看著紙巾良久也未能反應,但心卻如鹿撞,越跳越快,冷不防再聽到一句:「幹什麼?不好意思嗎?還是害羞呢?堂堂一個大男人,拿張紙巾也沒膽量嗎?真是看不出啊!要便拿,不要便說不要,我很累呢!」阿早回過神來,戰戰兢兢的拿了紙巾,小聲地說了一聲謝。
「不用謝,大家難得是一場同學,是一種緣份,同學理應互相幫助,不是嗎?我上次有看到你打球,真的很帥呢!雖然落敗,但敗在全校搶分能力最強的人手裡,雖敗猶榮,我們今年的班際籃球比賽靠你們了,加油啊!」她面帶笑容地說,「啊,忘了自我介紹,我叫梁詩情,歐陽早,以後請多多指教!」說罷吐一吐舌,一臉稚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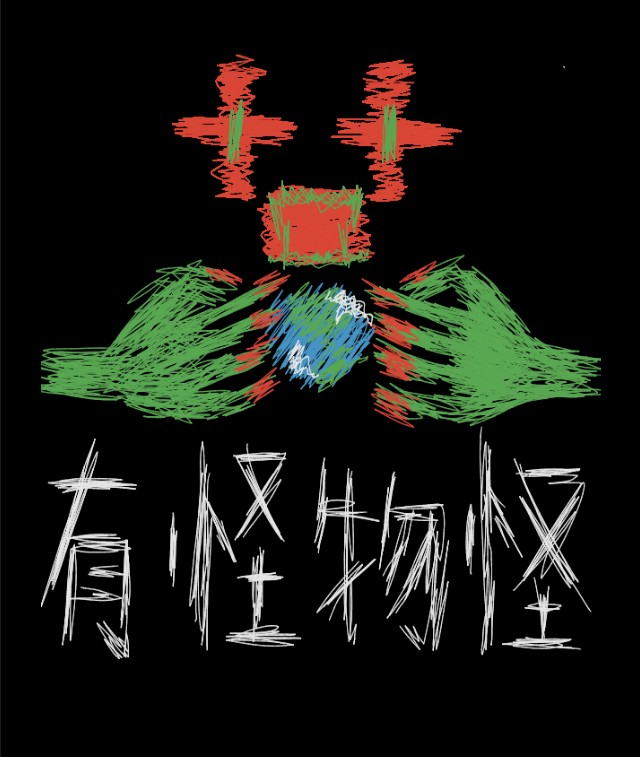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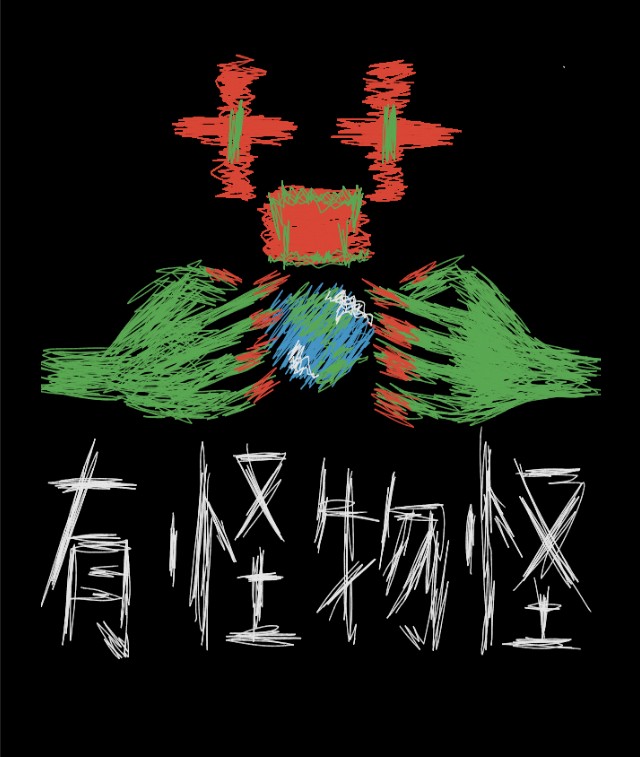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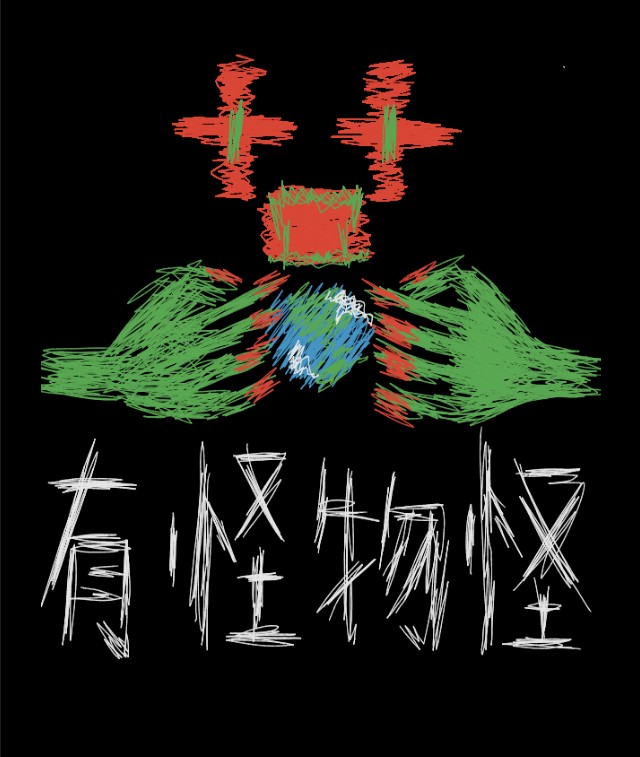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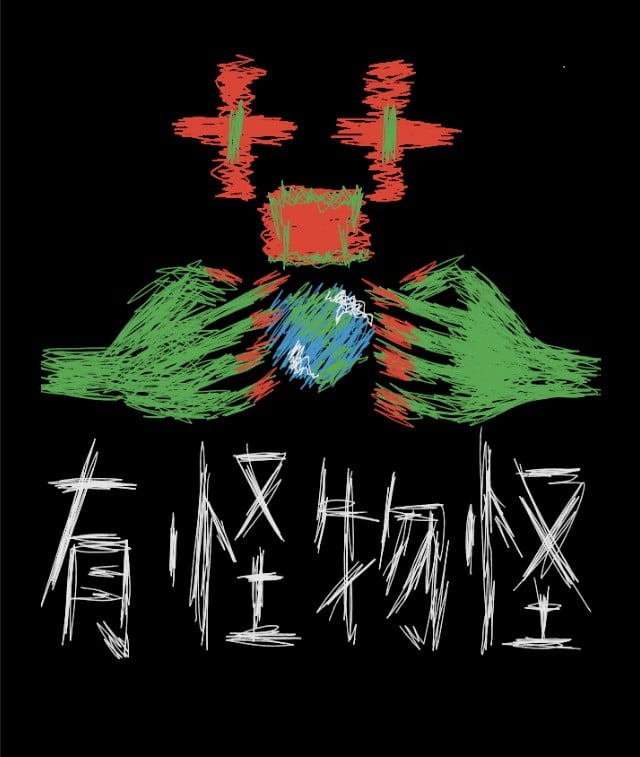

.jpeg)
.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