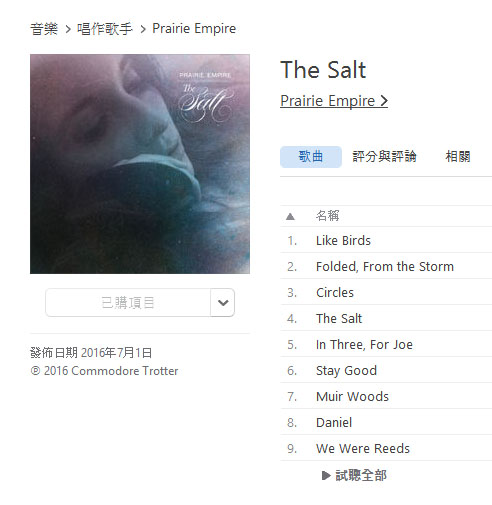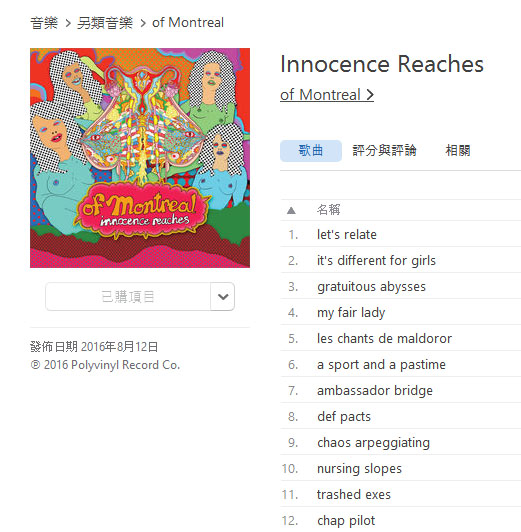晚黑,屋外刮著厲烈的寒風,從兩扇玻璃窗的縫隙間,寒意被一拼帶入屋中,響起哨子般尖銳和刺耳的聲嚮,加上雨水不停對窗面窮追猛打,有如奏著亨利‧考埃爾的鋼琴音樂。不過,這間屋,並不是「死」的,只是「生命力」比較弱,若果仔細傾聽和觀察,會發現屋中淡淡的燭光,正在描繪客廳黝黑的佈置;而且,還會隱約聽到一段段屬於一位女性的呼吸聲。
這間屋子建於海灘附近,從窗口望出去,後面是長得高高、一模一樣的椰子樹,泥地上有一雙雙的足印,朝屋子的方向走來,應該是屬於這位女性。
這位女性平躺在梳化上,穿著一條連身花裙,看似年約二十,是位漂亮的少女。她頭部微微靠在扶手上的軟墊,左手屈曲搭在心腹間,右手則自然地,垂低在離地面的一兩寸之上。靠近聽起來,呼吸非常有節奏,而且輕輕的、很溫柔。一切看似平靜。
不久,少女卻被轟隆的雷聲驚醒,可她仍然沒有移動,直至過了大約一分鐘,她意識到這間屋子,只有她自己一個,也許,並不是第一次有這樣的認知。
少女緩緩從梳化站起來,走進廚房,從冰箱拿出最後兩瓶啤酒,用開瓶器打開蓋子,回到梳化就坐,這好像已經花光了她全身的力氣。她伸出疲累的手到旁邊的茶几拿取一面相架。相架中是一張有她和一位與她年紀相若的少年的合照,兩人看似很高興。
她一邊喝著啤酒,一邊用她緊餘的力量盯著相片中的少年。
最後,酒瓶掉在地上;唯相架放於心腹間,陪她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