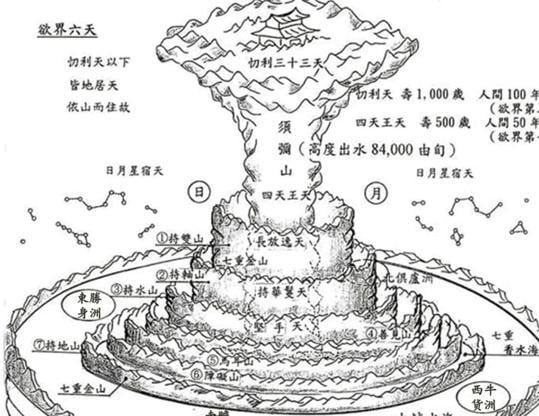在澄明的月光下,我與朋友L走過貫通周莊的小河河畔,來來回回在古鎮圈裡繞了好幾圈。縱使在夜裡還有燈火照明能走的地方着實不多,因為房子起得很矮很密,門前的小巷多只夠兩位成年人走過,許多路一到了夜裡便回歸寧靜。也正因為如此,我倆能閒逛的範圍不大,只能圍着最繁華的主河道兩岸前端,也就是開着許多客棧和餐廳的左右兩條石道,就算到了晚上九點多亦依舊是燈火通明,與在走深一點的巷子完全不同。
又再一次走到古鎮出入口處,踏上全功橋,也就是遊客進入周莊古鎮後看見的第一座石橋。它也是眾橋裡頭最高大、最有威嚴,就像是一家之主,佇立在家門口迎接自四海內外來的朋友。站在全功橋之上,不該屬於六月的風即迎面吹來,往古鎮街道望去,柳樹、河道、月亮、古風石材建築,是它們盡收了江南獨特的味道,亦或是因它們而散發着這種讓人捨不得將目光移開的浪漫情懷,那便不得而知了。朋友L問了我對自己的處世看法,雖然在此情此景之下再要我想自己有點煞風景的厭惡,但再細想,面前純真的地方剖析最真實的自己,豈非一件挺合適的事?
「最重要的是兩點吧。」
我故作一本正經,以一副淡然於世的嘴臉自全功橋走下,一隻小黃貓在大樹根旁躺着休息,我不由得走到牠身旁,彎下身子在牠頭上輕輕地摸了幾下。雖然牠一直背對着我,我也沒打算要強行逼牠與我四目交投,但我確信那時牠小小的臉蛋上必然掛着舒適的滿足表情。也許是瞇着成兩條小線的眼睛,小嘴依舊像是煞有不滿地往下拉,但也不難想像牠確實有散發愉悅的心情。正當我意猶未盡之時,牠突然起身,恰似不滿意我的技術往別處頭也不回地緩步走遠。受到無情拒絕理應是該感到一絲沮喪,更甚是該不堪羞恥心作祟而惴惴不安,但我心卻有如頭上明月般澄明而滿足。
牠就是貓,放蕩、不羈、脫俗、出世、瀟灑、孤高、傲慢、寂寞,無論你多麼想靠近牠、或是討厭牠、或是氣憤牠、或是埋怨牠,牠都是依故在世上像昨日的自己一樣活着,而昨日的牠,同樣沒有拋棄牠心中關於自己的真實面貌。我看着牠的四爪有序地踏着石板路,心中羨慕得很。我喜歡貓,就是喜歡牠的自我。朋友L看着小黃貓離我而去,不忘揶揄我自作多情。說實話,當時牠或者已經將我忘記了,所以根本不存在「離我而去」這套說法。相忘於江湖,是牠的處世之法。所以,我也已把牠拋於腦後,然後起身再往燈火闌珊處走去。
「是哪兩點呢?」
朋友L期待聽下去的語氣讓我有點不安,好像突然間就將我推到高築的台上演講一樣,要不是微風剛穿過在柳邊拂到臉上,稍微舒緩,恐怖我將甚麼都說不出口。我想了一想,確實能具體說出的也真的只有兩點,於是便好整以暇,故作很隆重地道出自己黃湯落肚後胡思亂想總結而出的所謂處世手法。
「第一,不要管別人的看法,不論是好是壞,都不要管。」
「說多點。」
「在意讚賞,會使人心浮;在意批評,會使人心亂。自己每做一件事,都要在意每個人心中對自己的看法。想要得到誇獎,於是總是想要為了得到它而帶着功利的心做人;又或是害怕受到評價,為了逃避別人不負責任的嘴巴而營營役役活在不安之下。那做人實在太累了。」
像貓一樣活着。
我嘗試整理心中的感受,將它們捏成說得出口又能讓人輕易明白的語言泥塑,與其說是談想法,倒不如說是感慨更加貼切。心中慶幸自己能順利說出心裡所想,卻又為了內容過於認真、不似人前的我而突感陌生。
當朋友L點頭示意時,我們已經走到住宿之處,叫作「隆興客棧」的小樓。老闆娘是個老好人,每次與她對話都總是以笑臉相迎,卻絲毫沒有老闆對着客人藏着的那種富侵略性的虛假,只是掛着笑臉,別無其他心思。晚上的周莊,許多店舖都已關門,只剩有賣宵夜的餐館和三家播放吵耳音樂的酒吧還在營業。雖然酒吧正好坐落在我們住的客棧對面,但可能是心理作用上對這些與古鎮一點都不配的消遣起了忽略的作用,才讓我能繼續帶着平靜如河水的心,繼續享受古樸的純潔。
「再走一圈吧。」
「再繞過那橋吧。」
那是距離客棧不到五十步路程的小石橋,喚作「雙橋」,以世德、永安兩道石橋組成,眼瞅大概就四尺多寬,比起客棧裡的雙人床也就寬一點點;也只有十來米長,尤其是那座永安橋更是藏在直路上顯得有點不起眼,而世德橋則是以拱狀橫跨在河岸兩條大街上,橋下拱成半個洞,平時有載着旅客的小舟划過,伴隨舟娘熟練地唱起船歌,一擺一擺地就如此穿過洞口。這裡在日間熱鬧得很,站在高高的拱橋上方眺望前後各有風味的江南水鄉景緻,小橋流水人家就如此分佈於河水兩岸,岸邊還栽滿了婀娜多姿的垂柳,在盛夏的六月吐露鮮嫩的綠,不時隨着輕風吹送,便微微揚起尾擺舞動。稍長的柳枝會直接插進綠水之中,在風的靈感下,在水中與水面間上下划動,像畫一幅江南美景圖,將所有美好都收納裡畫中,不受時空限制,亦能讓人品味足以回味無窮的魅力。
那時的雙橋並沒有太多人,我從不遠處望去,只有一位與我年紀差不多的年輕人和一位唱水歌的阿婆,阿婆以朗亮的歌聲對着年輕人唱着周莊的歌,聽他們說,這些都是以前留下來的歌,以當地的語言唱,而會唱的也只有當地的人。我們在河畔晚飯時就已經有幾位年齡老邁的阿婆曾到桌前問要否聽水歌,十元三首歌,阿婆即席表演,要不是同行其他友人好似沒太大興趣,我倒是非常樂意讓他們好好為我多少添點寫意。
當我和朋友L踏上雙橋前,我便請求一定要在這坐一下,安靜的雙橋非常吸引不喜歡熱鬧的我,加上早晚景物雖然一樣,可是感覺就差了好一大截,就算不算上來來往往的人,早上橋上的風景叫作悠悠揚揚,而晚上的風景則叫作蕭蕭瑟瑟。而此般冷清的蕭瑟,除了依賴晚風的涼意之外,讓得歸功於自朗朗晴空揮灑而下的月光,讓周圍環境好像加了一大塊濾鏡一般暈開了冷冷的藍色,藍色的憂鬱肆意在寧靜的夜晚隨細膩的微風在我眼前遊走,我必然捨不得放過此般純淨的哀美。那紮起雙辮的阿婆在我們坐在橋中心旁邊石墩時,剛好唱完了不知道第幾首歌,然後對着手提着啤酒罐、坐在另一邊石墩上的年輕人,說着我也聽不太明白的話,大概是問他要不要再聽幾着之類的。只見他舉起空着的手在半空中左右擺動,然後伸進口袋裡拿了幾塊錢交到阿婆手上,邊說着「我就只有這麼多」。
阿婆有着樸實而親切的笑容,亮起了在夜色裡仍清晰可見的整齊牙齒,對着那年輕人弓身做了好幾下鞠躬。那已是晚上十時多,就算不看時鐘,單以明月高掛即知時間不早,阿婆挺得不直的腰骨讓她看起來更加疲憊不堪,當矮小的身軀背靠着我往自己的手提袋子走去時,甚至讓我想起了死去的奶奶。而正在她彎下身子想拿起放在地上的袋子準備離開時,我才想起這位紮着兩小根辮子的,正是我們在飯床上拒絕過的其中一位老人,正因為她那嬌媚得不甘向少女示弱的雙辮,讓我印象頗為深刻。我與朋友L像是心有靈犀一般,都同樣把目光投在了這位勤奮的老人身上,就在她準備離開之際,我終於忍不住月色朦朧之美,向她的背影呼喚:
「請為我們唱幾首。」
她馬上回過頭來,以碎步輕快地往我們身前走來,臉帶着掩蔽疲倦的笑靨,向我們介紹自己想唱給我們聽的歌。她的口音實在太重,可惜我只聽得懂不足五成,便不好意思地打斷她的話,故作瀟灑地對她說:「你隨便唱你想唱的,我都可以。」
她也沒有多回話,只是點點頭,便開始搖擺起身體開始放歌而唱,與其說擺動的身體使她找的節拍非常的準,倒不如說那只是她習慣了的晃動,就像聽了歌曲便會自然起舞、看見心上人就會心臟噗通地跳、嚐到美食就會情不自禁地會心一笑,都已經是反射作用了,不必勉強維持,也能隨心所欲。
我忘了她唱了甚麼歌,也不清楚她唱的是何些詞句,只知道在她的歌聲下,世界好似清澈了許多,就算酒吧那吵耳的歌聲在身後有意侵擾,卻始終進不了由景緻與心靈營造出來的世界。我想,心中的天秤在傳統與創新之間,已經無庸置疑地傾向了前者了吧?不,與其如此,倒不如說我在實與虛間、美與醜間、善與惡間,都毫不猶豫地做了抉擇,也許價值的選擇並不能得到全世界的認同,但我也慶幸在感觀的交錯之間,我在月色下感受到更加澄明的自己。
眼前阿婆只管繼續高歌,我不知為何突然很想四處張望,這並不是出於對歌者的不尊重,乃是自內心激起了一種按捺不住自己的浮動,使我不得以表現形式吐露心境。我向右上方望去,正好是月亮高掛的方向,月下是一座有着古式建築外貌的咖啡店,月光洋洋灑灑地落在店上層層疊疊的紅瓦上,讓人有種回到過去的錯覺,抬頭一望,好幾顆星也同時懸在看似很近的天際上,更讓人捨不得眨眼,想要永遠留住此等時光,是使自古雅士惆悵不已的苦事。
一隻黑貓從金字型紅瓦屋頂的另一頭走出,先是露出一對尖尖的雙耳,然後是圓滾滾的頭顱和一雙會發光的眼睛,接下來緩緩踏上最頂端,又慢慢朝我的方向往下走來幾步。牠像一位放蕩的浪子,悠然在人家的屋企上盡情地打了一個哈欠,沒有理會酒吧的音樂、沒有理會阿婆的歌聲、沒有理會江南的風光、沒有理會皎潔的月光,更沒有理會正凝視着牠的我,只留下了一個哈欠,便又回頭不知往何處繼續走去。
大概過了三首歌的時間,我便讓阿婆停下來了。並非我不喜歡這樣的氣氛,而是我怕她唱得太累了,阿婆她仍自告奮勇讓我們再聽一首渡船歌,並說還會加上姿勢伴唱,是非常地道的水歌。見她盛情難卻,也只好讓她興致勃勃地再唱一首。她前後擺動老邁的身驅,作出與真相划船無異的動作,賣力地演唱。待她將最後這一首歌完成後,我問她需要付多少歌費,她說隨心就可以了。我想,她或許知道我並非只為了聽歌這樣坐在這裡,就像遇到了知音人一樣,為了讓這樣美麗的歌聲留下,她倒是付了不少心血。
想起三首歌的「公價」是十元,也有不少人會討價五元十首。我拿出錢包,向她遞上四十元,她臉上有一絲驚訝,可我也很想告訴她,這遠不到我心意想給的呢,只是自己並非大富大貴之人,只是一介窮書生,也只能給這些了。價錢與價值,在我心中雖然永遠不一樣,四十元,不過是我為她的辛勞奉上的回饋,而心中的崇敬,則是遠非金錢所能表達的。
離開後,便直接往客棧走去,朋友L沒有問起我第二點是甚麼,我也忘了,我到底想說甚麼。要是往後再問起我的話,我會說:別太打理世間的價值觀,為自己的而活着吧。
還有,我喜歡當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