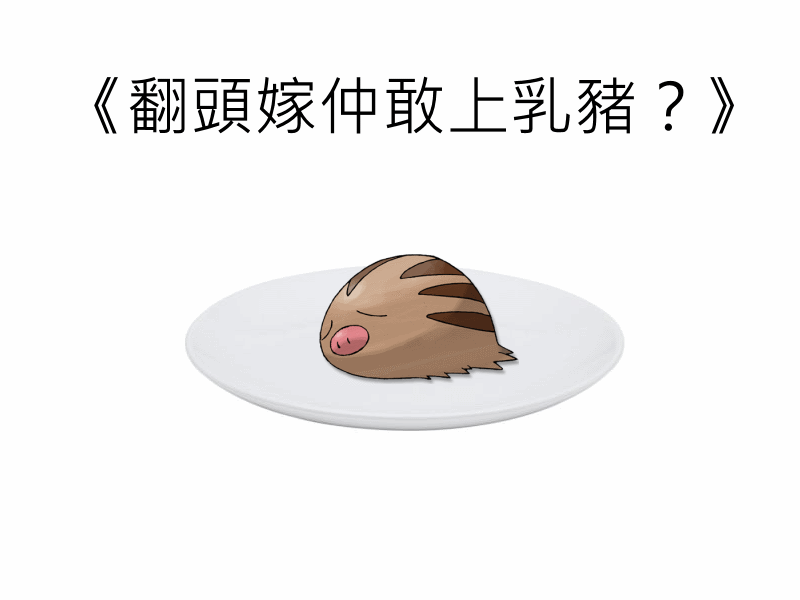午後的陽光格外猛烈,穿過落地玻璃窗的光線,如一道曙光照到我前方,空氣中的飄塵,被陽光照得清晰可見。從玻璃窗望出去,我看見一群師弟妹正在球場上揮灑著汗水,不免一聲長歎,想著昔日我在球場上留下了多少汗水和足印。
我穿著連身的黑色長袍,最後一次以學生的身分——也許已經不是,坐在這充滿歷史價值的學校禮堂內,聽著校長說著些甚麼前程似錦、心繫母校之類的說話,可是我卻無法專心聆聽他的一字一語。
這特別的日子對我還有另一個重要意義,就是我出生的第十八個年頭。可笑吧,大喜日子卻要身穿黑袍,戴著四方帽而非生日帽,還要配上一顆沉重的心。
在校長的一番致辭之後,我隻身到了學校的每一處漫步,我還真是第一次如此悠閑的在校園裡走著。看著花園中比學校更年長的「斜樹」,聽著嘈雜而優美的蟬鳴,呼吸著最後幾口屬於青春的空氣,走著每一個六年來自己留下的腳印。
經過中一的課室,黑板上一道長長的刮痕仍在,我想起了班主任當時怒髪衝冠的樣子,才發覺這幾年她的白頭髪多了不少。二樓的雜物房,是學校裡「罪惡的溫床」,那時頑皮的我,每星期都總會來這裡翹了幾天的英文課堂,最記得的,就是每次來這裡翹課時都總會見到幾張熟悉的臉孔。
三樓的實驗室,給了我一次可怕的經歷。某次實驗過程中,我的領帶被本生燈燒著了,還差點燒到上脖子,嚇得我沒了半條命了。五樓的這間課室,是我高考兩年的課室。這裡的風景怡人,窗外可觀水清見底的河畔,還幾乎能伸手觸及鳳凰木紅紅的樹冠。某次上文學課時念亦舒的《影樹》,望向窗外,簡直就能置身其中。我的座位總寫了一些「高考加油」的字眼勉勵自己,還刻有一句「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的銘言,最終高考的成績的確滿意,希望將來坐在我座位的師弟或師妹,都能夠明白箇中的意義吧。
我走到課室外,靠著圍欄站立,看著花園中的「斜樹」,額上流著汗水,心裡卻泛起涼意。
六年來,我上學總期待放學,恨不得能早一點離校。可今天,我站在圍欄邊,卻只望時間能停下來,讓我站多一會兒。作者張讓說過,「到達」不僅是物理上的身處該地,而是心靈上對該地有歸屬感。原來在這六年的匆匆歲月裡,我已在不知不覺間「到達」了學校。
「到達」之後,我可以選擇不離開嗎?不可以。
紅日乘搭了下坡車西斜,我也跟一眾同學在校園中留下倩影,準備拂袖而去。站在校園門前,回望母校的大門,我見到六年前的自己在鐘聲響起的瞬間衝門而進,而六年後的我卻在悄悄中與母校奏起別離的笙簫。
心中不捨嗎?對,十分——不,是十二分。
奈何人總是要不斷的放棄然後接受,離去然後迎新,沒有人能夠逃過這樣的命運。與其在不捨和離別中掙扎,不如爽快拂袖,然後往前路看。
十八年的生命裡,我大多時間都活在校園當中。有人說過畢業袍是黑色的原因,是由於它是一套葬服,而畢業禮正是青春的葬禮。這個說法雖然合理,但未免有點兒誇張。畢業袍為我中學的句子劃上句號,而十八歲生日則為我青春的段落劃上句號。現在的我,不應困苦於這段落的句號能否再延後幾格,而應執筆為下一段落寫下精彩的內容。
我背著母校,背著西斜的太陽離去,在艷紅的影樹作背景之下,向著初起的月亮走去。
再見,母校。
再見,十八歲。